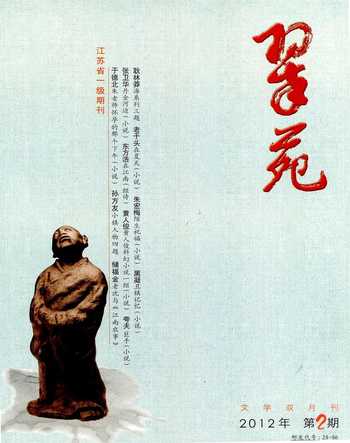恩师
2012-04-29周荣池
有些人永远不能够忘却,他们或许没有做过什么轰轰烈烈的大事,却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在生命和记忆里划下了深深的烙印。我们曾经贫困的生活、混沌的青春、高远的梦想因为他们而改变。当我们的一切改变了以后,他们也只能是我们的记忆里的一个片段,尽管这些对于一个人的成长而言是那么的重要。
一
村子里的小学就在庄台南面的一块空地上。几间简陋的房屋里几十个调皮的孩子和三个老师构成了这个学校的全部。除了屋前空地上的一根竹竿上飘扬的五星红旗之外,这里和平常人家的屋舍没有什么区别,它淹没在了村庄里,成为村庄的一个部分。尘土飞扬的操场上,我们蹦跶之中开始了求学之路上的起点。
学校里的三个老师都是村里人,他们是初中毕业以后就在村里教书的,吴老师教幼儿园,另外两个冯老师分别教一三年级和二四年级。学校里校长由女冯老师担任,男冯老师除了教学以外负责每天用那一根铁棒敲挂在屋檐下的那一块铁,校园里就有了钟声——这真正是“校长兼校工,上课带打钟”。他们下课之后就是农民,我们的教室外面就是大片的农田。坐在教室里我们可以听到农人的叫喊,也偶尔有人趁闲时站在窗外羡慕地看着读书的我们。我们就在庄稼的味道里大声地朗读那已经卷了边的书中的课文。
那时候我家里穷,连30块钱的的书杂费都凑不齐。父亲的性子急在教师外面大声地和老师吵起来,他粗鲁的叫喊声里尽是酒味。教我的是女冯老师,没有交齐学费她照样答应我进教室上课,并且在课后不止一次地和我说要刻苦学习,“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同学门都买新华字典的时候,我只能用和高年级同学借来的没有了检字表的旧字典查字。她把我叫到办公室,把自己的那本崭新的字典送给我。
老师整天和我们在一起,只有起早贪黑地去做农活。体育课的时候我们一起溜到老师的地里帮忙扛稻把。她也不阻止我们,只是微笑着看着我们,像是看着自己懂事的孩子一样欣慰。我们鼓足了劲在地里跑来跑去,在家里做事情也没有过这样卖力。现在想想,这可是充满着一种情感的,我们希望通过自己微薄的力量报答老师。我们慢慢地长大,到四年级结束的时候就转到大一点的学校里上学。而他们依旧在村子里守侯着新来的孩子。村子里每一个人都叫他们老师,他们几乎是村里每一个读过书的人的老师,我们的父母然后是一辈辈的孩子。
岁月在流变。我们都出息了,小学校也因为孩子太少而被其他学校并掉了,房子还空在原来的地方,长满了野草,朗朗书声已不在。他们因为清退的政策回家做了农民,他们本来就是农民。他们没有水平去大的学校继续教书,只有永远在村子里的路上来来回回,默不作声。见到我们从外面回来还是回微笑着问我们学习怎么样,然后关照那句话要好好念书,“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笑容和关怀没有改变,只是脸上的皱纹深了一些。
二
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高厚明先生的名字,这个名字在村子里简直就是一个传说。父亲总是喝得醉醺醺地朝我喊:“你要是能像高厚明一样,老子就是拆屋卖瓦也要供你上学。”先生出生贫寒几近家徒四壁,父子两人相依为命,后家里又遭火灾,更是雪上加霜,但是先生的父亲坚持供他读书。热心人帮助先生的钱舍不得买一件新衣服,悉数用来买书。最终,先生考上大学,做了教师——虽不是显赫的职务,可在我们那个穷困的村庄已绝对是“鸡窝里飞出个金凤凰”了。因此,先生成为我们村子里是勤学成才的典型,家长们教育子女总是以他为榜样的。
到我上高中的时候,坐着父亲请来的拖拉机开到了学校,终于见到了“传说”中的先生。他个子不高,一身朴素的衣着,脸上也总是挂着朴素的笑容。父亲离开学校的时候,大声地对他说:“孩子就交给你了,不听话就打。惯儿不惯学。”他总是这么粗鲁,声音里都能听出粗鲁的酒气。
先生教政治,热心研究马克思主义,素有“高克斯”之称,就连爱女也起了“燕妮”的名字,可见其痴迷。他的“抄写”读书法,虽然辛苦但是效果很明显。据他介绍,他考上政治系之前将政治书抄写过不下10遍,所有内容了如指掌。上课的时候根本不用打开教材,所有内容熟稔于心,娓娓道来。他学习上的勤奋给我们极大的感染,那时候早读课的时间早,寒冬腊月里他总是第一个坐在教室前面开始备课,学生们一个个地在他之后进入教室,很是感到愧疚。因此,向来以懒散著称的文科班,早读是没有人迟到的。
他上课语言极其幽默,有一次突然变声叫道:“我有钱上买天,下买地,中间买空气的啦……”其滑稽的表情令全班大笑不止,大家便记住了剥削剩余价值的资本家嘴脸。他上课内容翔实,绝无虚言。尤其是先生设计的“地毯式轰炸”的练习题,令人喘不过气来,久之我们便训练有素,大受裨益。他注重点滴的积累,从不夸夸其谈。教室前面的墙壁上设计了一块园地,他每天在上面写一句励志名言从不间断,高考期间则是每天将收集到的报刊上的招考资讯剪贴在上面供大家参考。那一年,他的头发突然白了很多,为了我们文科班,他真是呕心沥血。他让师娘辞职在家照顾生活,孩子的学习也顾不上,教学楼里只要灯亮着却都能见到他忙碌的身影。
先生思想也有“顽固”的时候,甚至不近情理。班上有城里来的孩子,穿着怪异,他便严厉批评,毫不留情面。女同学只得换上平常的服装。那时,班上有出名的调皮鬼闯了祸央人到他门上求情,被他断然拒绝,来者所带特产被他扔在门口的地上。大家都认为先生清高得有些不近乎人情,很多人甚至恨其“顽固不化”,并且找到了根源:先生的父亲也极讲原则,在世的时候学校请他当门卫,按照学校的时间到了夜间12点后任何人不得进门,先生的父亲把握得很严格,师生们都不敢迟到,否则便是“一只麻雀也别想飞进来”。据说有一次校长先生夜间迟归,无奈只得偷偷地翻过铁门进来。
班上同学大多来自农村,生活费经常是青黄不接。他在班上设了规矩,凡是吃饭有困难可以向他借生活费,从来不曾吝啬。我的母亲病重卧床,父亲身无分文,他了解情况之后带头捐款,并在班级动员募捐,还找到校长为我减免学费。拿着充满爱心的捐赠,我几度热泪盈眶。
毕业那年,先生鼓励我填报师范学院,我一口气将所有的志愿都填上了师范院校。我拿到高校的录取通知书的那天,他正好在外学习回来。站在路边就迫不及待地让我打开信封,看到我的通知书他很兴奋,露出宽慰的笑容,这种笑容好像他自己当年从村庄里走出去一样快乐。
大学毕业以后,我回到了母校任教。其时,先生已经调离学校。我从工作的第一天起就勉励自己做一个正气、勤奋的教师。当班上的孩子叛逆出走的时候,我会陪着家长在寒冬的深夜里去网吧寻找;当有学生生病的时候,我会陪着他去医院,并垫上医药费;当学生静静地休息的时候,我会幸福地从宿舍前走过……我做这些心中总是幸福的,就好像是报答自己的老师多年前对自己的关爱。
三
上大学之后,我的生活稍有改观。可是面对当时所有志愿里的中文系,我曾经觉得很有虚无缥缈的。中文系这个听起来浪漫的名字在现实中显得有点空虚。我经常在学校外的路边停停走走,寻找那份很不踏实的梦想。当我找到自己那支还能写字的破笔的时候,我似乎找到了行走的拐杖。这一切因为一个诗人,一个老师,也就是陈义海先生。尽管他似乎并没有给我很多直接的对话和帮助。但是,我在他诗人的长发和气息里找到了自己要走的路。
义海教我们西方文学和比较文学。他站在教室的过道里,中等的身材几乎被学生的目光湮没。他语调深沉,讲到激情的地方,忘情地朗诵莎翁的诗文。他流利的英语和深情的朗诵让我们为之陶醉,尽管有时大家未必能全听懂。有一次教室里全部安静下来,沉默之后爆发出掌声。他浅浅地一笑,有些羞涩地推推眼镜,继续介绍缪斯女神。
义海老师学外语有一个很神奇的经历。他上初二的时候外语都一窍不通,偶然有一天顿悟似的理解了那些豆芽一样的文字,发狂似的要学外语。父亲咬牙给他买了收音机,听了半天的英文节目也没有听懂一句,后来才知道听的是日语节目。他的学英语的热情很高,放牛的时候牛吃草,他读单词,大有“对牛弹琴”的意思,以致村里人觉得他有精神病。他带1块7毛钱去买英语书,为了省5分钱举着衣服游过100米宽的河水,为了去县城买英语书,他甚至隆冬的午夜就悄悄出发。
这些事情从书上读来,泛黄的纸上好像仍有他执着的脚步声。义海毕业于外语系,却有在学校墙壁上写诗的疯狂。他长长的头发就好像是一首诗。他读的是英文,研究的是新诗,后来又师从孙景尧研究比较文学,他的骨子里有的却是传统文人的特质。这大概是家族基因遗传。先生祖父少读诗书,到80多岁时两耳失聪,老眼昏花,却仍能诵读《四书》《五经》,且很有意味:天气晴好的时候,他经常提着一面小铜锣,走村串户唱古书。这让我想起先生朗诵诗歌时的样子,他的那首深情的《西茉纳之歌》:
西茉纳,时间将温柔下去/为了你也为了我/我站在山顶上/看见你和麦浪一样/骄傲,布满山谷
他沉醉地朗诵的时候,其实内心一定和他的祖父一样是孤独的。我们这些80后和那些愚昧的村夫一样不能懂得这些纯美的东西。诗人是孤独的,诗人也只能孤独。先生那深情的声音和那小铜锣的声音一样具有孤独的特质。可惜我等也是美的失聪者,听不到那些天籁一般的吟咏。
先生是一个绅士,为人和善,对学业的要求却很严格。他从来不布置学生之间可以复制的作业,考试之前也不做任何提示性的复习。这在学生之间引起很多的怨愤,但是他仍然只是浅浅地一笑。他不需要成为那种“好好先生”式的教授,那些先生大概会担心学生们不及格,他的课程及格率却很高,因为大家都很认真地去温习,现在想来这对学业大有裨益。
先生去英国期间,发电邮鼓励我继续读书考研,我当时在偏僻的乡村教书,物质精神都很匮乏。我于是拼命地读写,最终也没有能考上研究生,但是因为读书写作离开了那里(并不是埋怨乡村的不是,可是离开对于我个人而言意味着更多的可能)
他在英国的酒吧里也吟诗,作为来自中国的诗人,他用自己原创的英文诗歌征服掌声和英镑。我想,在朗诵结束时他一定还有浅浅的微笑,那是诗歌一般的微笑。一直记得先生的号码,却久不去打扰他。他不需要无谓的问候,他是一个诗人,和诗歌一样是用来怀念的。他说他的手机通常放在家里,等下班的时候看一下,他知道有人记得他就好。
读懂义海,我是在深夜那些泛黄的纸上,在他的那些优雅绅士般的文字里。这样的义海,像秋风里飒飒作响的叶子,能把风最美的声音表达出来。这些也让一个糊涂的孩子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并且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作者简介:
周荣池,江苏高邮人。80后。江苏省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在乡间做过2年教师,现供职高邮市教育局。作品散见《文学报》《美文》《散文百家》《散文诗》《雨花》《翠苑》等报刊。在《盐城晚报》开专栏“诗经中的里下河”。作品《故纸》入选《2010年我最喜爱的散文100篇》。著有长篇小说《绝境》、散文集《草木故园》(江苏文艺出版社)。获第四届汪曾祺文学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