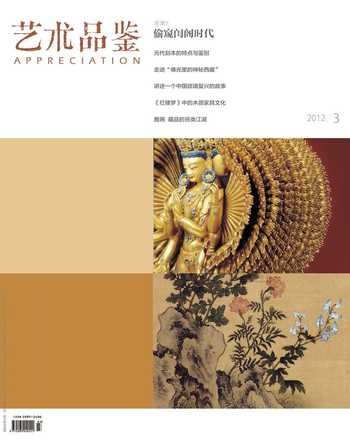北宋米芾书画鉴藏生涯
2012-04-29吕友者
吕友者
北宋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到了中后期,随着商品经济的昌盛与统治者推行的文治政策,使得社会上好古之风愈演愈烈。有的人为了收藏书画,甚至忍饥挨饿,正如时人苏轼所言:“虔州吕倚承事年八十三,读书作诗不已,好收古今帖,贫甚,至食不足。”炽热的鉴藏风气促进了书画市场的进一步完善,艺术品交易活动日益频繁。同时,亦形成强大的收藏群体,而米芾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员。
米芾(1051-1107),又称米南宫,初名献,字元章,宋代有名的书画家和鉴藏家,与宋代苏轼、黄庭坚、蔡襄合称宋四家。因狂放并有洁癖,人称“米癫”。其人天资高迈,能诗文,擅书画,精于鉴赏,尤好收藏历代名迹。
那么,如此爱好收藏的米芾,他到底收藏过哪些法书名画?他如何阅玩、装裱和保护书画?他所藏书画的来龙去脉如何?
书画的收藏与赏玩
米芾出生于官宦世家,是北宋初期开国大将米信的五世孙。祖上几代虽都为武官,但家庭的书香氛围却甚为浓厚。其父米佐(字光辅)亦为军职,曾在淮州做过著名将领余靖的僚属,官至左武卫将军、会稽县公。由于受宋代重文抑武政策的影响,开始“亲儒嗜学”。米芾母亲为阎氏,曾为英宗皇后高氏的乳娘,赠丹阳县太君。受家庭文化熏陶,米氏少年英才,“六岁时日读律诗百首,一再过目辄成诵。”七岁起学习颜真卿楷书,十岁刻写碑文,并临习宋代书家苏舜卿、周越的行草书。此后的为官生涯,便开始了收藏活动。史载“是时元章名能书,适官太常,一旦奉诏,以黄庭小楷作《千文》以献,继进所藏法书名画,赐白金络钱甚腆。”张邦基《墨庄漫录》也有类似的记述:“崇宁中,初兴书画学,米芾元章方为太常博士,奉诏以黄庭小楷作《千文》以献,继以所藏法书名画来上,赐白金十八笏。是时禁中萃前代笔迹,号《宣和御览》,宸翰序之,诏丞相蔡京跋尾,芾亦被旨预观。”从中可见其收藏的规模不小。
这时期北宋文人收藏之富的确令人叹为观止,米芾《画史》曾记过如此独特的赏玩方式:“凡收画,必先收唐希雅、徐熙等雪图,巨然或范宽山水图,齐整相对者,装堂遮壁,乃于其上旋旋挂名笔,绢素大小可相当成对者,又渐渐挂无对者。盖古画大小不齐,铺挂不端正;若晋笔须第二重挂,唐笔为衬,乃可挂也。”此种豪奢的赏玩方式,足以让后世的鉴藏家瞠目结舌。事实上,时人的收藏更倾向于文人画或士大夫画,很少有画工画。北宋画院画家除黄筌、易元吉外,其他人的画一概没有,即使是文人画也要区别对待。
然米芾则认为“鉴阅佛像故事图,有以劝戒为上;其次山水,有无穷之趣,尤是烟云雾景为佳;其次竹木水石;其次花草;至于仕女翎毛,贵进戏阅,不入清玩。”他的收藏理念较看重的是画面内容,特别喜欢天真率意且富于变化的书画。从其对各家的评价中,都可看出这种美学观。如《书史》开篇就写道:“刘原父收周鼎篆一器,百字,刻迹焕然,所谓金石刻文,与孔氏上古书相表里,字法有鸟迹自然之状。宗室仲忽、李公麟收购亦多。余皆尝赏阅,如楚钟刻,字则端逸,远高秦篆,咸可冠方今法书之首;秦汉石刻,涂壁都市,前人已详。”一篇金文,米氏竟认为它可以冠古今法书之首,原因就是其天真质朴,有鸟迹自然之状。
同时米芾收藏态度亦是厚古薄今的,曾说“今人画亦不足深论。赵昌、王友、潭簧辈,得之可遮壁,无不为少;程坦、崔白、侯封、马责、张自芳之流,皆能污壁,茶坊酒店,可与周越仲翼草书同挂,不入吾曹议论。得无名古笔差排,犹足为尚也。”并且指出收藏书画要力求精品,提倡“其物不必多,以百轴之费置一轴好画不为费”,可见其收藏的观念。
那么对于米芾来讲,到底藏有哪些名迹呢?米氏自言:“余家晋唐古帖千轴。”明代陈继儒有如此评价:“余观近代酷收古帖者无如米元章,识画者无如唐彦献。”据明代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米南宫秘玩目》记载,米氏所藏的既包括书法,也包括绘画。其中法书的有王右军《官舍》、《尚书》二帖、《快雪时晴帖》、吴融《博士帖》、谢安《慰问帖》、大令《中秋帖》、陶隐居《朱阳帖》、梁临《乐毅论》、智永《临右军五帖》、《春雨帖》、《褚模兰亭》、幕大令《范新妇帖》、陆柬之《头陀寺碑》、张长史《秋深帖》、李琶《多热》、颜真卿《朱巨川告》、怀素《去夏帖》等。名画有曹不兴《如意轮图》、顾恺之《维摩天女飞仙》、戴逵《观音》、六朝人画《王戎像》、薛稷《二鹤》、王维《雪图》六幅、《山居图》小卷、韩
《调马图》短卷、张黄《韦侯故事》六幅、唐人画《扬子云像》、李《危峰茂林》、荆浩《夏山图》二幅、关仝《仙游图行卷》、董源《雾景》、李成《松石》、范宽《秋山瀑布》、巨然《海野图》、易元吉《芦苇鸽鹤乳》等。
对于自己收藏的书画,米芾会经常拿出来赏玩。其阅玩书画的方式多种多样,如有秘玩方式。米芾收藏的一些稀世珍品,一般是秘不示人,只有至亲好友,比如苏轼这类人过来才可一见。且每天阅玩之后,都要锁在箧中,晚上睡觉则置于枕边。另一种方式就是持所藏书画参加文人雅集,互相交流,共同欣赏。所谓米芾“一日林希会章悼、张询及余于甘露寺净名斋,各出书画。”即是一例。除此之外,张挂于壁、旦夕赏阅也是一种把玩方式。米芾说:“晋画必可宝,盖缘数晋物,命所居为宝晋斋,身至则挂之,当世不复有矣。”传米氏每次出行乘船中,都要在船中张挂书画,插一旗帜号“米家书画船”。而且就是在家中也要张挂书画。
既然作为一位知名的收藏家,当然少不了与藏家之间的交往。米氏交往可谓十分广泛,正如其所言“漫仕平生四方走,多与英才并肩肘”。与他交游的书画藏家人数众多,既有宗室子弟、朝中重臣和寺院高僧,又有江南藏家、画商画贩等。但以上人物为数不多,其交往对象主要也还是以文人为主。他周围的许多朋友如苏轼、黄庭坚、李公麟、王诜、林希和晚年的书画友薛绍彭、刘泾也都收藏书画。此外,他还与禅僧交往,如与守一法师、宝月大师、僧道清等的交游。


艺术品的来源与作伪
随着艺术品市场的逐步繁荣,书画交易已是相当普遍的事情。加之文人们经常举办各种雅集活动,因此少不了交易。那么米芾书画的来源又是通过何种方式而来的呢?
他许多藏品是通过交换而来的。如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十二月帖》、欧阳询《语茂帖》、杨凝式《大仙帖》等都是与别人交换而得来。我们常看到米氏有以藏品相交换的记录,并且以数轴易一轴,如:“余家收古画最多,因好古帖,每自一轴加至十幅以易帖,大抵一古帖不论货用及他犀玉琉璃宝玩,无虑十轴名画,其上四角皆有余家印记,见即可辨。”又有一次,他以众多的藏品去换得王献之的名帖:“王献之《送梨帖》……刘季孙以一千置得,余约以欧阳询真迹二帖、王维《雪图》六幅、正透犀带一条、砚山一枚、玉座珊瑚一枝以易,刘见许。”为了得到自己喜爱的晋唐法帖,不惜拿名画折换,一些藏家窥得此机,因此获利不菲。
米氏亦经常用购买的方式获得艺术品,特别是一些他十分酷爱的法书,甚至不惜钱财。如王羲之《桓公破羌帖》、张旭《秋深帖》、张僧繇《犬王图》、李异《危峰茂林》等都是花钱购入。米芾曾经和宰相富弼的女婿范大同去相国寺,并以七百金从常卖处买得《雪图》一幅,缣绢破碎,却古意盎然:“如世所谓王维者。”另一次,他在相国寺仅用“八金”就购得了徐熙的真笔《纸桃两枝》。
同时也有赠送而得来的。由于米芾交友广泛,喜欢助人,经常帮人鉴定和题跋书画。因此《宣和书谱》称他“寸纸数字人争售之,以为珍玩,至于请求碑榜而户外之履常满”。长此以往,他人难免也会以书画相赠,如谢安《八月五日帖》就是蔡京所送;王羲之《丙舍帖》为薛绍彭所赠。





据《书史》、《画史》记载,米芾常送书画给刘泾,礼尚往来,想必刘泾也会有不少书画赠送给他。
自行摹拓也是藏品的来源之一。当米芾在别人手里看到好的书画,而主人又不肯辍手时,他就自己动手复制,如虞世南《积时帖》就是从李熙处借摹了一本,张旭的《前发》、《汝官》、《承颜》三帖则是遣人从杭州陆氏家摹拓。另外,还有托人代购的方式而获得藏品。不过米芾似乎往往所托非人,所托之人往往代为自取了,如“梅泽有张操涧底,葛氏物。余托购,乃自取之。”
然而,以上多种方式获得来的藏品,在米芾手中不断地更新与流出,他曾说:“书画不可论价,士人难以货取,所以通书画博易,自是雅致。今人收一物,与性命俱,大可笑。人生适目之事,看久即厌,时易新玩,两适其欲,乃是达者。”赏玩书画被看成是一种自娱的方式,同时也反映出藏品流通之快。
书画流通的加速,促进了艺术市场的繁荣,同时也引发了作伪之风的泛滥,鉴藏家们也不可避免地参与作假。据说米芾就是一位作伪的高手,由于对古代名画的长期揣摩与临写,以致所作之画几于逼真。关于米芾在绘画方面的作伪,可以肯定其作伪并不少。这在米氏的经验之谈中可以反映出来:“画摹多似,人物马牛尤易似;书临难似,第不见真耳,对之则惭惶杀人。”又说:“大抵牛马人物,一摹便似,山水摹皆不成;山水,心匠自得处高也。”从这两段话中,可以推断米芾作伪以牛马人物画为主。
不只是米芾,还有上文中提到过与他交往颇深的大鉴藏家刘泾,也同样做过手脚:“余昔购丁氏蜀人李,以易刘泾古帖,刘刮去字,题曰李思训,易与赵叔盎。今人好伪不好真,使人叹息。”像刘泾这种用小名头伪题为大名头的事情,在鉴藏圈里是相当普遍的,米芾对此作了简洁的概括:“大抵画,今时人眼生者,即以古人向上名差配之,似者即以正名差配之。”人们遇到古画,凡今人看来觉得风格与图式陌生的,便会找一个名气稍大一些的托伪他的真迹。再如果风格与某名家相似的,会直接以某名家的名头当作伪托,就像王诜、葛藻、吕公儒都曾拿米芾的临帖作伪。米氏就曾亲眼看到王诜将他所临的王献之《鹅群帖》,用来“染古色麻纸,满目效纹,锦囊玉轴,装剪他书上跋连于其后,又以临虞(世南)帖装染,使公卿跋。”
米芾的作伪亦是相当巧妙。有时他会利用借他人藏品幕拓,然后真赝并还,让人自择。有眼力的就收去真本,没有眼力的就收去伪本,自认倒霉,如宋人张知甫在《可书》中写道:“米元章攻于临写,在涟水时,客鬻戴嵩《牛图》,元章借留数日,以摹本易之而不能辨。后数日,客持图乞还真本。米讶而问曰:‘尔何以知之?客曰:‘牛目中有牧童影,此则无也。”借他人书画摹拓,然后用赝本到第三者那里交换真迹,可知其作伪技术的高超。
事实上,米芾不仅是位收藏家,更是当时一位知名的鉴定家。



书画的鉴定与保护
米芾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书画收藏与作伪并存的时代,因而也是一个需要并产生鉴定家的时代。从史料来看,苏东坡、李蒿、黄伯思、董逍、刘泾、薛绍彭、唐彦献、勾处士等都是当时知名的鉴定家。
关于米芾鉴定书画的水平,各种史料虽然褒贬不一,但可以肯定其鉴定能力并不低。《宋史》说他“精于鉴裁,遇古器物书画,则极力求取,必得乃已。”另《四库全书》中提到《画史》时也写道:“史称其妙于翰墨绘画,自名一家,尤精鉴裁。此书皆举其平生所见名画,品题真伪,或间及装梢收藏及考订伪谬。历代赏鉴之家,奉为圭皋。”可知其书画的鉴定水平之高。
他时常鉴定各种历代名画。如对于阎立本的《步辇图》,米氏鉴定结果是:“《唐太宗步辇图》,有李德裕题跋,人后脚,差是阎令画,真笔。今在宗室仲爱君发家。”另外,对于《照夜白》,他也说:“王晋卿的韩马《照夜白》,题曰‘王侍中家物,以两度牒置易颜书《朱巨川告》于余。”
实际上,米芾鉴定书画有自己的一套方法。他会通过“笔势”的雅俗来鉴定书画的真伪:“晋庾翼稚恭真迹,在张丞相齐贤孙直清汝钦家。古黄麻纸,全幅无端末,笔势细弱,字相连属,古雅。论兵事,有数翼字,上有窦蒙审定印。后连张芝、王澳草帖,是唐人伪作,薰纸,上深下淡,笔势俗甚,语言无伦,遂使至宝杂于瓦砾,可叹。”
另外,观看画面的笔法,也是米芾鉴定绘画的方法之一。《书史》中写道:“后世传《黄庭经》多恶札,皆是伪作,唐人以《画赞》犹为非真,则《黄庭》内多钟法者,犹是好事者为之。”虽然王羲之学钟繇书,但二人笔法不同,因此通过笔法即可确定所传王羲之《黄庭经》非为真迹。又如:“马,佳本,所见高公绘字君素二马,一吃草,一嘶,王诜家二马相咬是一本,后人分开卖;苏激字志东家三匹,王元规家一匹,宗室令穰家五匹,刘泾字巨济家三匹,皆笔法相似,并唐人妙手也。”这就是通过笔法确认不同藏家的马均出于唐代妙手。
而且米氏也会运用比较法鉴定书画。由于米芾饱览大量书画,不同时代各个画家的作品面貌了然于心,所以常用比较的方法鉴定书画。或者将不同朝代的画家进行比较,或将同一时代不同画家进行比较,或将真伪进行比较,使真者见真,伪者见伪。如不同朝代画家进行对比:“江南周文矩士女,面一如昉,衣纹作战笔,此盖布文也,帷以此为别,防笔秀润匀细。”这是将五代南唐的周文矩与唐代的周昉进行比较。

利用印章和题款来鉴定书画,亦是米芾常用的方法。他十分重视印章在鉴定中的作用,并认为“画可摹,书可临而不可摹,惟印不可作伪,作者必异,王诜刻句德元图书记,乱印书画,余辨出元字脚,遂伏其伪,木印铜印自不同,皆可辨。”因此很注重对历代书画家和收藏家印章的研究。他不仅通过印章鉴定书画之真伪,而且也根据印章区别自家收藏书画的真伪优劣,曾说:“余家最上品书画,用姓名字印,审定真迹字印,神品字印,平生真赏印,米姓秘箧印,宝晋斋印,米姓翰墨印,鉴定法书之印,米姓秘玩之印……其他用米姓清玩之印者,皆次品也,无下品者。其他字印有百枚,参用于上品印也。自画古贤唯用玉印。”可见其对印章之重视。在对谢安《八月五日帖》的鉴定中,即可窥见米芾对历代印迹的熟悉程度,他说:“内谢安帖,有开元印,缝两小玺,建中翰林印。安及万帖有王涯永存珍秘印,大卷前有梁秀收阅古书印,后有殷浩印,殷浩以丹,梁秀以储,是唐末赏鉴之家,其间有太平公主胡书印,王溥之印”。
米氏亦会利用“避讳”方法来鉴定书画。在古代,为了表达对帝王、师长、祖先的尊重,在落笔行文之际往往采用“避讳”制度。米氏巧妙地运用这一制度,使误定书画恢复其真实年代或作者:“唐越国会钟绍京书千文,笔势回劲,在垂相恭公侄陈开处,今为宗室令穰所购,诸贵人皆题作智永,余验出唐讳缺笔。及以遍学寺碑对之,更无少异。大年于是尽剪去诸人跋,余始跋之。”、“唐辩才弟子草书千文,黄麻纸书,在龙图阁直学士吴郡滕元发处。滕以为智永书,余阅其前空‘才字全不书。固已疑之,后复空‘永字,遂定为辩才弟子所书,故特缺其祖师二名耳。”这些记载表明了米芾十分看重避讳在鉴定中的作用。
此外,他还使用书画工具和材料辨识绘画。并发现“古书画皆圆圈,盖有助于器,晋唐皆凤池研,中心如瓦凹,故曰研瓦。如以一花头瓦安三足尔。墨称螺,制必如蛤粉,此又明用凹砚也。一援笔因凹势锋已国,书画安得不因。”
除鉴定书画时要运用各种手段以外,也要了解作伪者的伎俩。对于书画做旧的依据,米芾做了说明:“熏纸烟色,上深下浅;染纸湿色,纸纹栖尘;劳纸作茧,纹软。”还有刮去真名填假名的:“余昔购丁氏蜀人李细秀而润,上危峰,下桥涉,中瀑泉,松有三十余株,小字题松身曰蜀人李,以易刘泾古帖,刘刮去字题曰李思训,易与赵叔盎,今人好伪不好真,使人叹息。”这些都是识破作伪的经验总结。
对书画的保护,米芾也是相当重视。特别是年代久远的古画,应尽量做到不脱不裱,以防损画。历代收藏家在得到古画时,往往喜欢重新装裱题跋,宫庭收藏尤其如此。米芾有感于斯,主张古画不脱则不裱,因为裱一次损坏一次,他说:“古画若得之,不脱不须背。裱若不佳,换裱一次,背一次,坏屡更矣,深可惜。盖人物精神发彩、花之稚艳、蜂蝶,只在约略浓淡之间,一经背多,或失之也。”但到了非裱不可时,米氏也有个人丰富的经验。在对古书画进行重裱之前,首先要求清洗。对于清洗,他总结个人心得:“余每得古书,辄以好一置书上,一置书下,自傍滤细皂角汁和水,需然浇水入纸底,于盖纸上用活手软按拂,垢腻皆随水出。内外如是,续以清水,浇五七遍,纸墨不动,尘垢皆去。复去盖纸,以干好纸渗之两三张。”同时,阅玩书画也要洗手,以免弄脏书画。人们都知道米芾有“洁癖”,这其实就是因为观阅书画时,经常洗手的习惯而转变成一种强迫心理,他自己也说:“龟澼虽多手屡洗,卷不生毛谁似米。”即使邀请他人观赏书画,也要求对方洗手,且不准对方凑得太近,禁止用手触摸书画。据《米襄阳外纪》记载,米氏还制订了一个观赏规则:“洗二案相比,芾以纸缫铺讫,濯手亲取书于奁中,铺展以示客。客拱而凭几坐,从容细阅,芾趋走于前。客云展,芾展;客云卷,芾卷;客据案甚尊,芾执事趋走甚卑。”
米芾还认为盖章会破坏画面,在盖印方面要注意保护书画,尤其不可用大印破坏书画的本来面貌。他说:“印文须细,圈须与文等。我太宗‘秘阁图书之印,不满二寸,圈、文皆细,上阁图书字印亦然。仁宗后,印经院赐经,用上阁图书字大印,粗文,若施于书画,占纸素字画多,有损于书帖。近三馆秘阁之印,文虽细,圈乃粗如半指,亦印损书画也。王诜见余家印记与唐印相似,始尽换了作细圈,仍皆求余作篆。”
此外,对于书画长期保存时,应确保其卷舒与柔性。米芾指出:“文彦博以古画背作匣,意在宝惜,然贴绢背着绷,损愈疾。今人屏风俗画一二年即断裂,恰恰苏落也。匣是收壁画制,书画以时卷时舒,近人手频,自不坏。岁久不开者,随轴干断裂脆,粘补不成也。”
拥有如此精富藏品的米芾,他的古帖和古画最后去向如何呢?这是一个很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明代范明泰《米襄阳外纪》云:“米元章晚年学禅有得,知淮阳军,未卒先一月,区处家事,作亲朋别书,只焚其所好书画奇物,造香楠木棺,饮食、坐卧、书判其中。前七日,不茹荤,更衣沐浴,焚香清坐而已。及期,遍请郡僚,举拂示众曰:‘众香国中来,众香国中去。掷拂合掌而逝。”可知在米芾去世之前,已将其部分所好书画先行烧毁,这是毋庸置疑的。因为这与米氏的信佛有关,他把死亡看作是到众香国,所谓众香国即西天极乐世界。既到极乐世界,当然也要带上自己平生所好的书画宝玩。不过,米芾在《画史》中却说:“余家晋唐古帖千轴,盖散一百轴矣。今惟绝精,只有十轴在,有奇书亦续续去矣。”很显然,他的藏品在《画史》完成之前已经在不断地散出,而古画多用来换古帖,古帖已散出十分之一,剩下的绝精古帖也不过十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