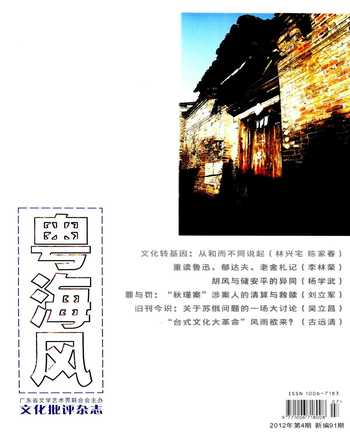记忆与忘却
2012-04-29王际兵
王际兵
自传是一种不适合中国人的文体。
如何记忆自己的故事本无成规,世间没有一个约定俗成的自传模式。但比较一下别传,我们不难发现自传潜在的特性。写作别传,关键是考订人物的行动与事件,探寻历史演变的“规律”;一旦有人指出考订不实,所传之言也就成了笑话。自传也免不了这方面的问题,不过作者所经历的诸多事件,尤其是一些琐事,往往没有旁证,作者其实是自说自话,真与假的标准起不了作用。而且除了行动和事件,传主能够充分地表现自己的情感和思维,生动地展示内在生活是自传者的专利。如此说来,自传不惟记录历史事件的真实,而是在行动史与精神史的结合中展现一个生命的形成、变化、挣扎和奋斗,展现一个鲜活的、具体的人。难怪法国学者勒热讷给自传做出了这样的定义:“一个真实的人以其自身的生活为素材用散文体写成的回顾性叙事,它强调的是他的个人生活,尤其是他的个性的历史。”[1]纵而观之,汉语世界的传记历来偏重外在事实的记录,甚少有人专注自己,专注自己个性的历史。诸多自序、自记、自述等作品,仅仅表明所写的内容是与作者有关的事情而已。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可谓古典名篇,但是三言两语标榜清高,活脱一副组织鉴定的口吻,没有多少自传的味道。晚近以来,西学大举东渐,名之自传者蔚然大观,不仅文人墨客、政界风流,而且商贾老板、演艺明星、市井小民都在下笔为文。一股“打捞”记忆的文化热潮正从上世纪末开始兴起,自传写作显然构成了其中重要的一环。如前几年问世的《王蒙自传》三大本,洋洋洒洒达到一百二十来万字,文坛政道的人与事说不完道不尽。娱乐明星出版自传还曾引起一些非议,这也多少折射了传统里对传记残留的神圣幻觉。同时随着现代传媒的发展,影像也成为了传记往昔的一种方式。变化的发生令人欣喜,然而从内在来看,它们又很少通向作者的内心,很少通向人物的灵魂。
那些作品经常是以个人的经历串起社会的见闻,得出若干历史、政治或社会的意义,作者往往并无自己可传。如陈独秀在《实庵自传》里的道白:“我现在写这本自传,关于我个人的事,打算照休谟的话‘力求简短,主要的是把我一生所见所闻的政治及社会思想之变动,尽我所记忆的描写出来,作为现代青年一种活的经验……”[2]自传不是反省所为所想而是记忆所见所闻,不是检点自己的生命却是为了教育后人,削足适履的人物必然有些装模作样!《王蒙自传》也大抵如此,与其说作者在描绘自己,不如说作者在讲述国家生活中的风风雨雨,讲述文坛故事。一如书中的自侃:“从一九五三年开始写作以来,我的回忆太围绕着个人的遭遇了。其实我比较不喜欢一味地说个人那点臭事,委委屈屈,得得失失,恩恩怨怨,酸溜溜,灰溜溜,叫苦连天。尤其是一个写作者,如果他的写作离不开个人的那点得失悲喜,离不开他个人周围三尺三方圆的那点破事,烦人不烦人,丢人不丢人啊。”[3]不去“搜集一切琐碎的遗事”,而是离开自己,追逐外物,为大家总结“伟大”的经验,这就是国人写作自传的惯有宗旨和方式,至于作者是个什么人,人生有那些对错,倒没有太多意义。在一个兼济天下的梦中,需要总结的只是国家、社会、他人,自己已经六根清净超然物上。有等而下之者,便专好搜罗和传述别人的逸闻秘事,满足世俗的窥秘心理,从而填补叙述自我时的苍白。如许作品还是称之回忆录更加恰当。我们其实只有回忆录意识而没有自传意识。
当然,有些作者也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感受,只是这些文字或者像一个旁观者自觉地以外表而不是内心来鉴定自己,或者在“创造性记忆”中以目前的缅想替代旧时的心思。《鲁迅自传》那篇短文就很像是生硬的中学生作文。作者为《阿Q正传》的俄文读者作“著者自叙传略”,粗线条敘述人生经历,原属正常;后来却只是略加增订,又写作一篇自传出来,实在索然寡味。因为文章仅仅是对历史事迹及少许原因再简单不过的交待,那比《野草》、《朝花夕拾》、《两地书》等作品意味深长地审视人生,何况有关内容早已述说多次。侧重叙述自己的外在生活本来无妨,只是把内在生活完全作为对外在生活的合理的解释,自己也就成了一个提线木偶,一个活死人。人的心灵或者丰富或者简单,人的意志或者坚定或者柔弱,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所做与所想完全是统一的,尤其处身于现代社会的复杂环境。用黄远生1915年在《忏悔录》中的话说:“余深信凡吾人所敬仰之青年,其灵魂必曾一度或数度被其躯壳所囚狱。若曰未曾,其将来必入此牢狱,以此牢狱乃人生必经之阶级,犹人之必入鬼门关也。”[4]国人叙述自己时往往忽略此中关系,机械地追述行动,更像是编纪事年表。《七十年代》则是一部新近出版的引人瞩目的记忆文字集。有些篇目确实触及了灵魂的悸动;有些作者却在慷慨陈词,自诩人生的先知先觉以及超越意识形态控制的“启蒙”行为,回忆出来的人乃是今天的自己。自传如果写成后者这样,根本没有传记的必要。一个人生来就是天才,这是人种学家、生理学家研究的范畴,凡人只能望而却步。人物的灵魂乃是他思维的过程,而不是思维的结果。如果在叙述中内在与外在统一,过去与现在统一,思维失去了进程,内心失去了秘密,这样的人物不过一个机械产品,这样的文字也只配做故纸堆的材料吧。
相形之下,西方自传中的名人无疑趣味太庸俗、行为太卑劣。奥古斯丁396年写成的《忏悔录》大胆而不加掩饰地悔过罪孽,不料开创了西方自传那种写给上帝看的传统。富兰克林竟然说自己做议会的秘书,趁便为自己的印刷所揽了许多议会的活儿;自己有恩于别人,竟然去胁迫对方要行苟且之事。卢梭不仅说自己的性欲甚至变态心理,而且说自己偷窃反倒诬陷别人的几件恶行。如此大胆地说出私利以及罪恶的做法如果发生在中国,简直是自投罗网,卫道士的牙根正好缺少了作料。对于那些自揭其短的做法,我们不会赞赏作者与自我抗争的反思意识和勇敢精神,反而会站在道德的高点对作者的人格进行批评、教训、挖苦,满足于一种虚幻的优越感。至于他人来揭短,同样不能忍受,必将与之针锋相对。斯风久远,中国一直无法形成一种批评的氛围。方舟子的学术“打假”遭受人身袭击便很有民族特色的遗风。
记忆昨天的苦难,不为扫除污垢,只是炫耀财富,炫耀比没有那些经历的人拥有更多话语权的资格。没有了改革自我的冲动,也无需反思过去、设计未来,记忆更像是以历史为噱头的娱乐消费,是“在美化的谎言之镜中照自己,并带着一种激动的满足感从镜中认出自己”[5]的媚俗。
早在1923年,俞平伯先生的《重印〈浮生六记〉序》就对中国的自传问题有过一番解说:
记叙体的文章在中国旧文苑里,可真不少,然而竟难找一篇完美的自叙传。中国的所谓文人,不但没有健全的历史观念,而且也没有深厚的历史兴趣。他们的脑神经上,似乎凭了几个荒谬的印象(如偏正、大小等),结成一个名分的谬念。这个谬念,无所不在,无所不包,无所不流传,结果便害苦了中国人,非特文学美术受其害,及历史亦然。他们先把一切的事情分成两族,一正一偏,一大一小……这是“正名”。然后甄别一下,与正大为缘的是载道之文,名山之业;否则便是逞偏才,入小道,当与倡优同畜了。这是“定分”。
申言之,他们实于文史无所知,只是推阐先入的伦理谬见以去牢笼一切,这当然有损于文史的根芽,这当然不容易发生自传的文学。”[6]
沈复的《浮生六记》自述一个平常寒士的现实人生,没有了传统书生之意气、腐气,才能“得这一个真性情的闲人”。瞿秋白的《多余的话》大胆展示内心的“勉强”,不讳“历史的误会”和人生的“滑稽剧”,才有了“小资产阶级知识者的自我分析”。韦君宜的《思痛录》虽然是言说集体,倒也审视了自己个人“无法坦然”的“革命”经历。只是这些少之又少的“真性情”话语,不过是阴沉的天空里偶然渗漏的一抹霞光,而且为大众接受的过程还颇不顺利。《浮生六记》在进入现代文人的视野之前已经寂寥百年,而且最后两记也湮没不传;《多余的话》先是有人怀疑作者的真伪,后来作者更是受其累成为“叛徒”,骨灰受刑;《思痛录》在1990年代也经历了要求更名、拖延及删节出版等多种周折。呜呼,直面一个内心的世界对于我们真是无比艰难!
英国作家伍尔芙评论蒙田的文章时曾说,成为自己是与灵魂的沟通,这意味着健康,意味着真实,意味着幸福。[7]可惜我们不过是些无物之物胜利的虏获品,很少能够享受这些健康、真实、幸福,不仅在生活中,而且在写作中。
(作者单位:广东教育出版社)
[1](《自传契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201页
[2]《陈独秀著作选(第三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413页
[3]《王蒙自传·半生多事》,花城出版社2006年版,163页
[4]《黄远生遗著(卷一~卷二)》,台北文海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125页
[5]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167页
[6]《浮生六记(外三種)》,长江文艺出版社二00六年版,215—216页
[7]《伍尔芙随笔全集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59—6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