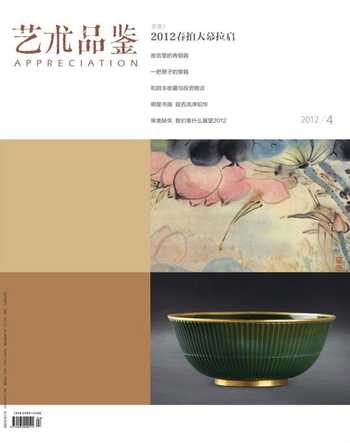纸上年华
2012-04-29胡建君
胡建君
一
日趋远离了自然,所以格外珍惜那些贴近自然的物件,比如棉麻布料与各式纸张。怀念手不释卷的学生时代,还有天天在等信与写信中度过的好时光。我对学生们说,多看看实体书,在纸上写写字吧,电子读物和邮件虽然便捷,远远代替不了纸质书籍和手写书信带给我们的充实与美好,回忆中的纸上年华多么温暖可靠。
以前常在旅途中给朋友写信,在车上,在水上,伴随着车厢的一灯如豆或者船舷上的星光和月光,涂鸦一般似乎在梦中书写。有次在鸣沙山上写信,朋友收到的信纸和信封里夹着细沙,似乎听得见写字那刻的漫漫风涛。比较喜欢各种质朴的手工笺纸,量轻而质厚,不太光滑,吃得住字,甚至有毛毛的手撕边。有时会在纸上画些小插画,或粘贴花叶,那时总觉得与众不同才好。曾在南京捡了大朵的银杏叶给朋友写信,为此填过一首《满庭芳》,其中写道:“金陵,长记取,南园银杏,聊注衷肠。把胸中锦绣,醉伴黄粱。歌舞六朝梦觉,平生意、任自游扬……”
大学时期的节假日,总和朋友王浓埋头在老家利利小店挑选各种台湾信纸和明信片,挤在一堆小小的孩子中间,多年以后依旧记得那时的欢喜。去年在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约见老朋友虹子,我们送给对方的礼物,居然不约而同都是牛皮封面的手工纸笔记本。她在香港读书时给我写信,洋洋洒洒总有十几大张,我的回信自然也都不简短。那时收信和写信都是莫大幸福的第一要事,最好的文字留在了那些信笺上,随风而去了。年前我在美国境内的尼亚加拉瀑布边给爸爸寄了一张明信片。三十年前,爸爸也在大瀑布边给我寄过相似的明信片,只不过那时他在瀑布的另一边,加拿大境内,那时我刚上小学。
有个朋友写给我的信纸常是匪夷所思的,比如丝袜的包装纸,书的扉页,说明书的空白页等,她说那样表明写信心情之迫切,饥不择纸。王小波给李银河的书信写在五线谱上,还用蓝色墨水笔写字在镜子上,涂满了整面镜子,像蓝色的月光。袁拿恩老师在菩提叶上书写心经,用恭肃严整的蝇头小楷,写一片花费三个多小时。贝叶心经带着斑驳的古意和静气,后来他送了一片给我,十分令人欢喜。他是刘海粟的关门弟子,生性浪漫,还说起曾用山东煎饼抄写佛经,竟然非常好写,玉米做的那黄色的感觉也像寺院用纸。开始是抄着玩,最终还吃进肚里,因为觉得是佛经须恭敬有善终,也当然因为煎饼可吃。如果玉米煎饼用来写信,那真是精神与物质食粮的二合一了。台湾导演魏德圣曾讲起,有一封信,大概是民国时期一位太太写给留洋的丈夫,因为那个时候用油灯,常喷油滴出来,落到纸上。那妻子写道,如果你闻到这信纸上的油灯味,我们这一刻的心意是相通的。
法国的朋友魏建强告诉我,他今年1月份在古董市场买了张一战时期带邮票的明信片,上面的内容令他很是感慨:一个法国战士被俘虏了,进了德国战俘监狱。冬天,身上厚衣服也被扒了,很冷。他写这个明信片给在法国的太太,告诉她,他目前的处境,还有一些生活细节,以及传达自己的思念。也不知战乱的年代,那封信是否平安抵达家人手中,她的太太读着明信片又会如何牵挂担心呢?魏还收藏了一个信封,是二战时期,一个法国人在上海寄给法国家人的,信封上贴着孙中山的邮票,盖着法国驻华使馆的印章。这封信辗转到法国的时候,法国刚好被德军占领,于是信件就被德国纳粹军方截住,开信审查,随后贴上德国纳粹军事审查封条后再次寄出给他的家人。感觉就像是恢弘史诗的一个片段。
从前的诗笺都是亲手制作,我也曾用捣碎的旧报纸、宣纸、花叶掺和云母、淀粉,摊在旧纱窗上制作再生纸,拿来做书签贺卡倒也斑驳古拙,但和古人相比,却是粗糙不已了。唐代女诗人薛涛曾采集百年芙蓉树的花瓣与树皮,精制成深红色的浣花笺,那是用来书写相思的吧。《浮生六记》中的芸娘,春扫落花夏采蕉叶,捣烂成汁,和了云母粉入纸皴染成彩笺,不愧是文学史上最美的女子。
偶尔我还精选信笺,自制信封,写给亲爱的人。内容并不重要,收信的人自然会懂,即便无纸无字,放上几片花叶,也有聊寄一枝春的心意吧。

朵云定制陈佩秋用笺
二
无意间看到鲁迅写给许广平的信,没想到横眉冷对千夫指的鲁迅有如此柔情的一面,令人莞尔。1929 年5 月15 日他用画着枇杷和莲蓬莲子的信纸给许广平写去一封信。许广平收信后相当欢喜,即刻回复道:“自然打开纸张第一触到眼帘的是那三个红当当的枇杷,那是我喜欢吃的东西,即如昨天下午二时出去寄信也带了一篓子回来,大家大吃一通……所以小白象首先选了那个花样的纸,算是等于送枇杷给我吃的心意一般,其次那两个莲蓬,附着的那几句甚好,我也读熟了,我定你是小莲蓬,因为你矮些,乖乖莲蓬!你是十分精细的,你这两张纸不是随手捡起来就用的。”附着的那几句指的是笺纸上的题诗:“并头曾忆睡香波,老去同心住翠窠。甘苦个中侬自解,西湖风月味还多”,都是同心之语。鲁迅收到回信又欣然提笔:“我十五日信所选的两张笺纸,确也有一点意思的,大略如你所推测。莲蓬中有莲子,尤其我所以取用的原因。但后来各笺,也并非幅幅含有义理,小刺猬不要求之过深,以致神经过敏为要。”那时许广平已经怀孕,从互相的昵称“小白象”、“小刺猬”来看,二人的感情十分甜蜜。而承载这一份甜蜜与相思的,正是笺纸。
古人尚风雅,在各种笺纸上书写诗词歌赋和心情,从素笺一直写到彩笺。即便民国时期,还有我们熟悉的“红八行”笺纸,信封则是白绵或宣纸糊成的长方形,名址皆由右至左竖写。如今,网络普及,用纸笔写字写信的人越来越少了,更不用说毛笔和笺纸了,让人不仅追忆起那些纸上年华。
被我们渐渐遗忘在尘埃里的纸,其实伴随我们已经两千多年了。相传纸发明于汉代,自出现以后,便逐步应用于书写和绘画。初期,纸质比较粗糙,不能胜任较精细的笔法。三国时期,有赖于纺织技术的长足进步,绢地材质有了较大发展,使得魏晋南北朝时期,以绢代纸成为主要的书写绘画底子。东晋十六国时期,后赵国君“石季龙与皇后在观上为昭书,五色纸,著凤口中,凤既衔诏,侍人放数百丈绯绳,辘轳回转,凤凰飞下,谓之凤诏。”可见当时已出现染成五色的凤诏了,像是一种凤凰传奇。南北朝的《玉台新咏》记载:“三台妙迹,龙伸屈之书,五色花笺,河北胶东之纸。”可知雅致的五色花笺的名字在当时已经流行了。
隋唐时期,国盛民富,造纸技术进步很快,纸的应用进一步普及,特别是麻纸的应用比较普遍。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曰:“好事家宜置宣纸百幅,用法蜡之,以备摹写。”即用宣纸加蜡,用以摹写图画,这是最早关于宣纸名称的记录。唐代制纸工艺以四川为翘首,而蜀中笺纸又以上文提及的“浣花笺”最为出名。相传薛涛在成都浣花溪百花潭畔购置住宅,雇工匠经办造纸作坊。她根据前人用黄檗叶染纸的原理,以芙蓉为原料制造彩色笺纸。据《唐音要生》载:“诗笺始薛涛,涛好制小诗,惜纸长剩,命匠狭小之,时谓便,因行用。其笺染演作十色,故诗家有十样变笺之语。”她设计的纸是长宽适度便于随时取用的小张笺纸,以十张为一扎,诗人尤为适用。薛涛还用涂刷加工方法制作色纸,将红花中提取的染料掺入胶料涂刷于纸面,比传统的浸渍染色方法更方便快捷,也节约了成本。优雅的花笺加上薛涛的个人魅力,成就一段造纸业的传奇。
然而当时尚无笺纸上刻印山水花卉纹样之记载。五代末,“姚顗子侄善造五色笺,光紧精华”。砑花之法,是先在木板上雕出阴线图案,覆以薄而韧的彩色笺纸,然后以木棍或石蜡在纸背磨砑,使纸上产生凸起的花纹,十分精致可爱,号“砑光小本”。砑纸板乃用名贵的沉香木制成。这种砑光纸直到清代,尚在各地南纸店里砑制。
经过隋唐三百多年的技术发展和经验积累,造纸术已成完整的体系。两宋时期,画法变革,水墨画法逐步兴盛,纸质材料愈来愈突显其适用性和优越性,迅速得以普及。我的博士论文写到元祐文人,他们的书写用纸让我艳羡不已。比如东坡用的一种麻纸,只有在成都浣花溪的水边才能制成。他还试过海苔、竹或藤制作的书纸,皆紧薄可爱。李煜特制的澄心堂纸历来令人心仪,“肤如卵膜,坚洁如玉,细落光润,冠于一时”,至宋代依然风行,但东坡甚至用过比澄心堂还得心应手的天台玉板纸,更细薄光润,坚洁如玉。看古人的笺纸名称就使人神驰,如碧云春树笺、粉蜡笺、芦雁笺、清江笺、水纹笺、鱼子笺、砑花纸等。其中砑花纸还分杏红露、桃红、天水碧,上面砑着隐隐的人物麟羽花竹。米芾的传世书纸上就隐有云中楼阁的图案。
北宋各类加工方式如染色、砑花、印染、描绘、加料、泥金银,以及金银屑、金银粉及其他色料、药料的运用,名目繁多的笺纸种类开始大量出现。前代的加工纸在宋代都继续发展,其他还有新的制作精良的砑花纸、水纹笺、染黄纸、鱼子笺等优质纸品出现。其时谢景初制作笺纸很有名,人称“谢公笺”,俗称“鸾笺”或“蛮笺”,他制作的笺纸因有深红、粉红、杏红、明黄、深黄、浅青、深绿、浅绿、铜绿,听起来都那么赏心悦目。
元代造纸延续了宋的风华,但也没有更多的创新。史载有绍兴出的彩色粉笺、蜡笺、花笺、黄笺、罗纹笺等,还有江西的白篆纸、观音纸等。宫廷中有纸上绘金如意的诗笺,到了明清皆有仿制,但民间雕版印刷彩笺尚无记载。这个纸上平淡的时代正在为后世笺纸的繁荣多彩暗暗蓄势。

朵云仿古名笺之一

朵云诗笺之一
朵云诗笺之八大瓜月笺


朵云诗笺之二

朵云轩云母笺小信封之一
三
由于分工繁复的木版水印技术的发生发展,笺纸的巅峰时代终于到来。至明代,木版水印笺纸令人目不暇接,各种山水人物花鸟甚至天文象纬、服饰彩章等图案陆续出现,杂彩纷呈。正如明人李克恭在《十竹斋笺谱》序中所言:“昭代自嘉隆以前,笺制朴拙,至万历中年,稍尚鲜化,然未盛也;至中晚而愈盛矣,历天崇而愈盛矣。”《十竹斋笺谱》乃胡曰从于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刻成,“精工富丽,备具重美,中国雕版彩画,至是叹为观止”。这部笺谱采用了多种印制方法,包括饾版、拱花技术,代表了笺纸印刷技术的巅峰水平。郑振铎曾赞叹其“人物潇洒出尘,水土则澹淡恬静,蝴蝶则花彩斑澜,欲飞欲止,博古清玩,则典雅清新,若浮纸面”。
清初的笺纸艺术遥接明末余绪。李渔在《闲情偶寄》中“笺简”一节写道:“我能肖诸物之形以为笺,则笺上所列,皆题诗作字之料也。”“已经制就者,有韵事笺八种,织锦笺十种。”王世襄所谓活着玩,玩着活,也就是这样一种生活态度与方式吧。乾隆时期,皇帝风流,上有所好,下必行焉,笺纸在宫廷颇为流行,像成亲王所用的笺纸,其精雅品格不亚于“十竹斋”。同时,文人自印笺纸依然风行。赫赫有名的如翁方纲、孙星衍、潘祖荫、吴大澂、杨沂孙、俞樾等,都自制笺纸,多用金石、古玩、法书等图案,金石书笺流派尽一时风雅之盛。道光、咸丰以后,苏浙沪的各种纸品店出现很多以画家画作为图案的笺纸,如任伯年、虚谷、吴昌硕、王一亭等人的作品经常被印制于笺纸之上,很有文人雅趣。清中叶之后,随着沿海城市工商业经济繁荣,花笺甚至常被生意人取作信笺,普遍用于书信往来了。清末,上海有人刻制了印有大彼得、华盛顿、拿破仑、俾斯麦等国外强人形象的诗笺,意在倡武备,振国祚。笺纸艺术自此异彩纷呈。
笺纸的最后高峰是在民国初期,文人画的兴起给笺纸带来新的生机与繁荣。民初画坛领袖姚茫父、陈师曾等都用心参与笺纸的制作。其后,名画家张大千、齐白石、溥心畲、陈半丁等均涉足笺纸,笺纸图样多集诗、书、画、印于一体,格调高华,从此红笺小字,说尽平生意。其时刻印高手众多,纷纷选用上好宣纸,采用精湛的木版水印技术,光印制笺谱的店铺,在京城就有20 余家。荣宝斋即在其中脱颖而出,与上海的朵云轩雄峙于大江南北。
荣宝斋用木板水印法制作的《七十二候诗笺》、《二十四节令封套》等,鲁迅、郑振铎见后盛赞为琉璃厂诸笺肆中之“白眉”。1896年,荣宝斋设“荣宝斋帖套作”机构,开创木版水印事业,初始便着手印刷供文人雅士书写的信札、吟诗作赋用的诗笺。最有名的作品属上世纪30年代鲁迅、郑振铎主持印制的《北平笺谱》,被誉为“中国木刻史上断代之唯一丰碑”。1958年,这部笺谱得以重印,更名为《北京笺谱》。诚如鲁迅所言,“此事恐不久也将销沉了”,笺谱的结局只能流籍于人们的记忆深处。戊子年秋,邯郸的徐天一追慕上个世纪的风华,从笺谱中精选十八种,由荣宝斋印制,并著文《北平笺谱重印记》,也是对旧时光的挽留。
创建于1900年的上海朵云轩同样为文人所耳熟能详。朵云轩的老店主与倪墨耕、王一亭、赵子云等海上名家均是至交,谈艺之余,一起吟诗作画、拍曲弹唱,朵云轩如同艺术沙龙,被艺坛称为“江南艺苑”、“书画之家”。20年代,初到上海的张大千能拜在曾熙门下学习书艺,也有赖于朵云轩从中牵线搭桥。朵云轩初创时的经营品目就有:“自制朵云名笺,薛涛槟榔名笺,十景木匣诗笺,青赤泥金贡笺,各色冷金贡笺,洒金描金蜡笺,藏经磁青名笺,玉板煮硾名笺,猩红真硃贡笺,六吉单夹贡笺……”其木版水印复制艺术独具特色,形成悉仿古制、刻意乱真、工细兼及、神形并重的风格。其中泼墨大写意画的复制,水墨淋漓,酷似原作,连原作者都无法识别,一度享有盛誉。
张爱玲说到三十年前旧上海的月亮,该是铜钱大的一个红黄的湿晕,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迷糊。这样的文字令我从小对朵云轩心驰神往。后来每去书画出版社,就晃到郑名川所在的水印木刻部看看各色笺纸,赖他送我几张特别的,也算暂留住一段风雅的岁月吧。

傅抱石致贺天健信札(朵云笺纸)


荣宝斋信笺之王师子花卉

荣宝斋信笺之北平笺谱三

沈增植致康有为书札(朵云笺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