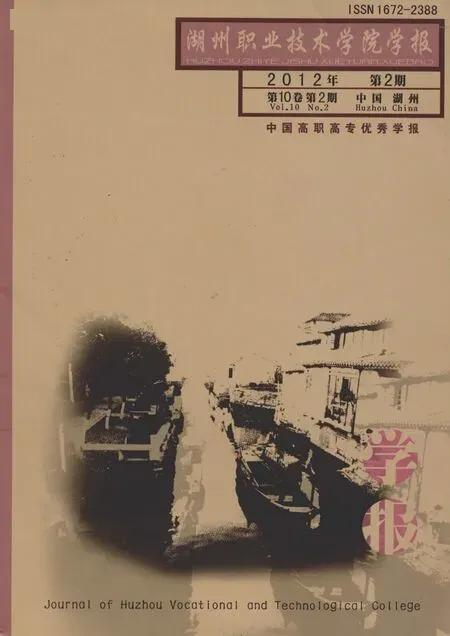试析1990年代“精神”诗*
2012-04-13王昌忠
王 昌 忠
(湖州师范学院 人文学院, 浙江 湖州 313000)
与1990年代物质化、世俗化的社会文化景观对应的是“精神生活缩减到零度以下”和“思想的空场”。[1](P93)在这样的生存境遇中,文学往往也会被裹挟着放弃精神的标高、思想的重量,以求适应于市场的“招商”和消费的“胃口”。这大概就是在1990年代的文学现场里,从表面上看,各种文学现象狼烟四起、喧嚣不断、花样翻新,但尘埃落定之后,真正能凭其文学分量“留驻”于文学史视野的却并不多见。之所以在陈晓明看来,“90年代中国文学唯一还有创造性和生命力的可能就只剩下诗歌”[1](P93)了,恐怕就在于,1990年代诗歌写作者通过“精神伸越和语词锤炼”,坚守住了“精神”和“思想”“这孤寂的领地而不退缩”:既在物质、肉身、世俗等多种力量的引诱、冲击、干扰、破坏中,大义凛然、毫不妥协地把诗歌贴上“精神”、“意义”的标签,“表达对这个纷乱、矛盾、混杂不明的世界的经验,以他们对人类精神性生活的坚执,在不可能中寻找可能,在无意义中寻找意义,在混杂无序中寻找秩序,在失望中寻找得救,在缺乏诗意中寻找诗意”;[2](P361)又在灵魂枯竭、思想“处于严重衰减状况”的时代气候中,关注、呵护、滋润灵魂,“以一些单薄的思想片断填补思想空场”。[1](P110)本文所要讨论的1990年代“精神”诗,正是1990年代诗歌精神性的鲜明见证,也是1990年代诗歌写作者坚执关注精神、体认精神、呵护精神、彰显精神、张扬精神、吁求精神、打造精神的诗歌立场的直接体现,因而在1990年代的诗歌版图上以其突显“精神”形象而引人注目。1990年代“精神”诗,应该说只有在1990年代的诗歌语境中才能被有效“命名”,其生存价值和意义也才特别明显和突出。因为,它是在“精神”缺失时段和地段中亮出的“精神”声音和影像。在自觉或不自觉中,它的“亮相”总有“对抗”和“建构”——通过精心打造并自适自珍精神家园,以对物质、商品、浮躁、喧嚣、庸俗、浅薄、粗鄙进行隐讳和婉曲抵制和排斥——的意味在里面。就诗歌事实来看,对于有着特定指称意义的1990年代“精神”诗,我们可以从以下三种类型的诗歌来把握和分析:感受、体认精神性存在的诗歌,把握、张扬人、物的精神的诗歌,传达精神吁求、呈现精神营构的诗歌。
一、感受、体认精神性存在
所谓精神性存在,自然是相对物质性存在而言的。其实,究竟何为精神性存在,何为物质性存在,则是由作为某“存在”接受、应对主体的“人”说了算的,而其言说、界定的依据则是此“存在”作用于“人”的方式、效果:惯例地说,如果此“存在”是作用于人们的肉体、感官,满足人们的生理需求和维持人们形而下的物质生活,则归于物质性存在的范畴;相反,如果此“存在”是作用于人们的精神、心灵,满足人们的心理需求,维持人们形而上的精神生活,则应划在精神性存在的队列。扫描1990年代的生存图景,我们不难发现:随着肉身需求、感官满足、世俗欲望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物质、金钱、商品从时代场景的每一角落,飞舞、填塞进了思想意识的几乎全部空间。而与此同时,与拜物教、金钱崇拜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代生活使精神陷入尴尬” 的畸变情形。也就是说,在1990年代,由于上文所界定的“物质性存在”顺应了人们追求物质的心理动机,也在事实上满足了人们的物质生活,因而人们把目光集体性地锁定在了它们身上,以至于不会或很难分出些许以投放给“精神性存在”。然而,在“落叶纷飞/风中树的声音/从远方溅起的人声、车辆声/都朝着一个方向”(王家新《转变》)了的时代版图上,诗人——在1990年代,他们自称为1990年代诗歌写作者,却迎风而上、特立独行地把目光聚焦在了“精神性存在”上。其实,诗人,除非在被当作政治教化工具、意识形态宣谕奴隶的异化时代,一直都把关注和呵护、守护和操持灵魂与精神,把提升灵魂、丰富思想和满足、充实精神生活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在诗人的生命操守里,对于精神性存在的关注、重视和感受、体认,总是超过了对物质性存在的兴趣和注意。在某种意义上,关怀、操持精神、灵魂的诗人自身,以及诗人借助修辞技艺、表意策略等语言手段,以思想、灵魂、精神为质料制作而成的精神性产品——诗歌,本身都是一种耀眼的精神性存在。既然关乎着、包纳着自己及自己的成果,他们理所当然要关注、重视和体验、感受精神性存在。不得不说的是,对精神性存在的过分疏离和冷落,与1990年代灵魂下滑、道德崩析、信仰危机、诗意枯竭、理想塌陷等不堪入目的时代精神“写真”有着必不可分的内在联系。关于这个事实,也许一般人会麻木不仁或熟视无睹,甚至幸灾乐祸、拍手称快,但1990年代诗歌写作者却敏锐而强烈地意识到,而且还传递出了忧虑、困惑、批判的精神意向。因此,1990年代诗歌写作者对精神性存在的关注、重视和感受、体验,除了为自己寻求心灵寓所、建构精神家园这一单一目的,恐怕还在于,以“对抗”和“挑战”对物质性存在趋之若鹜的社会风尚的姿态出现,为“拯救”时代精神境况、“改写”时代精神样态作“虽然无济于事”的“一种努力”。
精神性存在只可能出现、存活在人们的精神性生活中。也就是说,只有过着精神性生活的人,才会留意并感知到它们的存在。对于1990年代的大多数人来说,由于全身心地投入在物质性生活中而无意或不屑于精神性生活,精神性存在自然无法“介入”他们的生命王国,至于说对其的感受、体认,当然就更无从谈起了。但对于1990年代诗歌写作者来说,恰恰因为倍感物质性生活的强大挤压和诱引,所以要深入精神性生活以求解脱灵魂、轻松心灵、安顿生命。这样一来,所谓的精神性存在也就浮现在了他们的生命领地,而对这些精神性存在的感受和体认,其实正是他们所谓的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和方式。同时,也是由于物质性存在的围攻和冲击,1990年代的精神性存在置身在了不幸和悲剧性的处境中。一般来说,人们对不幸和悲剧性的存在总会投以更多的关注和观照,也更愿意将其纳为自己的感受、体验对象,并且产生更为深刻、强烈的感受、体验。所以,1990年代诗歌写作者对1990年代的精神性存在就更有理由投入深刻、强烈的感受、体验。精神性存在与形而下的物质经验无关,也与形而下的肉身体验无关,只是一种超验的形而上的存在,因而无法如同对待物质性存在一样,用感官去捕获、把捉,也不能像感受、体认物质性存在一样去感受、体认。既然是精神性存在,只有动用精神、心灵去捕获、把捉,也只有动用精神、心灵去感受、体认。在1990年代,欧阳江河、西川、王家新等诗人,都在各自的精神生活中,从心灵深处对精神性存在投去了“深情”的一瞥。“风筝火鸟”在常人的感官体认中,不过是纸糊的赏玩、娱乐之物,但当欧阳江河深入到他所营构的精神生活中,却把它“看”成了精神性存在——“飞翔”在“天上”的“火焰”,并且对于这种精神性存在产生了这样的心灵感受和精神体认:“不过飞起来该多好。/身体交给风暴仿佛风暴可以避开”、“飞翔在高高无人的天空,/那种迷醉,那种玉石俱焚的迷醉”(《风筝火鸟》)。在《男高音的春天》里,尽管“从所有这些朝向歌剧院的耳朵,/人们听到了飞翔的合唱队”,但是“我”——自然可以看成诗人欧阳江河自己——却拨开世俗的喧闹、物质的嚣嚷,听到了“歌剧本身的沉默不语”和“远处一个孤独的男高音”等精神性存在,同时抓拍和摄取到了“男高音”的精神肖像:“他在天使的行列中已倦于歌唱。/难以恢复的倦怠如此之深,/心中的野兽隐隐作痛。”西川,这位屹立在“精神的高地上”的诗歌写作者,捕捉、打量并领会、呈示精神性存在是其1990年代诗歌的重要精神指向。在“大风吹来的傍晚灵魂动荡/多少面孔争相浮现,又急忙躲藏”的物质现实里,他注目的是“唯有鸽子乳白色的胸脯在风中闪光”,“聆听”的是“一曲/来自心灵深处的音乐”(《黄昏三章》)。而通过《夕光中的蝙蝠》、《十二只天鹅》等诗篇我们同样能看出他对精神性存在的广泛关注和深度体察。昌耀、臧棣等在各自的诗作中,提供了1990年代诗歌写作者及其诗作这一精神性存在的鲜活“素描”,也传递了他们对其的切己体认和感知。在昌耀的《僧人》中,诗人是“继续追寻自己的上帝”的“僧人”。他们因为有“上帝”“那强有力的形象以美妙的声音潮水般袭来/冲洗灵魂”而“感受到了被抽筋似的快意。”而在臧棣的《临海的沙丘》中,诗人就是“躺在自身的赤裸中”的“临海的沙丘”。对于这一精神性存在,臧棣的切己感受是:“我能感到/它强烈地吸引着我的兽性”、“我能明显地感到它的肌肤/有一种深度:尽管松软/却无法穿透。我的践踏/也不能令它产生伤口,/或是类似的记忆。”
二、把握、张扬人、物的“精神”
这里所说的“精神”,相当于“人是需要一点精神的”这句话中所谓的“精神”,指的是人格、品质、秉性、道德、操守、意志、良知、正义等构成人内在生命的具体精神性要素。与1990年代社会物质文明建设取得累累硕果、人们的物质生活空前繁富、物质欲望空前高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社会、大众的精神状况陷入了重大的危机:“这时大众的精神状态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一曰无所事事,二曰惊慌失措。……这样,生活方式就成为超越一切的头等大事,而生命,要么被与生活方式混为一谈,要么就成为根本无意义的东西。于是,那种与传统道德理想、价值判断盘结在一起的社会审美趣味便会发生动摇。”[3](P59)也许,物质欲求、感官享乐与精神操守、精神状况并非水火不容、完全对立,但是,为了满足物质欲求而放弃、不顾道德、人格、品行等精神操守,却是司空见惯的事实,而沉溺、迷醉于肉身享乐、感官饱足也是会消沉、懈怠、磨灭人的精神状态的。所谓“玩物丧志”、“乐不思蜀”,即是这个意思。在1990年代的世俗生存“乐园”里,物质生活质量的高低、感官欲望的满足程度、财富的个人占有量成为度测一个人“成功”与否的主要甚至唯一尺度。在此单一价值尺度的牵引和推动下,凡是那些妨碍或干扰,甚至是无助于人们谋取财富、满足物质欲望的道德、良知、正义、人格等传统的精神性要素,都被剔除、清洗掉了,从而使得由个人而及民族的精神状况显现出疲软、委顿的态势。就拿1990年代作家来说,尽管有着“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之誉,但不少作家还是拗不过物质和财富的巨大蛊昧,纷纷放弃作家应有的精神性、心灵性操守和价值立场,倒向“市场”而成为“迎合社会趣味的作家”:“写出一些摹写生活方式的作品,并因此广受欢迎,成为时代生活中过眼烟云式的重要人物。”[3](P59)不过,在1990年代“精神”日见稀薄的现实时空中,不甘于精神缺席而竭力发现、寻求、把握并彰显、张扬精神性要素的,还是大有人在。1990年代诗歌写作者便是其中极为显眼的一群。固然在整体社会格局中由中央滑到了边缘和外围,也固然在物质话语的遮蔽下成为了“失语”的“零余者”,但是,1990年代诗歌写作者并没有放干血液中所有的“精神贵族”的成分,也没有从“知识精英”、“文化英雄”逃向“精神侏儒”的大军,而是“退守到”“最后的营地”,“在词语间抵达、安顿”,并在“群山如潮涌来”的时候“燃起”“最高的烛火”(王家新《最后的营地》)——把握、张扬人和物的“精神”自然属于这“最高的烛火”的重要组成部分。“诗歌不仅体现了人类古老的审美想象力和创造力,它更是历史本身锻造出来的一种良知。……正是这种良知使诗歌超出一般审美游戏而成为人类精神存在的一种尺度。换言之,正是这种良知使诗歌在历史中获得了它的尊严。”[4](P3)在1990年代严肃、正直和富于正义感的诗歌写作者看来,在物质亢奋而精神瘫痪的异化时代,诗歌良知的体现之一就在于,不是“对世界‘柔软温和’的抚摸,或对各式‘鲜活场景’的津津乐道”,[4](P3)而应该是从现实物质世界的缝隙或空挡着力发现、把捉出那些还没有完全断气的精神要素,同时对这些精神要素加以彰显、光大,以给“软骨”和“贫血”的时代肌体补充精神的钙质和铁质。
在人的生命世界里,能划归“精神”范畴的具体要素其实很多,诸如道德、信仰、人格、意志、良知、正义、品质等等。1990年代诗歌写作者在他们的诗歌写作中,对多种正值向度的精神要素都加以了“开采”、“挖掘”和张扬、彰显。在前一部分,我们说,1990年代诗歌写作者及其诗歌作品,本身就是一种精神性存在。这里,我们要说的是,作为一种精神性存在的诗歌写作者及其诗歌作品,还有诗歌写作这一“行当”,在物质欲望、肉身吁求和世俗生活的围攻、冲击和破坏、诱惑中的存在,本身就迸射、喷薄出了本部分所指认的“精神”。这就正如孙文波指出的:“即使抛开当代诗歌实际上获得的成就不谈,仅就中国当代诗人在写作中面对困境的不屈不挠的精神,就应该获得尊敬。”[5](P262)反过来说,正是由于这种“精神”的作用,作为一种精神性存在的诗歌写作者及其诗歌作品,还有诗歌写作这一行为才得以在1990年代的社会文化中存在。因此,1990年代诗歌写作者对他们自己身上所内蕴和外显的精神特质和精神要素有着十分到位、精微的把捉、体认,也自然要对此作出自我“推介”和“挺立”。在张曙光的体察中,在“一整个冬天雪在下着,改变着风景/和我们的生活”的物质性生存境遇里,虽然“裹着现实的大衣”也“感到寒冷”了,但“扮演着上帝/或一个蹩脚魔术师”的诗人,不仅“不会放弃这场游戏”,而且还要“像植物”一样“持续地增长”(张曙光《这场雪》)。这样的诗人所张扬、彰显的无疑是一种捍卫诗歌、坚守精神阵地、维护知识分子品格、决不与现实妥协的挑战、对抗的勇气、操守、意志力和信念,而一旦他们的精神性要素得到张扬、彰显,“它最终将淹没一些事物”——自然是世俗性、物质性的事物,也会“带给你一束新的启示”——自然是关于精神的启示。1990年代的一些女性诗歌写作者,比如唐丹鸿、伊蕾等,延续着1980年代后期翟永明们建立的“女性话语”的诗歌写作立场,所极力张扬和彰显的是女性冲出男权话语禁锢、突破习俗成见羁绊的斗争精神,女性渴望生存自由、追求心灵解脱、释放生命本能,从而维护生命价值和尊严的精神要素。在《清洁日》里,唐丹鸿把她所发现和把捉到的一个自主自立意识觉醒了的女性,所爆发出来的这种精神要素进行了充分张扬、彰显:几千年来施加在女性身上的价值标准、陈规陋习,被“我”当作了束缚女性个性自由、生命活力和生理本能的“一堆活动垃圾”。所以,在“今天”这个“清洁日”,在“我期待已久的/环境保护运动”中,“我”要把它们交给“你”,“供你铲除”。而伊蕾所把捉和张扬的是“辉煌的金鸟在叫”(《辉煌的金鸟在叫》),一种不甘于世俗幸福、陈腐生活的女性生存态度和意志,女性生命精神和立场。其实,如果联系到1990年代的特定诗歌语境,唐丹鸿们的诗歌在精神指向上,自然可以单独从女性对封建观念的反叛、挑战和对性爱自由、生理本能的追求、呼吁,影射进、延展成1990年代诗歌写作者以及所有人对物质奴役、金钱束缚、肉身钳制的抵制、反抗,对精神自由、心灵解脱的渴望、向往。吕德安、昌耀等诗人,则在诗歌创作中把握、体会并张扬、昭示出生命固有的呈现、释放强力和活力的精神特质,其主旨动机在于激活、引动、催化出因耽于肉身欲望、物质享乐而退化、弱化了的人们的生命力。吕德安的长诗《适得其所》里“那条蛇”的坚韧、强劲、绵延的生命力落实在“找回自己的尾巴”的行动和意念中。而昌耀在《内陆高迥》、《哈拉库图》、《听候召唤:赶路》等1990年代诗篇中,通过立足于存在意义上对人生命题形而上的思考和把捉,所体认的则是生命的强大内力,是生命本体喷发出来的抗争宿命、拷问生命终极意义的提升力,是内在生命和灵魂的毅力和意志力,是“为战胜生存荒诞所进行的恒久的人格升华与完善”和“对生存悖谬的知不可为而为之的绝望搏击”。《内陆高迥》堪称精微而入木三分地揭示生命强大内力的典范之作:“一个挑战的旅行者步行在上帝的沙盘”——人世的追求、理想原来不过是像蚂蚁在沙盘里行走一样可笑荒诞。然而,面对命运的这种必然性悲剧,人类并没有止步和退却,而是凭依天然具有的崇高,凭依与“宿命抗争的精神”、“迎接上帝的挑战的精神”、“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追求精神”,[6](P259)体现出不屈的意志力、坚韧的耐力、搏击命运的强力和进击世界的伟力:“河源/一群旅游者手执酒瓶伫立望天豪饮,随后/将空瓶猛力抛掷在脚底高迥的路。/一次准宗教祭仪。/一地碎片如同鳞甲而令男儿动容。/内陆漂起。”
三、传达精神吁求、呈现精神营构
在1990年代高扬着“个人写作”的诗歌现场中,曾经“粉墨登场”过五花八门的“个人性”诗歌话语,比如,大谈“技术主义”、“形式主义”和“不及物”、“非历史化”的,“用平面、冷漠的物体碎片占据人在诗中的位置……把诗歌变成闲适、无聊的语言玩具”[7](P508)的“纯诗”;比如,“关心的只是自己……对于小小的自我的无休止的‘抚摸’”[8](P242)的“身体”物语、“隐私”话语;还比如,“接受商业主义和金钱决定论”的以迎合大众低级、世俗阅读趣味的流行歌曲似的消费主义诗歌,等等。然而,这其中的一些诗歌话语固然“讨好”了消费时代,但却终归与“诗歌良知”背道而驰。因而,没有丢失或重新找回“诗歌良知”的1990年代诗歌写作者,不断地审视、自省、检讨着它们,并不断地调整、转换、修正着自己的诗学立场和诗歌抱负。诗人,总是寄身在特定的社会背景中的,诗歌写作也总是“同时代‘语境’交融在一起”[9]的。总的来说,诸如上面列举的诗歌,要么是对语境的疏离、游移,使得诗歌写作“脱离人,脱离构成个人现实存在的具体处境”(周伦佑)而成为“与现实生存脱节”的行为;要么无视语境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在一个充满钢铁与对抗的时代中”,借助诗歌写作“刻意营造的,是一个与伪文学的‘莺歌燕舞’相对应的‘风清月朗’的世界”(周伦佑);要么在应对1990年代世俗化、物质化、肉身化的语境时,持的是一种认可、投合、“‘柔软温和’的‘抚摸’”和“津津乐道”,而不是诗人(知识分子)应有的批判、反思的态度、立场,使得诗歌写作“丧失了大胸襟和大抱负”而成为“粗鄙化”的“私人性的吟咏”(谢冕)。前面提到的1990年代诗歌写作者的调整、转换、修正,就在于,“当历史强行进入我的视野的时候”(西川),他们不再无视“语境”的存在,而是带着明显的“语境”意识进入诗歌写作,并在诗歌写作中“将其直接凸现出来”;同时,在诗歌写作中传达对既有语境的审视、批判、质疑的精神立场、情感态度,并发出更新、重构“语境”的努力的信号。在本就属于“精神性存在”的,以“精神性”和“心灵性”著称的1990年代诗歌写作者的打量、检视与感受、体认中,1990年代诗歌“语境”主要是物质猖獗、商品泛滥、肉身嚣嚷、感官亢奋等“物质性存在”以及“消费主义的物质本位主义”的意识形态、社会心理搭建、铺张而成的。而在沉重的“物质”负荷的挤压、窒息中,“精神”的气息在这样的语境中就显得过于稀薄、缺失了,以至于无处栖身。的确,不管是第一部分界定的“精神性存在”,还是第二部分指认的“精神要素”,在1990年代的诗歌语境中都是微乎其微的。尽管1990年代诗歌写作者借助诗歌写作对其加以了把捉、体认,而且还加以了张扬、彰显,但还是不能将诗歌语境中的“精神”含量增补、提高到应有的理想指标。——而这,在诗歌写作者看来,似乎又是不能容忍和难以接受的。于是,1990年代诗歌写作者不仅通过“诗歌写作”这一行为本身在“物质世界”中坚执和挺立、操持和守护“精神”,而且还在他们的“精神”诗中传达对“精神”的吁求、向往与追寻,并在诗歌中建筑、构造着“精神”,从而投射出丰富诗歌语境的“精神”成分,改善诗歌语境的“精神”质量的动机意向。
深陷在物质的包围中,一方面,1990年代诗歌写作者因为呼吸着精神缺失的空气而感到自身生存的艰涩和枯滞、憋闷;另一方面,他们更为这个因精神荒芜、灵魂沙化而严重失衡的世界以及生存其上的被“物质”异化、扭曲了的人而焦虑、沉痛。因而,他们在“精神”诗中,表达着坚执精神的意志、操持精神的决心、追寻精神的立场;或者传递出向往精神、渴望精神、吁求精神的强烈声音。《傍晚穿过广场》是欧阳江河在1990年代初期创作的重要诗篇。在这首诗里,诗人面对“一个通过年轻的血液流到身体之外/用舌头去舔、用前额去下磕、用旗帜去覆盖/的广场”的“消失”,深深感受到的是“精神”的消失。对此,诗人通过作出“正如一个被践踏的广场必将落到践踏者头上,/那些曾在明媚的早晨穿过广场的人/他们的黑色皮鞋迟早会落到利剑之上,/像必将落下的棺盖落到棺材上那么沉重”这样的诅咒性提醒和忧患性警告,传达了把持、注重、珍视而不能弃置、拒绝、逃避“精神”的强烈吁求。在另一首诗歌《空中小站》里,欧阳江河把在物质现实“包裹”中对“精神”的向往、追寻,拟喻为人在风尘仆仆的旅途劳顿中对“一个/高于广场和楼顶花园的空中小站”的向往、追寻。西川、王艾、沉河等,也分别在现世纷扰中自设了能寄寓精神向往和心灵追寻的物象,如:西川“时常拍打我的肩膀”、“把我带向远方”的“音乐”(《音乐》),王艾“血液深处浸红”的“响铃”(《深处的响铃》),沉河“我所瞻望的一个方向/我所讴歌的一缕芳香”的“河边公园”(《河边公园》)。对于发出“灵魂的居所远比吃饭重要,我需要的是唯一的伴侣”(《灵语》)之声的昌耀来说,更是因为“到处找不到纯净的水”而有“难耐的渴意从每一处毛孔呼喊”(《生命的渴意》)着“精神之水”。这种对精神的呼唤,对于昌耀来说,就“像黑夜里燃烧的野火痛苦地被我召唤”(《呼喊的河流》)。
除了投递吁求精神,追寻精神的嘹亮声音,1990年代诗歌写作者还推卸掉物质的重重阻难,在诗歌中自我建构着“精神”、营造着“精神”,从而给自己的心灵和内生命打造、提供自适自足、自珍自爱的止泊、安顿凭依和空间。张曙光在《香根草》里把自己“培植”成了“穿过天空和果树”的“在明亮而平缓的气流中滑翔”的“香根草”,因为凭着自由的精神和“滑翔的思想”而“穿过篱笆和起重机的阴影/穿过纠结的蓝色线条,上升/并吐出红色的果实”。欧阳江河建构“精神”的方式是,在象征“精神”的“广场”从这个时代“消失”后,作为诗人的个人,却让那种“精神”“在良心和眼睛里交替闪耀,/一部分成为叫做泪水的东西,/一部分在叫做石头的东西里变得坚硬起来”(《傍晚穿过广场》)。读写诗歌、关注精神、操持灵魂,诸如此类的精神性行为,作为1990年代诗歌写作者的“本行”和“本事”,自然成为了他们营建“精神”的主要方式、策略。因而,他们在“精神”诗中也呈现了他们通过诗歌写作、阅读等建构“精神”的事实。在《傍晚,他们说》一诗中,肖开愚指出,也许在世俗的眼光下,“我”用“大半生活”写成的“诗”,显得“沉闷而又烦琐”,但是,“我”却看出“它们”“闪着亮光”——精神的亮光,“它们”在物质世界中的“闪光”如同“易拉罐在垃圾堆里那样有机地闪光”,因而,“我”的诗歌写作行为就是打造、营建“精神”的劳作。孙文波正是“在持续的阅读中”铺就了自己“精神”“地图上的旅行”:“它们就像/另一条河流,带着我走得很远”,并且把“我”引向了“精神”的归宿:“我形容它们。/就像我看见刚刚吐出丝把自己缠住的蚕蛹。”(《地图上的旅行》)而在《在傍晚落日的红色光辉中》,孙文波对诗歌写作这种精神“虚构”的深远意义和重要价值更是给予了直接而明确的标榜和宣示:“可以/给予一只鸟人的灵魂,给予一块石头/飞翔的能力,给予一朵花在火焰中盛开的特性。/它还可以使太阳不落下去,使风雨不来,/使什么时候需要黑暗就让黑暗降临。”
参考文献:
[1] 陈晓明.语词写作:思想缩减时期的修辞策略[A].王家新,孙文波.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2] 洪子诚.序“90年代中国诗歌”[A].王家新,孙文波.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3] 西 川.写作处境与批评处境[A].赵汀阳,贺照田.学术思想评论(总第1辑)[Z].沈阳: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
[4] 王家新.从一场蒙蒙细雨开始[A].王家新,孙文波.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5] 孙文波.生活,写作的前提[A].王家新,孙文波.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6]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7] 周伦佑.90年代中国现代诗走向[A].陈 超.最新先锋诗论选[C].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8] 谢 冕.诗歌理想的转换[A].王家新,孙文波.中国诗歌九十年代备忘录[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
[9] 西 川.90年代与我[J].诗神,199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