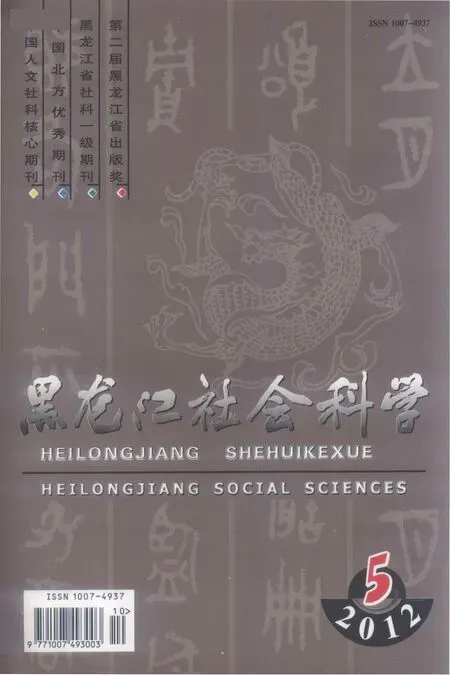性别、民族与半殖民性:刘呐鸥、穆时英的都市风景线
2012-04-13王丽丽
王丽丽
(哈尔滨商业大学基础科学学院,哈尔滨150028)
现代文学一个经久不衰的主题,就是令人魂牵梦绕的乡土和喧嚣世俗的都市的截然对立。长久以来,在重农抑商的国度里,城市始终扮演着斑驳陆离、暧昧不清的角色。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城市意识”才恢复成为现代性新话语中的一个中心词。就此而论,在现代中国,再没有哪个流派像新感觉派小说那样站在西方现代主义的角度来表现都市了。作为半殖民都市的畸零者,刘呐鸥和穆时英既审视都市又为都市代言,他们借助一系列妖娆、摩登的女性形象,拟构一种全新的城市人生观和两性关系。这道独特的“都市风景线”,在不期然间,便成为中国在风起云涌的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民族寓言。
一、欲望与诱惑:都市的另一张面孔
本雅明在描摹巴黎时,曾这样说:“巴黎城是以豪斯曼赋予它的形式进入这个世纪的。”“一本与巴黎规模庞大的改造工作潜在相连的书完成于进行这种改造的数年之前。”[1]他称这本书就是诗人心中的“巴黎图景”。由此可见,一个城市的新兴,不仅需要经济硬件做基础,更需要新的文化范式做代言。显然,与十里洋场那块“飞地”水乳交融的新感觉派,无疑承担了这个角色。
新感觉派小说通常都聚焦于城市生活漂浮不定的情感体验,这种体验基本上环绕着一个两性故事而展开。为此,刘呐鸥将感觉化的叙事方式发挥到极致。他采用一种拍电影的方式,让主人公的目光像镜头般自由游走:繁华的城市生活如无数的活页画面,画面的中心是饮食男女演绎着非理性、迷乱状态的情欲故事。在他的小说中,男主人公不再是“智慧的主体”,他们把欲望加诸一个对象化的女性身体上,自己却成了自信十足的现代女性手中的“玩物”。他的女主人公是第一批都市“现代性产物”,象征着半殖民都市的城市文化,以及速度、商品文化、异域情调和色情的魅惑。由此她在男性主人公身上激起的情感,是极端令人迷惑又极端叛逆的,其实质传达了这个城市对新感觉派作家的诱惑和疏离。
《两个时间的不感症者》无疑完美体现了这种女性。“她”——“sportive 的近代型女性”[2],当H和T尚在为如何支开对方、独自拥有“她”而使尽浑身解数时,“她”却突然起身说:“你们都在这玩玩儿去吧,我先走了。”撇下两个发呆着的男子,扬长而去。小说《礼仪与卫生》中那位渴慕东方女性的法国先生普吕业在形容女人时说道:“她们动不动便要拿雌的螳螂的本性来把异性当做食用。美丽简直用不着的。她们只是欲的对象。”刘呐鸥的《游戏》中的男性眼睛,“忽然间看见一只老虎跳将出来……急忙张开眼睛定睛看时,原来是伏在那劈面走来的一位姑娘的肩膀上的一只山猫的皮毛”。惊魂未定,鳗鱼式的、叮嘱他“五点半,别弄错,带你的嘴唇来”的女子,已令他发疯。末了,他为自己的“瘦”,为自己在她面前的“战栗”而深感“悲哀”。
fontegnac,这些形象特殊而且流光溢彩的汽车牌子,显然是现代性的物质表征,是时间与速度的象征。刘呐鸥小说中将女人和汽车并置暗示了“这个城市的节奏就是现代女子更换男友的速度,就是现代女子对风驰的电车的喜爱:一时的场景一时的罗曼史,一个充满飞车和短暂邂逅的都会”[3]。与此同时,《流》里的男主人公还把拥挤的车辆比作小甲虫,不断吞吐着人们。从中可以看出,即使是在颂扬工业文明所带来的便利时,它也引起作者深深的焦虑。《方程式》这篇小说的标题是很具代表性的。从刘呐鸥的第一部小说《游戏》开始,故事所引起的激动慢慢消解,徒劳的追逐、爱的三角等等,就像方程式变得越来越明晰。一个四人“旋转的游戏”,一男三女他们没有身份,甚至连名字也被规约为一个大写字母,就像数字一样。小说讽刺的是婚姻游戏本身,以及一个都市白领无人格的日常生活。
在刘呐鸥的小说里,不管他描摹的都会女郎多么具有异域色彩和象征意味,她们不过是都会舞台上一个叙事人物。她被写得很浮表,正是因为她要在一个更深的意义上来象征这个城市。作为城市生活如鱼得水的享用者和创造者,他们既批判性地嘲弄都市的生存方式,又沉溺于城市的物质温床之中。即使是这个都市的道德沦丧在这样的语言裱糊之下,也显得相当有魅惑力。
二、民族寓言:女性躯体的文化隐喻
和刘呐鸥一样,穆时英也征用了都会景观里所有的灯红酒绿,依然用摩登女性来建构上海的城市话语。所不同的是,他把笔墨更多地集中在女性身体上。作家调动了多种修辞方式拟想了这类有着“深海的电气鳗”[4]魅力的女性何以会让一个原本秩序井然的男性世界轰然塌崩的震撼感。同时在女体想象中,作为“无意识的无产阶级者”,完成了一个有关国家、民族的寓言。
对女性的诱惑力和震撼力的极致想象,《白金的女体塑像》堪称经典之作。正如标题所暗示的,这个故事讲一个医生对一个女子身体的“探究”。静静仰躺着的女体是一种自在物,她与道德、与感情、与物质全无联系,它只是一具“金属性的,流线感的,视线在那躯体的线条上面一滑就滑了过去似的”女性躯体。以一寸一寸的活的肉、血管、骨骼诸细部诱发着医生的男性欲望。“消瘦的脚踝”,“没有骨头的胸脯”,“白桦树似的身子安逸地搁在床上,胸前攀着两颗烂熟的葡萄,在呼吸的微风里颤着”[5]。正如这“谜”一样的细节像“骨蛆”似的钻进医生的意识里,深深地诱惑着他。直到没有标点的紊乱文字的出现,男性叙事进入癫狂状态,并反复发出一连串的片语“主救我白金的塑像啊主救我白金的塑像啊……”在这一连串的意识流似的祈祷中,“白金塑像”和“主”平等置换,女体成为男性叙事膜拜的对象。
在《Craven A》中,女性身体更多了一层寓言的维度。故事一开始,男主人公看到舞厅里坐着一个静静抽着香烟的女郎,他便开始认真地研读起来,并用夸张的比喻来描述她的身体和脸,这样她的身体很快就变成了一张国家地图。“在桌子下面的两条海堤,透过了那网袜,我看见了白汁桂鱼似的泥土。海堤的末端,睡着两只纤细的、黑嘴的白海鸥,沉沉地做着初夏的梦,在那幽静的滩岸旁。在那两条海堤的中间的,照地势推测起来,应该是一个三角形的冲积平原,近海的地方一定是个重要的港口,一个大商埠。要不然,为什么造了两条那么精致的海堤呢?大都市的夜景是可爱的——想一想那堤上的晚霞,码头上的波声,大汽船入港时的雄姿,船头上的浪花,夹岸的高建筑物吧!”[6]
其实早在穆时英之前,像萧红这样具有爱国情怀的作家,就曾把遭受日军践踏的满洲国比作是女人的身体,并受到鲁迅的强烈推崇。在《生死场》中她是用女性身体与民族主义话语并置的方式来书写战争的。《生死场》1935年版的封面是黑色的块面包含小说的标题,一起叠印到深红色的背景上的。黑色的图案是一幅妇女头像的剪影,这恰巧与满洲国的地图相契合,图中切过封面的斜线则象征着中国被切割的国土。《生死场》中女性的身体为观察民族国家的浮沉提供了批评的视角,也显示了萧红对于性别与民族思考的深刻张力。相形之下,穆时英的这幅色情身体属于完全不同的范畴:他把祖国母亲视为魅力无穷的女性神话,借此来压倒“自以为是的男性主体”。穆时英成功地创造了女性那美妙无比的身体,却屏蔽了女性的心理和行为。尽管如此,在一个女性身体不受优待的文化传统里,比起其他的作家,穆时英的创作是具有先锋意味的。应该说,面对国家的生死存亡,穆时英也在不断地进行着文艺观的改造。他意识道:“在此时此地的中国,我们也不能不提出时代表现了并鼓吹了民族生存斗争这一点作为作品底社会价值底评价基准。”“拿铁和血去拥护我们民族底独立自尊与自由发展。”[7]和普罗文艺所说的求大多数人的幸福的观念相比,穆时英剔除了阶级的内容和意识,而代之以人类的视野。实际上,穆时英在写《上海的狐步舞》时便有一个宏伟的计划,这就是他准备写的小说《中国一九三一》中的“一个断片”[8],换言之,他是希望让都会景观承载更多的意义,借此成为民族寓言的一部分。茅盾的《子夜》副标题是“一九三0年的一个中国传奇”。尽管这两位作家的意识形态不同,他们的作品在小说设计上却有惊人的相似:用城市作为在关键岁月里的国家缩图。
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茅盾的《子夜》是采用了历史发展和阶级矛盾的“宏伟叙事”,而穆时英的《上海的狐步舞》则是在空间的喻体上架构起来的都市断片。“一个断片”,即一组等待被剪辑进一部电影定本的镜头。它的“叙述”靠的是场景序列,以电影的方式透视的都会空间。在这个电影般的小说场景里,角色和情节都无关紧要,人物则约化为被这个城市“光、热、力”的旋风所俘虏的纸板人。穆时英在小说的结尾处写道:“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很显然,它暗示了上海既是天堂,又是地狱,又是一幅充斥着声光魅影华丽的文化地形图。穆时英在《公墓·自序》里看出:“在我们的社会里,有被生活压扁了的人,他们可以在悲哀的脸上戴了快乐的面具的。”这些带着“快乐面具的人”与其说是个喜剧人物,不如说这是一群被生活抛离的孤独者形象。穆时英身处其中,并在文本中对他们倾注了永恒的人性同情。尽管穆时英总是以精英自诩,然而他常被人们误解为天才的孤独者。
三、半殖民地性:摇摆与暧昧的知识分子立场
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可谓是披着俗艳外衣的、充满异域情调的“尤物”。外国势力的相互争夺造成了对中国多元和多层次的殖民统治状态。而“半殖民地”的性质加剧了中国现实的碎片化,破坏了中国社会的稳定性。面对西方异质文化的诱惑,中国的现代主义者们处在一种屈从与反抗的暧昧状态。他们一方面将现代性视为充满诱惑的、迷人的、值得相望的东西;另一方面,又在自己地区范围内修订、再定义、再创造着现代性。
尽管新感觉派作家在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下也满怀“羞辱和愤怒”,但都不愿离开,因为他们同时也享受着上海的种种物质便利和通商口岸的租界庇护。殖民主义、现代性和民族主义这些东西交融在一起,构成了特殊的历史语境下的知识分子话语。刘呐鸥和穆时英在生活方式和知识趣味上属于最“西化”的群体,而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曾在任何意义上,把自己视为相对于一个真实的或想象的被殖民的“他者”。相反,在中国作家营造他们自己的现代想象过程中,他们对西方异域风的热烈拥抱倒把西方文化本身置换成了“他者”。在他们对现代性的探求中,这个置换过程是非常关键的,因为这种探求是基于他们作为中国人的对自身身份的充分信心。实际上,在他们看来,现代性就是为民族主义服务的。
霍米·巴巴相当微妙而模糊地定义了“戏拟”。按他的说法,“殖民戏拟就是对一个变了形的但可辨认的他者的欲望,他基本上,但又不完全就是那个差异的主体”[9]。因此,巴巴的理论暗示了即使是殖民客体的“部分代表”,也可以是既谦卑又带有颠覆性的。尽管刘呐鸥、穆时英的写作带着喧哗的西化色彩,但他们从不曾自己想象为或被认为是因太“洋化”而成了洋奴。在他们的作品中,我们得出一个明显的结论,即虽然上海有西方殖民存在,但他们作为中国人的身份意识却不曾出过问题。正是因为他们那不容置疑的中国性使得这些作家能如此公然地拥抱西方现代性而不必畏惧被殖民化。尽管上海居民在现代性面前也有焦虑和迷茫,但他们是欢迎以具体的“机械化”形式到来的现代性:火车、电报、电车、电灯和汽车。这并不意味着,在中国,整体而言的国族现代化构造已经完成了。现代化远未完成。但在20世纪30年代早期的一段时间里,一种源于对国族自治的呼吁而产生的民族主体论思潮却是规模空前的。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正好达到了城市发展的一个新高度——新造了很多摩天大楼、百货公司和电影院。这种新的城市景观成了新感觉派作家笔下小说的背景,他们见证了上海的辉煌奇观,也共同参与了现代性的建构。
[1] 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107.
[2] 刘呐鸥.都市风景线[M].上海:上海水沫书店,1930:93.
[3] 史书美.刘呐鸥的上海都会景观[M].亚洲研究杂志,1996,(4).
[4] 片冈铁兵.刘呐鸥小说全编[G].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133.
[5] 穆时英.白金的女体塑像[G].上海:上海复兴书局,1934:3-5.
[6] 穆时英.公墓[M].上海:上海现代书局,1933:110.
[7] 穆时英.电影艺术防御战——斥掮着“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的招牌者[N].晨报,1935-09-07.
[8] 穆时英.公墓·自序[J].现代杂志,1931.
[9] 霍米·巴巴.论戏拟和人:殖民话语的矛盾性[M].伦敦和纽约:儒特爵父子公司,1994:86-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