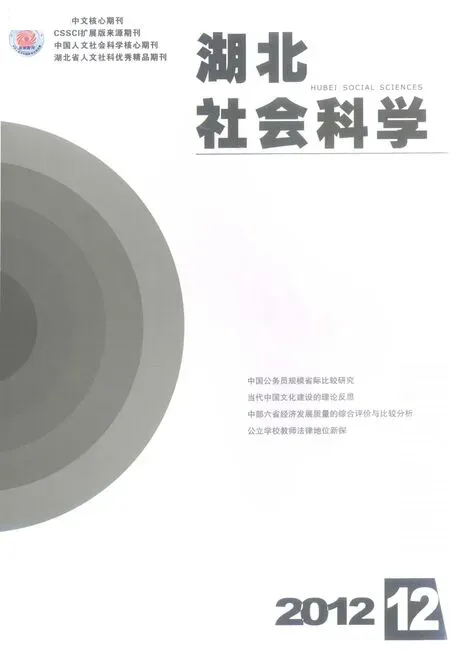多重语境下的湖北漆艺发展
2012-04-12刘茂平
刘茂平
(湖北美术学院 教务处,湖北 武汉 430060)
水墨、陶瓷、大漆是中国三大传统艺术媒材,也是对东方中国具有标识意义的艺术样式,水墨经过千年的发展,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和西方油彩抗衡的绘画种类,水墨画在今天的中国经过深入探索,形成了传统延续和实验性水墨等多元发展的局面。陶瓷自不待言,中国因陶瓷而被西方命名,在陶瓷基础上发展而成的陶艺,今天不仅发展成为世界性的艺术种类,为世界各国人民所喜爱,而且陶艺的当代创作也十分活跃,陶瓷产品和每个人的生活都须臾不离,而陶艺也获得了极强的当代性,陶瓷在发展的过程中较好地处理了实用和艺术的关系。
反观漆艺,其发展还不能和陶艺同日而语,实用漆器基本退出了现代人的生活,而作为艺术样式的漆艺发展也不尽如人意,和周边邻国如日本、韩国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随着岁月的流逝,时代的发展,漆艺在中国虽然不够兴旺,但漆艺的美,当然也包括漆器的实用,并没有随时代的发展而消逝,相反,在廉价工业品充斥的时代,它仍有一种不可替代的美和极其丰富的实用价值,正是因为如此,作为楚地的故乡,在一座战国墓葬就出土一千多件漆器的湖北,应以宏大的手笔,具体的措施,有力地推动漆艺在湖北的发展和复兴,打造具有历史传统的文化名片,重现楚国漆器艺术的辉煌。
一、楚国漆艺的伟大传统
楚国漆器传统是湖北漆艺发展的历史语境。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认识漆和使用漆的国家,考古发现证实,我国在距今七千年前就有了漆器的使用,中国漆器不仅历史悠久,而且也是世界漆手工艺的发祥地,对天然漆的使用,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重要贡献。从新石器时代发展至战国和汉代,漆器工艺发展较快,应用范围也变得十分广泛。秦汉是漆艺发展的鼎盛时期。在魏晋南北朝,漆器因受到绘画的影响,打破了平涂的风格,出现了晕色技法。唐代发展了金银平脱漆器和雕漆漆器。宋元两代,戗金、雕漆等技艺进一步发展,漆器更加繁荣。明代和清代,中国漆器发展至全盛时期。中国的漆艺不但形成了自己艺术史上最为灿烂辉煌的乐章,而且影响了朝鲜、日本等周边国家的漆艺发展,并逐渐流传到欧洲乃至全世界。但是漆器由于材料的特性,主要是收缩变化乃至朽坏,难于长久保存,虽然从故宫和各地博物馆收藏来看,不乏元明以来传承下来的精美漆器,但历代流传漆器和其他文物相比,不仅数量少,而且年代更久远的就极少了,是考古发掘,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奇诡灿烂的“漆器时代”。正如皮道坚在《楚艺术史》中论及江陵出土战国楚漆器时所言:“漆器的应用范围涉及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几乎无所不包。因此有人说楚的上层社会简直就是一个‘漆器的社会’”。[1](p128)如果我们拿墓葬实物来佐证,就知此言不虚。以出土成套编钟闻名于世的曾侯乙墓,其实最大宗的器物是漆器。主要有礼乐器、盛食器、酒器、其他生活用具、车马具、兵器以及丧葬用具等62种,共1047件。在已经清理发掘的五千多座楚墓中,有近千座出土了大量漆器,在8座已发掘的楚国封君一级的墓葬中,哪怕是已被盗和遭破坏的,仍然出土大量漆器,少则一百多件,多则为1994年发掘的河南新蔡葛陵达344件。[2](p10-12)可见,所谓“漆器时代”的结论是以楚国的漆器为依据的。
楚漆器的伟大贡献不仅在数量多,而且有十分优良的品质,笔者曾多次假设,比附于石器文明、陶器文明、青铜文明,应该事实上存在着一个漆器文明,这种假设是否立得住还需要深入的研究,但楚漆器的丰富多彩,其表现是多方面的。
1.品类繁多。楚国漆器种类极其繁多,多数是实用器,少数为明器,其漆器品类齐全,广泛地运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衣食住行的各种生活用品和杂物玩具到处都见漆器的使用。最常见的是日常生活用品,其次是军事和文化娱乐用品。按其用途可分成生活用器、兵器、神异器、礼仪用器、丧葬用器等。
生活用器包括饮食器、梳妆用器、居家用器、服饰车马等。 有盒、樽、豆、俎、奁、盤、碗、勺、羽觞、禁、虎子、几、案、床等等。如荆州马山楚墓出土的凤鸟纹漆盘,江陵雨台山楚墓出土的彩绘漆鸳鸯豆,曾侯乙墓出土的彩绘漆鸳鸯盒,杯体呈鸳鸯状,都采用了拟形设计,反映了战国时期漆工艺制作卓越的艺术想象力。
兵器有弓、盾、甲、剑盒、剑鞘、戈、矛、箭服等,而且工艺水准很高,如长沙出土的剑鞘至今光亮照人、色泽如新。
乐器有鼓、瑟、琴、笙、笛、排箫、五弦乐器和编钟等,如天星观楚墓出土的彩绘漆虎座鸟架鼓,融实用性和艺术性于一体,是楚乐器中富有代表性的打击乐器。
丧葬用具有镇墓兽、墓俑、卧鹿、立鸟、飞鸟、床和棺等。如天星观出土的虎座鹿角飞鸟,造型奇特,是楚墓中常见的丧葬用具。长沙浏城桥楚墓出土的镇墓兽,是楚国典型镇墓兽避邪用具,随县曾侯乙墓出土棺具内外髹漆彩绘的动物形象,似人非人,似兽非兽,为研究远古神话、巫术礼仪等方面提供了宝贵资料。
2.精良的胎骨工艺。楚国漆器的胎骨可分为木胎、竹胎、布胎、陶胎、皮胎、夹纻胎、藤胎和积竹胎等。木胎是楚漆器的主要胎质,不同的器形往往采用斫削、旋挖、粘卷、凿雕、隼嵌等多种不同的制作方法。为了增强胎骨的耐用程度,战国中晚期已在某些木胎上增加金属的口、耳和足等附件来加固胎骨,这种用金属嵌镶加固作为装饰的漆器称扣器,它的出现为随后汉代金银扣器的盛行打下了基础。竹胎一般用竹筒作成器形,然后髹漆。积竹胎仅见于戈、矛等兵器部件,胎骨具有弹性和韧性。战国中期楚墓中已有发现胎骨以麻布和漆灰做成的夹纻胎漆器,这是战国时代楚国髹漆工艺的又一重大进步,为我国后来脱胎漆工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皮革器、铜胎、漆纱虽然比较少见,但反映了楚国工匠对漆器工艺的多方面尝试,也说明了漆器运用的广泛。
3.华丽的漆器装饰工艺。楚国漆器在装饰方面纹饰优美、彩绘精工、题材广泛、装饰手法高超。楚漆器大多墨髹朱里,常用金、黄、红、赭等彩绘纹饰施于黑漆地上,色彩丰富,光泽绚丽。楚黑漆的做法有两种:一种是揩光黑漆,多为一髹而成,黑亮似玉。另一种是退光黑漆,其做法也有揩光和退光两种。有些漆器可能是用桐油作稀释剂,加色漆配成油彩绘饰各种花纹图案,因而光泽鲜明,色彩瑰丽,经久不变。装饰手法除彩绘之外,还有锥画、堆漆、填漆、镶嵌、描金银、金箔贴花等数种,说明二千多年前楚国工匠们就熟练地掌握了用金、银金属色的高度技巧。此外雕花、针刻、银金铜扣等技艺也被广泛运用,使之华丽奇巧。如临澧楚墓出土了金箔贴花漆器。
4.丰富的漆绘图案。楚漆器纹样极富变化,颇有特点,有单独纹样、二方连续和四方连续纹饰。比较有特色的图案是以禽兽为主,再辅以传说的龙、凤或与现实生活中的虎形相结合而构成想象奇特的“神兽”、“神鸟”图案。其主要纹样有云纹、龙纹、凤纹、鸟兽、花草、车马和人物等图案,于是一个光怪陆离、富丽堂皇的缤纷世界便跃然而出。湖北荆门包山圆奁,胎是在麻纱两面贴以皮革,以生漆粘接。通体内髹红漆,外髹黑漆,用深红、橘红、土黄、棕褐、青等色彩绘纹饰。盖顶面用红漆绘三周圆圈纹。中心圈内用深红、橘红、土黄、青四色绘相背对称四分龙凤图案。外圈用红、黄、金三色绘二方连续龙凤图案。盖外壁上、下各绘一周红色带纹,带纹之间用橘红、土黄、棕褐、青等色绘一组由二十六个人物、四乘车、十匹马、五株树、一头猪、两条狗和九只大雁组成的出行、迎宾图。器身外壁用深红、土黄、青三色绘折线式二方连续变形凤鸟纹和变形兽面纹。器底绘两周红色带纹,其间绘折线式二方连续勾连云纹。此外,众多的楚漆器上还有丰富的文字内容。
5.神秘的漆器造型。楚国漆器非常讲究艺术造型,其造型以大方和美观为主要特色,或小巧玲珑,或奇特雄伟。有各类木俑,动物形象如虎、鹿、凤、鸟、蛙、蛇等,都传实写真,形神肖似,生动逼真。楚墓中如虎座飞凤、虎座凤鼓架、木雕小座屏等。镇墓兽是楚墓中的典型器物,采用复合型造型,一般包括方座、兽身、鹿角三部分,构思独特,想象雄奇,成为楚人观念中的魔幻世界的神物,是楚人引魂升天、除恶避邪含义的形象化,反映了楚人“信巫好祀”的巫文化背景下漆器的造型特色及其社会意识。王祖龙在分析楚美术复合造型思维特征时指出:“复合型造型实际上是一种自然属性相加的视觉表达,它不仅要达到和体现万物有灵的目的,同时还直接为‘互渗律’的思维方式所孕育”。[3](p92)
二、漆艺发展的现实语境
作为古代漆器艺术发展取得辉煌成就的楚地,在现代漆艺发展的过程中,觉醒其实是比较晚的。不仅落后于日本、越南、韩国等传统漆器艺术保留和现代漆艺发展较好的东亚诸国,就是在国内而言,相较福建、北京、四川等地,也还有很大差距。因此,我们了解一下当前国内外漆艺发展的一个基本背景或语境,对我们漆艺的发展,应该是大有裨益的。
(一)漆艺发展的国际语境。
虽然日本漆工艺是从中国传过去的,但日本极大地发展漆艺的运用范围和表现力,以致在世界是被称为漆国。据相关考古证实,公元前200多年,中国的漆艺就流传到日本,2000多年来,日本在发展漆艺的过程中,除继承中国传统漆艺技术之外,还发展出很多具有本国特点的漆工艺,如沉金、莳绘等。日本的现代漆器在设计定位上力求贴近市场和大众生活,并且不断拓展漆器的运用领域。如在医疗保健领域,开发出具有杀菌、保温功能的漆器制品,日本的现代漆器,表现内容丰富多彩,表现手法也有许多创新。他们的漆器中既有能反映日本民族精致细腻特点的元素,又有能反映时代特点的简洁、流畅、明快的具有时代特点的现代元素。日本有大批从事漆艺创作的艺术家和制作漆器的工匠,艺术家和工匠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日本的漆器,高、中、低档都有,手工制作和机械化生产共存。手工制作的漆器作为高级艺术品,为上层富裕者使用或供出口。机械化生产的漆器产品因为生产效率提高,故售价低廉,能为普通家庭所承受。在日本,漆器专卖店很多,大商场里一般都有漆器专柜,画廊里能看到漆艺家们的漆艺作品。日本人借助现代科技手段研究漆器,在漆器的原料配方、工艺技巧和艺术造型等方面都获得了许多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这一切是怎么实现的呢?这与日本政府对传统工艺的保护和提倡密不可分。早在1927年,日本就将工艺作为第四类形态的纯美术与日本画、油画和雕塑并列展出。既然工艺作为“观赏的工艺”,就可以抛开实用,像纯艺术那样发挥想象和创造,在国家政府主办的 “日展”中的地位被确立下来。1950年,日本文化财产保护法颁布,由国家制定政策对在历史上、艺术上具有极高价值的工艺美术技术,进行保护扶植。1954年,日本人间国宝制度建立,促成了由日本宫内厅支持的“日本传统工艺展”。1959年,在工艺应该原本属于日常生活的理念影响下,“日本生活工艺设计协会”创立,并组织了由通商产业省支持的“日本生活工艺设计展”。1988年,在以上展览活动的基础上,随着当代艺术在世界范围内的活跃发展,特别是作为日本当代艺术的代表“物派”的影响,一批由东京艺大漆艺科毕业生为主的12人,在东京ISOGAYA画廊,举办了“漆的现在性”特别展(材料与技术系列I)。从以上的年表看,几乎贯穿整个20世纪,日本的漆艺文化生态多元的氛围可见一斑。呈现了一种可以由各自相对独立见解、主张的群体组合,不相诋毁,互不干涉,既有非常古老传统的根系脉络,也有极为新异当代的新芽血液。今天,日本漆艺界,形成了诸如:自由抒发个人情感审美表现的所谓——“日展创作派”。传承古典审美意境技艺的所谓——“传统工艺派”。融入民众当代时尚生活的所谓——“生活工艺派”。追求材料技术当代性表达的所谓——“漆艺的现在派”等多种风格、门派同时并存,共生、共荣的局面。
现代工业文明的迅猛发展,几乎对所有国家的传统工艺文化都产生了极大的冲击。但是在日本,传统文化与现代工业文明之间的矛盾,却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控制。漆艺文化在日本也同样形成了自己的多元生态,同时,日本的莳绘漆艺开始反过来对我国的漆器工艺产生了重大影响。1907年日本原田教授就应邀到我国的福建传授漆艺,1924年福建漆艺大师李之卿去日本原田所在的长崎美术工艺专科学校研习漆艺,1936年我国近代漆艺的代表人物沈福文也东渡日本,在松田漆器研究所学习漆艺。80年代以后,两国漆艺交流更为密切,双方互派留学生,漆艺学者互访,举办漆艺交流展等。目前,日本漆艺在工艺、材料、加工、设备等多方面已在世界上确立了领先地位。可以说,在整个20世纪至今,以漆艺为代表日本的传统文化艺术与现代工业文明并行不悖,都得到了高度发展,不偏不倚、相得益彰,尤其值得我国借鉴。
下面我们来看越南:生漆质料的坚固特性,很早就被越南人所认识,越南语也有一句成语“如胶似漆”,越南许多文学作品也是以漆的坚固性来形容友谊和爱情的。史书记载,李朝(公元十一世纪或更早些)时代的一些庙守中已经出现了很多装饰极为精致的漆制品,河内文庙及顺化省阮代帝王的庙宇中的一些漆艺装饰品,都是十分宝贵的越南漆器。同时,越南早在15世纪就与中国开始漆艺交往,后黎时期(1443—1460年)曾派出一位叫陈相功的使节来中国考察并学习漆艺,回国后,在越南京都地区推广,此人至今仍被认为是越南的“漆祖”。
现代越南的漆艺成就,主要表现在磨漆画方面。越南的磨漆画起始于20世纪20年代,在法国殖民统治时期的1928年前后,印度支那高等美术学校的学生们在学习油画技法的时候,偶而将他们家乡父老和工艺师傅的漆艺技术带到美术学院的课堂中来,透明漆和其他色漆产生的肌理和审美的魅力使学院的老师和学生们大吃一惊。这种漆画技法特别引起了很多法国画家和教授的兴趣,大家将这种绘画称之为磨漆画,在法国教授的鼓励下,越南的一批美术工作者和印度支那美术学院的学生,将传统的漆艺髹涂工艺和漆艺材料,大胆尝试运用到平面绘画中,创作出以漆作材料,表面磨平推光的平面绘画作品。
到了1932年间,美术学院的学生又研究了日本的漆艺技术,并结合了越南漆艺的传统技法,创造性地使用金粉、银粉的装饰方法,即将金银箔放在网筛中碾碎后,根据纹样需要撒在色漆上,如竹子撒金粉,湖水倒影撒银粉等等,同时还改进了推光和抛光的技术。这些研究成果为越南漆画艺术的装饰方法开拓了更为广阔的前景。
在1935年到l945年的10年间,磨漆画艺术在画家们的进一步研究下得到了更快的发展。如在一些已经磨平光滑的漆面上,再用漆加炭粉或瓦灰堆出纹样成浅浮雕状;或将纹样阴刻在磨光的漆面上;或多层髹涂以后再研磨出纹样和肌理。画家们探索的新形式和新技术使越南民族艺术在表现形式上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进步。不仅如此,一批漆画家在研究新形式和技术的同时,还进行形式主义的探索,创作了一批模仿欧洲的抽象主义或形式主义的作品,扩大了漆画创作的可能性。
越南磨漆画在表现内容、形式语言、材料运用、制作工艺等方面经过数十年的实验与探索后,创立了洒金、雕填、嵌蛋壳、彩绘、变涂、研磨等一套自己的磨漆画表现技法体系。越南将绘画与漆工艺结合,创造了现代磨漆画,早于世界其他国家。越南的磨漆画极具本民族特色,对中国现代漆画创作的启示和现代漆画的独立进程,起到启示和直接的推动作用。
再看韩国:韩国在历史上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西汉时,朝鲜北部曾属于中国版图,当时正值中国历史上漆艺的黄金时期,可以想见,当时大量的漆器从中原流入了朝鲜半岛,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考古学者及著名漆艺家松田权六在朝鲜乐浪地区发掘了数以百计造型精美,色泽艳丽的汉代漆器。[4]在中国漆艺的启发和刺激下,朝鲜半岛的本土漆艺逐渐发展,走向成熟,尤其是在螺钿镶嵌技法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民族风格。二战以后,韩国政府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特别注重继承、保护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认为传统文化关系到民族的尊严与自信,有利于在世界上树立本民族形象和提高国际地位。漆艺被认为是韩国传统文化的象征之一,为此,韩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激励措施,民间组织也纷纷响应,在政策、资金等各方面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先进的现代材料加工技术以及良好的社会漆艺土壤,为韩国漆艺在上世纪中下叶的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当前,韩国漆艺的产业结构、艺术观念、表现技法在某种程度上均完成了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较好地融入了现代生活体系,具有了现代审美意识。韩国漆艺在短短20余年的时间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1.韩国政府的“无形文化财”保护制度,由政府文化机构对全国民间漆艺家进行评选、审核,对传统漆艺有特殊贡献者被授予“无形文化财”称号,每年投入一定的资金,以使其技术、经验得以保护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类似于我国近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韩国成立了现代漆艺家协会,并举办每两年一次的全国漆艺家会展,对推动韩国当代漆艺的发展起了关键的作用。
2.民间漆艺的丰厚土壤及传承是韩国漆艺繁荣发展的关键所在,近年来韩国各种漆艺材料的生产、加工、后期处理及销售体系更为完善,完善的材料加工体系也为韩国漆艺家在创作过程中提供了便利条件。韩国传统漆艺是以螺钿镶嵌为主要特点,器具主要为家具及日用品。当代韩国漆艺家在认真继承了传统的基础上积极探索韩国漆艺的现代表现与运用。在技法上,当代韩国漆艺已经不再局限于传统螺钿镶嵌,脱胎、变涂等工艺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作品个性化趋势日益明显,作品类型突破日常生活用品,独立欣赏型漆器、与环境相结合的漆艺装饰等公共艺术项目都有了极大的发展。
3.高等院校漆艺教育的普及化:韩国政府和民间组织把漆艺作为民族文化的象征之一,重视高等院校对漆艺人才的培养及学术研究,二十余年来在漆艺的高等教育方面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艺术院校设立漆艺专业,目前,东亚大学、新罗大学、大邱大学、培材大学、淑明大学等16所综合性大学都设立了漆艺专业和漆艺课程,师生及研究人员达数千人,其规模已经远超目前的中国。
4.当代韩国漆艺创作日益呈现出个性化趋势,风格迥异,流派纷呈。漆艺的材料技法、运用范围等方面均由传统模式向现代多元化方向发展,其中主要分为传统和现代两派,但区别并不绝对,现代派的作品能很好地体现传统的精髓,传统派也并非绝对的传统,在形式和内容上也具有一定的现代感。
现代派的代表人物为韩国著名漆艺家、中央大学的教授白泰元,大量使用化学涂料。作品色彩对比强烈,有现代色彩意识,图案充满张力、动感。传统派的代表人物为金圣洙教授,其作品以传统木漆工艺为主,多为家具,他注重传统精神与现代形式的融合,将传统漆艺融入现代生活保持其生命力。除以上两派之外,韩国同时还有一批居于在传统和现代之间的个人风格较强的作者漆艺家。
5.良好的漆艺市场。韩国把漆艺作为本民族的文化象征,具有良好的社会土壤,民众对日用漆器认同度很高,不同档次价位的漆器都有自己的市场,公共艺术使用漆工艺媒介的很多,同时学术与市场形成良性互动,为韩国漆艺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空间。反观我国当代漆艺与人们生活起居相脱节,在日常生活中几乎完全放弃了对漆器的使用,造成一系列漆艺材料加工业的萎缩,使中国漆艺的发展又受到材料加工业的限制,造成恶性循环。
由此可见,韩国漆艺从传统角度看,在螺钿镶嵌技法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民族风格,而现代的漆艺立体作品突出,备受世界同行关注,当代韩国漆艺创作则个性化的趋势突出,风格迥异,流派纷呈。韩国漆器艺术在各方面逐步走向成熟并显示出的优势,尤其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除了东亚传统的漆艺大国,如今,漆艺因其材料的独特性及语言的丰富性,也已经发展成为真正的国际艺术语言和广受欢迎的艺术形式,在欧洲和美洲,都有不少从事漆艺创作的艺术家,东亚三国漆艺的发展,已给我们足够的启示,其他就不涉及了。
(二)国内近代以来漆艺发展的历程和当代漆艺发展的语境。
随着清王朝的灭亡,在封建皇室垄断下高度发展的漆工艺,盛极而衰,发展中断。中国当代漆艺的发展,是随着现代漆画的兴起,一步步发展起来的。其实,古代漆工艺中,已经有了不少漆画的实例,只是当时还没有进行漆画创作的明确意识。如马王堆汉代极具神秘色彩的抽象漆棺画;长沙南郊黄土岭出土的表现几位体态丰盈舞步翩翩的女子的战国人物漆画舞女漆奁;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的战国彩绘锦瑟,表现巫师作法、人兽交置的场面描绘,极具绘画感。值得专门提及的是1965年11月山西大同市东南十三里的石家寨村司马金龙墓出土的一组人物故事彩绘描漆屏风。[5]每块木板高81.5厘米,宽20.5厘米,出土时共有5块,所画内容与汉代以历史人物故事喻世教民的传统相承袭,所画人物用黑线作铁线描,脸、手涂铅白,服饰器具用黄白、青绿、橙红、灰蓝等色渲染,画风与东晋名画家顾恺之的作品十分相似,.漆工技艺十分高超。这件屏风不仅是极其珍贵的漆工艺品,更是北朝的绘画真迹,也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绘画真迹之一。
而中国现代漆艺真正走出传统漆器,以独立画面形式成为中国现代漆画,萌创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形成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期间有三个人是中国现代漆画的萌创者和奠基者,他们是:李芝卿、沈福文和雷圭元。李芝卿毕业于福州工艺传习所漆工科,曾入日本长崎美术专科学校学习。李芝卿在传统漆艺技法的传承和新技法的创造方面有很大的贡献,也对现代漆画的萌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沈福文曾赴东京松田漆艺研究所师从松田权六研修漆艺,是中国现代漆艺和现代漆艺教育的奠基者和开拓者,他的漆艺作品可以看作是漆画走出漆器的一种过渡。雷圭元是中国工艺美术教育的创始人之一,他大力鼓励和倡导新漆画的创作,与庞薰琹等人提议并安排乔十光、李鸿印到福建学习漆艺技法,他本人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即创作有多幅漆画,被称为中国现代漆画创作的第一人。
虽然漆器是中国古老的发明,漆艺最早是从中国传到亚洲邻国,但文化的交流,不可能是单向的。如果说在历史上,亚洲诸国主要是向中国学习的话,那么,上个世纪,主要是中国向邻国学习。第一代漆艺家主要学习日本,而第二代漆艺家则受越南影响较大。1962年,“越南磨漆画展”先后在北京和上海展出,对我国美术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可以说越南漆画对中国现代漆画作为画种的确立起到了催生的作用。前已提及,越南漆画起步于1925年法国人维克托尔·塔尔丢(Victor Taraieu)在当时的法属殖民地越南创办“印度支那美术学院”时期。法国人并没有把西方教学体系完全强加于越南学生,而是鼓励学生挖掘本民族的东西,发展自己的民族艺术,他们甚至把民间艺人请进课堂并尝试把传统的漆艺技法融入绘画中,从此便有了越南漆画的开始。此后,越南漆画(后称磨漆画)在越南画坛的地位日益巩固,逐渐发展成为越南的“国画”,开始在国际上产生影响,这大大刺激了作为漆艺故乡的中国人、中国漆艺家和画家。就在越南磨漆画来中国的次年,文化部派广州美术学院的蔡克振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的朱济赴越南学习磨漆画。蔡克振受教于越南著名漆画家黄积铸教授。1971年蔡克振筹建创办了广州美院漆画工作室,招收第一届漆画专业学生。与此同时,后来成为著名漆画家的乔十光,于1964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漆画专业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乔十光的漆画,生活气息浓郁,装饰性和工艺性都很强,达到了“技”与“艺”的较好统一。如果说李芝卿、沈福文、雷圭元是中国第一代漆画家的话,那么蔡克振和乔十光便是中国第二代漆画家。他们对新时期中国漆画队伍的迅速壮大起着直接的影响和带动作用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中国现代漆画的发展,虽然从上世纪30年代就已经起步,但后来发展一度中断,建国后的第二代漆画家,是在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亲自关心下成长起来的,漆画也在60年代开始有意识地发展,1964年的全国美展以及文革十年动乱期间的地方和全国性美展都有漆画入选。漆画真正走向良性发展轨道,是在改革开放以后,在1979年的建国30周年全国美展(第五届全国美展)上有蔡克振的《瓶中百合》和乔十光的《泼水节》两件漆画入选,其中乔十光的《泼水节》获银奖。1984年全国第六届美展,漆画以120幅的规模展出于中国美术馆,其中3件作品获银奖,4件作品获铜奖。1986年首届中国漆画展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行,展出作品500余件。1989年第七届全国美展,漆画有1件作品获金奖,2件作品获银奖,11件作品获铜奖。1994年第八届全国美展,又有5件漆画作品获优秀作品奖。1991年成立了中国漆画研究会(乔十光任会长),2001年的中国漆画艺术委员会成立。2002年中国美术家协会和中国漆画艺委会共同主办了“首届中国漆画展”(厦门)。2003年,中国美协艺委会和中国漆画艺委会联合举办了 “首届中国漆画高研班”(厦门鼓浪屿)。2005年,“厦门2005年中国漆画展”再次于厦门举办,同年,“第二届中国漆画高研班”在厦门鼓浪屿继续举办。漆画高研班后来移师广州、南京,今年第六届在武汉举办。最近的2009年,第十一届全国美展,漆画作品获金奖1件,银奖3件,铜奖2件,优秀奖4件,当获奖的漆画作品与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等画种的获奖作品并列在中国美术馆展出时,无论是从视觉效果、艺术水准还是从画幅体量来看,漆画都毫不逊色。可以说,正是因为漆画被纳入到国展的体制,漆画得到了艺术家的重视,漆画得以进入良性发展轨道。而以漆画为主要漆艺类型,在和世界日益频繁的交流中,中国漆艺家眼界也越来越开阔,漆艺的探索意识越来越强,漆艺的样式越来越多,才逐步形成了今天漆艺多类型的多元发展格局。这应该是我国漆艺发展的一个总的语境。
三、湖北振兴漆工艺的努力
如前所述,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福建、北京、广东、四川、江苏等省都形成了漆艺家的创作群体并在全国的大展上频频获奖,与此相比,作为有着及其丰富传统漆文化的资源和得天独厚的漆树种植资源的我省,漆艺创作队伍力量还显得比较单薄,但湖北的努力已经开始。
(一)政策规划与漆树种植。
湖北作为漆器艺术曾经的中心,省政府及各级文化部门有着强烈的文化品牌意识,不仅注重以漆器为代表的楚文化旅游品牌,更注重对漆文化的传承,同时,在十一五规划的文化规划方面,作为物质文化遗产发展项目,已成功申请立项,省文联即将联合湖北美术学院等高校,成立湖北漆艺术研究中心,推动湖北漆艺事业的创作研究和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目前,作为漆树原产地的湖北,漆树种植和古漆树资源已经受到重视和保护。我省恩施州利川县毛坝镇,是漆树的传统种植区。漆树因其气候、土壤、环境等不同,漆的质量有所不同。毛坝风景旖旎,山林肥沃,海拔适中,气候温润,非常适合种植漆树。所产之漆质地最佳,含漆酚量超过75%。当地有“坝漆清如油,照见美人头,摇动琥珀色,提起钓鱼钩。”的民歌,由此可见一斑。毛坝在1952年全国供销联社主任会议上,政务院赠给一面锦旗,由周恩来亲笔题字“坝漆名冠全球”。日本被西方称为漆国,正如中国被称为瓷国一样,英文Japen即是漆的意思。但漆其实是中国传过去的,迄今为止,日本90%的生漆都从中国大陆进口。日本漆艺界只要谈到毛坝,都十分恭敬,曾有不少日本漆艺界人士到毛坝认祖归宗。1991年,咸丰县被定为全国唯一生漆生产基地示范县,产品销往日本、越南、美国等几十个国家,农民因此获得较高的收入。但近10年,由于漆商在产品中掺杂使假,毁了坝漆出口销路,许多农民只得告别坝漆生产。加之茶叶的收益比漆树高,一些漆农也不愿种植漆树。近年来,由于对文化遗产的保护和重视,以及市场对坝漆的需求旺盛,当地政府加强了扶持和引导,坝漆是毛坝乡的传统产品,也是乡政府鼓励农民发展的三大支柱产业之一。2003年以来,按照国家《退耕还林条例》的相关规定,坝漆乡给老百姓发放漆树种苗进行恢复性生产,乡政府无偿提供种苗,通过小额贷款的形式,乡政府贴息3年,逐步壮大了坝漆产业。群众发展坝漆积极性高涨,利川现有漆树面积3万多亩,可采割面积2万多亩,产量3000多担,“坝漆之乡”又重拾希望。
漆树是漆器产品的原材料,没有漆,振兴漆艺只能是句空话。随着漆树的大量恢复种植,加之其他配套的振兴政策和措施的实施,可以想见,必将为我省漆艺的振兴带来丰富的物质资源基础。
(二)研究与保护。
作为漆器文物大省,以湖北省博物馆和荆州博物馆为中心的博物馆有非常丰富的漆器收藏。湖北省各地博物馆基本都有漆器文物。因此,湖北的漆器研究也一直走在全国前列,荆州博物馆是全国漆器脱水保护的中心,有全国领先的漆器脱水保护技术。
漆器、丝织品和青铜器是楚国文物中最有特点的种类,在漆器的研究方面,近年来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先后出版了《长江流域古代美术》、《楚秦汉漆器艺术》多部大型的楚文物图集。从艺术史角度,皮道坚最早在《楚艺术史》中对漆器作了系统的研究,后来,邵学海的《先秦艺术史》又从文化史的角度对漆器进行了梳理和比较。王祖龙从文化观念和美学精神方面对楚艺术做了系统研究,先后出版了《楚艺术图式与精神》、《楚美术观念与形态》,省博物馆研究员陈振裕是著名的漆器研究专家,其在2007年出版了《战国秦汉漆器群研究》,为漆器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在汉的大专院校及各级文化研究机构,在荆州、宜昌等地都有相关艺术研究机构和大批学者从事楚艺术的探索与研究,涌现了大量学术成果。
(三)人才与教育。
漆艺术是中国的发明,日本结合本民族特点作了大量创新,笔者前几年在东京机场转机时,看到机场漆艺商店的陈列,其工艺之精湛、器用之丰富,令人惊叹。漆艺在日本,不仅传统在延续,而且融入了日本民族独有的美学意识和独特的技法,大漆仍然是常新的素材,提供着多种新的美感。后来才知道,日本各级学校都十分注重对漆工艺在内的传统工艺的教育,使之和民众的生活一直保有密切的联系,日本很多艺术大学都有漆工专业。有鉴于此,湖北的教育界也已形成共识,不仅中小学美术教材的内容有漆器文物的介绍,更重要的,各大学的设计学院都开设了漆艺课,并建立了不少的漆艺工作室,已有不少从事漆艺创作的教师在从事漆艺教育和研究工作,湖北美术学院在藏龙岛新校区建设了高标准的漆艺工作室和漆艺车间,中南民族大学美术学院的漆艺工作室条件也非常完善,这两所学校还在2012年暑假联合承办了全国漆画艺委会举办的第六届全国漆艺高研班。而且正在和省文联筹建“漆艺研究中心”,湖北美院已连续招收了多届漆艺研究生,每年也有学生以漆艺作品参加本科毕业展览,学院也正在创造条件申报漆艺专业本科方向,培养更多的漆艺创作人才。
(四)展览与艺术推介。
在振兴湖北漆艺方面做得最有声色的莫过于湖北美术馆,湖北美术馆自成立以来,秉承“立足本土、面向世界、兼顾历史、重在当代”的办馆宗旨,策划推出了不少有创意和学术内涵的展览,短短几年就跻身于全国重要美术馆行列,本着强烈的本土意识和推进民族文化的宗旨,先后在2009年和2010年举办了两届漆艺展。2009年1月16日—2009年3月15日期间,中国美术学院展示文化研究中心和汉雅轩(香港)在湖北美术馆举办了《造物与空间—中国当代漆艺学术提名展》。
诚如湖北美术馆馆长傅中望所言,传统漆艺的当代转型及其当代意义,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课题。如果说《造物与空间》展览选在具有楚文化漆艺传统的湖北举办,是为了起到了古今对话、文脉相通作用,借此契机衔接“以漆造物,以漆造美,承漆于世,传器之道”的传统,从而推进中国当代漆艺的创作与发展的话。那么,《2010湖北国际漆艺三年展》,则可以视为这种推进的制度性学术措施。
《2010湖北国际漆艺三年展》由长期研究并关注漆艺发展的著名学者、策展人皮道坚、张颂仁和优秀的漆艺家也是漆艺理论家陈勤群担任策展人。“2010湖北国际漆艺三年展”凝聚了7个国家的41位优秀漆艺家的精品力作,很显然,湖北美术馆希望通过以国际通行的三年展的方式,持续发现一些优秀的作品和优秀的艺术家,为他们提供高品位的学术平台,推动漆艺的整体创作水平不断提升,湖北乃至世界范围内的漆艺创作都将活跃起来,促使更多更精湛的漆艺作品问世,成为当代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造物和艺术品。
四、在漆艺振兴中应注意的问题
漆艺既是一门艺术,更是一门工艺,或者手艺,那么它一定会以工艺品乃至日用器皿的形式存在。因此,振兴漆艺的手艺问题,是建立漆产品和民众生活的联系。目前,在百姓的日用器皿中基本没有漆产品,虽然湖北的文物商店里也有一些大漆产品售卖,但基本是复制古代器物,仅当作文物仿制品。
要解决这个问题,笔者认为可以从当前民众比较关注的问题入手,大力宣传大漆产品的优越性能,这就是环保健康理念。现在民众普遍认知的油漆是化学硝基漆,不管是哪一类化学油漆都是有毒的,也是不环保的。而大漆是一种天然材料,湖北又是全国大漆最重要的产区,人类使用大漆已达数千年,大漆具有耐热、耐磨、耐酸、耐氧化等优良品质,而且还有质轻抗摔打等特性,是一种高档日用器皿材料。如果宣传得当,又有一定数量高品质的产品源源不断产出,大漆产品进入百姓日用生活应是不难的。
艺术从来就是普及与提高并相互促进的,因此,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真正提升漆艺水平,使之真正进入当代艺术的批评语境,进入世界漆艺创作的艺术对话平台。
这里,正如在陶艺创作中我们看到的一样,既要注重工艺实用的陶器和艺术创作媒介的陶艺之间的关联,也要注意二者的区分。这正是陶艺和漆艺与纯艺术之间的不同,在漆艺这里,还有另一重要区分,就是,大漆和一般油漆之间的区分,只有这样,方能突出漆艺的工具媒介的自我特性和独特艺术表现手法,使之保持语言的纯化,而不是丧失自身,失去边界走向消亡。
我们在漆艺创作已经看到了这两种弊端的同时存在。
一是器、艺不分。部分创造者没有漆艺语言的自觉,比较简单地把某些材料漆上大漆,或进行组合,形成空间,空间倒是有了,但这个空间、材料是否漆上大漆,反而不重要;有的干脆就是一些器物或现成品涂上一层漆,在这里漆失去自己应有的语境和语言能力,变成了一种简单的材料涂料。在一些漆艺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直白的观念,看不到漆艺语言的特性。
笔者认为,漆产品可以大致分为三类:日用品,高中低都应有,以满足不同层次消费者的需求,扩大漆器和民众日常生活的联系,这是基础;漆画(前已述及,漆画已在事实上获得独立画种的地位)及漆媒材的公共艺术品,这是有了较成熟的基础和固定的展览陈设空间的,也是为大众较熟悉认同的;以漆为媒材的纯造型和探索性作品,这部分已经起步,现在漆艺展览很多作品可归为这类,但这部分作品的水准还参差不齐。当然,这三类作品的区分不是绝对的,可以有交叉融合。问题的关键在于,当代中国漆艺的特点是什么,正如日韩都有自己具有民族特性的漆艺一样,我们不能在自己传统最丰厚的艺术样式上,反而跟随别人学习。如何发挥我们的优势,找到具有中国民族特点的当代漆艺发展之路,恐怕是一件需要很多人持续努力才能实现的。
再就是大漆、油漆不分。现代合成化学油漆具有巨大的可能性,材料更丰富,使用更方便,处理得好也能获得大漆的外观效果,但它毕竟不是大漆,只是油漆工艺,这种混淆,会使得大漆自身的独特的语言和性状、特殊的工艺流程,在现代化学油漆的绚丽效果面前,失去其本质特征,,而徒具油漆的表面形式,这种失去材料本性的创新,无益于取消漆艺,因为大漆作品,由千年历史传承而来,其历史的厚度,甚至其稳定的材料性状都不是现代油漆所能比拟的。当然,我们不是简单的反对化学漆,化学漆有它的优势和特色,二者不可混淆和相互取代。
当代艺术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就是对材料的试验和探索,大漆材料的独特性为其艺术的独特性提供了物质材料前提,如何寻找将这种材料的独特性能发挥极致的方法,本身就是一个当代艺术事件,我们有理由期待。
邵学海在 《先秦艺术史》漆器艺术一章的结语中写道:“先秦漆器不论在雕刻塑造,或者彩绘装饰方面,都取得了远不同于青铜艺术的伟大成就。而且,由于漆器与青铜器各具不同发展节奏,当青铜艺术落下帷幕时,漆器成为延伸于汉代的一个重要艺术形式”。[6]我想,漆器不仅延伸于汉代,也延伸到了今天,作为中华先民的伟大创造,在中华民族复兴的语境下,作为传统漆器当代形式的漆艺一定会有光辉的未来。
[1]皮道坚.楚艺术史[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5.
[2]陈振裕.战国秦汉漆器群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
[3]王祖龙.楚美术观念与形态[M].成都:巴蜀书社,2008.
[4]容庚.乐浪遗迹出土之漆器铭文考[J].《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第一卷第一号.
[5]大同市博物馆.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J].《文物》,1972,(3).
[6]邵学海.先秦艺术史[M].济南:山东书画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