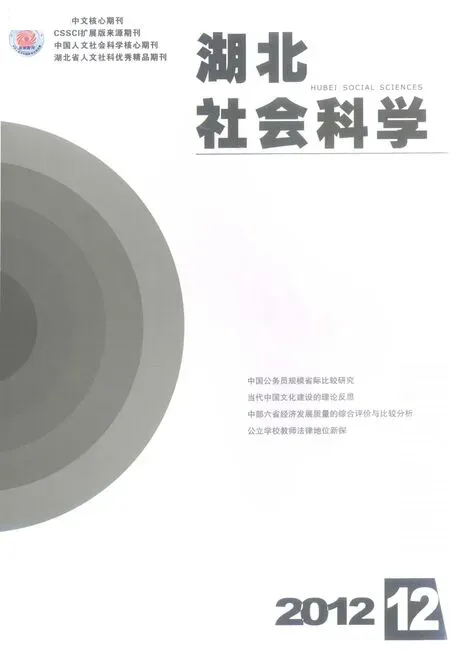清末湖北的宪政思潮论略
2012-04-12熊霞
熊 霞
(湖北省社会科学院 文史研究所,湖北 武汉 430077)
二十世纪初,湖北民族资产阶级开始形成,并形成相应的政治派系而展开活动。代表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君主立宪派,反对资产阶级革命派宣扬的暴力革命,他们希望通过“和平”方式改良社会,主张在保存清廷、防止革命爆发的前提下,推行若干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改革措施,建立议会和责任内阁,以“宪政”取代专制,走君主立宪之路。君主立宪的理论,由于立宪派的倡导和鼓吹,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一部分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方士绅的支持和参与,以及地方督抚的鼎力扶持,成为清末湖北思想界与反清革命思潮并起的两大主流思潮之一。
一、立宪思潮的社会基础
立宪思潮的社会基础是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一部分具有资本主义倾向的地方士绅,也包括锐意革新的官僚统治阶层。这部分人群大都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他们或具备渊博学识,或坐拥丰厚资产,或享有显赫官职,在当地均为受人尊重和景仰的官商学各界社会精英。具体说来有以下三类:
一是向资产阶级上层转化的开明士绅,以汤化龙、张国溶等为代表,是湖北立宪思潮的鼓吹者和倡导者。他们学识深厚,且接受新学,具有改革政治的意图。湖北立宪派领袖、先后担任过湖北咨议局议长、各省谘议局议员联合会主席、宪友会湖北分会会长的汤化龙很具代表性,他“光绪壬寅,乡试中式……旋成进士,授刑部主事。见世变益亟,朝局至不可问,发愤谓:‘政治不革新,国亡不可救;而欲救国,必更博求新知,止旧学不周于用。’”于是他“自请咨送留学日本,入法政大学。”[1](p386)在日本与乡人留学者倡设“留日湖北教育会”,后回鄂筹备立宪事宜,为立宪奔走呼号,被时人称之为“宪迷”。湖北立宪派中,与汤化龙具有相似文化背景的还有张国溶、刘庚藻、胡瑞霖等人,他们基本都是留学日本研习政治法律的清末进士或翰林。传统文化的熏习和欧风美雨的浸染,使得他们有别于传统文人和旧式官僚,这些堪称学界精英的新型士绅构成了立宪派的主体和核心,成为上层资产阶级和开明士绅的政治代表。1908年,汤化龙、张国溶等纷纷学成回国,当时清政府已经宣布预备仿行立宪来缓和激烈的社会矛盾,他们便以此为契机,力图通过倡导湖北的宪政运动,在全国实现君主立宪的理想。
二是拥有雄厚资本的大资本家、上层资产阶级,以刘歆生、蔡辅卿等商界精英为代表,成为湖北立宪思潮的主要支持者和积极参与者。著名的汉口地皮大王刘歆生,积极鼓吹君主立宪,成为“湖北宪政同志会”重要成员。在保路运动中,刘歆生被推选为“湖北商办铁路协会”的副会长,领导拒款运动。汉口八大帮行之一的药材行帮商董蔡辅卿,也是“湖北宪政同志会”重要成员,在汤化龙赴京请愿时,蔡辅卿曾组织100余个商团保安会和商业行帮,参加武昌阅马场大会,为汤送行,支持立宪。[2](p674)除刘歆生和蔡辅卿外,不少工商界知名人士也是湖北宪政同志会的筹备者和骨干成员,如汉口致中和丸药店的店东关少尧、武昌商会主席吕奎先、汉口商务总会总理李紫云等,他们为实现“宪政”呐喊助威,成为湖北宪政思潮有力的推动者。
三是大权在握而赞助立宪的地方督抚。督鄂十八载的湖广总督张之洞是积极支持立宪的地方督抚的重要代表,张之洞作为清廷重臣在清末宪政中的态度和言行,对湖北宪政思潮的起伏至关重要。1901年,张之洞曾联合支持立宪的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著名的 《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提出革除弊政、改良司法等政治改革主张,并在致刘坤一等人的电牍中,说明立宪政治是中国变法的根本,推崇西洋上下议院互相制衡的制度,“西法最善者,上下议院维持之法也” 。[3](p19)1905年,张之洞又与直隶总督袁世凯等人致电清廷,奏请实行立宪政体,以12年为期。为积极推动立宪,张之洞还在湖北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慷慨解囊白银5万两赞助五大臣出洋考察,并表示湖北每年认筹十万两作为五大臣出洋考察之经费。[4](p298)张之洞对宪政理论和行动的支持和襄助,使立宪思想在湖北思想界更具影响力。
汤化龙等开明士绅和刘歆生等商界名流,成为湖北立宪思潮的社会基础。这些属于资产阶级范畴的官商学界社会名流,一方面对君主专制制度严重束缚资本主义的发展十分不满,对清廷的昏聩腐朽深为愤慨,有着发展资本主义和参与政治改造社会的强烈要求。但一方面他们又与封建宗法制度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汤化龙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多有功名和一官半职,刘歆生等工商名流则较大程度上在封建势力的庇护下发展壮大资本。因此在改造社会的方式上,他们反对革命派的暴力革命推翻满清政府的主张,担心秩序一破,不可回复,从而危及他们的既得利益。于是他们在夹缝中寻找出君主立宪这条政治出路,既可保存清廷,不影响政局稳定、维护自身利益,又可一定程度上通过设议会内阁限制君权,推行若干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改革措施。在以工商学等各界地方精英为主体的立宪派的倡导及部分官僚阶层的推动下,立宪思潮在湖北地区上下结合而成澎湃发展之势。
二、立宪理论的深入宣传
立宪思潮在清末湖北的蓬勃发展,主要表现为立宪团体的比肩兴起、立宪报刊杂志的纷纷创办,由此立宪理论得到比较深入而相对广泛的传播。
1906年9月,清廷颁布“仿行立宪”的上谕,省内立宪团体一时勃兴。各地士绅集合团体研究政治和议论时事者日渐增多。1909年5月,湖北知名立宪团体湖北宪政筹备会于武昌成立,姚晋圻为会长,汤化龙、余德元任书记,张国淦任编辑员。1910年春,另一著名立宪团体汉口宪政同志会成立,由咨议局、省自治筹办处、省教育会、汉口总商会、汉口各团体联合会组成,又称国会请愿同志会湖北分会。该团体以促进实行君主立宪为宗旨,除鼓动绅商士子呈辞上书外,还联络各省代表进京陈述,并宣称为组织政党之预备,它模仿西方政党组织程序,建立了较严整的组织,如设宪政讲习所,分期轮训士绅;创办报刊,以宣传立宪、开通民智为宗旨。[5](p13)1911年6月,在汤化龙等各地谘议局领导人的推动下,全国性的资产阶级政党宪友会成立。当年7月,汤化龙、张国淦、胡瑞霖等以谘议局为中心,组成宪友会湖北支部,成为湖北又一影响广泛的立宪团体。
随着立宪团体的兴起,一批鼓吹地方自治、催促宪政的立宪报刊纷纷创办。较有影响的立宪报刊有湖北留日学生创刊于东京的《新译界》、《教育新报》、《湖北地方自治研究会杂志》及诞生于本土的《趣报》、《宪政白话报》、《湖北地方自治白话报》等。
湖北的立宪报刊起初由留日学生在东京发起创刊,1906年11月16日,湖北籍留日学生范熙壬任主编的《新译界》在东京创刊,该刊宣传君主立宪,支持清廷“锐意更新”,得到了清政府的支持,驻日公使杨枢等人曾捐资赞助。继《新译界》后,1908年5月30日,“留日湖北教育会”会刊《教育新报》在东京创刊,该报《简章》规定:“本报以输入关于教育之新知识,谋内地教育之完全发达为宗旨”,主张通过教育启发民智,从而为实施宪政铺平道路,成为鼓吹立宪的另一喉舌。《湖北地方自治研究会杂志》也是湖北立宪党人创办于日本的重要传媒,它创刊于1908年11月15日,馆设东京,由湖北地方自治研究会主办,吕嘉荣、张伯烈先后任主编。该杂志以研究各国地方自治之学说及制度,唤起国民精神,俾人人乐于自治为宗旨。另有诞生于湖北本土自称为“风月报章”的《趣报》,实是与立宪派、铁路协会关系密切的报刊。立宪报刊中影响较大的为汉口立宪同志会的机关刊物《宪政白话报》,该刊创办于1910年5月上旬,以“宣传立宪,开通民智”为宗旨。《宪政白话报》立言严肃,政治色彩浓厚,以通俗浅近、生动活泼的文字,适应现实政治之需要,引导百姓了解立宪,大力宣扬宪政,成为湖北立宪思潮及运动的重要舆论阵地。[6](p197-220)
除上述报刊外,立宪党人及倾向宪政的新式知识分子也充分利用其他舆论阵地,鼓吹君主立宪,如被称为“汉上三大报”之一的《公论新报》和被誉为“革命之喉舌”的《江汉日报》都曾刊载过较多主张宪政的文章时评。这些报刊宣传的“宪政”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启发民智,唤醒百姓的政治热情和参政意识。立宪派及支持者利用报刊的教育功能,通过普及宪政知识,揭露清廷立宪骗局,希翼提高国民政治能力,拟为宪政争取广泛的社会基础。针对当时普通群众缺乏公民意识和宪政常识的现状,范熙壬在《论立宪国之教育》中尖锐指出:草莽市井之人茫然不知宪法为何物,国会为何事,弃权利而不知取,背义务而不知尽;主张通过实行国民教育改善现状,“所谓无立宪之实而徒剽立宪之名,求立宪之利而先蒙立宪之害者,是岂立宪之为咎也邪,盖无教育耳”。[7]《江汉日报》多次刊文揭露清廷立宪骗局,也从侧面在启发民智、教育国民方面发挥重要作用。该报在刊载的《政府立宪之概观》中认为,“今咨议局为资政院之附属,而自治会与府县议会又为咨议局所发生,层层节制,着着羁縻,为上下之相乘,非平等之各边。”指出清政府所谓立宪只是“夜叉换形,幻作美人”,名为立宪,“不过专制之变相耳”。[8]这些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教育了读者,为实行宪政奠定了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
其次,鼓吹地方自治论。地方自治是宪政的重要内容,国民政治能力的提高,是地方自治的重要保障。湖北留日学生吕嘉荣在《湖北地方自治研究会杂志》的序言中指出:“非先行地方自治养成国民政治能力,则欲国民之能运用宪法而收国会之利益,乃万不可得之势”,“宪政、国会为国家根本解决之问题,而自治则解决根本之根本问题也”。[9]《公论新报》刊发《国民当自治》,提出:“朝廷已决意立宪,则是教我们个个知道爱国,个个知道忠君,要提起精神,做一番事业,不能全靠地方官来治我们”。[10]另有一篇题为《论下议院吾民当自知亟起建设》的社论,言辞颇为激烈地指出:“今欲立下议院则必以自治会之为基础,官吏不可从而干预之”。并指出,如果不迅速建立下议院,朝廷本是“迫不得已而曰立宪”,必“授其权于地方官,地方官奉行故事建议院举议员,爱憎取舍一惟地方官之命是听,则是吾民于地方官之外又多于一议院之官而已”。[11]
再次,宣扬国会政治,力主责任内阁制。国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是君主立宪思潮的核心内容。议会和内阁是限制君权的重要机构,也是立宪党人追求的精华所在。汤化龙在刊发的《议会论》中,从理论上系统探讨议会的性质和作用,主张君主立宪,实行议会制度。[12]实行政党政治。后《江汉日报》又独家刊发康有为代草之《中华帝国宪政会联合海外二百埠侨民公上请愿书》,敞言迅即召开国会、归行政等,请愿书的要害在于要求慈禧太后撤帘归政于光绪,实行君主立宪。
三、立宪思潮的黯然回落
在内外交困的压力和以地方精英为核心的立宪派的推动下,清政府徐徐拉开宪政帷幕。1909年10月14日,湖北咨议局举行第一次常年会议。谘议局的筹备和成立,给立宪派提供了合法的政治舞台和活动基地。通过谘议局,立宪派取得了“国民代表”的合法资格,成为清末一支极为活跃的政治力量。1910年10月,作为“立议院基础”的资政院在北京召开第一次常年会。议员们高谈国事,抨击政府,中外记者到会旁听。报刊报道评说,颇有民主气息,对于长期生活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的中国人来说,是一次难得的启蒙教育。立宪派通过谘议局和资政院这两大平台,深化了参政意识,从政能力得以锻炼和提高;民众虽于此相对隔膜,也感受到了民主的氛围,公民意识和参政意识萌发并加以强化,立宪思想得到更加广泛而深入的宣传。然而立宪派在欢欣鼓舞的同时,很快发现参政议政的愿望难以实现,君主立宪的理想也日益遥远。
根据清政府的规定,各地谘议局的活动必须遵循清廷颁布的《钦定谘议局章程》。章程规定各省督抚对本省谘议局的全部议案拥有裁夺权,皇帝对这些议案操有最后审定权。章程还规定如果谘议局有逾越权限不受督抚劝告者,“督抚得令其停会”或“奏请解散”。不难看出,谘议局从筹办到成立以至开局议事,全然是在清廷封疆大吏的直接操纵和控制之下进行的;谘议局的形式和宗旨,也被毫不含糊地限定在清廷的专制制度许可的范围之内。资政院的状况也不容乐观,资政院的决议案得“请旨裁夺”,朝廷或敷衍了事或严加申斥,资政院的核议大多不起作用。
“谘议局之见厄于政府,资政院又为非驴非马之议会,俱不可恃,因有联合请愿国会之举。”[13](p446)立宪党人把召开国会作为实现宪政的最大希望。1910年,立宪党人组织了三次规模宏大的国会请愿运动,要求缩短预备立宪年限,请求速开国会,然而清政府或断然拒绝或拖沓敷衍,甚至驱赶和镇压请愿者,使立宪派与其之间的嫌隙急剧扩大。1911年严重违反立宪精神的“皇族内阁”的出台更给立宪党人当头棒喝,在立宪党人要求取消皇族内阁的合理要求再次遭到拒绝后,气愤不已的谘议局联合会代表痛斥王公亲贵们所作所为是“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为专制”,[14](p73)清廷假立宪集权于皇室的用心大白于天下,政府所谓“预备立宪”,实质上只是一场骗局。立宪派及支持者与清政府之间的裂痕越发难以愈合。
立宪梦想越来越远,立宪党人失望之余,开始徘徊于反清和拥清之间,最后确立的“推倒政府”的目标,从而在实际上与革命党有限度地携起手来。湖北立宪派头面人物汤化龙在此表现尤为突出,他接受过革命党人詹大悲的门生帖子,积极参加过保路运动,已俨然成为革命党的同盟者。而另一重要立宪代表人士张国溶也在多次国会请愿失败后,思想受到很大震动,深感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因而同情革命,并投身于民主革命的洪流中。武昌起义前夕,张国溶等以咨议局作为革命的秘密据点,与革命党人在此共商革命大计。[15](p656)立宪派政治态度的转变,说明资产阶级上层和开明士绅已从清廷一边撤离出去,清朝的统治基础更形狭窄,陷入空前的孤立之中。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反清民主革命思潮由理论走向实践,清廷在湖北的专制统治终被推翻。与此相应,轰动一时的君主立宪思潮便在武昌起义的胜利呼声中黯然回落,归于沉寂。
[1]汤化龙行状.蕲水汤先生遗念录[A].武汉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C].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1.
[2]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北省志·人物志[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3]张之洞.致江宁刘制台等[A].张文襄公全集第4册[C].北京:中国书店,1990.
[4]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
[5]湖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湖北省志·政党社团[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
[6]刘望龄.黑血·金鼓——辛亥前后湖北报刊史事长编[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
[7]教育新报第三号.
[8]江汉日报,1908-05-01.
[9]湖北地方自治研究会杂志第一卷.
[10]公论新报,1907-01-22.
[11]公论新报,1907-09-04.
[12]江汉日报,1908-04-03.
[13]心史.宪政篇[J].上海:东方杂志,1909,6,(13).
[14]谘议局联合会宣告全国书[J].上海:国风报,1911,(14).
[15]蒲圻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蒲圻志[M].海口:海天出版社,1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