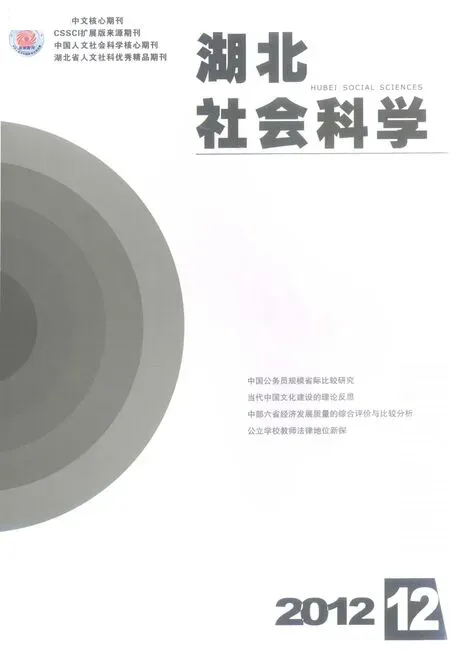中国传统“俭”、“奢”消费思想的当代辩证厘思
2012-04-12韩晓玲
韩晓玲
(宁夏大学 国际教育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中国当代的和谐消费意识应该是什么,用一句话来说,就是要求人们消费得和谐,它是从消费的角度来促使人们建立一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相互协调、和谐发展的意识,其间的和谐关系反映出来的是人类自身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传统的消费意识作为中华民族深层次的文化结构体现在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这种消费意识是否真的适合于当下中国社会的发展状况,需要我们对传统消费观进行取精华、去糟粕的辩证厘思,从而实现消费意识的现实转换。
一、中国传统的消费观
中国传统的消费思想从一开始就沿着两条不同的路线向前发展着,《左传》庄公二十四年(在公元前670年)记鲁国大夫禦孙说过:“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1](p58)虽然以俭为美德的消费思想很早就在中国社会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历代不少的政治家、思想家根据现实需要也提出了“尚奢去俭”的主张,所以,主次并存、因时制用可以说是中国传统消费观的发展模式。
1.以俭为尚的消费观。
以俭为尚作为传统主流消费思想,先秦儒家思想在其中的作用是举足轻重的。由于先秦儒家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突出地位,它所倡导的节俭消费观对中国古代社会消费模式的形成可谓是影响最大的。
先秦儒家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孔子在其礼义的视阙下提出:“礼,与其奢也,宁俭”,[2](p53)“奢则不孙,俭则固。 与其不孙也,宁固”。[2](p129)孔子认为礼所反映的是人内在的美德,所以不需要以奢侈的浪费去体现礼义,奢侈会让人不知礼,与其越礼不如节俭从事就可以了。这种宁俭勿奢的消费观,在孔子的思想里不仅指向对个人消费行为的约束,而且还涉及到了国家消费的层面。对个人而言,孔子认为,奢会引起人们消费的欲望,使自身的消费行为失去道德的约束,而俭则可以约束人们的欲望,从而规范人们的行为道德,所以“以约失之者鲜矣”,节俭的人会犯错误是非常少见的。对于国家而言,“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2](p24)治理国家也要做到节俭开支,进而维护社会的稳定,让百姓安居乐业。
老子从“少私寡欲”的角度出发,认为“持而盈之,不知其已。揣而锐之,不可常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3](p24)一个人一旦处于富贵之中,往往就会变得骄傲自大,进而陷入奢靡,甚至于因财富自我炫耀而招至灾祸。节俭可以使人无欲,因此,老子说:“我有三宝,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3](p173)
孟子和荀子继承了孔子尚俭去奢的思想,分别从礼义以及社会生产的角度提出了节俭消费的原则。在道德礼义上,孟子和孔子的思想如出一辙,认为“贤君必恭俭礼下”,[4](p82)尚俭是君子品格之一,而节俭的途径就是“寡欲”,“养心莫善于寡欲”。孟子还反对摆阔性的消费,认为“宝珠玉者,殃必及身。”[4](p256)在《荀子·富国》中,荀子认为节俭是富国裕民的根本方法,“足国之道,节用裕民,而善藏其余。节用以礼,裕民以政。”[5](p140)他认为,在一个国家里,首先要节俭生活,不仅贫者要节俭消费,富者也要按照不同的等级地位标准来节制消费。在此基础上,再“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4](p269)只要再加强社会生产而又节约开支,就能够积累社会财富,从而百姓生活富裕;反之,“本荒而用侈,则天下不能使之富。”[5](p269)
以先秦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尚俭去奢的消费思想在经历了千年的历史更迭,早已深入人心,在这之后的中国学者也只是在其基础上传承发扬了尚俭的消费思想。在其传承的过程中,中国消费思想还出现了另一种截然相反的观点,那就是以奢为尚的消费观。
2.以奢为尚的消费观。
关于“尚奢去俭”的消费观,较早出现于汉初成书的《管子》。首先,在《管子·侈靡》中认为“饮食者也,侈乐者也,民之所愿也”,[6](p108)每一个人都有消费的欲望,侈靡可以满足人们的欲望,提高人们的生活积极性,而“伤心者不可以致功”,[6](p108)只有“足其所欲,赡其所愿”,[6](p108)才能为统治者所用,国家才会繁荣昌盛。其次,富人的侈靡生活还可以为贫穷的人提供谋生的渠道。“雕卵然后瀹之,雕橑然后爨之。丹砂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此百姓之治生,百振而食,非独自为也,为之畜化。”[6](p108)富人奢侈的消费,可以扩大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以致于鸡蛋要绘上彩画再煮,木柴要雕上花纹再烧,富余的劳动力因而可以得到解决,富者、贫者互惠互利。《管子》倡导奢侈,目的是为了刺激生产,富足百姓。
如果说《管子》的“莫善于侈靡”还只是停留在理论上,那么,范仲淹却把这一思想真切地贯彻到了实践中。公元1050年,浙江地区发生了严重的灾荒,时任地方知府的范仲淹不仅每天和众人在西湖上饮酒作乐,奢侈消费,还大兴土木,动用工人达千余人,他对自己的作为解释道:“所以宴游及兴造,皆欲以发有余之财,以惠贫者。贸易、饮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于公私者,日无虑数万人。荒政之施,莫此为大。”[1](p58)奢侈的消费使得社会分工越加细化,财富在这样的消费过程中得到了重新分配,穷人在这种消费行为中能够通过自身的劳动获得较好的生存条件,这就表明奢侈消费在稳定社会、巩固政权中有着它积极的作用。明代经济思想家陆楫在《蒹葭堂稿》中说道,“予每博观天下之势,大抵其地奢则其民必易为生,其地俭则民必不易为生者也。”[1](p60)陆楫认为在消费奢侈的地方,大都经济比较发达,因而百姓谋生的机会比较多,与其相反,在消费领域中太过节俭的地方百姓不易为生。奢侈消费可以促进国家商业的繁荣和经济的发展,人人都能在这种消费模式中各取所需,因而应崇奢去俭。
鸦片战争后,谭嗣同指出中国是一个用度之俭的国家,然而这样的一个国家却处在了“人人俭而人人贫”的局面,之所以尚奢在于“惟静故惰,惰则愚;惟俭故陋,陋又愚。普此两愚,固将杀尽含生之类,而无不足”,[7](p72)所以,他认为“俭之为祸”。对于当时的中国如何摆脱内忧外患发展自身,谭嗣同批驳了荀子“节其流,开其源”的主张,认为“故理财者慎毋言节流也,开源而已。源日开而日亨,流日节而日困”。[7](p70)
可见,“尚俭”与“尚奢”都是因时制用的消费观,而这两种消费观是否适用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进一步地辩证厘清。
二、我国当前不合理的消费现象
高消费、高享受的生活方式,从表面上看,是人对物的控制,实质上却是物对人的征服,消费者在追逐商品享受的过程中逐渐扭曲着自身的消费价值观,这种不合理的消费意识主要表现在:
破坏生态平衡的消费。这种消费对个人和国家来说都是危害极大的。自然界给我们提供了充裕的生产生活资料,可这些资料不是无穷尽的。我们可以从全球气候变暖,从中国水土流失严重、森林覆盖率降低、矿产资源减少等等中发现,那些被人们所忽视的浪费资源性的生产生活消费充斥着我们整个生活,过度的生产生活消费给我们带来的是生态平衡的危机。
物质与精神失衡的消费。这种失衡性表现在物质消费超前,而精神文化消费滞后。中国作为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刻不容缓的事情,这种倾斜经济的发展模式促使人们开始追逐物质商品所带来的心理满足感,“金钱至上”成为了大众的主流意识。所以,需要引导、鼓励以及尽可能地提供各种条件,建立当代人以知识、品德、社会责任感等为价值观的主流意识,让人们的精神领域变得更加充实。
财富资源浪费式的消费。现今很多中国人都把购置房产看成是财富快速积累的方式,“房子就是家”的传统文化意识使得房屋的买卖双方都能够从中获得更大的收益,因此大量的农田被用来建筑房屋。一些中小城市,甚至一些大城市的发展也都在大量占用农田。有数据表明我国目前城镇化率约46%,几乎是西方发达国家两次城市化的过程,土地城镇化超过了人口城镇化。无节制地卖地、买地、拆建、重建以谋取利益,只能是对财富资源的极大浪费。
三、中国传统消费观的现代转换
在中国传统消费思想中,先秦的儒家思想侧重于消费的道德礼义,节俭消费可以让人知书达礼从而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尚奢去俭思想又从经济层面阐述了消费的社会功能,只有奢侈的消费才可以促进社会生产的发展,进而解决人们的衣食之忧。两种观点相互矛盾却各有它的社会价值,因此,只有把这两种观点进行融合与现代转换,才能够指导并建立起国人正确的消费价值观。
1.应树立正当的消费观。
20世纪4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在二战后得到了迅速增长,社会财富大量增加,很多人都认为社会的财富是用之不尽的,由此,一种主张追求体面的、无节制的物质享受和消费,并把它作为生活目的和人生价值的消费主义思想随之产生,并得到了社会大众的认同。同样的事情在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中已悄然上演。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纵欲主义和享乐主义的消费行为成为了我们这个时代人们生活中比较具有象征性的消费方式。这种消费方式显露出的是人们对自身价值的不自信,通过消费奢侈品来标榜自己的社会地位与权力,这不仅改变了人们正常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关系,而且也改变了整个社会的消费价值观。消费是为了满足生活必需和陶冶愉悦心情的,而不是向他人证明自身的地位与权力,过度对商品的追求,使得社会关系不再是单纯的人与人之间发生的关系,其中,商品成为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支配者。所以,如何正当地消费,一直是我们这个时代讨论的话题。
老子曾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3](p32)人们一旦纵情于骄奢无度的生活,那么奢侈将会蒙蔽人的心志,使人的行为不正常,所以“是以圣人为腹不为目,故去彼取此”。[3](p32)老子所处的时代,社会动荡不安,在百姓居无定所、无法温饱的情况下,老子认为贤者圣人应在满足生存需求的基础上放弃无止境的感官享受。虽然时代不一样,可是无节制的奢靡消费所带来的“目盲”、“耳聋”、“心发狂”、“不正常”却存在于当今的社会。正当的消费并不是如老子所说,让人们完全放弃情欲的享受,因为满足一定的情欲可以愉悦人们的心情,让人们以积极乐观的心态面对生活,所以,正当的消费是要求人们在生活中追求感官享受的同时不要失去做人的基本原则和起码公德。对于国家,正当的消费可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有利于生产与消费的均衡,不易造成极大的浪费;对于个人,可以提高自身的修养,真正实现自我价值。
2.应树立适度的消费观。
从中国的封建社会到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的社会物质财富一直处于匮乏状态,社会生产力低下导致了生产与消费的不平衡,所以,儒家以节欲实现节俭的消费思想贯穿了国人消费行为的始终,并对当时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而当今社会提倡节俭,原因在于过度的消费促使了过度地生产、消耗,周而复始,自然资源的枯竭、生态环境的恶化给人类的生存以及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所以,有人推行节俭的生产生活方式,但是,也有人认为过度节俭将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提出奢侈消费可以拉动内需,刺激生产规模的扩大,进而带动相关服务行业的快速发展,这样便可以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改善经济的发展环境,这种观点与中国传统“尚奢”思想的出发点是一致。可以说,这两种消费观点是当今社会的“崇俭”、“崇奢”论。其实,这两种消费方式都具有两面性。过于节俭不能促进经济发展,过于奢侈会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平衡,因此,我们强调适度的消费观,它是一种使消费者既能满足自身的生活需要,又不为商品所控制的消费观;是一种既不主张禁欲主义式的过度节俭,又不赞成对财富毫无节制消耗的消费观。适度消费要求人们在生产方式上,把对自然资源和能源无节制索取的生产方式转换为以节约资源和资源再生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是一种既可以发展生产又不会浪费资源的生产方式;在生活方式上,它要求人们以实用节约的方式适度消费,是一种既可以推动经济发展又可以幸福生活的生活方式。适度消费观要求人们的消费行为不仅要考虑自身的利益,还要考虑他人和社会的利益。因此,它使人们的思想更理性化,在道德上更自律,生活上也更注重健康生活。
3.应树立注重精神消费的消费观。
人类的社会生活包括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生活的极大满足往往是不能给人带来精神上同样的满足。当今社会,人们对物质的追求远高于对精神的追求,货币符号代替了人作为社会的人的品德、义务和责任等。过度追求物质享受,放纵人的无止境欲望,正如老子所说会使人的心志与行为异常,形成藐视社会道德和法律规范的畸形心理意识。但是,儒家“罪莫大于可欲”的消费思想扩大化了人的欲望,认为一切罪恶都来自于人的欲望,其实,适度欲望是人们获得幸福生活的前提,是人们追求精神享受的动力。所以,在适度消费的基础上,强调人们消费行为中的精神文化含量,进而改善人们的精神消费行为,才能使人们自身逐步趋向完善并全面发展。注重精神文化的消费不仅有利于人们树立正确的消费价值观,而且有利于营造良好的社会道德规范,为建设和谐社会提供健康文明的社会风气基础。
4.应树立保护生态平衡的消费观。
消费是人类为了满足生产生活需要而耗费各种生产资料的过程,这一过程既是人们不断向自然界索取的过程,也是人们不断产生生产生活废弃物的过程,消费的两端必然联接着人与自然,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应当是相互依赖、相辅相成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和谐、协调是以在满足人们合理需求的基础上充分考虑生态发展的客观要求为原则的,所以,人们以什么样的消费方式生产生活直接影响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影响到了生态环境的平衡。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改变了人们的生活质量,但是这种改变往往是以牺牲生态环境为代价的。据国家环保局2010年统计数据,全国废水排放总量为617.3亿吨,比2000年高出了48.7%;工业废气排放总量为519,168亿立方米,高出了275.8%;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总量为240,944万吨,高出了193.9%。这些数据的“产生”需要能量的高耗费,能量的高耗费来自于对自然界无节制的索取,经过生产生活的奢侈消费,产生出的废水、废气、废物又进一步对自然界造成污染,循环往复,人类亲手摈弃了自身赖以生存的环境。除此,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大国,《管子·八观》中曾言:“行其田野,视其耕芸,计其农事,而饥饱之国可知也。”[6]而今天,中国的城市发展靠占用大量的农田,商人追求经济利润靠占用大量的农田,这不仅让农民失其业,在城市的重建、扩张过程中还造成了生态平衡的破坏。这种消费行为与范仲淹提出的“荒政之施,莫此为大”的尚奢观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农业生态的破坏,便可知中国是否饥饱之国。我们所要做的是珍惜人类的生存条件,努力保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平衡。
[1]叶世昌.中国传统消费观述要[J].世界经济文汇,2005,(4).
[2]钱逊.论语浅解[M].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8.
[3]李红.老子本义[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9.
[4]杨伯峻,杨逢彬,注译.孟子[M].长沙:岳麓书社,2001.
[5]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6]梁运华,校点.管子[M].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
[7]罗炳良.谭嗣同仁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