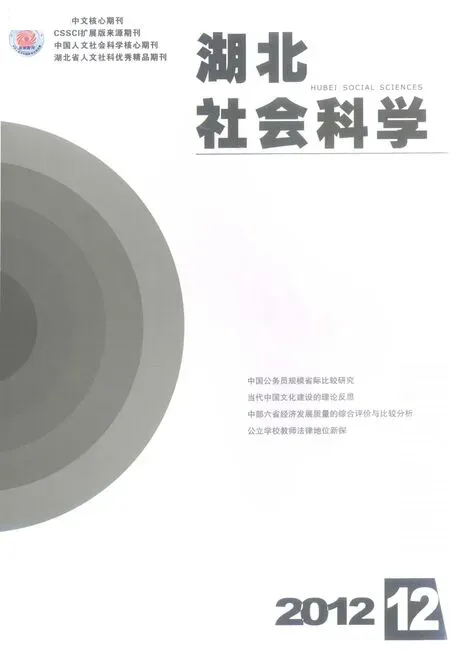社区广场的渗透策略与权力机制研究——以上海市某社区广场为例
2012-04-12卢俊秀
卢俊秀
(华东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上海 200062)
改革以来,中国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一个不可回避的现实与理论问题是如何处理与不断获得发育和增长的基层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成为地方基层政府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在城市社会中,作为基层社会力量发展壮大的显著表征——城市广场,由于其提供城市人文化娱乐活动及社会交往的公共空间,弥补了私人空间所不具备的社会交往特质而得到关注。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方法
转型社会以来,国家与社会(社区)之间的关系研究层出不穷,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种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近20多年来的经济社会变迁使得国家在邻里所展现的力量大为下降,城市社区主要是由生活世界的机构和制度所组成的,城市社区居民的联结纽带是一种在共同生活中形成的“默契”、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社区文化,而城市社区广场成为该文化的一个主要体现平台。[1](p226)第二种观点强调了社会转型背景下的社区建设运动所带来的城市政权向基层社会的渗透,以及国家以各种形式在邻里中再现,或者说是国家政权的向下渗透,其中关于“社区行政建设”则是最好的注脚。[2]第三种观点中和了前两种观点,认为带有一定国家代理人的身份的居民委员会起到了国家与基层社会的 “粘连”作用,“国家”与“社会”在邻里(社区)中达成了妥协,彼此相安无事,形成一种微妙的胶着局面。[3](p67)
从以上观点可以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国家已经开始从许多城市社会场域退出,或者说部分的、逐步的撤退,虽然在目前的情况下,并不意味着国家从民间的视野中完全消失。而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国家仍然对社会(社区)具有强大的动员、控制、整合等能力,在很多场合下城市行政体系正力图实现对基层的渗透,或以各种形式重申自己在城市邻里(社区)中的存在。
伴随着二十世纪90年代“社区建设”运动,国家或者说政府更多的是以“社会服务”的角色出现在社区中,这可以从“社区自治”与“民主选举”中得到体现,但是同时,政府并未放弃对社区事务的实际领导,而通过类似权力的三重网络等制度运作,始终要将可能生长中的社会力量吸纳入国家可控的轨道之中。[2]可以说,社区服务和社区建设带有浓厚的官方色彩,而城市社区广场给人的印象更倾向于文化娱乐。
沿着国家与社会框架路径,再把目光聚焦到城市广场上来。何谓“广场”?其概念是一个合成词,“广”字强调空间的开敞,强调能容纳人的空间之大,“场”字则强调人的活动场所,强调广场容纳社会活动的功能。
应当说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就出现了许多从建筑学和城市规划学的学科视角来进行分析探讨广场的研究,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广场的景观设计这一方面,以及对中国城市广场建设的反思。就社会学方面来说,近年来关于广场的研究可以发现存在三种视角:其一,比较中外广场,探讨民众对公共空间诉求的差异。[4]其二,关注在广场这一空间形态中发生的种种复合型特质的社会活动,体现了其背后的社会力量争夺。其三,在国家与社会矛盾冲突中,通过广场这一特有形式关注市民社会的发育。
就城市广场而言,已经不是单纯意义上的物理空间或场域,更进一步地说,广场已经成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一个生动体现。以往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实证研究多放在社区组织、社区治理等领域。[5](p235)本研究拟将社区广场作为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实践的体验地,从而提供更为鲜活的实证材料。
二、个案社区广场
本研究采取个案研究方法,以上海市浦东新区某社区广场作为研究场域,本文所关注的是,在国家与社会直接接触的城市社区广场,这一常常被认为是娱乐休闲的场所,国家对社会是否仍保持着强大的整合和治理能力?研究该场域中作为基层社会力量体现的参与广场活动的民众与作为国家代表的基层政府之间的关系如何,其特质是怎样的?
1.上海某社区广场的概况。
本研究的个案社区广场位于浦东新区H社区,有意味的是该广场分为南北两块,夹在中间的就是H街道办事处。该广场于2000年修建,2002年投入使用。
H社区北广场是一个类似舞台式的设计,在舞台正底部则作为街道办事处的车库之用,在侧面底部作为H街道下属的Y社区居委会工作室。在舞台的正中央有一个大型的显示屏,常常播放一些公益广告片和社区公告、通知等。舞台的看台部分由两部分阶梯构成,同时其侧面被12根高柱环绕,并配了漂亮的灯饰,到了晚上便散发出绚丽的亮光。北广场的舞台型设计确实也发挥了其舞台效应,北广场常作为社区文化汇演,类似中秋节晚会、区级文艺汇演等之用。相对于北广场的富丽,南广场则朴实得多,只是在四面修葺了半人高的树木,树木下伴有供人休息的长椅、木凳。
北广场由于其设计的精致,即使在白天的时候人气十足,不过多是带小孩的老年人或者是退休的老年人,而南广场在白天的时候则只有寥寥数人了。但是到夜间则是相反的情况,北广场由于舞台、两块阶梯式看台的设计原因,导致场地不是很充足,许多文化娱乐活动不便展开。而南广场由于场地的开阔性,吸引了大量的人参与,本研究主要针对的是在南广场的广场文化活动。
2.一个“特殊”的广场文化活动。
在2002年社区广场得以使用之前,有的文化活动也是存在的,如扇子舞,由12名固定的约50岁左右的中年女性组成,她们原来是在周边农工商超市旁边的一个小块空地组织活动的,而交谊舞活动则是社区广场建成之后才成立的。除了扇子舞之外,在南广场还存在一个最大的文化活动,即交谊舞活动,这一点在下文中再讲述。在南广场的东南角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文化活动,即唱诗班。由于历史原因,在H社区有将近70多人的基督徒,他们秉承基督教义和做礼拜的传统,原来他们的礼拜活动都是在若干居民家中举行,或者到南京路上的教堂中去的。
在2002年广场刚成立的时候,社区内的教众的礼拜活动并没有改变场地,一直到2007年底的时候,这一局面才改变。笔者访谈了一名李阿姨,她是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今年56岁,是一家国企退休工人,嗓音很好,在唱诗班中担任领唱的职责。她告诉笔者:“原来我们在王阿姨家做礼拜的时候,怕影响到邻居,唱歌的时候,都不好意思大声。”笔者问到李阿姨,是否他们自己组织晚上到南广场唱圣歌的?李阿姨答道:“是的,那边场地开阔,有很多人晚上没事的时候都过去玩,唱歌跳舞散步什么的,原来我们好多人都没退休,现在好了,退休了都没事情了,那我想我们晚上过去去唱唱歌,肯定没什么问题。我们大家商量后,就决定去那里了,正好是在南广场最里面,灯光和椅凳都多。”
经过和其他教徒的交谈后,他们告诉笔者,刚开始进广场唱圣歌的时候,的确吸引了很多人的围观,有的教徒利用白布和木板做了一个简易的黑板,上面写上了歌词和音调,后来甚至有人来跟他们学习唱歌了。这种情况大概持续了两个多月的时间。
令人遗憾的是,李阿姨告诉笔者,在2008年3月底的时候,她在家中接到电话,“他也没告诉我是谁,只是说是街道办事处的,让我们不要在广场上唱歌了,说我们唱歌声音很大,有住在广场附近的居民投诉我们了,影响不好。而且,我还记得他的态度很不好,后来还给我们出了个通知,说我们噪音扰民。”“我想,既然政府不准了,那我们就算了吧,反正我们好多人现在都退休了,做礼拜就到人民广场那边的教堂去好了,那边还有很专业的音响,不像我们在广场上时都是从自己家带磁带和录音机那么不方便。”“但是,最让人气愤的是什么,没到一个礼拜,我们原来唱歌的那个地方改成卡拉OK了,一块钱唱一首歌,不是讲嫌我们唱歌声音大嘛,卡拉OK声音不是更大更吵人,明摆着就是不让我们唱呗,找什么借口!”遗憾的是李阿姨所说的那个通知,她并没有进行保存。的确如李阿姨所说,一直到现在为止,南广场内夜间的卡拉OK仍然存在,每天晚上都有人在那里引吭高歌。
就唱诗班的事情,笔者专门找到该H社区街道办事处办公室的张主任,向他询问此事。张主任说:“这个事情涉及到宗教信仰,不好讲(在上海话中,不好讲,意味着不能讲),也讲不好。原来他们在居民家里做礼拜什么的,那是个人行为,现在到广场上去了,那么多人,唱圣歌,总归是不好的,再者说了,南京路那边不是有个大教堂嘛,从我们这里坐地铁几站路就到了,要唱圣歌、做礼拜去那边好了。”
同时,张主任告诉笔者:“我们社区有很多文化能人,你看有的就是单位的文艺骨干,现在晚上有空了,到广场上来教教大家跳跳舞不是蛮好的嘛。那边那个交谊舞,我们还专门去找了个老师过去教大家跳舞,不是蛮好的。我们总要给居民提供点条件的,有时候我们搞搞文艺表演还要请居民帮忙的。”
3.H街道办事处的具体广场“作为”。
作为社区广场的存在,对其的维护与管理必不可少,那么是谁在承担这一指责,是H街道办事处。其职能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广场保洁,包括绿化、垃圾处理、公厕等。在这一点上,是由街道办事处交由专门的保洁公司来承担的。
第二,广场管理员的设置。在南广场的西南角有一个交谊舞音响设备区,这个区域不同于前面唱诗班的自备性质,而是由专门的人负责的。而这个专门的人就是H街道办事处的保安人员,每天晚上7点准时将音响设备准备妥当,再在9点半的时候将设备取走。除此之外,他们还负责南广场内的巡护职责,以防有人摔倒、发生口角之类的事情。
对此,笔者专门访谈了其中一位张姓保安,他说他已经在这个保安岗位上工作了近10年了,他原来就是H社区的居民,他家就住在南广场靠东面的小区内,1999年失业后在街道登记申请工作才得到这个保安岗位的。当笔者问及他是否会关注有哪些人,有哪些活动开展时候,他告诉笔者:“肯定会看到啊,天天都在这,经常能看到一些熟面孔,不熟都熟了,而且现在很多人都有特长的,如前面那个小区的赵老师,他是实验中学的音乐老师,会好多乐器的,他也经常过来义务帮人伴奏什么的,上次搞晚会,还是我推荐他上台表演的呢。”
当笔者问到唱诗班的事情时,这位张姓保安却表示他不知情。他说:“他们没唱多长时间,不到两个月,反正后来就没见再来了,也不知是什么原因”。
第三,区域的制定和划分。广场范围内的获取区域划分应当说,有很多都是自发形成的,如扇子舞活动,担任扇子舞活动的领舞是位57岁左右的王姓阿姨,就住在H社区某单元内,她原来是单位的文化骨干。由于企业倒闭,她几年前就下岗了,一直到2007年年满55周岁开始领取养老金。她告诉笔者:“我们刚开始搞扇子舞的时候,也就是想锻炼锻炼身体的,刚开始就两三个人在我家里练练的,我刚开始没想到要去广场跳舞的,还是02、03年广场刚搞好的时候,也没多少人,那时候我们几个姐妹就商量,还是到广场上去跳舞,毕竟家里太小,拉不开队形,然后我们就去了,去了没人讲我们,我们跳的时候,很多人围观的,后来还有人加入呢。”
王阿姨的扇子舞队伍总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活动,只有熟悉那里情况经常去广场的人能一眼就发现他们。周围的人都知道我们一般什么时候会到这边来,这个位子也就自然而然空出来了。由此可见,广场的区域取决于个人或团队自己的争取,当然也有周围群众的默认,这种默认是一种长期积累下来的习惯,当人们习惯了某种现象的反复出现时,这种习惯就成为了一种潜移默化的不容违背的规范。[6](p48)
扇子舞活动在社区广场的区域占有应当说是遵循了自发的原则,那么该广场内的所有活动是否都是遵循了该原则呢?显然并不是,唱诗班就是最好的佐证。如果说唱诗班的噪音扰民,显然并不是最主要的理由。广场的活动的区域的占有和划分,并不仅仅是单纯意义上的群众兴趣爱好的随机排列组合,这种区域性的划分还遵循着某种规则,而这个规则的制定者就是街道办事处。
三、广场渗透机制:策略性、选择性
1.城市广场的属性。
城市广场作为反映城市文化的一个窗口,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探讨:其一,城市广场建设的理念,即城市广场背后所蕴含的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也可以理解为城市广场存在的意义,是为少数人服务还是为整体市民社会服务;第二,城市广场的布局,也可以称为广场的视觉系统,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环境下由于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的不同导致广场建设理念的不同,从而使得广场的形态和布局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差异;第三,城市广场中公众的活动内容和形式,即广场的行为系统,广场的功能差异导致公众广场行为的不同。[7]
我国建国初期建成的多为城市广场,随着市民社会的发展,城市公共空间的孕育,尤其是地方政府在基层社区的加大投入,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很多城市开始在社区范围内兴建了社区广场(也即城镇广场),而这种类型的广场才是市民最常接触、最多参与的广场。在社区广场内,人们的活动更多的是追求个性,追求生活。对于社区居民而言,社区广场就是他们休闲娱乐的场所。
对于基层政府而言,以社区自治和社区服务为内容的社区建设,社区广场也被纳入其建设的范畴,但是这种“建设”并不是简单的广场建设和维护,单纯的维持治安、保洁之类的活动,而是通过各种娱乐休闲活动的形式,担负起基层社区治理的实质内容。如果说,居民委员会作为国家在基层社会的代理人身份实行制度运作的话,那么社区广场则成为国家进行基层社会治理的另一种渠道。社区广场的种种文化活动的开展,并非简单意义上的娱乐休闲,这些活动的是否开展以及如何发展,则要遵循着社区建设的基本原则。
2.社区广场的“渗透机制”。
在“社区建设”的话语下,国家与城市邻里空间的关系发生改变,国家策略性地为社会创设一定空间,通过社区组织、社区网络、社区代理人等等从而实现其制度运作,始终将生长中的社会力量吸纳入国家体制可控的轨道之中,它反映了政府的统制欲求。
在推进社区建设的过程中,国家对基层的治理形式已发生重大变化。这种变化首先体现在一系列政治话语的提出,“社区服务”、“社区自治”以及“民主选举”等具有更多社会利益倾向性的概念成为社区治理的主流话语,国家的“身影”好像逐渐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场景中淡出,实则不然。
在社区广场,这一常常被人们认为是娱乐休闲的场所,广场和广场文化一方面表现了其特有的群众参与的自由性,另一方面却也反映了国家权力渗透的深度。最直接的内容体现在:什么样的活动是可以开展的,什么样的活动是可以进一步鼓励的,什么样的活动则是要禁止的。这种来自基层政府的社区广场渗透机制带有策略性和选择性的特质,通过提供场所、人员及服务的形式,实则达到社区治理的最终目的,但它并不等同于“粘连模式”,应当说这种渗透机制更具有隐蔽性,却也能起到更好的效果。[3](p69)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社区广场应具有的另一价值,即政治性价值,作为使国家和基层社会力量得以“和谐”的场域。
在某种意义上说,广场这一场域已经被塑造成国家与基层社会都共同认同并尊崇的象征性符号,在广场中,国家与基层社会皆能存在并进一步发展,且后者时刻处于前者更为清晰的解读中,这也就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广场及广场文化。
[1]林尚立.社区民主与治理:案例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2]朱健刚.城市街区的权力变迁:强国家与强社会模式[J].战略与管理,1997,(4).
[3]桂勇.邻里政治:城市基层的权力操作策略与国家-社会的粘连模式[J].社会 2007,(6).
[4]闫整.“传统城市广场的演变研究”[J].山东建筑工程学院学报,1999,(3).
[5]徐勇.中国城市社区自治[M].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
[6]李友梅.基层社区组织的实际生活方式——对上海康健社区实地调查的初步认识[J].社会学研究,2002,(4).
[7]徐永祥.社区发展论[M].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