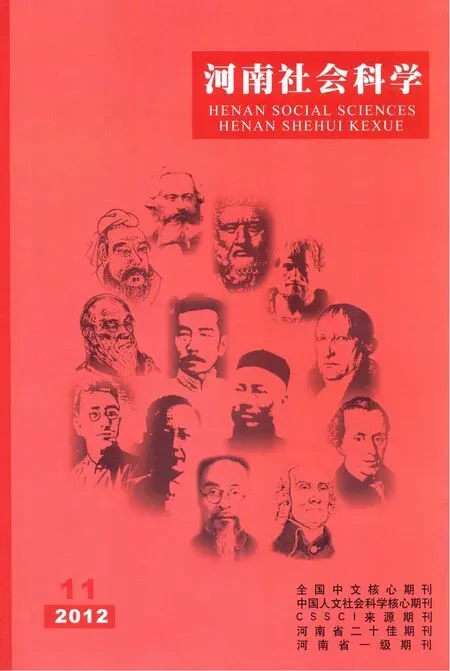近10年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若干重要问题综述
2012-04-12张宇
张 宇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进入21世纪以来,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越来越得到社会和学术界的广泛重视。一方面,学科建设有了质的飞越。2001年2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正式挂牌成立,这是该学科全国普通高等学校人文社会学科重点科研基地,标志着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逐渐走向正规和成熟。另一方面,许多学术刊物开辟了专门的栏目,刊载相关论文,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的学术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使学者得以相互讨论,彼此激发创意。在以上因素的推动下,在21世纪头10年(2001—2011),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得到了迅速发展,有必要对本学科研究现状进行一次学术梳理,进一步明确认识这一时期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的成果及发展状况。由于作者学识有限,不可能综述整个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领域中涉及的问题,本文主要针对其中比较重要的四个方面,即天人关系、君主论、史学批评、少数民族史学的研究成果,进行概要综述。
一、关于天人关系研究
“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中最早提出的问题”[1],是历史理论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一时期关于天人关系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贯通研究。贯通研究是指对天人关系进行宏观考察的综合性研究。这方面的成果主要是瞿林东的《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大势》[2]一文,作者按照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形成(先秦秦汉时期)、发展(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繁荣(五代宋辽金元明清时期)三个阶段,对天人关系作了初步梳理。作者认为在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形成时期,天与人的关系可以包含“天命”与“人事”的作用、“天道”与“人道”的区别等,并且指出二者演进的轨迹是“‘天’、‘天命’、‘天道’所笼罩的神意逐渐被怀疑、被轻视,而‘人’、‘人事’、‘人道’所具有的现实作用逐渐被认识、被重视”[2]。在发展阶段,作者认为尽管这一时期史家、史书还经常说到“天命”,但是“天命”越来越成了摆设,人事才是真正被关注的对象。在繁荣阶段,作者指出:“由于理学的兴起,理学家们关于‘天理’和‘人欲’的诠释,不论其有多大的合理内核,都给史学的发展带来了某种消极影响,但它毕竟不能改变史学家循着‘人事’的‘势’与‘理’去思考和解释历史。”[2]作者在这篇文章中,初步地勾勒出了天人关系在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中发展的大致过程。此外,瞿林东还有《天人关系和历史运动》[3]和《历史理论的本质性变革——确立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中心位置》[4]以及《天人古今与时势理道——中国古代历史观念的几个重要问题》[5]三篇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天人关系进行了宏观性的阐述。在《天人关系和历史运动》里,作者将天人关系主要分解为“论天”、“论人”、“论‘势’和‘理’”三个方面,并按照时代顺序分别予以阐述。在《历史理论的本质性变革——确立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中心位置》一文中,作者指出人在历史中的作用是客观存在的,虽然“天命”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但是随着历史的进步,经过漫长的轻天命、重人事阶段,人们逐渐走向了自觉,阐说人在历史位置中的重要作用。这一过程,由“《春秋》开其端倪,《史记》集其大成”[5]。而在《天人古今与时势理道——中国古代历史观念的几个重要问题》一文中,作者则对天人关系这一范畴作了重要的理论性总结,指出“天人关系是探讨社会历史的存在及其所发生的种种变化,是天命安排的,还是社会历史中的人和人事决定的,这是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5]。
其次,是专题研究。专题研究主要是指就天人关系在某一时期或者某一具体问题方面进行的研究。相对于贯通研究而言,专题研究的涉及面更宽,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方面是天人关系在某一时期的变化。马艳辉在《试析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人关系论的转变》[6]一文中,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史家对天人关系的讨论出现了不同于前代的演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这主要表现在“天命”与谶纬之说、宗教神学的结合以及“天人相分”之说的进一步发展。她指出这一时期“史家对于天人关系问题的讨论出现了两种情况:一种是沿着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论’发展,以新的形式将‘天命’继续留在人们的思想中,并往往用来说明现实社会中的重大事件,尤其是用以附会朝代的更迭、盛衰;另一种是沿着‘究天人之际’路线发展,进一步走向‘天’与‘人’相分的思想境界”。
另一方面是就具体问题进行论述。这方面尤以讨论司马迁及其《史记》的文章为多。崔存民认为司马迁在《史记》里面通过对天人感应学说的怀疑,以及对一些事例的分析,否定了天命决定人事,指出了人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7]。王振红则就《史记》中所述的天的观念进行了详细分析,认为“在五帝时期呈现明显的自然属性,夏商时期又具有了浓厚的宗教性,而在殷周之际,天的观念又以道德为主导”[8]。李宏对司马迁与班固在“天人关系”方面的认识作了比较研究[9]。
总的来说,这一时期关于“天人关系”的整体宏观研究已经达到了比较深入的程度,但是专题方面的微观研究还有待于进一步深入探讨。
二、关于君主论研究
10年中,关于君主论的探讨,一方面是对君主的个案研究,另一方面是对史学家、思想家在君权、君道等方面的论述进行研究。
第一,关于君主的个案研究。瞿林东在《一代明君的君主论——唐太宗和〈帝范〉》一文中指出,在唐太宗《帝范》以前,君主论的论述“大多是就某一君主而论,或是就某一君主同另一君主相比较而论,而非把君主作为一种政治现象作综合的理论阐述。唐太宗所撰《帝范》改变了以往认识上和撰述上的这种局面,鲜明地反映了一代明君的君主论。他从历史和现实的结合、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对君主现象作综合的分析,提出了在那个时代具有普遍意义的认识”[10]。这是对君主及其自身所作的君主论进行的研究。此外,就君主自身而言,还有一些作者把政治史、人物传记与君主论结合起来进行综合研究,以探究君主的政治主张与政治实践,以及君臣关系。如曹升生在论到唐太宗的时候说到在唐太宗以史为鉴的政治实践中,“包含着驾驭大臣以构建和谐君臣关系的努力,正是通过对历史知识的援引发挥,唐太宗向大臣们灌输了忠君思想,宣传了治国理念,进而培育了尊卑有序、和衷共济的官僚系统”[11]。此外关于君主个案的研究,还有一些君主传记。主要是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系列丛书,包括《隋炀帝传》(袁刚著,2001年版)、《汉武帝传》(杨生民著,2002年版)、《刘秀传》(黄留珠著,2003年版)、《唐玄宗传》(许道勋著,2003年版)、《秦始皇传》(张分田著,2003年版),《万历传》(樊树志著,2003年版)、《刘备传》(张作耀著,2004年版)、《孙权传》(张作耀著,2004年版)等,这些传记不仅仅是简单的史事叙述,往往还就君主个人以及后人对这些君主的评价作了分析,体现了政治史与君主论研究的相互结合。
第二,史学家、思想家的君主论研究。就君主论研究而言,古代史学家、思想家们对于君主论的研究是中国古代历史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也是君主论研究的主体。而这些史学家、思想家对于君主的论述主要体现在对君权、君道、君臣关系方面的认识。如对于明亡前后士人的君主论,赵园认为这是明代政治批评的重要方面,并试图将这一时期的君主论置于当时语境中,置于士大夫与“君臣”有关的伦理实践中,得出了当时的士大夫是借君主批评以表达自身的诉求这一结论[12]。靳宝在《两汉“君主”阐释》一文中,从断代的层面,就一些思想家、史学家的君主论作了重要研究,他指出:“两汉学人在先秦诸子思想的基础上,从君主的内涵、称号、治道等方面,明确论证一统尊君与君国一体的国家观,对君主的本质及其作用进行思考,呈现出君主集权的意义,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君主论特点。”[13]
三、关于史学批评研究
10年中史学批评研究得到了较快发展,一方面是召开了专门以史学批评研究为主题的学术会议,即2008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和大连大学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全国研讨会(大连),会后出版了研讨会论文集《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进一步推进了史学批评研究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关于史学批评研究的专著开始出现,如白云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论纲》(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等,该书“全面梳理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之发展脉络,具体划分为萌芽、确立、渐趋成熟、繁荣四个时期,深入挖掘了各个时期中国史学批评之遗产和成就;较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之传统和理论;初步构建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的基本框架,对推动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研究有着积极的意义”[14]。
关于史学批评具体问题的研究,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史学批评自身的学科认识。瞿林东指出:“史学批评是史学理论发展的动因之一,许多理论问题是在史学批评中提出来的,又是在史学批评中得到深入阐说和系统发挥以至于形成体系的。史学批评又是史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之一。批评的展开是活跃史学、繁荣史学的重要手段。”[15]这就明确指出了史学批评的重要性,为史学批评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张越从史学批评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之间的关系角度指出:“在史学理论方面,史学批评表现为‘论’;在史学史方面,史学批评表现为‘史’。史学批评与史学理论和史学史都有着密切关系。”[16]阐明了史学批评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科中的重要地位。
其次,史学批评的范畴研究。罗炳良就中国史学批评的范畴作了初步归纳,分为三大类型:特定时代的史学批评范畴、史学批评的一般范畴、史学批评的基本范畴。他还对史学批评范畴研究的理论价值作了重要阐述:“通过对历代史学范畴发展的考察与研究,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中国史学思想与历程的演变轨迹,有助于把握中国史学发展的脉络。”同时还指出现在“中国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对自身范畴的研究相对薄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学科自身的深化和提高”[17]。刘开军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史权”是史学批评的又一个重要范畴[18]。
再次,史学批评的方法与标准研究。瞿林东认为在如何看待同一史事不同评论、不同史书的题材的长短、历史撰述诸因素的关系等问题时,应该用辩证方法。他说:“辩证方法是史学批评中的重要方法,古代史家所提供的思想资料和批评例证,在今日的史学批评中,仍有借鉴、参考价值。”[19]乔治忠认为历史主义方法是史学批评的基本方法:第一,实事求是、兼指得失,是史学批评的基本出发点;第二,史学批评联系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以及相关的客观条件予以分析,是历史主义方法的主要特征之一;第三,评论一部史学著述、一种史学思想、一类史学观点,要将之置于思想、文化、学术及一般历史进程中分析和定位[20]。在史学批评的标准方面,罗炳良认为古代史学批评的标准可以概括为学术标准、政治标准、道德标准三项主要内容[17]。周一平对这三大标准中的学术标准予以详细阐述,认为学术标准应当包括反对门户之见、学派框框,创新,体例严谨,史事真实、资料可信,追求思想、学术价值,简约,文采等方面[21]。
最后,对于史家或史著的史学批评的研究。10年中,由于史学批评研究发展较快,对于历史上的一些史家及史著的研究,呈现了蓬勃发展的趋势,所涉论文较多,难以一一评述,现将相关论文稍加排比胪列于下:周文玖的《刘知幾史学批评的特点》(《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3期),李振宏的《刘知幾史学的批判精神》(《史学月刊》2011年第2期),吴怀祺的《〈通志〉:富有活力的史学批评著作》(《光明日报》2001年8月14日),罗炳良的《传统史学理论的终结与嬗变——章学诚史学的理论价值》(泰山出版社,2005年),彭忠德的《章学诚“史德”说新解》(《武汉大学学报》2009年第2期),朱政惠、陈勇的《章学诚的史学批评理论及其借鉴意义》(《史学史研究》2010年第1期),王秀青的《梁启超:史学比较方法的倡导与实践》(《云南民族大学报》2004年第2期)、《梁启超与中国史学史学科的创立》(《学术前沿》2004年第5期),白云的《孔子的史学批评》(《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06年卷),施丁的《王充〈论衡〉的史学批评》(《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宋馥香的《高似孙〈史略〉之史学批评管窥》(《郑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5期),蔡克骄的《南宋浙东学派的史学批评》(《郑州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向燕南的《王世贞的史学批评及其理论贡献》(《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研究》,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年),白云的《论钱大昕的史学批评》(《红河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刘开军的《王鸣盛对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批评》(《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段润秀的《易代修史中的史学批评问题探论——以清代〈明史〉修纂为例》(《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等。总的来说,对于大多数史家和史著的史学批评研究,虽然尚未形成系统,但是从总体来看已经呈现了蓬勃发展的趋势。
四、关于少数民族史学研究
10年中,少数民族史学研究得到了深入发展,相关著作论文日益增多,但是它作为新兴的研究领域,发展仍相对薄弱。目前来看,论著所研究的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学科方面的认识。这主要包括对少数民族史学的定义、研究对象、研究资料等问题的探讨。总的来说,对于少数民族史学的定义,已经由模糊、混乱——主要体现在民族史学、少数民族史学、少数民族史学史等概念的认识上——逐渐走向清晰、准确。瞿林东指出:“这里所说的少数民族史学,是指在中国史学发展中,那些记述各少数民族历史或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记述少数民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治统治实体及其统治范围内有关少数民族的历史,以及记述少数民族地区及其同中原地区民族与政治统治交往的历史。”[22]这就为少数民族史学作了明确的定义。罗炳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区分出“少数民族历史→少数民族历史研究(少数民族史学)→少数民族史学研究(少数民族史学史)→少数民族史学史研究(少数民族史学史之史)”[23],使相关的各层概念进一步明晰。关于研究对象,罗炳良老师认为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研究对象应当包括四个方面:(一)记载和研究中国境内现存各少数民族历史的史学成果,如藏族史学、蒙古族史学等;(二)记载和研究中国境内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少数民族历史的史学成果,如契丹族史学、女真族史学等;(三)记载和研究各个历史时期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社会历史发展的史学成果,如对古今各个时期中央政权管理下的周边少数民族历史的撰述;(四)20世纪以来的民族史撰述成果,如对撰写各民族发展史、民族精神与历史文化认同等方面历史著作的研究[23]。关于研究史料的范围,罗炳良综合为四个方面:(一)今天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口耳相传的记忆和文献资料;(二)历史上曾经存在的少数民族留下的文字史料;(三)汉文史籍中记载少数民族历史的史料;(四)20世纪民族调查资料与民族史撰述成果[23]。
其次,少数民族史学的贯通与专题研究。关于贯通研究,瞿林东先生将少数民族史学的发展过程分为六个阶段:(一)先秦、秦汉时期的少数民族史学,这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起步阶段;(二)魏晋隋唐间的少数民族史学,这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其特点是多途发展局面的形成;(三)辽、宋、夏、金、元时期的少数民族史学,这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第二个高潮,其特点是深入发展的趋势;(四)明清时期(1840年前)的少数民族史学,这是中国古代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第三个高潮,其特点是全面发展的态势;(五)中国近代(1840—1949年)的少数民族史学,其特点是在少数民族史学研究和撰述中,民族危机意识和民族觉醒意识的不断提升与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及发展;(六)现代的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少数民族史学,这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研究的新阶段[23]。汪受宽把隋唐五代之前视为少数民族史学的初步发展阶段,并分为先秦时期、两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期、隋唐五代时期,指出“中国少数民族史学自先秦产生,历经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终于得到初步发展”[24]。关于专题研究,主要体现在少数民族史学的断代研究以及从少数民族史的角度去研究少数民族史学。在断代研究方面,董文武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个社会大动荡时期,社会现实的巨变深刻影响着这一时期,民族观念的变化,而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对史学的重视更是直接推动了民族史学的发展。这一时期,史家的民族史撰述越来越体现时代特征,并表现出进步的民族一统观、民族同祖同源观,而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和各民族共同发展依旧是这个时期史家民族思想的主流。”[25]瞿林东对魏晋隋唐间的少数民族史学作了详尽梳理。他说:“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发展的第一个高潮。《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的有关著录反映了这一高潮的基本面貌。这个时期成书的各朝正史中的民族史专篇,发展了司马迁、班固撰写民族史专篇的优良传统。《华阳国志》和《蛮书》记述了西南少数民族的历史;《十六国春秋》和《晋书·载记》则记述了北方少数民族的社会历史;《魏书》和《周书》因其自身的特点而具有少数民族史的性质;《通典·边防典》本质上是一部古代少数民族史。以上这些,反映了这个时期少数民族史撰述的盛况。”[26]乔治忠亦说道:“入关后清朝官方史学,还是归入中国传统史学观念、史学方法的主流,承续了中国两千多年史学长足发展的成果,其性质不能属于少数民族的史学,仅包含着少数民族的史学因素而已。这在中国历代官修史学中是独一无二的,其中的政治文化意义不可漠视。这种少数民族文化因素注入传统史学主流的进程,恰与中华民族融合与统一的进程相一致。”[27]从少数民族史的角度去研究的少数民族史学方面的文章近年著述颇多,大致胪列如下:东人达的《彝文古籍与彝族史学理论评述》(《史学史研究》2005年第1期)、《“探根”现象与彝族史学的社会功能》(《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1期),刘勇的《藏族传统史学学科概念分析》(《中国藏学》2006年第2期),孙林的《文本话语与行为规范:西藏宗教人物传记的史学史意义》(《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4期)、《藏族史学发展史纲要》(中国藏学出版社2006年版),杨富学的《回鹘文文献与高昌回鹘经济史的构建》(《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4期),陶玉坤的《辽朝家族史研究》(《史学史研究》2007年第4期),才让的《藏文历史名著〈贤者喜宴〉史料价值探析》(《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1期)等。
总的来说,21世纪的头10年(2001—2011)里中国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取得了重大发展,涌现了一大批重要的论著,在深度与广度上都有了相当程度的突破,并得到了学术界与社会的广泛重视。但是依然存在着研究不够系统化等问题,这还需要广大史学工作者们继续努力。
[1]瞿林东.中国古代历史理论[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11.63.
[2]瞿林东.中国古代历史理论发展大势[J].河北学刊,2011,(1):40—48.
[3]瞿林东.天人关系和历史运动[J].史学月刊,2004,(9):5—8.
[4]瞿林东.历史理论的本质性变革——确立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中心位置[J].学习与探索,2007,(4):206—210.
[5]瞿林东.天人古今与时势理道——中国古代历史观念的几个重要问题[J].史学史研究,2007,(2):1—6.
[6]马艳辉.试析魏晋南北朝时期天人关系论的转变[J].郑州大学学报,2011,(4):107—111.
[7]崔存民.究天人之际——司马迁历史哲学思想引论[J].北京印刷学院学报,2004,(3):42—45.
[8]王振红.《史记》述“天”与历史理性的萌生[J].湖北师范学院学报,2008,(6):80—85.
[9]李宏.司马迁与班固历史观的异同[J].渤海大学学报,2007,(5):67—70.
[10]瞿林东.一代明君的君主论——唐太宗和《帝范》[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6):14—18.
[11]曹升生.以史为鉴:唐太宗构建和谐君臣关系的实践[J].船山学刊,2009,(1):67—70.
[12]赵园.原君·原臣——明清之际士人关于君主、君臣的论述[J].中国文化研究,2006,(2):12—33.
[13]靳宝.两汉“君主”阐释[J].咸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1):28—33.
[14]白云.趋势和走向——中国史学批评研究30年[J].廊坊师范学院学报,2011,(4):34—42.
[15]瞿林东.关于影响21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几个问题[J].史学月刊,2001,(6):5—9.
[16]张越.史学批评与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学科的关系[J].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08,(6):98—100.
[17]罗炳良.中国古代史学批评与史学批评范畴[J].郑州大学学报,2009,(1):137—139.
[18]刘开军.论“史权”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范畴[A].史学批评与史学文化研究[C].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9.
[19]瞿林东.略说古代史家史学批评的辩证方法[J].求是学刊,2010,(5):125—131.
[20]乔治忠.历史主义方法是史学批评的基本方法[J].郑州大学学报,2004,(1):9—11.
[21]周一平.中国传统史学批评的学术标准[J].郑州大学学报,2009,(1):139—142.
[22]瞿林东.少数民族史学的发展与统一多民族国家观念的形成[J].河北学刊,2007,(6):91—94.
[23]罗炳良.略谈中国少数民族史学史的定义、研究对象及史料范围[J].郑州大学学报,2008,(1):115—117.
[24]汪受宽.中国少数民族史学的产生与初步发展[J].史学史研究,2008,(1):54—63.
[25]董文武.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史撰述与民族一统、同祖同源观[J].河北学刊,2007,(6):94—97.
[26]瞿林东.魏晋隋唐间的少数民族史学(上)[J].河北学刊,2008,(3):67—78.
[27]乔治忠,崔岩.略论清朝官方史学中的少数民族因素及其启示[J].郑州大学学报,2008,(3):137—1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