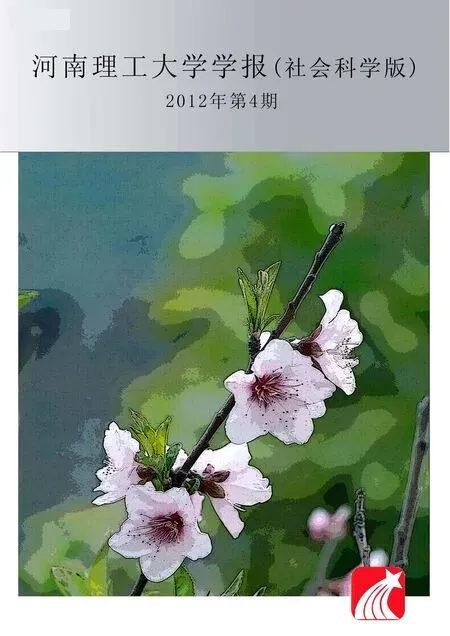略论《唐六典》①的注
2012-04-07徐适端
徐适端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重庆 400715)
略论《唐六典》①的注
徐适端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重庆 400715)
《唐六典》的注,从内容到形式创造性地承继、借鉴了《汉书》地理、艺文二志自注的优点和裴松之、郦道元等史家的注史特色,开创了典制史专著的自注新法;它集唐开元以前史注之大成,并进行了发展与创新;《唐六典》的注完善了史书的自注体例,对后世典制史的自注体例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历史编纂学上的地位和历史文献价值,都不可忽视。
唐六典;自注;溯源;训释;编纂学;文献学
在历史编纂学史上,史书注释一直颇受史学界的关注与研究。史注总体分为两大类:一是史家注他人之书,一是作者注释己著。前者至魏晋南北朝已取得很大成就,并出现了不少注史名家和多种注史方法[1];后者称为自注,刘知几《史通·补注》篇曰“子注”,这是史注中极富特色的一种体式,是著者在撰述中对于历史文献的一种特殊处理方法。它始于西汉,《史记》为其权舆②。
对于史书的自注,学术界一直很推崇唐代杜佑《通典》的注,并撰有专文进行研讨①
①有关《通典》自注讨论的专文有曾贻芬《论〈通典〉自注》,《史学史研究》1985年第3期;瞿林东《魏晋至隋唐的历史文献学》,《学术研究》2000年第1期;谢保成《隋唐五代史学》第九章第二节“杜佑创史书编纂新体系”中言及“自注,也是《通典》在编纂方面的一个特点”;其余有关《通典》自注的论述均散见于各种《中国古代史学史》著作中。。而对于集唐开元以前史注之大成、创典制专著注释新法的《唐六典》之注,却绝少问津。故本文专就《唐六典》的注进行考察,并探讨其性质、特点和价值,以此求教于方家。
一、《唐六典》之注的性质
《唐六典》是唐玄宗开元十年下令开始编修的。初,玄宗亲笔“手写白麻纸凡六条,曰理、教、礼、政、刑、事典,令以类相从,撰录以进”[2],并明确要求,“错综古今,法以周官,勒为唐典”[3]。玄宗的御旨,实际在暗示奉旨撰臣要仿效《周礼》这部儒家经典的定制,分国家职能为六大块,将职事“以类相从”,以职官联系各种制度,编纂一部既能体现《周礼》的精神和原则,又能反映大唐现行制度、展示天朝大国气象的、前无古人的集大成之典制巨著。这实在是一项无旧例可循的工作,现行官制与《周礼》六官已大不相同,两者如何兼顾?旧有的编纂体例是无法完成的。当时知集贤院事的张说将此事“委徐坚”,使“于典故多所谙识,凡七当撰次高选”[4]的“徐坚构意岁余”,竟不能确定其体例。最终由“雅有良史之才”的韦述经过反复揣摩,才确定《唐六典》仿《周礼》,“以令式入六司,象《周礼》六官之制,其沿革并入注”[2]的编撰体例和方法,即在正文中沿用《周礼》设官分职的分类之法叙述唐代现行政府各级部门的机构设置、编制、员数、品秩、职掌、属司和相关的业务范畴、规章制度,此为全书之经线;将注文作为全书的纬线,置于相应之处,以记述职制的历史渊源、废置,包括当朝典制的沿革、变化情况;并进一步解释和补充说明其职掌、规章。这样既清楚地将唐代六官之制及其变化记载下来,又满足了追述唐以前职官的沿革,撰成历代职官典制之集大成巨著的要求;保证了既“详今”,又不“略古”。后经萧嵩、张九龄主持,参与编撰者有徐坚、毋煚、余钦、咸廙业、孙季良、韦述、刘郑兰、萧晟、卢若虚、陆善经、苑咸等十多人[5],“历经十六年,四易主持人”[6],至开元二十六年(738)才撰成此书;第二年,李林甫奉旨负责的注亦撰成奏上。“这是集贤院撰修著作中历时最长,用功最为艰难的一部集体创作。”
由上可知,《唐六典》的编纂是集体的力量。《唐六典》的注,完全是编纂者事先构思的内容、规定的形式,是全书统一结构中的特殊撰述形式。《唐六典》的注者,同样是该书的编纂者,其注释只是参编者们的一种分工。毫无疑问,《唐六典》的注,理应是自注性质,从编纂之初便是与正文不可分割的有机部分。但《唐六典》的自注不同于一般个人私修史书的自注,它是官修,显示了集体的力量。《唐六典》的自注,是编纂该书的一种重要技术手段;它与正文互为经纬,真正体现了“著者在撰述中对于历史文献的一种特殊的处理方法”。《唐六典》的撰臣们利用自注的形式,使编纂内容获得了相对自由记载的空间,最终圆满完成了唐玄宗编纂此书的“荒谬使命”②*②语出严耕望《略论唐六典之性质与施行问题》:“事实上,此为一无法完成之荒谬使命,任何人思之,虽千百年,无从措手。”《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24,第73页,1953年。,正如明王鏊在《唐六典序》中所赞誉的:“蒐一代之制,著于简策以为后法,固非谫薄之所堪任……周之后,莫善于唐,唐有《六典》。”因此《唐六典》的自注,有其独特之处。
二、《唐六典》之注的内容特色
《唐六典》编纂方法上的创意,其核心就在于它的自注。
典制体史籍中的自注,创始于班固《汉书》的地理、艺文二志,其作用主要是进一步对史书有关内容做必要的说明,目的是使正文连贯而简洁,使所述内容更加明白、清晰和丰满。然而此后的典制史籍没能很好地继承此自注之法,少数史籍即便使用了此法,其自注内容也多为补充说明性质,且较简略③
③唐初所撰《晋书》中地理、律历二志,《隋书》中地理、经籍、百官、音乐、律历等志也不同程度地使用了自注,但自注内容仍多为补充说明性质,大多比较简略。。《唐六典》的撰臣们独具慧眼,既继承了《汉书》二志自注的优长,还借鉴了裴松之、刘孝标、郦道元等诸家注史特色,创造性地发展了史书自注的体例,使《唐六典》中的自注内容非常丰富,而且极具特色。《唐六典》的注文内容大致可分如下几方面:
(一)追述历代制度的沿革变迁
追述历代制度的沿革变迁是《唐六典》自注中最主要的内容。《唐六典》在编撰之初,便规定了将“沿革并入注中”,因而“溯沿革”成为注文中篇幅最大者。它一般置于每一职官或制度之首下,先注明该职衔的由来、沿革或某一制度的渊源,一直述至当朝,然后说明其职衔的品级、职掌、服饰、印绶、上朝班第、俸禄等,并具体介绍历代员数的损益及曾任此职而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其源大多溯自秦汉,也有远溯自夏、商、周乃至尧、舜、禹或传说中的黄帝等。对本朝新置者,则以开元时期的变化尤为详明。如:
卷一“三师”条正文“太师一人,正一品;太傅一人,正一品;太保一人,正一品”。注:“《尚书》云:成王既黜殷命,灭淮夷,归酆作周官,立太师、太傅、太保,兹为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孔安国曰:师,天子所师法。傅,傅相天子。保,保安天子于德。《义礼》云:设四辅及三公,不必备,惟具其人言使能也。汉承秦制不置三公;汉末以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为三公,师傅之官在三公之上。后汉因之……皇朝复置,仪制依隋氏……”共用了525字,从先秦作《周官》时“三师”的始建历史起,一直述至开元时期的沿革变化。此注文字数是正文21字的25倍。
又卷六“尚书刑部”条,“凡律一十有二章……而大凡五百条焉”,仅64字。其注云:“律,法也。”接着,从战国时“魏文侯师李悝集诸国刑书造《法经》六篇”叙述起,一直述到隋《开皇律》,再到当朝“永徽复撰《律疏》三十卷,至今并行”止,把历代刑律的制定、种类、沿革变化详详细细地作介绍,此则注文特长,共2450字,为正文的38.2倍,俨然一篇开元以前的刑律发展简史。
《唐六典》这种溯源的注文内容并不局限于制度史,其他如宗教史、文化史内容也较丰富。如:宗教史方面,卷四“尚书礼部”“僧持行者有三品:……大抵皆以清静慈悲为宗”。注:“释氏之源,秦、汉已前未传中土。至汉武元狩中,遣将军霍去病讨匈奴……帝以为神,列于甘泉宫……不祭祀,但灯香礼拜而已。及至张骞使大夏,闻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国,有浮屠之教。哀帝元寿元年,受大月氏王使浮屠经。后汉明帝永平三年……遣郎中蔡愔使于天竺国,写浮屠遗范。愔乃与沙门迦华摩腾、竺法兰东还洛阳。中国有沙门及拜礼之法,自此始也……愔之还也,以白马负经,汉因立白马寺于洛城雍关西。浮屠正号曰佛陀……所谓佛者,本号释迦文,即天竺释迦卫国王之子……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惠为宗,所谓六波罗密者也。自齐、梁之后,其道弥尊。”全文约350字,恰是一段佛教传入中国缘起、经过的简史,还介绍了佛之生、戒义、传说等内容。又,同卷“道士修行有三号……大抵以虚寂自然无为为宗”。注:“其法出于老子……其要在清静理国,立身之要出。至后汉,张道陵号天师,阐扬其化,周于四海者,以显其德。”用约240字对道教的渊源,教义、内部结构作了介绍及评说。
文化史方面的内容则更广。如卷10秘书省:“秘书省:监一人,从三品”的注文大约1 000字,俨然一部关于古代典籍的编纂、搜求、收藏管理制度简史。而卷二十二“少府军器监”正文“诸铸钱监:监各一人”,其注文共900余字,则是一部历代铸钱制度小史。
总之,《唐六典》的溯源式自注涉及方面很多:官吏、制度、法律条文、租赋、礼制、宗教、建筑、选举等,均追本溯源,内容丰富,清晰明了,史料价值极高。因此,该书不仅成了“以开元年间现行的职官制度为本,追溯历代沿革源流,以明设官分职之义的考典之书”[7],也是一部较详细的历代各类制度沿革变迁的通史,充分体现了编纂者们的会通思想。
(二)补充说明正文的各种制度和职守
此类自注多在具体职官执掌事务或各项业务范畴、规章制度的正文之下,对其作进一步的补充解释或说明。这是除“溯沿革”之外内容最多、最具体详细的一类注释。如:
卷五“尚书兵部”条“每烽置帅一人、副一人。”注:“其放烽有一炬、二炬、三炬、四炬者,随贼多少而为差焉。”卷八“门下省”“侍中之职”条,对正文的“奏抄”、“奏弹”、“露布”、“议”、“表”、“状”的自注,用了约400字,清楚而具体地补充说明上述六种章奏格式和使用规程。又如卷五“尚书兵部”“员外郎”条,注文对于有关武贡举的具体考核录用制度用了800字,注释得很细密具体。
这类注释,吏、户、刑、礼等部的补充内容尤其详细,字数亦多。
如卷二“尚书吏部”“侍郎二人”条,正文叙述其负责铨选官吏,“以四事择其良:一曰身,二曰言,三曰书,四曰判”。注文则补充说明试判过程曰:“每试判之日,皆平明集于试场,试官亲送侍郎出问目试判两道,或有名学士考为等第,或有试杂文以收其俊乂。”在“考功郎中”条,其注则对有关科举考试举士的考试内容、考试程序、方式、录取比例、等第划分乃至考选时间、远近不同距离的职官考选所用时间等都注释得十分详细。“郎中”条的注文还补充说明有关致仕的程序、应履行的手续、归家途中的待遇等,具体而且操作性极强。
户部所职,是涉及国计民生问题,无论行政区划的变迁、州郡山川的位置以及水陆交通、物产、贡赋、水利的变化等包罗万有,因此该书卷三“户部”的注文补充说明内容最为丰富。如:
正文“仓部郎中一人……凡常平仓所以均贵贱”。注云:“今太府寺属官有常平署,开元二十四年敕:常平之法,其来自久。比者,州县虽存所利非广,京师辐辏,浮食者多,今于京城内大置常平,贱则加价收籴,使远近奔委,贵则终年出粜,而永无匮乏也。”又同卷“郎中、员外郎掌领天下州县户口之事,凡天下十道任土所出而为贡赋之差。一曰关内道。古雍州之境。今京兆、华、同、岐、邠、陇、泾、宁、坊、鄜、丹、延、庆、监、原、会、灵、夏、丰、胜、绥、银,凡二十有二州焉。”注:“其原、庆、灵、夏、延,又管诸蕃落降者,为羁糜州。”“东据河西抵陇坂,南据终南之山,北边沙漠。”注:“河历银绥延丹同华六州之界,陇坂在陇州之西,终南山在京兆之南,沙漠在丰、胜二州之北。”“其名山有太白、九嵕、吴山、岐山、梁山、泰华之岳在焉。”注:“太白在京兆武功县,九嵕在奉天县,吴山在陇州,岐山在岐州,梁山在同州韩城县,华岳在华州。”“其大川有泾、渭、灞、浐。”注:“泾水出泾州至京兆入渭,渭水出渭州历泰、陇、岐、京兆、周、华六州入于河,灞、浐并出京兆。”而对于只有笼统数字的正文如“又望县有八十五焉”,注文则分别具体注出38州名及其分别所辖的85个望县名称。本卷的注文多近似于正史书中的食货志、地理志之内容。
对于卷六“尚书刑部”,注文补充记载了大量如何判案之类极具操作性的资料原文,将许多较为模糊、抽象的概念,以注的形式给予量化、具体化。如关于死罪处置条,“每岁立春后至秋分,不得决死刑”。注:“若犯恶逆及奴婢、部曲杀主,不依此法。”而“都官郎中、员外郎”的职掌条:“凡初配没有伎艺者……凡诸行宫与监、牧及诸王、公主应给者,则割司农之户以配。”注:“诸官奴婢赐给人者,夫、妻、男、女不得分张;三岁已下听随母,不充数。若应简进内者,取无夫无男女也。”“其余杂伎则择诸司之户教充。”注:“官户皆在本司分番,每年十月,都官按比。男年十三已上,在外州者十五已上,容貌端正,送太乐;十六已上,送鼓吹及少府教习。有工能官奴婢亦准此。业成,准官户例分番。其父兄先有伎艺堪传习者,不在简例。”注文补充得非常具体,便于参照执行。
特别是卷四“尚书礼部”所载之礼节规制,由于繁缛细密,大多以注释作补充,以免影响正文的连续性,使正文简洁、结构清楚。
卷十一“殿中省”的“尚食局”、“尚药局”和卷十四“太常寺”、“太医署”的注则补充了丰富的中医药物、医疗、食疗知识,卷十“秘书省”、“司历官”属文后的注文中更有不少天文知识。
总之,《唐六典》中这种补充说明性质的自注,尽量将正文所叙官职、制度、名物等补充清楚、详细。既保证了正文结构的完整,又将所载制度说得明明白白,大都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三)训释词语名物,解释制度
这类注文主要置于正文中有关体制的专有名词术语之下,对相关专有名词进行必要的训释。
如:卷一“尚书都省”条,正文“左右司郎中……凡上之所以逮下,其制有六:曰制、敕、册、令、教、符”。自注训释曰:“天子曰制、曰敕、曰册,皇太子曰令,亲王公主曰教;尚书省下于州,州下于县,县下于乡,皆曰符。”又正文:“凡下之以达上,其制亦有六:曰表、状、笺、启、辞、牒。”自注解释曰:“表上于天子,其近臣亦为状、笺,启于皇太子,然于其长亦为之,非公文,所施,九品以上公文皆曰牒,庶人曰辞。”又同卷正文“左丞一人……右丞一人……”注:“丞者,承也,言承助令、仆总理台事也。”
又卷十三御史台正文“大事则冠法冠,衣朱衣……”注:“法冠一名豸冠,一角,为獬豸之形,取触邪之义也。”又卷六“尚书刑部”正文“凡《令》二十有七……而大凡一千五百四十有六条焉”。注:“令,教也,命也。《汉书》:杜周曰: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亦谓法也。”
(四)对所引史料进行考辨
如卷一“尚书都省”条,正文“左丞一人……右丞一人……”注引司马彪《续汉书》云:“尚书丞一人,秦所置,汉因之。至成帝建始四年置列曹尚书,更置丞四人。至光武减其二,惟置左、右丞各一人。”注者紧接着就彪书所载至成帝置“列曹尚书”及员数事进行考辨,曰:“然汉列曹尚书四人,成帝加至五人,彪言成帝置列曹尚书,恐误也”。
此类注文虽不多,但反映出编纂者撰著时对待史料的严谨态度。
(五)对某些制度加以评论
《唐六典》虽然是官修,但注文中仍然不乏修撰者的主观评论。如卷二“尚书吏部”,对正文“凡授左右丞相、侍中、中书令、六尚书已上官,听进让;其四品已上清望官,才职相当,不应进让”。注:“按:旧制,御史大夫、六尚书已上要官皆进让。臣林甫等伏以为进让之礼,朝廷所先,两省侍郎及南省诸司侍郎、左右丞,虽在四品,职居清要,亦合让也。”明确地表达了作者对“进让之礼”的观点。又如卷八“门下省”:侍中“凡法驾行幸,则负宝以从”。注:“秦、汉初置侍中,主诸御物,品秩亦卑。晋、魏以来,其任渐重。至隋,乃为宰相之任。负宝之仪,因而不改,抑非尊崇宰辅之意。”显然,这是撰者对侍中身为宰辅仍做“负宝以从”这种小事的看法。
由上可见,《唐六典》的注文绝非单纯的“溯沿革”。
三、《唐六典》注释原则与方法
通考《唐六典》全书之注释,其注释原则与方法大致可归纳为如下几点:
(一)有话则长,无话则短
《唐六典》注文,根据“沿革并入注”的编纂体例和正文需要,其溯源时的注文字数有多至几千字者,如卷一“尚书都”省“尚书郎”一职的注释就用了1 532个字,是正文字数的90倍。又卷六“尚书刑部”“凡《律》一十有二章……”共64字,注文却有2 450字,是正文的38.2倍。但注文中最少者却只有2个字,如卷六“尚书刑部”“死刑二”,注:“绞、斩。”就各卷来看,卷一的注文字数是正文的5.3倍,卷九的注文是正文的4倍;而第二十四、二十五、二十七、二十八、三十等卷的注文,则还不及正文多。可见注文内容字数的多寡,完全根据实际需要而来。
(二)编撰者的直接解释
此主要用于词语、名物以及地名古今变化等的训释和对当朝典制的变化、具体职官的各项业务范畴、规章制度作进一步的补充解释。这种注释所占注的分量较重,内容广泛。
如卷六“尚书刑部”对“十恶”的注释:其一曰谋反。注:谓谋危社稷。二曰谋大逆。注:谓谋毁宗庙、山陵及宫阙。三曰谋叛。注:谓谋背国从伪。四曰恶逆。注:谓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五曰不道。注:谓杀一家非死罪三人,支解人,造畜蛊毒,魇魅。六曰大不敬。注:谓盗大祀神御之物、乘舆服御物,盗及伪造御宝,合和御药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误,若造御膳误犯食禁,御幸舟船误不牢固,指斥乘舆情理切害及对捍诏使而无人臣之礼。七曰不孝。注:谓告言、詈诅祖父母、父母;及别籍异财,若供养有阙;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诈称祖父母、父母死。八曰不睦。注:谓谋杀及卖缌麻已上亲,殴、告夫及大功已上尊长。九曰不义。注:谓谋杀本属府主、刺史、县令、见受业师。十曰内乱。注:谓奸小功已上亲,祖、父妾。又卷一“尚书都省”:“左右丞相掌总领六官……今则专统焉。”注:“初亦宰相之职也。开元中,张说兼之,后罢知政,犹为丞相。自此以后,遂不知国政。”
其注明地点者如卷十七“太仆寺”“沙苑监:监一人,从六品下”。注:“沙苑在同州。”注明地名古今变化,如卷三“尚书户部”“九曰剑南道,……北通剑阁”。注:“剑阁在剑州普安县界,今谓之剑门。”“十曰岭南道……福禄、庞”,注:“郁林、平琴二州复名……福禄一州复名。”“凡天下之州、府三百一十有五……岐、蒲为四辅州”,注:“蒲新升入。”
或对古代有而今不常置之官职作专门交待。如卷一“尚书都省”:“八座之官但受其成事而已。”注:“自太师已下,皆古宰相之职,今不常置,故备叙之。”卷六“尚书刑部”:“凡决大辟罪皆于市。”注:“古者,决大辟罪皆于市。自今上临御以来无其刑,但存其文耳。”
或采用夹注形式,对注文中引文、书注给予进一步注释。如卷一“尚书都省”“尚书令一人,正二品。”注引《汉书》中所及“中尚书”一职。便夹注曰“中尚书,谓中书及尚书也,中书典尚书奏事,故连言之”。
(三)使用参见法以避免注文的重复繁杂
卷二“尚书吏部”:“凡天下官吏各有常员。”注:“开元二十三年……减冗散官三百余员。其见在员数,已具此书,各冠列曹之首;或未该者,以其繁细,亦存乎《令》《式》。”
卷九“中书省”:“右补阙二人,从七品上”。注:“废置已详门下省左补阙注。”“右拾遗二人,从八品上。”注:“已详左拾遗注。”“起居舍人二人,从六品上。”注:“起居舍人因起居注而名官焉……其设官沿革,起居郎注详焉。”卷十四“太常寺”:“鼓吹署……乐正四人,从九品下”。注:“其说已具太乐乐正下。”
《唐六典》注中,参见法的使用约20例。
(四)实事求是,如实注明资料有缺
卷八“门下省”“典仪”条,注文分别引《周礼》《齐职仪》等说明历代均有典仪一职及其员数、职掌,但同时注明“史阙其品秩。梁有典仪之职,未详何曹之官”。又卷十七“太仆寺”“车府署”条,注文从“秦置车府令”溯起,直至“皇朝因隋”止,其间明确注出“后魏阙文”。卷二十五“左右羽林军卫”,注:“羽林禁兵旗帜、名数,秘莫得知,略之。”体现了撰者严谨的注史态度。
(五)主持、撰修者用“案(按)”形式补充、修订此前注释者的缺失
全书注文中有“案”者共16条,其内容大率如下:
或为补充解释注文所引,如卷一“三公”“司空一人,正一品”条,注引自《尚书》,“孔安国曰:‘司空主空土以居人。’案:空,穴也,古者穴居。”使所引更清楚明白。
或补充注文在溯源上的不足,如卷一“尚书都省”“左司郎中一人,右司郎中一人,并从五品上”条,注文用了1 400多字历述“尚书郎”之职的沿革,直叙到“皇朝改郎为郎中,又每曹置员外郎”。后注者案:“左、右司郎中,前代不置。炀帝三年,尚书都司始置左、右司郎各一人,品同诸曹郎,从五品,掌都省之职。皇朝因改曰郎中。至龙朔二年,改为左右承务;咸亨元年复故。其服章与诸司郎中并同:玄冕、五旒,衣无章,裳刺黻一章,两梁冠。”以补充强调说明“左右司郎中”为当朝之制。
或补充注文遗漏者,如卷一“尚书都省”“都事六人,从七品上”条,注文引书只叙及历代令史的职掌、员数、任职条件及礼仪,却无具体品秩的说明。故后注者案:“历代令史皆有品秩。汉尚书台令史秩二百石。魏氏令史皆八品。《晋百官公卿表》云:尚书都令史八人,秩二百石,与左、右丞总知都台事。齐、宋八人,梁、陈五人,品并第八。梁武天监初……隋开皇初,改都令史为都事,置八人,正八品上……”以补充说明历代令史的品秩。
或补充说明最后撰者当时发生的职官、礼制变化。如卷九“中书省”“中书舍人掌侍奉进奏,参议表章……”按:“今中书舍人、给事中每年各一人监考内外官使。其中书舍人在省,以年深者为阁老,兼判本省杂事;一人专掌画,谓之知制诰,得食政事之食;余但分署制敕。六人分押尚书六司,凡有章表皆商量,可否则与侍郎及令连署而进奏。其掌画事繁,或以诸司官兼者,谓之兼制诰。”
综上种种,可见《唐六典》的注文不仅内容宏博,而且形式灵活,方法也多样。
四、《唐六典》注文的价值及其影响
《唐六典》的注文在历史文献学和编纂史上的地位、价值和影响都是不可低估的。
(一)《唐六典》注文具有极珍贵的历史文献价值
《唐六典》正文(包括每卷目录)约7.072万字,注文约12.08万字,注文字数约为正文字数的1.71倍。其中注文为400~500字者有16条,500~600字有4条,600~700字有5条,700~900字有4条,925字1条,1 532字1条,2 450字1条。所引用的历史文献共约244种(篇):经部书约33种(篇),其中小学书6部;史部书约148种(篇),其中起居注5部、地理书4部、刑法书53部(篇)、目录书5部;子部书约43部(种),其中医书(包括方技)约23部;集部书10部。《唐六典》注文大大超过了职官制的史料范围,使该书“无论政治、经济、财政、文化、选举、边防、军制、舆地、方物、交通、职官、礼仪、刑律、朝章、服饰,概言之,上至朝纲大政国策方略,下至贩夫驿卒田事刍荛,旁及四夷边防要典”[8],几乎包罗万象。为我们认识唐开元及其前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流变提供了丰富的文献史料;也为我们保存了大量唐代开元以前的典籍,其中如汉武帝时期《禁中起居注》、后汉明德皇后时期《明帝起居注》《汉朝杂事》、辛氏《三秦记》、杨楞伽《北齐邺都故事》、牛弘《大兴记》等约有60部书籍,至《新唐书·艺文志》就已不见著录,这些非常宝贵的史料对我们今天整理古代典籍、辑佚唐以前的文献,具有极其珍贵的参考价值。
注文中引用了大量诏敕政令,其中唐以前的律、令、格、式近30种,唐代的数量更巨。单从开元五年至二十六年22年间就记载了69道敕文;其中二十三年22道、二十四年9道,二十五年15道,三年共记载了48道敕令,不仅使《唐六典》的史料更具有严肃性、权威性,也为我们研究开元年间政策法令的修改变化提供了非常可靠的史料依据。
(二)《唐六典》在历史编纂学上的地位不容忽视
《唐六典》的注既充分继承了班固《汉书》“地理志”、“艺文志”的自注体例和方法,同时借鉴了两晋南北朝时期裴松之、郦道元、刘孝标等诸家史注的优长,并根据实际需要注出了大唐典制完备的时代特点,内容丰富,方法多样灵活,充分体现了开元撰臣们的会通思想和创新精神。因而《唐六典》的注在历史编纂学上,独具特色,影响深远。
首先,《唐六典》首创注文与正文互为经纬、动态地记载一代典制的崭新记述方法。其独出心裁的自注体例,使注文与正文具有异曲同工之作用。它使该书突破了只“记一朝之故事”的断代时限,拓宽了专类典制的史料范围,使这部唐代职官制度专史实际上具有了综合性的典制通史性质。正如章学诚对史书自注的评价云:“夫翰墨省于前,而功效多于旧,孰有加于自注也哉!”[9]
其二,《唐六典》首创典制专著之自注体例。它开创了以注文溯源的史注新法,进一步完善了史书的自注体例,是开元以前史注之集大成者。对后世典制史的编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典制古今变化的溯源,对某些典制的解释说明以及评论的注释方法等。此后的典制专著,无论官修还是私撰,都仿效《唐六典》的自注,以解决必要的制度沿革流变及具体内容的阐释、补充等。而最受学界推崇的典制专著杜佑《通典》、马端临《文献通考》的自注,正是借鉴《唐六典》自注的成功典型。例如《通典》,曾有学者对该书之自注进行研究,并归纳成:解释词语、注明时间、标明避讳、申明选材标准、解释制度、存疑、古今变化、点出制度的起始和源流、考辨史料、补充正文、说明正文、附加评论等共12类[10],并概括总结为“征引已有注释的历史文献时,酌情将原注连同被征引的部分随文转录”和“自撰之注”两大类[1]。这种注释方法、形式乃至部分内容,很明显地是受了《唐六典》自注的影响。当然,《通典》是私修,且有明确的“经世”目的,因而其评论的分量和质量是官撰《唐六典》之注所不能企及的。其后苏冕之《会要》断代为制,利用自注进行制度溯源、补充史事经过、进行名物诠释的方法以及记载史料的全面丰富,同样处处都有《唐六典》自注体例的影子。
其三,《唐六典》的自注具有极强的操作性,此为官修国家政典自注的一大特色,此特色为私撰典制专著所不可替代。其后历代官修“会典”如《明会典》、《清会典》的注释都效法《唐六典》,足见《唐六典》自注对后世官修私撰典制专著的借鉴、启迪和影响。
当然,首创者难为工。《唐六典》之注并不是完美的,其最明显的不足之处有三:
一是注文中所叙沿革,涉及《周官》之处常多附会之说,如卷二“尚书吏部”的“五等之爵,盖始于黄帝”之类的注;还有如关于佛教、道教的注释中也不无附会之语。这或许与《唐六典》的编纂者禀承玄宗意旨,要借此书展示大唐典制完备、繁盛气象之目的所致。但是,正如陈仲夫先生的评价:“其注文中所叙沿革……自秦、汉而下则相当详实,多为后来杜佑修《通典》所本。”[7]
二是引用文献体例尚不规范。《唐六典》注中绝大多数的引文要么只有书名,没有篇卷名,要么只有篇名没有书名,更少标明作者;且引用书籍和篇章的名称也随意简称、省称,格式不统一。如注中用《周礼》的地方最多,但大多只写书名,没有篇名;要么就直接省称篇名,很少地方用《周礼考工记》这样全称的。又如《汉书·百官表》,常省为《汉百官表》,甚至直用《百官表》;而注称《汉仪》,不知是《汉旧仪》,还是《汉官仪》。如此等等,这都是由于撰修时间长,主持人、参撰者均数度易手所致,这也是集体修纂的弊病。
三是由于官修,因而注中虽有评论,然远不及后来杜佑的《通典》、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等书深刻、全面而丰富。这些则是御旨官修不可避免的通病。
尽管有如此瑕疵,但《唐六典》的自注在历史文献学、历史编纂学上的贡献、价值和地位仍是不可忽视的。本文在此只是作一粗浅探讨,还有待于专家学者们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以使其能更好地为今天的学术研究服务。
[1] 瞿林东.魏晋至隋唐的历史文献学[J].学术研究,2000(1):91-97.
[2]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六[M]//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湾: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3] 顾德章.东都神主议.[M] //徐松.全唐文·卷765.北京:中华书局,1983.
[4] 刘昫.旧唐书·卷199·徐齐聃传附[M].北京:中华书局,1986.
[5]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五十八·艺文志·史部·职官类[M].北京:中华书局,1975.
[6] 钟兴龙.《唐六典》撰修始末考[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6(3):8-12.
[7] 陈仲夫.唐六典简介[M] //李林甫.唐六典.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
[8] 韩长耕.关于《大唐六典》行用问题[J].中国史研究,1983,(1):84-92.
[9] 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三·史注 [M].北京:中华书局,1985.
[10] 曾贻芬.论《通典》自注[J].史学史研究,1985(3):1-10.
[责任编辑 位雪燕]
OntheAnnotationofTangLiuDian
XUShi-duan
(SchoolofHistoryamp;Culture,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The author studies the annotation ofTangLiuDianin aspects of content and form in detail. The annotation ofTangLiuDiannot only takes the advantage of self-annotation inHanShuand the annotation features of history of some historians, but also creates the new self-annotation method for the monograph of institutions. This kind of annotation develops and innovates on the basis of all annotations of records in history and data before Kai Yuan years of Tang Dynasty. Besides, the annotation ofTangLiuDianmakes the self-annotation style of history more perfect and greatly influence on the quality and perfection of the following self-annotation style of institutions monograph. It has an outstanding position and value in the historiography and philology.
TangLiuDian; self-annotation; to trace to the source; explain; historiography; philology
2012-06-05
徐适端(1949—),女,汉族, 四川省邛崃县人,教授,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中国古代社会史、中国古代妇女史、中国历史文献学的研究工作。
E-mail:zxj@hpu.edu.cn
①本文所用《唐六典》主要系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92年排印版。参以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日)广池千九郎校注、内田智雄补订、三秦出版社1991年影印本。
②章学诚《文史通义·外篇一·史篇别录例议》说:“史家自注之例,或谓始于班氏诸志,其实史迁诸表已有自注矣。”见《章氏遗书》卷7,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
H02
A
1673-9779(2012)04-047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