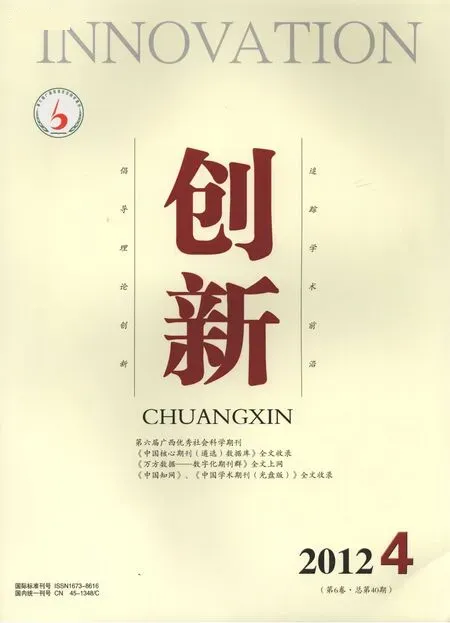“外儒内法”之再辩正
——以明代的法律实践为中心的考察
2012-04-01朱声敏
朱声敏
“外儒内法”之再辩正
——以明代的法律实践为中心的考察
朱声敏
我国封建王朝的法律实践,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都体现了依礼制法、以礼入法、以法护礼、以法行礼的原则与精神。明代的立法和司法两方面的法律实践都证明,“礼”是明朝统治者统治的最高准则与核心,从而进一步证明了我国封建王朝的统治是“外儒内儒”,而非学界一向认为的“外儒内法”。
外儒内法;明代;立法;司法
学界向来认为我国封建王朝的统治是“外儒内法”,即以儒家为表,行法家之实。笔者以为这种说法夸大了儒、法两家的对立,忽视了儒家对于法(或刑)的包容和统摄。2012年1月,笔者不揣浅陋,在《创新》杂志上发表了拙作《“外儒内法”之辩正》,[1]先辨析儒、法两家治国主张的根本差异,再阐述中国古代法的起源和指导思想,最后厘清情、理、法三者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以证明我国封建王朝的统治无论是治国主张还是治国实践均体现出以“礼”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也即是“外儒内儒”,而非“外儒内法”。为了将这一观点论述得更加清楚,笔者在本文中以明代的法律实践为对象,从立法、司法(执法)①中国古代行政与司法不分,故本文对两个概念不做区分,“司法”一词包含了现代“司法”、“执法”的内涵。两方面分析我国封建王朝统治中的儒、法关系。
一、明代立法——依礼制法、以礼入法
立法是法的运行的起始阶段。“立法”一词,在我国最早见诸战国时代,《荀子·议兵》就有“立法施令,莫不顺比”之语,此“立法”即为树立规范、制定法令条例之意,与现代语义接近。“立法”通常指特定国家机关依照一定程序,制定或者认可反映统治阶级意志,并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活动。制定法律的工作,早在上古就已产生,但古代中国并没有设立独立行使立法权的专门机构,皇帝(君主)便是最高立法机关,皇帝的意志对于法律的性质及功用,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秦朝推行法家学说,以吏为师,但二世而亡的教训使得后继朝代的统治者不得不在法家之外寻找新的意识形态作为施政的理论基础。在经历了汉初几十年的徘徊之后,汉武帝终于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从而使儒学上升为惟一的官方意识形态,儒家经义也逐渐渗透在法律制度之中。当时的儒生纷纷开始用儒家伦理来解说法典条文,用注释儒家经典的方式来注释法典,对汉初的法典进行儒家式改造。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儒生直接“以经立法”,当时的几部主要法典,如《魏律》、《晋律》、《北齐律》,无一不是儒家之作。《唐律疏议·名例律》开篇即云:“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两者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儒家经义的精神,俱以礼的名义渗入到了条文之中,考究《唐律》的法条来源,绝大部分可以在儒典中找到注脚,甚至《唐律》中的个别条文就是儒经的翻版。②参见徐晓庄《〈大明律〉之特点琐谈》,载《天中学刊》,2005年第1期。迨至宋、元,以经义立法、德主刑辅的精神以至律典的大部分内容总是一脉相承。正如《明史·刑法一》中所说:“自汉以来,刑法沿革不一。隋更五刑之条,设三奏之令。唐撰律令,一准乎礼,以为出入。”朱熹“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又在前代尤其是孔子政刑德礼的基础上,以“礼乐法制”体系阐述德主刑辅,从而使这一法律思想臻于完善。①参见肖建新《朱熹的德刑观新论》,载《孔子研究》,2006年第4期。
元朝末年,朱元璋投身于农民起义的行列,并很快崭露头角。在削平群雄和反元斗争中,朱元璋重儒任贤,朱升、刘基等儒士不但助明开国、兴学育才、制礼作乐,且与朱元璋讲说经史,使其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陶安对朱元璋“所陈皆王道,所论皆圣学”,[2](卷1《太祖纪一》)陈遇向朱元璋进“保国安民至计”,劝其“以不嗜杀人,薄敛,任贤,复先王礼乐为首务”。[3](卷135《陈遇传》)于是,朱元璋攻下金陵之后,即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并命陶安、詹同等人各发挥其所长,按照儒家学说,制定各种礼仪,其后又命李善长、刘基等遵唐律议定律令。[3](卷93《刑法一》)
可见,明律是在以唐律为蓝本的基础上删改修订而成。明初先后制定了《大明律》、《大明令》、《大诰》、《教民榜文》等法典,明中期又制定了《问刑条例》、《明会典》,这些都是明代最基础、最重要的立法。尤其是《大明律》,可与唐律媲美,也是中华法系自唐代形成之后,集古代社会后期法律之大成,在我国法律史上的地位很高。②参见张晋藩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第七卷,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其重要特点即是明刑弼教和以礼导民。“明刑弼教”一词出自《尚书》,③《尚书·大禹漠》曰:“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后人概括为“明刑弼教”。本是儒家的政治思想,与“德主刑辅”有异曲同工之妙。明代的刑、教与以往的德、刑在表述次序上确有不同,但没有根本区别,也没有改变德主刑辅的主次关系。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对刑部尚书刘惟谦说:“仁义者养民之膏梁也,刑罚者惩恶之药石也。舍仁义而专用刑罚,是以药石养人,岂得谓善治乎?”[3](卷94《刑法二》)可见其治国重礼的立法思想。
至于明朝建国初期朱元彰采取的重点治吏政策,用严刑峻法治贪④参见杨一凡《明初重典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是非常情况下采取的特殊措施,虽有些矫枉过正,但必须看到朱元璋重典治国的同时也讲轻法恤刑,强调先教后刑,基本上还是沿袭传统法律的德主刑辅思想。朱元璋曾批驳商鞅、韩非等法家代表人物的重典思想,“夫威以刑戮,而使民不政犯,其为术也浅矣。且求生于重典,是犹索鱼于釜,欲其得活难矣。故凡从轻典,虽不救其生,自无死之道”。[4](卷25,吴元年九月戊寅)即便是在胡惟庸案发生后,他仍向群臣谕示他将礼制视为强化集权的思想:“治天下之道,礼乐二者而已……有礼乐不可无刑政。联观刑政二者,不过辅礼乐为治耳……大抵礼乐者治平之膏梁,刑政者救弊之药石。卿等于政事之间,宜加此意,毋徒以礼乐为虚文也。”[4](卷162,洪武十七年五月庚午)
《明史·刑法一》评论曰:“始,太祖惩元纵弛之后,刑用重典,然特取决一时,非以为则。后屡诏厘正,至三十年,始申画一之制,所以斟酌损益之者,至纤至悉,令子孙守之。”与此相呼应,建文帝即位后,谕刑官曰:“夫律设大法,礼顺人情。齐民以刑,不若以礼。其谕天下有司,务崇礼教,赦疑狱,称朕嘉与万方之意”。[3](卷93《刑法一》)不难看出,这完全是孔子“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厂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思想的继承。《大明律》修成后,朱元璋曾告诫群臣:“朕仿古为治,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刊著为令。”[3](卷93《刑法一》)可见,《大明律》是在上述教刑观、德刑观指导下不断修纂完善的。
虽然历代律令的指导思想是儒家学说,但考究其具体条文,也随处可见德、礼的影子。如《大明律》首列二刑图,次列八礼图,朱元璋对皇太孙朱允炆解释这是重“礼”的表示。⑤参见(清)张廷玉《明史》卷93《刑法一》。正因如此,“礼”不但对明代律典的刑名、条款起着提纲挈领的作用,而且也是量刑的尺度。⑥参见杨一凡《明初重典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22页。为了严厉打击侵犯封建皇权、父权、夫权的行为,维护“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从南北朝开始出现“重罪十条”,稍后逐步演变成了隋朝“十恶”,明朝沿用其罪名,保留其内容。前代对老幼妇残在定罪量刑时给予特别照顾的“恤刑”制度,亲属相犯按照亲疏远近制裁的“准五服以制罪”制度,以及大赦制度,明代律典照单全收,鲜有改动。如
《大明律》中“殴大功以下尊长”条规定被殴者与殴人者越亲,殴人者所受的处罚就越重。①参见萧榕主编《大明律》卷20《刑律斗殴殴大功以下尊长》,《世界著名法典选编·中国古代法卷》,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772页。再如“不孝”一直被列入“重罪十条”和“十恶”之中,为了严惩不孝以弘扬教化,朱元璋在《大诰》中特别强调:“申明我中国先王之旧章,务必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5](《婚姻第二十二》)同样,也是为了弘扬孝道,“犯罪存留养亲”一条中规定:“凡犯死罪、非常赦所不原者,而祖父母,父母老疾应侍,家无以次成丁者,开具所犯罪名奏闻,取自上裁。若犯徒流者止杖一百,余罪收赎,存留养亲。”[5](卷1《名例律·犯罪存留养亲》)
儒家讲究“亲亲”、“尊尊”,主张有差别的秩序,封建法律的要务即要维护君臣上下、尊卑长幼的身份等级制度。汉代出现“上请”,魏晋南北朝时出现“八议”、“官当”,延及隋唐,形成了系统、完备的“议”、“请”、“减”、“赎”的贵族官吏特权制度。与《唐律》相比,《大明律》虽然限制了官吏贵族的特权,但是“八议”、“应议者犯罪”、“职官有犯”等制度和条文还是给予了官吏贵族不少封建特权,“亲亲”、“尊尊”的身份差别秩序仍得以维持,如“职官有犯”条规定五品以上官犯罪,有司必须奏闻请旨,不许擅问。②参见萧榕主编《大明律》卷1《名例律职官有犯》,《世界著名法典选编·中国古代法卷》,第774页。
此外,为了体现君父体恤臣子,反映统治者仁德治国的“恤刑”、“慎刑”思想,汉朝起我国就逐渐确立了录囚、死刑复奏、三司会审等制度,明代继承了这些制度,又新创九卿会审、圆审、朝审、热审等一系列制度,在形式上使“慎刑”思想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最后,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推崇“阴阳五行天人感应”之说,认为秋冬有肃杀之气,“天罚”必应合“天意”,否则将招来“天谴”,如汉朝的桓宽就曾指出“春夏生长,利以行仁;秋冬杀藏,利以施刑”。(《盐铁论·论茁》)为了与这种学说相吻合,汉代统治者规定春夏不执行死刑,除谋反大逆决不待时以外,一般死刑须在秋天霜降以后,冬天以前执行。③“秋冬行刑”制度的施行,统治者既可借以标榜“代天行罚”,同时也有“不误农时”的考虑。明代袭用了秋冬行刑的制度。
上文所举,足以证明明代律典的制作修订,与《唐律》、《宋刑统》一样,充分体现了明代法律实践中依礼制法、以礼入法、以法护礼、以法行礼的原则与精神。《明史·刑法志》论及《大明律》的总体精神,曰:“或间采唐律,或更立新制,所谓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者也。”[3](卷93《刑法一》)
二、明代司法(执法)——以法护礼、以法行礼
据学者考证,“司法”、“执法”二词,中国古已有之,为官署、官职名称。在现代法律语境中,“司法”指国家司法机关运用国家制定和认可的法律,惩罚犯罪行为,处理民事、经济纠纷的活动。“执法”,亦称法律执行,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照法定职权和法定程序,行使行政管理职权和实施法律的活动。鉴于古代行政与司法不分的情况,本文对这两个概念不作区分,将“司法(执法)”定义为:国家机关执行法令的活动。古代的立法活动体现了礼高于法、以礼入法、以法护礼,司法活动也是如此,其具体表现主要有“春秋决狱”、身份等差、情理法结合等。
汉代,董仲舒新儒学开始成为封建王朝正统官方意识形态,为历代王朝的法律表达和实践作出了最高的原则指示。在思想一统、儒家独尊的官方意识形态导向和精神追求的推动下,“以礼入律”拉开了帷幕。“以礼入律”的第一步就是“春秋决狱”。“春秋决狱”又称“经义决狱”,是指在司法审判中直接援引《春秋》等儒家经典精神或事例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在司法实践中,法官(行政官员)可以直接引用儒家的经义作为判断案件的依据。所谓“经义”即是儒家的最高道德准则“礼”,其在当时被赋予了“法理”的效力。“经义决狱”的基本原则是“论心定罪”,④也作“原心定罪”,见《后汉书·应劭传》,“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春秋繁露·精华》解释为:“《春秋》之听狱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恶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论轻。”即决狱时判定嫌疑人是否犯罪,依其主观善恶而定,而对主观善恶的认定则完全以儒家经义的精神为准则。
究其本质,“春秋决狱”是由儒生开创的一种在情与法之间寻找平衡的审判技术。中国古代的法律是典型的“硬法”,缺乏弹性,刚有余而柔不足。当法律制度的设计因为种种原因不能达致“善”的结果,就需要依儒家经典学说采取变通的办法。①参见梁治平《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6页。如乙与丙争吵打架,丙用佩刀刺乙,乙的儿子甲遂用棍子打丙,却误伤其父。对甲应如何处理?有人说甲应该因殴父论罪。《春秋》大义中有许止进药的故事,许止的父亲病了,许止给父亲喂药,父亲却死了。审案的君子原心定罪,赦免了许止死罪。到了汉代,董仲舒认为:父子至亲,儿子看见别人与父亲打架,拿着棍子去帮忙,并非有意伤害父亲,不应依殴父罪定罪处罚。[6](卷640)
无论法家还是儒家,都承认社会等级差异的存在。儒家肯定这种差异,孔子本人便是等级制度的支持者,其所向往和追求的“礼治”秩序其实就是宗法名分的等级秩序,他认为这样才是公平的秩序,且要维持这种差异的存在,就要施行“礼”。因为“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中庸》)。“礼”本身不是目的,只是用以达到“有别”的手段。“故先王案为之制礼以分之,使其贵贱之等、长幼之差、知贤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载其事而各得其宜”(《荀子·荣辱篇》)。儒家极其推崇“礼”,欲以“礼”为治世工具,极力提倡礼治。法家也承认社会等级差异的存在,但是他们对此持否定态度,认为贵贱、尊卑、长幼、亲疏的分别对治理国家有弊无利,主张去私任公,认为“亲亲则别,爱私则险,民众而以别险为务,则民乱”(《商君书·开塞》)。商鞅曾指出:“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忠君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守法守职之吏有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商君书·赏刑》)韩非子云:“法不阿贵,绳不饶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韩非子·有度》)这种不讲私爱,毫不通融,一断于法的精神,与儒家的“亲亲”、“尊尊”的主张截然相反。儒家从根本上否认社会是整齐平一的,认为人有智愚贤孝之分,社会应有贵贱上下的分野,家族中有尊卑、长幼、亲疏的分野,“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中庸》),“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滕文公上》)。
面对这一尖锐的交锋,深受儒家思想浸润的法官们似乎都毫不犹豫地倒向儒家一边,如朝朝著名的清官海瑞就说:“天下孰为重?德义为重。”[7](《下篇·其嗟也可去》)他坚持礼义是治国经邦之本,主张礼法结合。海瑞还提出听讼断狱的基本处理原则为依长幼尊卑而定,“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如果狱讼涉及钱财,则“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若涉及礼教,则“与其屈乡官,宁屈小民”。[7](《上篇·集兴革条例》)这种做法正是儒家道统的发挥,其目的就是要求任何人都遵守礼教,各安其位,以使国家太平、社会安定。
明代法律实践的另外一个重要特征,即情、理、法相结合。我国封建社会的法律又被称为“情理法”,或称为“伦理法”,道德教化的色彩非常浓厚。“上顺公法,下顺人情”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法谚,能否将情、理、法三者相融为一炉,往往是世人衡量法官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典故纪闻》记载了洪武时期的一个故事:
太平府民有兄弟相讦者,刑部请罪之。太祖曰:“兄弟骨肉至亲,岂有告讦之理?此因一时愚昧,或私妻子,争长竞短,怒气相加,遂至此耳。然人心天理未至泯灭,姑系之狱。待其忿息,善心复萌,必将自悔。”明日,二人果哀求改过。遂释之,合好如初。[8](卷 5)
在故事中,朱元璋接到报案后并没有立即依法处理,而是推测兄弟相互责骂,从情理而言,往往出于一时激愤,待冷静下来,必定会反悔。情理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它与中国传统的社会生态相契合,人们在行事时讲究以情待人,以理服人,总是力图找到一条平衡的中间路线,照顾各方利益,从而圆满解决问题。日本学者滋贺秀三考察古代中国的法律实践时认为,人情具有至高地位,“‘法’不过是得到了明确化和被赋予了强制性的‘情理’核心部分而已”。②[日]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王亚新等译,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页。情理,本质上与儒家的“礼”具有一致性,因为礼之产生,本于人的生理性情,出于对人的生存欲望和人的天性的把握。在中国古代听讼断狱中,以情理作为审判依据,其实还是“礼在法先”这一传统表述的客观落实,它表面上放弃的是法律,实质上得到的却是判决结果在更大范围内的可接受性及有效性。
关于情理审判,中国古代特有的“代刑制”不得不提,该制度至晚在汉朝已经出现,这是一种十分能体现儒家伦理道德内在价值的刑罚执行制度。所谓的“代刑”即子女或兄弟出于亲情孝义,自愿代犯罪的父、祖或弟兄接受刑法处罚,且这种举动常常会为政府所允许及褒扬,及对原应受刑者或代为受刑者给予特赦或一定程度的宽宥,这其中,“义”、“孝”承载的是封建礼教,是人伦大理。如洪武时期,山东青州有个卫卒,犯罪,被判处死刑,其妻到京城击登闻鼓,表示愿代夫受刑,朱元璋感其行而释其夫。①参见《明太祖实录》卷196,洪武二十二年夏四月丁卯。弘治年间,有女杨氏,其丈夫的兄弟被判死罪,杨氏丈夫念兄为嫡子,请代兄受刑。当时杨氏尚未及笄,也入京陈情,愿代夫受刑,结果夫妻一起获释。[3](卷321《列女一》)
三、结 论
由以上分析可见,自汉代以降,儒家在古代国家政治生活中取得了独尊的地位,一大批儒家礼义、道德原则及礼节仪式通过法典编纂的形式,被逐渐引入律中,从而使得法律儒化,明代的基本法律《大明律》即是一部在儒家思想指导下制定的法典,儒家的理念、原则、规则上升到了法律层面。在法律施行的过程中,由儒家知识分子扮演的法官引经决狱,推崇“论心定罪”,听讼断狱讲究贵贱之等、长幼之差,将情、理、法三者融为一炉。这些都与儒家礼治理想相吻合,体现了依礼制法、以礼入法、以法护礼、以法行礼的原则与精神。因此,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执法),我国封建王朝的法律实践都有力地否定了“外儒内法”之说,同时也证明了“儒”(礼)是我国封建王朝统治的最高准则与核心,它既是政治统治的外表,也是政治统治的内核,即我国封建王朝的统治是“外儒内儒”,而非“外儒内法”。
[1]朱声敏.“外儒内法”之辩正[J].创新,2012,(1).
[2][清]夏燮.明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2009.
[3][清]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明太祖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5]刘海年,杨一凡.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一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1994.
[6][宋]李坊,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7][明]海瑞.海瑞集[M].北京:中华书局,1962.
[8][明]余继登.典故纪闻[M].北京:中华书局,1981.
Argumentation on“Carrying out Foreign Policy in Confucius way and Domestic Policy in Legal Way”——A Study on the Legal Practice of Ming Dynasty
ZHU Sheng-min
The legal practice of China’s feudal dynasties,either in legislation or in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reflected the principle and spirit of drawing up the law in accordance with etiquette,enforcing the law according to the etiquette, maintaining the etiquette according to the law,and practicing the etiquette in accordance with the law.The legal practice of the Ming dynasty,either in legislation or in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showed that“etiquette”is the highest criterion and core of the administration by the rulers of the Ming dynasty,which further proved that the ruling in China’s feudal dynasties is“carrying out its foreign and domestic policies in the Confucius way”,rather than the long belief of“carrying out its foreign policy in Confucius way and domestic policy in legal way”in the academic circles.
K207
A
1673-8616(2012)04-0093-05
2012-05-14
朱声敏,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广西财经学院工商管理学院讲师(江苏南京,210093)。
[责任编辑:杨 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