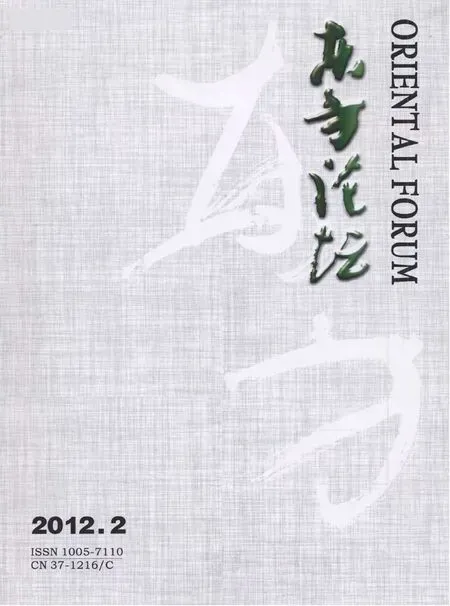自我启蒙·多元并存·面向世界
——为网络文学辩护
2012-04-01李钧
李 钧
(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自我启蒙·多元并存·面向世界
——为网络文学辩护
李 钧
(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如果说文学的本质是创造、想象与虚构,那么网络文学就是解放想象力、自我启蒙的文学;如果说20世纪是中国文学文体日益明确、细化和规范的时代,那么网络文学意味着跨跃文体界限并重新整合语体的文学新时代的来临。网络文学在形式、内容和审美追求三方面呈现出迥异于传统文学的新质,缝合了现代与传统、现代与后现代之间的断裂罅隙,破除了高雅与通俗、精英与大众等二元思维定势,确立了以市民文化为主流、以新传媒革命为界标的后现代艺术的牢固地位,也标志着融个性与民主、自由与开放、娱乐与审美于一体的后现代文学精神的诞生。
网络文学;新媒体革命;后现代文学
新事物总会让无知者、守旧者感到恐惧,令他们发出自扰之杞忧、陆沉之浩叹。当下就有一些评论者对狂欢化的网络文学予以蔑视、侮辱甚至全盘否定,但凡此种种只暴露出他们对后现代文学的短视与偏见。如果说拙文《网络文学:新媒体革命与“新新文学运动”》[1]侧重网络文学的“内部意义”,那么本文意在为网络文学辩污,从历史与社会学角度谈网络文学的“外部意义”。
网络文学:一个伪命题吗?
当下对网络文学的诋毁与指责主要有六种看法——
(一)“网络文学是垃圾!”
同济大学教授张闳说:“网络文学本身就是垃圾。网络写手写的东西本身就没什么价值……”[2]诗人叶匡政则在2006年就宣布:“文学死了!”[3]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可惜这种论断无视如下现实:初亮(笔名寅公)发表在红袖添香网站的作品《阳关古道苍凉美》成为“2008年全国高考语文试卷(卷一)”阅读考试材料,并被收入2009年8月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出版的中学语文教材[4];2009年大陆“网络文学十年盘点”,直接将前十名作品的作者吸纳为中国作协会员;2010年2月,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审委员会宣布,首次吸收网络文学参与评选……不知张闳教授、叶匡政先生对此做何感想?难道这些奖励都是奖给“垃圾”吗?他们在判语中都用了全称判断,而且像“先知”一样一厢情愿地宣判一个事物的“终结”、“垂死”或“枯竭”,这本身就是以偏概全的片面深刻,倒让人怀疑这是他们自我炒作的手法、制造眼球经济的话题。——我们固然不必做“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但也不必做一个“神经脆弱的抑郁症患者”!
(二)“网络文学是一个伪命题!”
青年评论家吕绍刚等人的此种说法是缺乏逻辑的。首先,“伪命题”是指不符合客观事实或不符合一般事理和科学道理的命题。网络文学早已成为一个不争的实存,而且表现出了与传统文学迥异的新质,评论者不能一叶障目,更不能视而不见。其次,如果说“文学就是文学,而无须添加前缀修饰”,那么按这种逻辑就不应有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外国文学等学科的存在。再次,网络文学是一个新事物,需要一个健全完善的过程。如果一个孩子刚出生,你就宣判他“死了”或是“一个伪命题”,那未免太过武断。人们对网络文学的认识也需要一个深化的过程,既使专家也不例外,比如欧阳友权2003年发表文章曾说:“网络文学作为网络时代的文学,技术的因素比历史上任何一种文学都要多,因而不仅容易出现‘只见网络没有文学’的现象,而且还容易导致文学的‘非艺术化’和‘非审美性’”[5],但欧阳先生现在主持着一项“网络文学”的国家课题,还在其任职的高校建立了研究网络文学的省级重点基地……也许网络文学今后的健康发展,会使持“网络文学是一个伪命题”观点的评论者改变态度。
(三)“网络文学很黄很暴力!”
对于网络文学的此类诬称最多,以致“针对目前网络文学存在的色情、低俗、暴力等问题,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正在进行调研,最晚将在明年出台有关网络文学出版服务管理办法,加强准入和内容管理。拟出台的办法将首先从规范网络文学出版网站入手,尤其是发布原创网络文学的网站。”[6]如此大动干戈,让人颇为诧异。
图7 为在室温和120°C温度下实验前后微滴的形貌图.可以看出,在室温条件下,微滴滑移前后形貌基本不变;而在120°C高温条件下,微滴滑移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形.此外,在实验过程中观察到,室温下树脂的形变可发生明显回弹,原因是E44环氧树脂作为热固性树脂,在刀口剪切力的作用下发生弹性变形,在作用力释放后又回弹到原来的形状;在120°C高温下,微滴在滑移过程中不仅发生弹性变形,还有塑性变形,释放作用力后难以完全回弹,产生了永久性变形.
只有了解文学的时代背景才能做知人论世的评论。只要翻检一下文学史就会发现:情色文学必是禁欲主义的产物或人性解放的武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以及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是地下情色文学的畸型发展时期。明白了这一点,才会理解柳鸣久先生编译“撒旦文丛”、把法国情色文学介绍到中国的意义,也才能理解网络文学中的“情色”原因何在。其次,情色文学作者往往“别有情抱”,如劳伦斯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中国的《金瓶梅》等。情色不是问题,问题是你从中读出了什么,正如鲁迅在《〈绛洞花主〉小引》中所说:一部《红楼梦》,“单是命意,就因读者的眼光而有种种: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再次,“屁股决定脑袋”,立场不同,对同一问题会得出不同结论。比如1929年“三民主义文学”批评家就认为创造社、太阳社的作品“很黄很暴力”,认为是一班颓废文人闭门造车的产物,作品内容不外乎“一,革命的:‘罢工,手枪,秘密会议,炸弹……’二,手淫的:‘性交,野鸡,女工,女招待……’三,颓废的:‘自杀,失恋,痛饮,花,树……’”[7]而当下的文学史绝不会这样评论创造社和太阳社。同样,了解网络文学的人都知道,情色描写只是其中极小的分子,何况木子美等人的“下半身写作”可算是女权主义的极端表达,不属于文学创作范畴。总之,网络文学有其内在发展规律,随着时间的大浪淘沙,某些不健康的东西自然会被淘汰,实在没有必要动用国家机器进行管制。——以“道德家”的话语去评说网络文学,真是不知文学为何物?!
(四)“网络文学远离现实!”
网络文学多玄幻、穿越题材,故有此断言。但是我们首先应明白什么是现实?是网络作者不想说现实?还是由于“管理”原因无法说现实?如果后者是中国文学面临的“现实”处境,那么何必别有用心地让网络写手去触摸高压线?!其次,新新人类的网络生活就是他们的现实。再次,与网络作者相比,传统作家才失去了“生活的根”:既失去了乡土又不懂得城市,陷在时代夹缝之中,处于尴尬难堪境地。近年来一系列的题材撞车事件正暴露出这一点:2005年“天涯社区”的一个帖子《李锐剽窃刘继明吗?!》称李锐的《扁担》(《天涯》2005年第2期)与刘继明《回家的路究竟有多远》[1](《山花》2004年第9期)情节雷同,有剽窃之嫌。事实上这两部小说都是根据一则新闻写成的,两位作家共同剽窃了“生活”。无独有偶,贾平凹的《高兴》(《当代》2007第5期)写农民工刘高兴背着五富尸体还乡,情节受凤凰卫视上一则“农民工千里背尸还乡”的新闻启发而创作;贾樟柯的电影《三峡好人》直接就是一个背尸还乡的故事……指责网络文学“远离现实、远离生活”的人应当对此慎思明辨。
(五)“网络文学=自动写作!”
这种指责源于2006年“诗歌写作软件”事件。2006年9月25日,一网友开辟“写诗网”,推出一款自己制作的“诗歌写作机”的写诗软件,声称只需输入几个词语,该软件就能自动合成一首“国家级诗歌”。短短十多天里,其注册会员超过4600名,并分成了后现代主义、浪漫主义、新鸳鸯蝴蝶派、自恋派等多个流派……虽然编程员说这只是娱乐或游戏软件,不应将这种“游戏”与真正的文学“创作”混为一谈,但反对网络文学的人却似乎找到了“网络写作=自动写作”的证据。
其实,任何一个清醒的评论者都不会对“写作软件”之类过分担忧。首先,“写作游戏”并不是网络“文学创作”。其次,这种“写作游戏”自己定位为娱乐,满足一些文学爱好者的心理需求,这至少比矫情的“梨花体”或余秋雨先生《含泪劝告灾民》之类“自渎式写作”好得多。再次,人们喜欢网络文学,缘于对当代中国文学的不满: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等模式化写作、“计划写作”的产物固然令人无法卒读,当下的严肃文学则既不能满足普通读者的需要,更未有可以获评诺贝尔文学奖的杰作,相反,人们看到的是体制化生产机制造成的文学堕落,大陆各种大奖的某些获奖作品令人感到莫名其妙。——坊间传说那是被权力部门“塞”进去的,而且每届评奖都会“预留名额”。那么,谁在左右着最终的评奖结果?官方扶植、专家评选与民众需要,哪一个标准更重要?这也正是人们渐渐对这些奖项的“权威性、公正性”发出质疑的原因。[8]至少,在网络文学中还未见这种“被导向”的事件,而且网络作者都知道网络是透明的,谁也不敢抄袭剽窃,反而强调自主的创造!
(六)“网络文学语言注水!”
网络作者为了多挣稿费而往作品中注水,这种现象不足为怪。首先,这是网络作者的活命之计。在中国最大的文学网站里,年收入10万元以上的签约作者仅有100人左右,其中年收入30万元以上的仅20多人,上百万元者仅10人左右。这个数字在签约作者总数中所占比率极小。[9]也就是说,以文学创作谋生绝非易事。但既然“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是人类的不二法则,那么“注水”以多得些稿费也无可厚非,读者的点击是最好的评判标准:如果写手注水过多,他就会被读者淘汰,因而没有哪个作者会冒巨大风险把作品注水到无味、得罪“上帝”的地步。其次,文学史上最杰出的作家也有过“注水”行为。比如香港现代主义小说奠基人刘以鬯在1960年代为了生存而沦为“写作机器”,“每天要写七千字,最多时竟达一万二。……我写连载小说,目的只在换取稿费。既已换过稿费,这些小说就变成垃圾了。是垃圾,没有理由不掷入垃圾桶。”“为了生活,我已写了六、七千万字的‘垃圾’,每一次别人称我‘作家’,我必脸红。”他还举了倪匡、崐南等“往往为生活而逼于无奈改写通俗作品”,“如现时以科幻小说畅销的名作家倪匡,26年前就写过一部正统文艺作品《呼兰池的微波》,是以内蒙古为背景的爱情小说,曾在他(刘以鬯)当年所编报刊连载,并出了单行本,但只卖了十本,其中八本还是倪匡自己买的。”[10](P12)中国网络文学在当下所面临的情形与刘以鬯当年的境遇相差无几,毕竟现在不是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中国网络文学才起步10年,大陆真正搞市场经济也只有20年时间。在这种转型期,让网络作家既养活自己又出精品,这是不人道的——那些拿着国家资助、养尊处优的专业作家写不出好作品,干嘛逼着网络作者出精品?!
人们通过以上分析就会发现:上述六种对网络文学的判词才是伪命题。我认为:网络文学是真正的自我启蒙的文学,而居高临下的精英文学多是灌输说教的制作;网络文学中包含着自由、民主、科学、法制与人的自觉,是“作为大众的写作”,而传统文学则多是主题先行、我注六经、“为百姓代言”的写作。我相信网络文学与米兰·昆德拉有相近的观点:“对我来说,成为小说家不仅仅是在实践某种‘文学体裁’;这也是一种态度,一种睿智,一种立场;一种排除了任何同化与某种政治、某种宗教、某种意识形态、某种伦理道德、某个集体的立场;一种有意识的、固执的、狂怒的不同化,不是作为逃逸或被动,而是作为抵抗、反叛、挑战。”因此,我愿做出如下预测:中国新文学的精品会出现在网络文学中,而不是体制化的写作中;文学精品会出现在自由竞争、读者第一的网络文学里,而不是被豢养的、粉饰虚伪的作家手里。
网络文学:后现代文学开始了!
任何试图拿传统文学理论与范式去约束和套用网络文学的评论者,都将面临失语,因为网络文学标志着多元并存、面向世界、跨语体写作的文学时代到来了。这种语境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多有神似之处。
网络作者多是“业余创作”,不受传统写作规范拘束。而检视五四时期的作家,就会发现他们大多非中文专业毕业,可说是“业余”:胡适最初到康奈尔大学学农学,最终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哲学博士学位;陈独秀是清末秀才,留学时先学英文专业,后入士官学校预科;李大钊毕业于北洋法政学校,在早稻田大学学习政治科;周作人最早学海军,后去日本学土木工程,又学政法、希腊文;鲁迅先后学过水师、路矿、医学;郭沫若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茅盾只读了北大预科就转到商务印书馆谋职;巴金毕业于成都外语专门学校,后投考北大未中;老舍只是中专毕业;曹禺初入南开大学政治系,一年后转入清华大学外文系;沈从文小学毕业,当兵五年,曾去北大旁听;张爱玲香港大学外文系肄业;钱锺书是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等等。但他们打破了中国传统“文章之学”的规范,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大师,他们以尝试的勇气与创作实绩建立了新的文学范式。这些经验使我们有理由对网络文学抱更大期望:如果说文学的本质是创造、想象与虚构,那么网络文学是最为自由开放的文学;如果说20世纪是中国文学的文体意识日益明确、细化和规范的时代,那么网络文学意味着跨跃文体界限、重新整合语体的文学创作时代的来临;网络文学将开启一场“新新文学运动”。
网络文学的“袪精英化”倾向,也与五四新文学本质相一致。钱玄同给胡适《尝试集》作序时说:“现在我们认定白话是文学的正宗,正是要用质朴的文章,去铲除阶级制度里的野蛮款式;正是要用老实的文章,去表明文章是人人会做的,做文章是直写自己脑筋里的思想,或直叙外面的事物,并没有什么一定的格式。”那么网络文学表明“文章是人人都会做的”,这有什么不好呢?!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提出八项主张: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须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烂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这八条改革意见是针对旧文学的腐败与堕落而提出来的,贯彻始终的基本观点是文学进化论,即“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那么我们可以说:网络文学的创造精神赓续了五四新文学精神,是当下的时代文学;它在网络上汲取世界的资源,因而意味着真正的“世界的文学”时代的到来;而随着电子书的出现,网络文学必将成为新文学的主流。
网络文学强调“表达的高度自由”,具有强烈的个性和非功利性色彩,具有自由、宽容、真实、平等的品格,有宽阔无比的向他人学习、向自我挑战的空间,有无拘无束、充分表达的民主权利,有多样化、创新性的语体形式……所有这一切都使网络成为“新新文学”发生、发展的策源地。尤其是网络新语体,必将打破古今中外的界限,使我们的文学语言在继承民族传统的同时走向创新和世界化;网络作者也将在与世界文明的沟通中,同构普世价值,消弭文明冲突,使人类变成一个真正的地球村。
网络文学是超越主客体关系的艺术生产。它强调互动性,强调不同主体(生产主体、传播主体、消费主体等)的协同参与,最符合接受美学;它强调生产、流通、分配、消费等环节的完整活动,这是最讲究市场机制的艺术生产。——如果说在此之前的中国文学是战争文学、计划文学、工具文学,那么网络文学是和平的文学、竞争的文学、多元的文学。
网络文学是属于市民社会的公共话语空间,它提供了宽广的、多元共生的中间地带。它不属于哪个阶级或权力机构,而是各种力量妥协的结果:妥协“是金色的,它不仅是美的,也是善的,真的。得到的是共同需要的东西,而将各自不想要的东西搁置一边,因此妥协的各方都是胜利者,没有失败者。在社会的两极之间,存在着一个非此非彼、亦此亦彼的中间地带,或者可以称作模糊地带。一切矛盾冲突都在这个地带通过交流、对话、较量、互相渗透、融合、转化……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另一种东西。这是一种合力作用的结果,谁也没有被吃掉,谁也没有被清算,可以说,中间地带就是促进妥协的地带,促进合作而不是分裂的地带,中间地带越扩大,两极地带越缩小,社会也就越稳定,越安全。”[11](P9-10)
网络文学标志着真正的后现代文学时代开始了。网络文学在结构、语言、题材、技术上最大程度地体现了随意性、未完成性和偶然性的后现代特征。其艺术结构无限开放,似乎处于永远的未完成状态;它抹平了生活与文本的距离,许多作品呈现出原生态品格,各种适合表达情感与思绪的文字、影像、音响都进入到网络文本中;文学的互动性在网络文学里得到了最完美的实践,网络文学读者由“被动的目击者”成为“合作的创造者”,那些集体创作的互动小说更使作者与读者的界限变得模糊;网络文学不仅弥合了现代主义高雅艺术与大众艺术的鸿沟,也破除了“高雅”与“通俗”、“精英”与“大众”等二元思维定势,确立了以市民文化为主流、以新传媒革命为界标的后现代文学的牢固地位,标志着集个性而民主、自由而开放、娱乐且审美等要素于一体的后现代文学精神的诞生。
网络文学的后现代精神还在于对各种“酷评”的漠视。网络文学作者知道:如果说真正的学术评论是以科学实证为前提的“学与思”的结合,那么“酷评”则是逞才使气的情绪批评,是以个人好恶为前提的粗暴批评,是疏于学理逻辑的印象批评,是詈街谩骂式的侮辱攻讦,是哗众取宠的话题炒作。“酷评”看似消解“宏大叙事”,实质上却不具备后现代主义精神,因为真正的后现代主义批评都具有明确的目标指向、衡定的价值标准、严谨的学术规范、宽容的共存态度,而“酷评”者操持的是冷战思维和二元标准,对网络文学的“酷评”也缺乏历史意识:他们处处拿“十岁的网络文学”与“百岁的新文学”作对比,并把传统文学未完成的使命如“审美性”、“艺术性”等都抛掷给网络文学,不免显得过分功利,仿佛要一个十岁的孩子去承担家庭重任或者要一只刚刚孵化出来的孔雀长出七彩翎羽。其实各位“酷评”者只要翻出自己十年前的作品就会发现:能够不“悔其少作”者实在寥若晨星,这就是变化。——既然任何事物都有一个成长成熟的过程,为什么不能用更宽容的态度对待网络文学?
尽管网络文学还存在种种不如人意之处,但网络文学已在形式、内容和审美追求三方面呈现出迥异于传统文学的新质:
穿越文体壁垒,消除僵化模式——文体解放;
建设网络语体,拆解语言套板——语体创新。
提倡中西融合,消弭文明冲突——普世价值;
追求古今贯通,缝合断裂伤口——本土元素;
致力自我启蒙,打破规训说教——人性自觉。
坚持自由身份,摒弃粉饰虚伪——真的情感;
倡导多元并存,反对一元独尊——善的宽容;
勇敢想象尝试,消解二元思维——美的创造。
网络文学的创新性成绩一定不止这“三纲”“八条目”,有识者可以补充我的观点。但若有人对我的上述观点质疑发难,请恕我不做回应,咱们不妨“走着瞧!”
[1] 李钧.网络文学:新媒体革命与“新新文学运动”[J].《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5).
[2] 钟刚,周思帆.网络文学十年:陷阱更多,秘密渐少[N].新快报,2007-03-29.
[3] 马赛客.叶匡政:文学死了,但我依然热爱它[J].榜样,2007,(8).
[4] 桑迪.盛大文学网络作品入选香港中学语文教材[N].光明日报,2009-08-14.
[5] 欧阳友权.网络文学:技术乎?艺术乎?[N].中华读书报,2003-02-19.
[6] 徐楠.网络文学将戴上紧箍咒[N].北京商报,2010-06-07.
[7] 绵炳.从“创造”说到“新月”[N].民国日报(上海),1929-02-17、24.
[8] 李钧.遗珠之憾与标准缺失[J].名作欣赏,2009,(2).
[9] 张黎明.市场化的黄金时代不等于最幸福的写作时代[N].北京晨报,2010-08-02.
[10] 潘亚暾.深孚众望的文坛翘楚刘以鬯[A].港台作家剪影[C].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89.
[11] 何家栋.灰色的民主和金色的妥协[A].亚当·米奇尼克.通往公民社会[Z].崔卫平译,内部资料,2004.
责任编辑:冯济平
Self-enlightenment, Pluralistic Coexistence and World-orientedness:A Defense of Internet Literature
LI Jun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China)
New things always make the ignorant men feel terrified. Nowadays some people contemn the Internet literature, but this only shows that they are short-sighted. If the essence of literature is creation, imagination and fiction, then Internet literature means the liberation of imagination and self-enlightenment. If the 20th century is an era of standardization of literary styles, then Internet literature means to break the style boundary and reshape the writing type. Internet literature can be called “post-modern literature”;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and modern literature in form, content and aesthetics. And “the spirit of post-modern literature” is an aggregation of personality, democracy, freedom, entertainment, aesthetics and openness to the outside world.
Internet literature; revolution of media; post-modern literature
I206
A
1005-7110(2012)02-0046-05
2011-12-28
李钧(1969-),山东齐河人,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现代中国文学与思想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