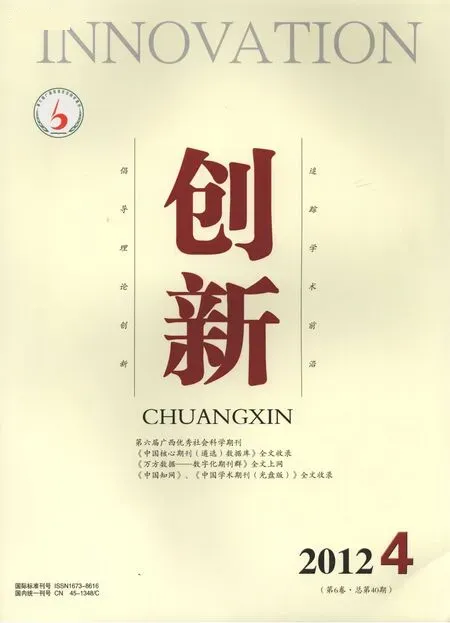中国文化现代性转型与世界意义上的建构
——兼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构建
2012-04-01章仁彪朱哲恒
章仁彪 朱哲恒
中国文化现代性转型与世界意义上的建构
——兼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族性和世界性构建
章仁彪 朱哲恒
在“现代性”的目标下,中国文化的近现代化转型是以批判和解构中国传统文化为主流。当代市场经济确立过程中,文化思想市场的建设滞后,文化创新与发展的紧迫性凸显。在当代文化的创新和发展中,应坚持传统与时代的结合、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西方文明在基本完成现代化的历程后,重新寻求“世界意义”的新路径时,将目光更多地投向中国文化智慧,这也是中华文化“世界意义上的建构”的时代性机遇。
中华文化;现代性;转型;民族性;世界性
在经济持续发展、物质文明成果不断累积、社会转型日益深刻的时代背景下,突出文化层面的建设,强调文化的社会功能,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既是对国内文化现状的自觉反省,也是基于国际文化交流的策略考量,更是构建融世界性与民族性为一体的时代新文化的战略性思维。中国现代化是以西方现代文明为主要参照的,相对于中国文化来说,现代化是一个舶来品,所以在文化的现代化过程中,在西方现代文化的外在冲击下,效法多于创新,虚无压过守成,极端者则鼓噪“文化的革命”。应该承认,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远未完成,文化的革故鼎新仍然没有过时。但中国文化的转型已从外在冲击阶段发展到内在转化阶段,文化建设中既要有文化自觉、文化自省,也需要文化自信、文化智慧。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文化建设要坚持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统一的原则,发掘民族文化的时代价值,构建新型的、有世界视域的民族文化,发挥优秀民族文化所应有的世界性影响力。
一、追求现代性:中国文化现代性转型的基本思想主题
在长达数千年的前现代时期,应该说中国文化是一个理论体系完备、思想特质卓异的自民族文化系统。这种以大一统帝国和官僚制度为基本框架,以制度化的儒家文化为凝结剂的自文化体系在东西文化碰撞的初始,留给西方的映像是“大汗的大陆”、“传奇的天朝”,是“理想国”的现实版本,即“孔教理想国”。然而,“孔教理想国”的中国形象的意义不在于其是否真实,而是西方文化自觉意识,表达的是对自身文明的不满,投射的是理想生活的一种乌托邦愿望。[1]423在这种启蒙性质的文化自觉中,西方文明开始了具有世界意义的文化再造,并最终导致了世界重心的转换,东西文化的民族性差异,演绎为时代性差异。工业革命开启了西方的现代化新时代,现代化以其巨大的势能,掀起了席卷全球的浪潮,人类社会的历史从民族历史阶段向世界历史阶段转进。某种意义上说,现代化的步伐与全球化的浪潮是相生相成的。在被迫纳进西方世界的叙事框架后,中国的神奇光环渐渐褪去,中国士大夫们也渐渐失去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相对于周边民族文化而言所具有的中心或主导地位,连自身的存在合理性都被重重地画上了问号。在西方进步大叙事中,中国文化的特征是停滞;在西方自由大叙事中,中国文化的本色是专制;在西方文明大叙事中,中国文化的标签是野蛮。作为现代性精神的最重要观念——历史进步观,成为现代性自我确证的基础,这种“今胜于古”的线性历史观,在空间表现形态则是“西方强于东方”的空间布展。在强势的西方现代性文化的冲击下,“历史悠久意味着历史停滞”,“荣耀也就成了耻辱”。[1]
中国文化近现代化转型的一个最突出特征是对现代性的追求构成了其基本的思想主题。徐光启、利玛窦等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者在16世纪就已经意识到中国文化没有发展出像西方文化那样严密的形式逻辑系统,开启了对西方现代性探求的步伐。鸦片战争之后,王韬、郑观应、康有为、梁启超等知识精英进一步强烈感受到了中西文化在注重智性方面的差异,开始尝试通过重新诠释,以凸显“智”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沿着这样的价值取向,五四新文化运动明确地以作为现代化之基本标志的科学、民主为旗帜,并成为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演进的基本精神方向,而尤以科学精神的显发最为突出。深深浸染传统的儒生们首开风气之先,对中国传统文化“弃之如敝屣”,感喟“变古愈尽,便民愈甚”,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等着眼于文化之物质层面的学习,到提出“统筹全局而全变之”,考器物背后的制度文化因素,倡议制度文化的创新,再到将文化转型的触角深入到精神理念,认为文化精神理念层面的觉悟是“吾人之最后的觉悟”,以“批判与革新”为主要特征的新文化运动成为汹涌的时代潮流。在对“科学”的热情拥戴后,作为“意识形态与科学的融合”的马克思主义日益作为科学的思想为人们所理解、接受和信仰。[2]63此间虽有激进与保守之争、科学与玄学之辩的“科玄之争”,科学、理性最终成为时代的最强音。及至当下,中国文化的转型仍在孜孜追求现代性目标。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三大主要社会思潮,虽彼此不无攻讦,但对“现代性”追求上保持着内在的一致性。作为社会指导思想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突出与时俱进为其理论品质,旗帜鲜明地追求现代化目标;自由主义思潮则旗帜鲜明地坚持彻底抛弃前现代的包袱,致力于促成中国文化的彻底现代化;20世纪中后期新儒家的兴起,有其浓厚的保守主义色彩,但基本主张是“按照‘现代性’的要求来重塑儒学之现代形态”,其区别于传统儒学的一个基本理想特质就是走向现代性。[3]422可以断言,现代性仍将是中国文化未来走向的基本指向标。
二、承继民族传统性:中国文化现代性转型的内在要求
如前所述,在西方强势文化的外在冲击下,中国文化可谓节节败退,成为贫弱、衰颓乃至愚昧的代名词。人们惶然发现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许多东西是与现代化相悖的。按照完备的、产生于西方的现代性价值系统来重新塑造“中国文化”的单向文化运动成为潮流。在对自身文化的批判和解构中,觉得中国的文化“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资不如人,不但机械不如人,并且政治生活道德都不如人”。[4]27愤激之至者将中国传统历史和文化的本质内涵归结为“吃人”。然而,无论怎样批判和解构,抑或是如李泽厚先生所说的“救亡压倒启蒙”的历史话语中,中国文化的近现代转型仍然承继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具有鲜明的民族性。
20世纪初西化最激进者莫过于胡适先生,其不无感慨地说:“凡一种文化成为一个民族的文化,其对内功能是抵御新奇风气的起来,对外能抵抗新奇方式的侵入。这是一切文化所公有的惰性,是不用人力去培养保护的。”[4]450他同时承认文化的“中国本位”,“应该虚心接受这个科技工艺的世界文化和它背后的精神文明,让那个世界文化充分和我们的老文化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借它的朝气锐气来打掉一点我们的老文化的惰气和暮气,将来文化大变化的结晶品中,当然是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那是毫无疑问的”。[4]452但胡适自身的经历却无法“摆脱传统的绝对给予,无力清理自己的精神家园”,在批判传统中成为一个颇具传统色彩的“书生政治家”,是“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5]李泽厚指出,从内在发展规律看,近代中国欢欣鼓舞地接受西方近代科学及其精神和方法,是中国传统精神在近现代的展现,是以人(人生)为中心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将“天道”与“人道”联接沟通起来的传统思维—行为模式的现代翻版,仍然是传统实用理性在现代的延续,即人们更愿意去选择企望解决现实的理性(现在是科学)来作为信仰和准则以指导生活。[2]57
在中国思想文化的近现代转型中,马克思主义思潮后来居上,成为一种在中国生根发芽的“全新的现代思潮”,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虽然在其早期曾经表现出某些“左”倾色彩,甚至提出过“与传统决裂”的口号,但无论我们如何评价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与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很多契合的理论构建,而不仅仅是适应中国近现代社会的特点和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实践性格非常符合中国人民救国救民的需要……重行动而富于历史意识,无宗教信仰却有治平思想,有清醒理智又充满人际热情。”[2]157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具有极鲜明的“中国风格”,毛泽东在阐述新民主主义文化时,将“民族的”放在首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为中国现代化转型中的主要文化支撑,以自己的方式推进中国文化的现代性转型。
文化传统是无法断绝的,无论是所谓的文化固有的“惰性”使然,还是文化承继者的文化自觉使然,当今世界的几大民族文明都有深远的文化根基和渊源。在现代化的语境下,民族文化必须是时代性的文化,具有世界性的话语,但文化又必须是民族性的,否则文化就是无源之水,离同化或消亡就不远了。
三、世界意义上的构建:坚持世界性与民族性统一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时代语境中,文化的发展转型就表现为时间维度上传统与现代的统一,空间维度上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在前现代社会,以市场经济和机器工业为代表的现代社会尚未兴起、人类统一的“世界历史”尚未形成之前,对于尚处于“自为”阶段的各个民族文化系统而言,其民族性表征明显,各民族文化的世界性内涵也只在本质意义上可以探究。然而建立在工业化基础上的西方文明,在世界文明进程中,首次“具有世界意义与价值”(马克斯·韦伯语)。西方文明由此开始成为非西方文明师法的样板,这种师法是在空间范围内演绎着从“前现代”到“现代”的时间逻辑。世界范围内的各民族文化所应具有的时代性特征就被归结为西方的“现代性特征”,西方现代文化所具有的民族性就表现为具有世界性示范意义的现代性。
然而以现代性为理想目标,以西化作为现代化之基本道路的“西方文化中心论”,在20世纪后期遭受诸多的质疑,尤其以后现代性的批判具有一定的颠覆性。在后现代思想家看来,“人们不再把现代性看作是所有历史一直苦苦寻求以及所有社会都应该遵守的人类社会的规范,而越来越视之为一种畸形”。“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我们可以,而且应该抛弃现代性,事实上,我们必须这样做,否则,我们及地球上的大多数生命都将难以逃脱毁灭的命运。”[6]文化发展的困境往往是文化新生的契机,后现代对西方现代性的颠覆性批判,为那些非西方文化重新思考人类文化的现代历程,并在此基础上谋求更为健康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理论空间,为发掘非西方文化中不尽同于西方文化的思想资源贡献于当代人类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这正是为我们当下重拾“文化建设”话题的“战略机遇期”。
从中国文化转型的现代化诉求的主题看,后现代主义的兴起及其现实影响无疑复杂化了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存在境遇。就中国文化自身建设而言,当中国文化还没有全面享受现代化积极成果时,西方则已对现代化的弊病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这样,前现代、现代、后现代这些在西方历时性的文化现象,在当代中国以共时性的形态被挤压在一个平面上。中国文化的发展因此陷入了两难困境:一方面,由于“现代”阶段的不可逾越性,当代中国文化没有理由轻言解构和颠覆现代性,从而终止走向现代化的历史的进程;另一方面,就人类文化面向未来的发展动向而言,现代化又处于被批判、被超越的地位,我们无法回避对现代性的反思。而这种反思的一个很重要结果或取向就是对中国“和合”文化的重视,对“东方模式”、“亚洲价值观”的重新估量。在此背景下,构建民族性与世界性统一的时代新文化就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构建面向新世纪的中国文化,首先必须有文化自信,切实挺立民族文化精神的主体性。在西化思潮盛极之时,我们往往对自己的民族文化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态度,试图以全新的异域文化取代“陈腐”的本邦文化,结果在传统与现代、前现代与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张力场中,无所适从,失去了方向。因此,挺立中华民族的主体文化地位,发掘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价值,同时按照“为我所用,以我为主”的原则,以主动、自觉、开放的心态审慎融会异域文化资源是成功构建面向21世纪文化的理论前提。如果说汤因比、李约瑟等西方学界泰斗倡导人类文化向中国文化复归还是某种个别预言的话,当代美国哲学家理查·罗蒂的态度已代表了当代西方思想文化界对中国文化的一般态度了:“在一切非西方的文化间,中国的文化无疑是最古老,最具影响力,也是最丰富多彩了。人们或许因此而可以希望,在西方理解自身过程中最近发生的变化,将有助于西方知识分子从中国方面多多获益。”[3]447其次必须立足于综合与创新。对于中国而言,尽管现代化有不尽如人意的弊端,但在相当程度上代表了人类文化前进的方向,我们没有理由丢弃现代化的目标,但同时必须对现代化的后果进行深切反省,从西方现代化中汲取警策,应当寻求一条即师法西方又在某种程度上超越西方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文化的近现代化伊始,我们对西方文明是“甘之如饴”,充分发挥了“后发优势”。当下中国的文化构建已进入“内在转化”的阶段,在整体上体现了一定的理论自觉。哈贝马斯断言现代性是一项尚未完成的事业,这方面,中华文化理应在构建成熟的现代化文化方面有所作为,在发掘中国文化传统所独具的优良民族特质、建立体现时代精神又具有充分的中国民族风格与做派的新型文化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现代化浪潮中,追求“现代性”是中国文化转型的思想主题,而当下,在全球问题凸显,全球治理的吁求日盛的时代背景下,在西方已走完现代化的历程后,当西方文明在寻求“世界意义”的历史路径,特别是1960~1980年代,在经历了一系列全球生态危机所带来的痛苦之后,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得到全球范围的共识,有人提出必须吸取东方“天人合一”的思想智慧,重新审视人类的主体意识,改变人类主宰自然的心态。和谐共存,逐渐成为全球范围内文化思考的方向,而有着显著“和”色彩的中国文化在这方面作为的理论前景很大。在这种意义上,坚持民族性与世界性的统一原则,构建面向新世纪的中华文明,就不仅是中国文化自身的转型问题,它同时也是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又一次“具有世界意义和价值”的文化建构。最近,已逾百岁的新制度经济学泰斗科斯先生在《财经》年会上致辞指出,中国的成绩令人惊叹,但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思想市场有待进一步发育,这也是中国经济诸多弊端的根源。只要重拾思想文化建设,假以时日,中国将成为“商品生产和思想创造的全球中心”。[7]
坚持世界性与民族性的统一是世界各个民族发展的共同旨趣。作为中华文化的当然继承者,我们没有理由在中华文化的“世界意义上的构建”中丧失应有的文化自觉。
四、构建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和民族性
作为当代中国具有主导地位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构建面向新世纪的具有“世界意义”的现代文化时,同样面临着世界性价值的构建问题,面临民族性和世界性的统一问题。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经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西化倾向,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20世纪中国的文化建设中也曾出现过重批判轻继承的问题。但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谋求一种新的、综合的文化形态是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一以贯之的基本文化主张。作为最早一批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就明确指出:“东洋文明与西洋文明实乃世界进步之两大机轴。正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缺一不可。而此两大精神之自身又必须时时调和,时时融合,以创造新生命而演进于无疆。”[8]这种主张在以张岱年、方克立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派那里得到了更为集中地体现。他们明确提出,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努力创造一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批判继承历史传统而又充分体现时代精神的,立足本国又面向世界的”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新文化。[9]
在近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永远在场”,并且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和时代价值,关键在于它坚守着自己原有的中国化立场和精神指向,满足了为当代中国现代化事业飞速发展和实现民族复兴而提供精神支撑这一最大的政治需要。“中国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特殊的时代立场和政治出口,而且也是它发挥重大政治效应和文化功能的根本途径。只有捍卫马克思主义研究的中国方向和时代立场,才能在与时俱进中保持政治上的清醒与坚定,并达到民族理性的自觉与成熟,从而从相对主义的无序纷争中解放出来,真正体现时代之重、把握文化律动、保持民族特性,在彰显其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同时不断提升其对民族精神的感召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使它的革命性、批判性精神作为普遍性的原则和方法全面贯彻于中华民族文化自我重构过程之中,从而成为民族精神之精华和时代文明之灵魂。[10]从现实上看,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以广泛传播以来,它早已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为一,并不断产生出真切体现马克思主义本真精神的民族表现形式。“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该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11]
另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发展,我们越来越感到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就不能准确地理解自己的时代精神和民族风格。但我们也同样感到,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和谐社会的新生活似乎存在着越来越明显的时空间距,在马克思已经做出的结论和推动人类最终解放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存在着一个裂隙。[12]在当代,如何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又使之获得民族性的当代表述,如何创建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主导文明,又赋予它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魂灵,如何彰显和谐社会建设的当代意识,又不被传统文化的负面影响蒙上眼罩,是一个具有两难性的理论悖论。一方面,时代精神的世界性在加强,因为新科技革命造就了使人类活动更加社会化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时代精神的民族性、国度的区别又很明显,因为各个民族文化都有其坚强的民族个性。一个不容否认的历史事实是,时代精神的世界性与民族性之间总是相互联系、相互丰富并不断趋于融合的,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成为现代中国革命发展进程中的指导思想,首先在于其思想体系本身赢得了世界历史的意义,并在“世界历史三大时代的每一个时代都使它获得了新的证明和新的胜利”。现时代也只有与时代课题保持紧密联系,以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构建思维坐标,才会真正显示出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力量。
人类文化的当代走势,昭示了中华文化在未来可能具有、也应当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和地位。这是民族文化振兴之必然结果,也是人类文明多元开放时代的理性选择结果。坚持文化的民族性与世界性统一,不断赋予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必由之路。
[1]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429.
[2]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3]李翔海.民族性与时代性——现代新儒学与后现代主义比较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4]欧阳哲生.胡适文集(4)[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沈卫威.自由守望:胡适派文人引论[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93.
[6][美]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M].马季方,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1.
[7]科斯.中国将成为商品生产和思想创造的全球中心[N].南方周末,2011-12-22.
[8]李大钊.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M]//忻剑飞,方松华.中国现代哲学原著选.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88:20.
[9]方克立.评“中体西用”和“西体中用”[J].哲学研究,1987,(9).
[10]朱荣英.马克思主义哲学本真精神的当代表述[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269.
[11]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534.
[12]胡大平.走出“后马克思主义悖论”——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教训及其启示[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3).
Modernity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Building of Cosmopolitan Significance—— On Discussion of Nationalit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Marxism and Building of Cosmopolitan Significance
ZHANG Ren-biaoZHU Zhe-heng
Under the objective of“modernity”,the mainstream of contemporary and modern transformations of Chinese culture is the criticism and deconstruction o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During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the contemporary market economy,the construction of culture market lags behind,and it is the urgent need to promote cultural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During the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culture,emphasis should focus on the combination of tradition and modernity,as well as the integration of nationality and cosmopolitan.After its transformation toward the modernization process,western civilization focuses more on the wisdom of Chinese culture during its exploration for new path to the“cosmopolitan significance”.This is also a time opportunity for Chinese culture to build its cosmopolitan significance.
Chinese culture;modernity;transformation;nationality;cosmopolitan
D61
A
1673-8616(2012)04-0021-05
2012-04-10
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专项任务《马克思主义民族性与世界性研究》(10J710031)阶段性成果
章仁彪,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上海,200092);朱哲恒,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200092)。
[责任编辑:潘丽清 实习编辑:冯 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