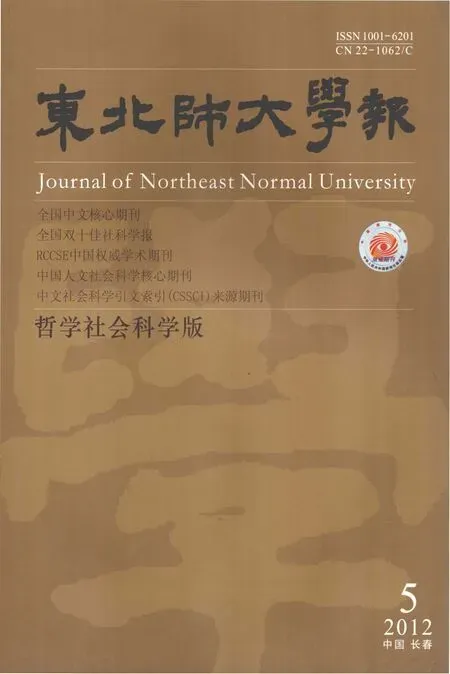祛魅的悖论:先锋文学的“精神真实”与“神秘主义”
2012-03-31李明彦
李明彦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130024)
祛魅的悖论:先锋文学的“精神真实”与“神秘主义”
李明彦
(东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吉林 长春130024)
20世纪80年代先锋文学的兴起,是以对现实主义文学话语的祛魅为旨归的。它以“精神真实”为旗帜发动了一场文学祛魅活动,以此反抗现实主义对“真实”解释的垄断权和意识形态霸权。然而,先锋文学提出的“精神真实”具有不可调和的自反性,最终导致在其文学创作实践中神秘主义的盛行。神秘主义的盛行反过来拆解了先锋文学努力建构“精神真实”,让这场文学祛魅行动呈现出悖论的一面:祛魅意味着赋魅,建构意味着解构。祛魅的悖论从反面显示出文学必须建立与现实、与世界、与大众的联系,才能让文学具有持久的和真正的生命力。
先锋文学;精神真实;神秘主义;祛魅;赋魅
一
西方现实主义文学的兴起本来是“祛魅”的产物,它与反对宗教神学和浪漫主义对文学的“赋魅”有关。现实主义代表着从巫魅中解放出来的理性化的人,获得自己理解世界、控制世界的主体性地位,“它(指现实主义)排斥虚无缥缈的幻想、排斥神话故事、排斥寓意与象征、排斥高度的风格化、排除纯粹的抽象与雕饰,它意味着我们不需要虚构,不需要神话故事,不需要梦幻世界。”[1]然而,现实主义的中国化的历程,却是一个政治权力对它逐渐“赋魅”的过程。在当代文学史上,现实主义文学和权力结盟,获得了垄断地位,是意识形态推崇并强制遵奉的、有着不可撼动地位的文学话语,因而它具有了“霸权”意义和“神性”光芒。这种带有巫魅性质的话语不可避免地给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带来“影响的焦虑”。在先锋小说家看来解决这种“焦虑”的必要手段就是对现实主义话语予以“祛魅”,建立先锋文学的话语系统。正像先锋小说家格非所说的那样:“在那个年代,没有什么比‘现实主义’这样一个概念更让我感到厌烦的了。种种显而易见的,或稍加变形的权力织成一个令人窒息的网络,它使想象和创造的园地寸草不生。”[2]格非的这番话代表了绝大部分先锋小说家对现实主义的认知态度。
“真实”是现实主义文学话语体系中一个核心的词汇,“崇尚真实在现实主义那里达到高潮”[3],真实甚至成了现实主义的代名词。现实主义的真实观,简要地说,就是不仅要如实地描写现实生活的外在表象,同时也要写出它的内在本质和规律。因此,现实主义真实观的立足点是现实生活,深层指向则是生活背后的本质和规律。但是由于政治权力的侵扰,所谓的现实生活、本质规律,往往是被意识形态化和象征化了的,政治权力垄断了对真实的解释权,这也使得现实主义的“真实”被人为地“赋魅”。因此,先锋文学提出“精神真实”来实现对现实主义的“真实”观念的“祛魅”,这种“祛魅”意在反叛意识形态对文学的规训。
“精神真实”概念的阐释主要来自于余华,“当我发现以往那种就事论事的写作态度只能导致表面的真实以后,我就必须使用一种虚伪的形式。这种形式背离了现状世界提供给我的秩序和逻辑,然而却使我自由地接近了真实。”[4]69精神真实意味着把判定真实的权力完全交给了主体,而隔离了与现实逻辑、日常经验、历史秩序的关联。在先锋作家看来,日常经验和现实逻辑在其发展历程中,附着了诸多的意识形态霸权和历史理性霸权,“这种经验使人们沦陷在缺乏想象的环境里,使人们对事物的判断总是实事求是地进行着”[4]66,它限制着作家的想像力,窒息了作家的才华,因而它对作家而言,是一个必须超越和反叛的对象。尤其是在当代中国,以“反映论”为基础的现实主义真实观,充斥着各种政治规训和历史诉求,对真实的解释,被人为地限定为对某种特定现实或理想的歌颂和赞美。先锋文学提出“精神真实”这一口号,显然是要对附着在“真实”上的意识形态霸权的一种“去蔽”。因此,对于先锋小说家而言,他们要做的不是要对这种意识形态化了的现实世界进行再现,而是深入精神世界,发掘被现实世界忽视的人类精神内核,精神真实才是文学应该追求的。对精神真实的强调,意味着解释现实权力的权威是作家而不是意识形态。因此,对现实生活表面的描摹和反映被先锋作家抛之脑后,作家具有无限的可能性和主动性,在精神真实的旗帜下,进行任何极端的文学实验都被视为是一种正当的、可理解的文学革命行为。
二
现实主义对真实的判断模式是以经验和理性为架构的,往往会把现实生活中种种复杂的心理情感、信念、妄语、梦境等被看作是非真实的,它们被看作是无意义的,如果说它们有意义,无非是把它当作一种叙事技巧——增加情节的跌宕起伏和可读性以及反衬出现实真实的一种技巧。先锋文学所宣称的精神真实,它否定了生活真实所提供的本质的、因果的、必然的、理性的、可知的认知模式,转而对内心精神提供的现象的、神秘的、偶然的、感性的、不可知的图景感兴趣。这种对“精神真实”的追求,在艺术上往往带来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拉康曾说过:“我们不能忘记,在历史上对真实的追求在精神领域里促动了神秘主义的兴盛、道德家的戒律、禁欲者的历程以及秘密祭礼祭司的发现。”[5]这也就意味着,先锋文学对生活真实的否定,对精神真实的追求,这种视角的向内转,必定会把精神导向超验的神秘之域,这也是先锋文学中呈现出鲜明的神秘主义色彩的缘由。
神秘主义的叙事风格,并不为先锋文学所独有。中国文学从来就不缺神秘色彩,从屈原的诗歌到六朝志怪、唐传奇、明清小说,都有神秘化倾向,这种倾向只不过在“五四”之后现实主义文学成为文学主流才有所改变。由于现实主义文学带有杰姆逊所说的“解神秘化”[6]的特点,它的一家独大并获得意识形态的支持一点点地压制了神秘主义的生存空间使之逐渐隐匿。先锋文学的神秘化倾向,既有本土的文学资源,也有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提供的养分,更有作家自身对“神性”等宗教的和对“自我”、“个人精神”、“非理性”等哲学的内在精神的把握,先锋作家“对于生活中那些物质性现实的真实性以及由理性所阐说的那些本质、规律、因果关系等持怀疑态度,大多把真实的问题归于‘自我’、‘个人精神’;……世界的构成变得无法描述与解释,一切都陷入真实与非真实的混沌中,从而使后新潮陷入更深的神秘主义之中。”[7]
先锋小说家大多数都是神秘论者。孙甘露曾直言不讳地宣称:“小说的刺激性、神秘性、不可索解性和新鲜的阅读经验就是他写作的目的。”[8]马原也曾把世界分为可以解析和无法解析的两个部分。他认为灵魂、思想、神学、哲学与艺术都属于不可解析,而他本人就是个“不折不扣的神秘论者”[9]189,马原不止一次说自己是泛神论者,还这样看待神秘主义和自己小说创作之间的关系,“宿命意识很早就渗入我心里,这也许是我最终成为小说家的关键”[9]167。作为先锋小说的先驱,马原在其小说中就惯常运用这种神秘化叙事策略。马原小说的故事背景都是发生在西藏,西藏作为世界上最具神秘性的地方之一,让马原的作品都染上了神秘色彩。在西藏这个大背景下,天葬、野人、转经、牧神、蛇阵、神秘的康巴汉子、宝物等都被马原一股脑地纳入到小说叙事中。
如果说马原小说的神秘主义得益于西藏这块土地的话,那么残雪小说中的神秘主义更多的来源于她童年的神秘性体验和湘楚大地的巫觋文化。残雪的小说中呈现的是一个异化的世界,幻觉的世界,这种异化和幻觉往往是人的变态心理造成的,因此,她的小说中的神秘化叙事带有一种荒诞感。《山上的小屋》姐姐胃里结出了小冰块,妹妹专以玩弄死蛾子、死蜻蜓为乐,整天像疯子一样到处乱窜,还有那能把自己孩子的后脑勺盯肿、窥视欲极强的母亲。《苍老的浮云》中,不停地喝椿树花熬的汤的慕兰,肚子里长满了芦苇的虚汝华,还有那像恶鬼缠身似地隔一两天就派一个秃头侄女给儿子送纸条的虚汝华的婆婆。残雪的这些小说带有极强的非理性和白日梦的色彩,她谈到自己的小说时也承认,“我是在一种无意识状态下创作的。但是这不是盲目的,而是在一种强有力的理性的钳制下进入无意识的领域和白日梦中。”[10]36残雪文本的神秘主义风格主要靠这些具有荒诞性的梦魇世界的展现而实现的。
格非小说的神秘风格依靠的不是故事本身的神秘性,更多地得益于他对意境与氛围的营造和叙述技巧的运用。前者我们可以看出格非深受废名小说的影响,后者可以看出博尔赫斯的影子。格非叙述故事的主要技巧就是“空缺”,各式各样的“空缺”在格非的小说中比比皆是。维特根斯坦曾把世界分为可说的世界和不可说的“神秘之域”,“不可说”就意味着存在着一种无法用语言填满的“空缺”的存在,神秘主义说到底,是因为存在着种种无法填满的空缺,导致了语言在面对世界无法做出有效的解释时的一种无能为力感。格非的小说中,正是由于有种种“空缺”,导致我们无法对文本做出有效的解释,从而造成一种神秘主义风格。在《迷舟》中,故事的关键性因素的空缺,造成了故事的不完整性,也使得文本的神秘性得到了加强。萧去榆关到底是去会情人还是叛变投敌送情报,这是一个关系着故事的展开和意义生成的一个关键性因素,然而格非却把它省略了,在小说《青黄》中,也存在这样的空缺。“青黄”作为一个词,它的本源意义在这篇小说中是空缺的。而“我”在填补“空缺”的同时,这种空缺却一再放大,变成一个更大的空缺,最后变成了找不到本源意义的神秘存在。这种有意的空缺技巧,引导读者去感受现实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神秘性。
余华的神秘化叙事总是和死亡、天命相连。生命是人类世界最大的神秘现象,人类对生命的诞生和逝去都充满着敬畏和沉思。尤其是死亡,人类的感性和知性对它都无法给予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解释,人类不得不以一种超验的神秘的姿态去看待死亡,这也为人类的玄思冥想、梦境幻觉提供了丰富的想象空间。在现实生活中,死亡往往会和一些偶然性因素相勾连,这也增强了死亡的神秘色彩。这种偶然性因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常常被表述为一个根深蒂固的神秘观念——天命相关。这种天命被解释为与人生息息相关,同时它又是超越的、神秘的和不受人为意志操控的。在余华的小说中,对死亡和天命的表现,让他的小说呈现出一种超验性的神秘色彩。《世事如烟》中,余华把生与死、现实与幻觉、偶然与必然糅合在一起,带有一种虚无缥缈的气息,呈现出一个神秘莫测的文本世界。在《难逃劫数》中,少年广佛被残忍地踢死,彩蝶的跳楼,东山对露珠的变态报复,这些人的死,除了阴谋和暴力外,文本中总是有意无意地向读者暗示,冥冥之中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主宰着人物的命运。在《四月三日事件》中,这种神秘性因素指向的是某种神秘的权威,这种神秘性权威带来的恐惧造成了四月三日事件。
三
先锋文学对“精神真实”的追求,最初目的是为反对被神性化和巫魅化的现实主义文学话语,是一种文学话语对另一种文学话语的“祛魅”。“精神真实”的提法蕴涵着对人的存在本相的追问,即人类存在的真实图景是什么。真是象现实主义认为的那样,人类通过理性的认知,通过对现实生活的再现,能够清晰地把握人类的存在真相?在先锋小说家看来,历史理性和经验常识都是不可靠的,现实主义的再现方式触及的只是表象,远远没有触及到人类生存困境的真实本相。只有破除现实主义的乐观,破除日常经验的藩篱,以一种虚无的突围姿态抛弃背负的历史负担和日常经验的禁锢,才有可能解释人类的存在本质。正如残雪所说的那样,“灵魂的文学的写作者以义无反顾的‘向内转’的笔触,将那个神秘王国的层次一层又一层地揭示,牵引着人的感觉进入那玲珑剔透的结构,那古老混沌的内核,永不停息地向深不可测的人性的本质突进。”[10]234也就是说,只有拒绝现实世界的生活真实,从主体的精神感知层面出发,才能够把握自身的自由状态,发现人性的本质。
先锋文学对“精神真实”的推崇,把它当作具有真理性和神圣性的文学观念,这本身也是一种带有“赋魅”意味的行为,而且,“精神真实”的内倾性导向促使神秘主义的盛行,神秘主义的出现意味着一种新的“巫魅”的出现。这也意味着先锋文学对现实主义文学的“祛魅”行为,在文学实践中逐渐变成了对自身进行“赋魅”的过程。神秘主义是人类最原始、最深层的情感,它也是对人类本质和意义进行思索的一种方式,并且是对意识形态化了的现实主义进行解构的有力武器,“神秘主义在当代人文思想中成为解构一切话语的力量、一切意识形态独断论的思想武器和诗性力量”和“解构西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思想力量”[11]。很显然,先锋文学提出的精神真实,无法拒绝神秘主义的侵入,尤其是精神世界的神秘性。实际上,精神的神秘性本身就是精神真实的内在诉求。
这就带来了先锋文学“祛魅”的悖论:先锋文学以一种强烈的反叛精神和解构倾向,以“祛魅”为目的反对一切对文学进行“赋魅”的活动,在这个“祛魅”的过程中,它所操持的武器是“精神真实”,这一观念又导致了神秘主义的盛行,“精神真实”变成了新的巫魅诞生的源头。这是先锋文学在高举“精神真实”大旗进行文学形式革命时所没有想到的。神秘主义的“赋魅”反过来是对先锋文学的精神真实的一种解构——既然先锋文学承认现实世界是神秘的,精神世界也是神秘的,神秘就意味着所谓的“精神真实”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世界和精神如果被冠以“真实”并能以文学的方式予以“真实地”言说,这说明主体对世界的解释和洞察有足够的信心,这就意味着没有神秘主义的生存空间。反过来说,既然先锋文学中神秘主义大行其道,这就说明先锋文学的“精神真实”是有问题的,因为只有“真实”难以达到的地方才会盛行神秘主义,先锋文学中大量神秘化叙事恰好反证了“精神真实”对世界解释的有效性是存在问题的。可见,神秘主义和精神真实之间既有相互助益之处,又有相互龃龉之处,精神真实导致文本中大量的神秘化叙事的出现,形成了先锋文学一种鲜明的审美风格;然而,大量的神秘化叙事对精神真实的构建并无多少助益,反而拆解了先锋文学努力建构“精神真实”,让这种祛魅行动呈现出悖论的一面:祛魅就意味着赋魅,建构就意味着解构。
先锋文学的“祛魅”运动有其历史意义,它对形式的解放和对人的生存困境的探索,拓展了文学书写的广度和深度。但这种以精神真实为旨归、以主观抽象化的方式把握现实显然存在很多弊端,“祛魅”的悖论也让先锋文学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既然先锋文学反对一切“赋魅”活动,是不是被“赋魅”了的先锋文学本身也属于“祛魅”的对象?那么这场文学的“祛魅”运动的终点又在哪里?因此,“祛魅”的悖论让先锋文学看起更象是一场没有终点的乌托邦游戏和自反性运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正是由于有这样的内在悖论,先锋文学在20世纪90年代不得不进行转型,重新走上现实主义的文学话语轨道,以一种回归的姿态对此前的“祛魅”活动进行调整。这似乎是一个历史循环的怪圈,实际上是艺术在经历否定之否定后的自我审视和自我修补。这也显示出文学必须建立与现实、与世界、与大众的联系,才能让文学具有持久的和真正的生命力。
[1]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M].丁泓,等,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230.
[2]格非.格非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35.
[3]南帆.文学的维度[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8:71.
[4]余华.虚伪的作品[J].上海文论,1985(5).
[5]拉康.拉康选集[M].褚孝泉,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73.
[6]杰姆逊.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A].比较文学讲演录[C].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33.
[7]王又平.新时期文学转型中的小说创作潮流[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139.
[8]王铁仙.新时期文学二十年[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219.
[9]马原.马原散文[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1.
[10]残雪.为了报仇写小说——残雪访谈录[M].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
[11]毛峰.神秘主义诗学[M].北京:三联书店,1998:403.
The Paradox of Disenchantment:the“Spiritual Reality”and“Mysticism”in Vanguard Literature
LI Ming-yan
(College of Literature,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Changchun 130024,China)
Vanguard literature which started in the 1980saims to the disenchantment of realistic literature discourse.It launched a disenchantment campaign in literature with“spiritual reality”as a banner,with the aim of fighting against the monopoly of the interpretation by realism and the hegemony of ideology.However,the“spiritual reality”advanced by vanguard literature has its self-contradiction,which leads to the prevalence of mysticism in the practice of literary writing.
Vanguard literature;Spiritual reality;Mysticism;Disenchantment;Enchantment
I206.7
A
1001-6201(2012)05-0148-04
2012-06-22
吉林省教育厅“十一五”社科规划项目。
李明彦(1980-),男,湖北荆州人,东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张树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