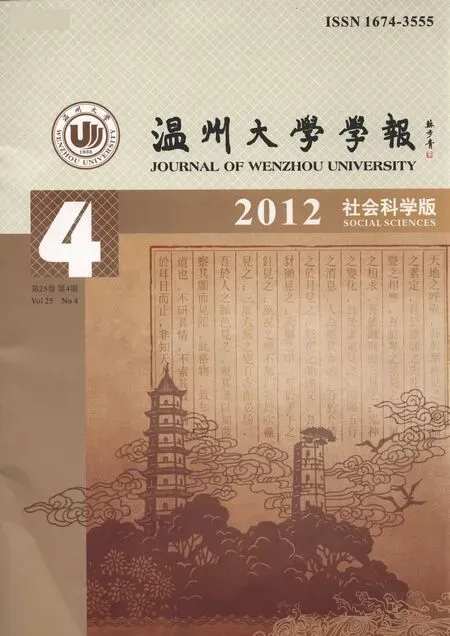刘向《列女传》简论
2012-03-19王守亮
王守亮
(山东轻工业学院文法学院,山东济南 250353)
刘向《列女传》简论
王守亮
(山东轻工业学院文法学院,山东济南 250353)
《列女传》作始于刘向,这从《汉志》著录、《汉书·楚元王传》、《列女传》文本、《说苑叙录》以及《论衡·超奇》等有关资料,均可得到直接与间接证明,因而否定刘向著作权的观点是不对的。《列女传》成书于成帝永始年间(公元前16年 – 公元前13年)。刘向以著述作谏书,企图劝谏成帝遏止后妃逾礼和外戚专权。在此意图下,刘向根据有关材料,有意虚构列女故事,从而使《列女传》具有了明显的小说性质,成为一部传记体短篇小说集,这实际确立了刘向作为小说家的文学史地位。
《列女传》;刘向;有意虚构
刘向(公元前79年 – 公元前8年),本名更生,字子政,今江苏沛县人,汉皇族楚元王刘交四世孙,历仕宣、元、成三帝,官终中垒校尉;于成帝时领校宫廷藏书,是西汉著名学者和文学家。刘向通达能属文辞,一生著述颇丰,流传后世的有《新序》、《说苑》和《列女传》等作品。以下就《列女传》的两个问题陈述己见,以就正于方家。
一、《列女传》作始于刘向
《列女传》是否作始于刘向一直存在争议。这一问题不仅关乎刘向著作权的确定,而且与《列女传》的文学史定位以及对汉代文学成就的评价相关,因此不能忽视。
在这一问题上,否定的意见认为,《列女传》是刘向校订,而非他所编撰。此论所据为刘向别录中的一段佚文,云[1]48:
臣向与黄门侍郎歆所校《列女传》,种类相从为七篇,以著祸福荣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画之于屏风四堵。
这段文字较早见诸《初学记》卷二十五器物部引用,明言《列女传》为刘向、刘歆“所校”,故有学者认为,刘向父子主要根据“著祸福荣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的意图,对《列女传》进行了校订。近人罗根泽就认为,《列女传》在“刘向时已有成书,已有定名,故刘向得读而校之,其非作始刘向,毫无疑义。”[2]在否定《列女传》作始于刘向的意见中,这种看法较有代表性。当今也有学者持类似意见,如聂石樵《先秦两汉文学史》认为,《列女传》和《新序》、《说苑》“皆刘向类辑先秦至汉初之典籍及民间传说而成,……因为不是刘向所撰述,便不作具体阐释”[3]。
然而,以上意见是不妥的,应当认真分辨。首先看《汉书》的有关记载。《汉志》著录《列女传》,同《新序》、《说苑》一样,明确说乃“刘向所序”[4]1727。《楚元王传》附《刘向传》亦载,刘向“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4]1957-1958。《汉书》记载说明,《列女传》是刘向采择包括《诗经》、《尚书》等在内各书所载列女故事,分类编撰而成,换言之,《列女传》作始于刘向。
其次,《列女传》虽以收录先秦列女故事为主,但同时也收入若干西汉当代女子的故事①历代公私书目著录《列女传》有七篇、八篇、十五卷(篇)等不同版本.北宋王回考订传文末有颂的篇章为刘向奏书, 定为八篇, 含传七篇、颂一篇, 题为《古列女传》; 后人续作的二十传则别为一篇, 号《续列女传》.王回的观点为后世所公认.南宋蔡骥将颂文附列女传文之后, 题《古列女传》七卷、《续列女传》一卷.今所见《列女传》各本即由此而来.本文以下所引诸篇, 皆出刘向《列女传》七卷, 不涉及《续列女传》.。卷四《陈寡孝妇》记陈氏妇少而守寡,事姑甚谨,淮阳太守上奏汉文帝,封为“孝妇”;卷六《齐太仓女》记汉文帝时齐太仓令淳于公少女缇萦救父故事。两则故事所记发生时间均为汉文帝时,且据《史记·扁鹊仓公列传》,知缇萦救父事发生在文帝四年(公元前176年)。卷五《珠崖二义》所谓“珠崖”为西汉郡名,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年)置;《郃阳友娣》所谓“冯翊”即左冯翊,高祖刘邦在秦内史地置河上郡,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更名为左冯翊②珠崖郡不见《汉书·地理志》, 据《汉书·武帝纪》, 元鼎六年定越地, 以为南海、苍梧、珠厓等九郡.左冯翊见《汉书·地理志上》.。虽然两则故事行文中并未说明故事的发生时间,但据“珠崖”、“冯翊”等地名可知,故事最早发生于汉武帝时。另外,卷五《京师节女》写京师称名曰“长安”,显然也是西汉当代故事。这些故事的发生时间与刘向的生活时代相当接近,如将这一点与《汉书》记载相参酌,则亦说明《列女传》成于刘向之前他人之手的可能性不大。这些故事很可能是刘向采自当代史料记载或故老传闻。
再次,刘向在领校宫廷藏书的工作中,并不排除校订自己的著述。《说苑叙录》云[1]47:
护左都水使者光禄大夫臣向言: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书,诬校雠。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者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後(按:当为“”)令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号曰《新苑》,皆可观。臣向昧死(谨上)。
这段文字中,刘向讲了《新序》、《说苑》和《百家》的编撰情况③参见: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 第3卷[M].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40-47.。刘向将《说苑》同已成的《新序》作了条目、内容的比对与整理,“除去与《新序》复重者”。这是刘向在领校宫廷藏书的过程中同时校订自己的著述。那么,《别录》佚文所说《列女传》的校订应当也属这种情况。且佚文说《列女传》七篇,而刘向本传称八篇,这一篇之差可能是刘向父子校订本和原著本的差别。
最后,王充《论衡》中的一段话亦可为刘向编撰《列女传》的旁证。《超奇》云:“儒生……或抽列古今,纪著行事,若司马子长、刘子政之徒,累积篇第,文以万数,其过子云、子高远矣,然而因成纪前,无胸中之造。”[5]在王充看来,司马迁《史记》与刘向的著作都采用了相同的撰写方式,即“抽列古今,纪著行事”、“累积篇第”而成其书。由此我们想到的是,历代以来,谁也不否认《史记》是司马迁的发愤著述,那么,《列女传》的著作权为何就不可属之刘向呢?
至于《列女传》的编撰时间,《资治通鉴》卷三十一将其系于汉成帝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近人钱穆附和此说[6]。然此说未明其据。1993年,江苏尹湾6号汉墓发掘出土了一批简牍,其中《君兄缯方缇中物疏》记有“《列女传》一卷”。据考,墓主的下葬时间在成帝元延三年(公元前10年)[7]。则《列女传》于本年之前即已成书。又,刘向《新序》、《说苑》分别成书于成帝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和鸿嘉四年(公元前17年)①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新序》条云: “《新序》, 阳朔元年上.”同卷《说苑》条云: “鸿嘉四年上之.”,而《列女传》的成书要晚于两者。因此,综合考虑,《列女传》可能成书于成帝永始年间(公元前16年 – 公元前13年)。
二、《列女传》有意虚构故事
刘向所以编撰《列女传》,乃出于西汉末年后妃逾礼和外戚专权的政治原因。《汉书》刘向本传云:“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4]1957因此编撰《列女传》。就写作意图而言,刘向企图借以劝谏成帝遏止后妃逾礼和外戚专权,从而重振暗弱的汉室。
写作目的决定材料的取舍。在组织材料、编撰故事时,刘向特别重视故事包含的“祸福荣辱之效,是非得失之分”,即故事的鉴戒意义和教育价值,而并不关心故事人物与内容是否真实可靠。这一点为后世一些学者所诟病。代表性的说法来自唐人刘知几。在《史通·杂说下·别传》中,刘知几指责《列女传》等书“广陈虚事,多构伪辞”,“故为异说,以惑后来”;列举《列女传》故事年世舛讹、事理附会等种种疏误,并云[8]:
案苏秦答燕易王,称有妇人将杀夫,令妾进其药酒,妾佯僵而覆之。又甘茂谓苏代云:贫人女与富人女会绩,曰:“无以买烛,而子之光有余,子可分我余光,无损子明。”此并战国之时,游说之士,寓言设理,以相比兴。及向之著书也,乃用苏氏之说,为二妇人立传,定其邦国,加其姓氏,以彼乌有,持为指实,何其妄哉!
文中所举之例,即《列女传》卷五《周主忠妾》和卷六《齐女徐吾》,本事来源于《战国策·燕策一》和《史记·甘茂列传》,均系无可考实的寓言故事。刘向因事发挥,增衍细节,刻画人物,使之成为首尾完具的传记体故事,读来恰如史上实有其事一般。从史学的角度看,这种“以彼乌有,持为指实”[8]的做法,严重违背了史书撰写的基本原则和要求——实录。所以,曾任朝廷史官的刘知几对《列女传》大为不满,认为刘向有意欺骗世人。
刘知几是一位严谨的史学家,既不能理解更不能容忍刘向的做法。但正如《汉书》刘向本传所表明的,刘向本来无意把《列女传》写成信史,因而也就谈不上“以惑后来”。刘向看重的是列女故事能够“戒天子”、“助观览,补遗阙”的鉴戒和教育功能,因而他根据写作意图的需要,整合有关列女材料,展开虚构故事,这实际上已经进入到文学创作的层面。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刘知几的批评之词,那么,其所关注的固然是史学的求实问题,但却同时表明了《列女传》有意虚构故事的文学创作特征。
先唐书籍的编撰往往两个措施并用:一是作者根据编撰目的,直接抄录旧籍;一是作者对既有素材进行加工与创作。《列女传》的编撰也属于这种情形。基于此,《列女传》有意虚构的文学特征可以从两个方面考察。一方面,它表现为不拒前人著作中言无根基的故事。如卷六《阿谷处女》,取自汉初韩婴《韩诗外传》卷一“孔子南游适楚”章,仅有文字小异。故事的真实性自然极不可靠,故久为儒者诟病。《孔丛子》卷四《儒服》篇云:“平原君谓子高曰:‘吾闻子之先君亲见卫夫人南子,又云南游过乎阿谷,而交辞于漂女,信有之乎?’答曰:‘……若夫阿谷之言,起于近世,殆是假其类以行其心者之为也。’”[9]刘向博学多识,并非不辨故事的荒诞虚无,他所以把它编选入带有褒扬色彩的《辩通传》中,重视的是阿谷处女言辞辩通、知礼守常的优秀品格。对比后妃逾礼、王教式微的现实政治,这则故事的鉴戒、教育之意不言自明。
另一方面,刘向根据既有素材,增衍情节,捏合人物,虚构故事,自主进行文学的加工与创作。这在《列女传》中是比较普遍的情形。上已述及的《周主忠妾》和《齐女徐吾》故事,即属此类。
再如卷六《齐管妾婧》,写齐桓公外出齐东门,听宁戚歌声而知为异人,遂使管仲迎之;宁戚赋诗“浩浩乎白水”,管仲不解其意,一连五日忧而不朝;妾婧询问得知原因,为释赋诗之意乃宁戚欲仕齐国;管仲以报桓公,宁戚因以为相,齐国大治。这则故事的素材分别见诸《管子·小问》和《吕氏春秋·举难》。《管子·小问》载[10]:
桓公使管仲求宁戚,宁戚应之曰:“浩浩乎。”管仲不知,至中食而虑之。婢子曰:“公何虑?”管仲曰:“非婢子之所知也。”婢子曰:“公其毋少少,毋贱贱。昔者吴干战,未龀不得入军门。国子挝其齿,遂入,为干国多。百里,秦国之饭牛者也,穆公举而相之,遂霸诸侯。由是观之,贱岂可贱,少岂可少哉?”管仲曰:“然。公使我求宁戚,宁戚应我曰:‘浩浩乎。’吾不识。”婢子曰:“诗有之:‘浩浩者水,育育者鱼。未有室家,而安召我居?’宁子其欲室乎?”
《吕氏春秋·举难》云[11]:
宁戚欲干齐桓公,穷困无以自进,于是为商旅将任车以至齐,暮宿于郭门之外。桓公郊迎客,夜开门,辟任车,爝火甚盛,从者甚众。宁戚饭牛居车下,望桓公而悲,击牛角疾歌。桓公闻之,抚其仆之手曰:“异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后车载之。桓公反,至,从者以请。桓公赐之衣冠,将见之。宁戚见,说桓公以治境内。明日复见,说桓公以为天下。
于是桓公力排众议,重用宁戚。汉初刘安《淮南子·道应训》也引用了这则故事。
《管子·小问》所写乃为家事——宁戚欲成家室,《吕氏春秋·举难》所写则属国事——宁戚欲仕齐国,事之大小不等,高低有别。在《齐管妾婧》中,刘向巧妙处理两则材料,将齐桓公、管仲、宁戚和管仲婢子四人以及本不相干的两个故事捏合到一起,加工改造成为管仲妾婧的一篇传记,重点刻画传主言辞辩通、才识颖悟的性格及其幕后为国荐贤的功劳。将管仲婢子与管仲妾婧相较,尽管她也言辞辩通,才识颖悟,但在所与事宜方面,究竟有着家事与国事的层次不同,故而形象上显得不如管仲妾婧那样高大可敬。这种形象上的变化和差别正是刘向精心结撰、有意虚构的结果。
《列女传》中类似情形尚多。通观《列女传》,刘向寄意笔端,虚构传主,造作故事,表现出明显的有意虚构的用心。在先秦两汉文学史上,有意虚构的风气肇自枚乘、司马相如等人。《七发》、《子虚》、《上林》等汉大赋,虚设宾主,假设其事,自觉运用虚构的文学手段,这被有的学者视为文学自觉时代的起点①参见: 龚克昌.中国辞赋研究[M].济南: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3: 89-92.。刘向是汉赋的重要作家之一,《汉志》著录“刘向赋三十三篇”[4]1748,其赋作数量居于西汉赋家前列。对于汉赋的虚构手法,刘向自然了然于心,亦必深有所悟。在编撰《列女传》时,刘向借鉴汉赋的创作,有意虚构列女故事,也就不足为奇了。
有意虚构故事是近代小说文体的首要特征。在这个意义上,刘向有意虚构故事,因而使《列女传》在史传的外衣下而获得了小说的实质,成为一部表现列女性格和形象的传记体短篇小说集。固然,刘向并没有如唐人那样“有意为小说”[12],但在客观上,《列女传》奠定了刘向作为小说家的地位,因此,在古代小说史的研究中,刘向应该占有一席之地,我们是不能忽略他的。
[1]刘向, 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 七略佚文[M].邓骏捷, 校补.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2]罗根泽.古史辨: 第4册[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228.
[3]聂石樵.先秦两汉文学史: 下册[M].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806.
[4]班固.汉书: 第6册[M].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5]黄晖.论衡校释: 第2册[M].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607-608.
[6]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M].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1: 49-50.
[7]连云港市博物馆.江苏东海县尹湾汉墓群发掘简报[J].文物, 1996, (8): 4-25.
[8]刘知几, 浦起龙.史通[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8: 378.
[9]孔鲋.孔丛子[M].影印本.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40.
[10]姜涛.管子新注[M].济南: 齐鲁书社, 2006: 372-373.
[11]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 下册[M].上海: 学林出版社, 1984: 1311.
[12]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6: 71.
Brief Discussion on Liu Xiang’s A Manual for Women’s Virtue and Moral
WANG Shouli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Shand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Jinan, China 250353)
A Manual for Woman’s Virtue and Moral was written by Liu Xiang.It could be directly and indirectly proved by several pieces of materials, including History of Han Dynasty, Biography of Chuyuan King of History of Han Dynasty, texts of A Manual for Woman’s Virtue and Moral, Art and Literature Record,and Collection of Stories and Chaoqi of Lunheng.So it was wrong to deny the copyright of Liu Xiang.The book was written during Yongshi yeas (16 BC – 13 BC).Liu Xiang tried to remonstrate with Emperor Cheng about those imperial queens’ improper behaviors and their relatives’ seizing on power.With this intention, Liu Xiang deliberately invented the story on the basis of some materials.As a result, the book became a biographical collection of short stories, which consolidated Liu Xiang’s status of writer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lassic literature.
A Manual for Woman’s Virtue and Moral; Liu Xiang; Deliberate Invention
I207.419
A
1674-3555(2012)04-0048-05
10.3875/j.issn.1674-3555.2012.04.009 本文的PDF文件可以从xuebao.wzu.edu.cn获得
(编辑:刘慧青)
2011-06-01
王守亮(1971- ),男,山东昌乐人,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