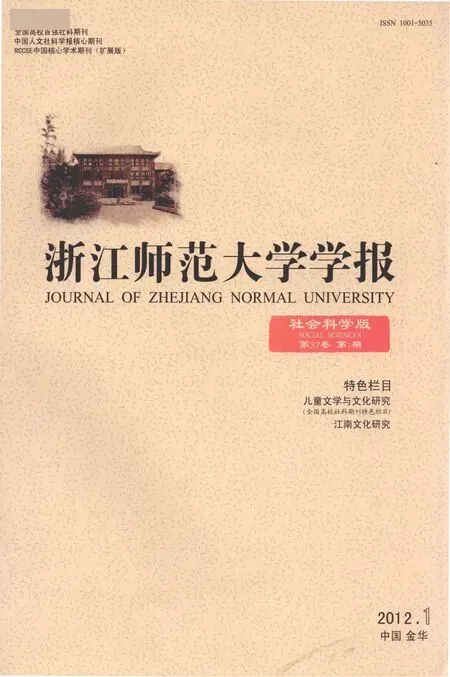文化与诗学的互构
——“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之辨*
2012-01-29李圣传
李圣传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 100875)
自20世纪90年代以童庆炳、刘庆璋、蒋述卓为代表的文学理论家提出“文化诗学”的理论构想以来,这一新的文学批评方法已经走过了近三十年的历程。在此期间,“文化诗学”研究无论是在学理的建构上,①抑或是批评的实践上,②都取得了一系列丰富的成果,极大地拓展了文学实践的批评视域,也将文学理论推向了一个新的理论格局。
然而,今天各种此起彼伏的社会文化现象似乎仍浓厚地萦绕在艺术的周围,也包裹着文学。在纸质、电子、媒介逐渐向“读图时代”位移中,日常生活的审美化也渐向影像化、视觉化、消费化的向度靠拢,大众文化的受众总量在“电信时代”中仍然有增无减。文化研究也在新的时代潮流中演绎得轰轰烈烈,保持着一股坚挺而旺盛的态势,一步一步地挑衅着传统精英文学的生存空间。众所周知,“文化诗学”提出的一个重要时代语境正是针对泛文化研究的“拨乱反正”。可惜的是,在今天的文学研究中,不少学人似乎仍无意识地陷入一种“文化研究”与“文化诗学”研究相混同的两难境地,盲目地标举着“文化诗学”的旗帜,甚至简单地直接将“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等同起来。那么,究竟“文化诗学”是什么?“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之间究竟存在哪些差异?解答这几个问题对于当前学界所提倡的“文化诗学”研究和文学理论自身的健康发展就显得极为重要。
一、“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殊名异义
所谓“文化诗学”(cultural poetics),就是从文化的角度出发,在宏观文化语境与微观文本细读的双向拓展中对具有文学性的文本进行批评,它既立足于当代本土现实,又积极从传统诗学和西方话语中汲取营养,在化合中西后形成新的话语体系,是一种沟通古今、连接中西又关注当下的批评方法。它是在文化现象广泛蔓延、学科边界不断模糊、人文精神日渐缺失、新理性精神急需提倡的现实语境下破土而出的。显然,“文化诗学”是一种方法论层面上学理范畴的思考,是一种对具有文学性意义的文本进行阐释研究的批评方法和策略。
“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则有着不同于“文化诗学”的更为复杂而庞大的含义。有学者认为,文化研究“是一种新的研究文化(the study of culture)的方式。许多学科——其中主要是人类学、历史学、文学研究、人文地理学及社会学——长期以来已把它们自己的学科关注带入到对文化的研究之中”。[1]而一般学术界提及的“文化研究”始于英国伯明翰大学1964年成立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其主要代表有霍加特、威廉斯及霍尔等人。中心成立之初是为亚文化族群,特别是个人阶级文化和青年亚文化族群作辩护,研究的对象也主要是阶级、文化及传播学,但他们对于文化研究的定义莫衷一是,或是“日常生活的文化形式和实践”、或是“文化与空间的关系”、或是“探究权利的形形色色,各不相同,包括性别、种族、阶级、殖民主义等等”、或是认为“文化研究是一个人们用来将他们对大众文化的迷恋合法化的技术性词汇”。[2]也许还是雷蒙德·威廉斯说得最精辟,他在《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派》一书中认为,文化研究对早期社会学的和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突破是从对作品的详细分析开始,但立场也是非常鲜明,那就是“以一种资产阶级经济作为先决条件,然后是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接着是某些复制了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文本”。[3]国内学术界的文化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其关注的主要对象是当下社会的各种热点问题,具有强烈的现实感和时效性,主要包括网络现象、时尚新闻、热门电视剧、流行音乐、选秀节目等等,无不纳入文化研究的视野。也正因如此,才有学者认为“迄今难以界定文化研究究竟是一门学科,还是一种方法,抑或是一个领域”。[4]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下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文化研究”,其指向的仍是日常生活文化、大众文化,它关注大众传媒、关注全球化、关注人的身份认同,展现的是与主流权利话语相对抗的质疑、消解和批判的立场。国内著名文化研究学者赵勇教授就认为“文化研究从它的诞生之日起,就在倡导‘穿越学科边界’的‘跨学科方法’(transdisciplinary approqch),也在积极地把文化研究打磨成一种进行社会斗争、从事社会批判的武器”。[5]
文化研究作为一门学科或领域,其开放性的批判是次要的,更为重要的是,文化研究是一种政治层面的强烈介入,是一种文化与权力关系的探讨,是一种对社会不良政治经济制度和操控舆论的坚决反击和批判。③
当然,“文化诗学”除了纯粹的作为一种学理的批评方法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强调现实的关注性。但与“文化研究”的泛文化性研究所不同的是,文化诗学关注得更多的是一种具有“历史—人文”张力的价值尺度。童庆炳教授就指出:“文化诗学的基本诉求是通过对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的文化解析,提倡深度的精神文化,提倡人文关怀,提倡诗意的追求,批判社会中一切浅薄、庸俗、丑恶、不顾廉耻和反文化的东西。”[6]童先生在《美学与当代文化讲演录》一书中更是犀利地指出:“文化诗学的基本诉求是什么?总的来说,就是要通过对文学文本和文学现象的文化解析提倡深度的精神文化、人文关怀、诗意的追求;批判社会文化中一切浅薄的、庸俗的、丑恶的、不顾廉耻的和反文化的东西。深度的精神文化,应该是本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与世界的优秀文化交融的产物,它追求意义和价值,那么这种深度的精神文化的主要特征就是它的人文品格:以人为本,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保证人的心理健康,关怀人的情感世界,促进人的感性、知性和理性的全面发展。”[7]刘庆璋教授也指出:“‘文化诗学’在‘诗学’前冠之以‘文化’,首先在于突出这一理论的人文内核,或者说,在于表明:人文精神是文化诗学之魂。”[8]在《走文化诗学之路——关于第三种批评的构想》一文中,蒋述卓教授也指出“文化诗学的价值基点是文化关怀和人文关怀,文化诗学的立足点是文化,但不能将其等同于文化研究,文化诗学要求文学的文化批评必须保持审美性”。[9]
可见,在学理内涵上,“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的差距是巨大的。“文化诗学”作为一种文学实践的批评方法,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该回归到文学文本的层面上来,而其指向又应该具有现实的人文关怀品格,具有积极的社会人生价值的精神导向功用。而“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商品经济时代背景下催生的后现代产物,其研究对象不再局限于传统的“经典”的精英文学,它更多的是对社会各种盛极一时、短暂即逝的新时尚、新现象及具有视觉和生理快感享受的大众化形式,表现出一种“有机知识分子”(organic intellectual)所特有的对社会政治体制问题的介入、质疑、消解和批判。
二、“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维度有别
“文化诗学”提倡的是一种深度的精神文化,要求在诗意维度的前提下进行文学的学理研究,所以“文化诗学”不仅具有审美的维度,并且其所指的“文化”也应该是符合“审美”这一内在特征的。同时,“文化诗学”是基于对文学语言的研究,强调文本语言的细读,因此“文化诗学”又应该具备语言的维度。所以,童庆炳先生将文化诗学归为三个维度,包括“语言之维、审美之维和文化之维”,[6]恰到好处地点出了以文学文本为轴心的诗学文本与审美文化之间的三维互构关系。
当下学术界以童庆炳、刘庆璋等老一辈教授为代表的学者对于“文化诗学”的长期思考,已经初步建构起了一套相对完整的诗学理论体系,其学理维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诗意旨趣和人文精神为内核的审美性为前提。这要求我们要用审美的观念来评判作品,如果作品经不起审美的评判,就不值得我们去批评了。
第二,“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双向贯通。我们既要警惕西方以政治研究或泛文化研究取代文学研究的倾向,也要注意防范因强调文学的外部研究就忽略内部研究的片面性,而要走向内与外相结合的综合整体性研究。
第三,文化诗学的立足点是关注现实。文化诗学就是要从文学作品中发掘出深度的人文精神和历史理性,以此回应社会现实,为文学研究探索出更为合理的研究路径和研究方法,求得学术的自身生存。
第四,跨学科的整体性研究品格。林继中教授指出,“整体性研究是文化诗学生命之所在”,“所谓整体性研究,体现在以宏阔的文化视野对文学进行全方位的审视,采用跨学科的方法,从人类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民俗学、经济学等诸多学科的视角观照诗学”,通过“打通”,“将这些不同学科视为一个彼此联系的整体”,“尽量全面地对产生该文学文本的历史文化母体进行修复,探索其生命的奥秘”。[10]
第五,注意文学与文化间互动、互构的研究。童庆炳教授认为,“文化诗学所要做的事情,就是恢复语言与意义、话语与文化、结构与历史本来的同在一个‘文学场’的相互关系,给予它们一种互动、互构的研究”。[11]
而“文化研究”作为一种后现代理论思潮,其研究的倾向也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1.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历史经典不同,文化研究注重研究当代文化;2.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精英文化不同,文化研究注重大众文化,尤其是以影视为媒介的大众文化;3.与传统文学研究注重主流文化不同,文化研究重视被主流文化排斥的边缘文化和亚文化,如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阶级亚文化、女性文化以及被压迫民族的文化经验和文化身份;4.与传统文学研究将自身封闭在象牙塔中不同,文化研究注意与社会保持密切的联系,关注文化中蕴含的权利关系及其运作机制,如文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5.提倡一种跨学科、超学科甚至是反学科的的态度与研究方法。”[12]
对比“文化诗学”与“文化研究”在学理维度和研究方法上的差异,我们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文化诗学”是基于学科品格的前提基础上而言的,是一种文学文本与文化之间互涵互构的研究,并且其文化应该是一种积极的具有诗意审美维度的精神文化;而“文化研究”则是对日常生活文化、大众文化,包括各种流行文化、消费文化的研究,它可以是日常生活的美学研究,也可以是泛文化研究。与传统的以文学文本为中心的批评模式相迥异的是,文化研究显现出一种积极介入社会的政治热情。
三、文化诗学:“诗学”与“文化”的双向互构
“文化诗学”既然谓之“诗学”,首先就说明它不是泛文化研究而是要强调其学科的审美内涵;而同时又在“诗学”前冠之以“文化”,也表明了其文化视野的维度。所以,“文化诗学”应该是一种“审美诗学”与“文化研究”的双重整合,既具有诗学旨趣的审美之维,又应该具备历史的文化维度,两者相互补充、相互建构。
基于此,“文化诗学”可以而且应该从两个不同的向度来对文本进行阐释研究:其一,研究文本中的文化,即应该重视文学文本与文化之间的互涵互构关系,将文学文本置于历史文化语境中来研究,揭示文本遗忘于历史时空中的原始文化遗迹,激活传统;其二,研究文化中的文本,即应该研究当下日常生活中各种鲜活的具有文学性的文化艺术形态,包括具有文学色彩的短信、文字图像、甚至更具时尚性的“微博语言”,关注现实。
(一)“文化诗学”是文学的文化研究,是诗的文化学,即:应该研究文本中的文化,重视文学文本与文化之间的互涵互构关系,激活传统。“文化诗学”研究的入手处就在于重建历史文化语境,强调“对知识与意义的双重关注”、“在文本与历史之间穿梭”。[13]只有将文本置于历史文化语境中,我们才能挖掘出蕴含在历史文本中的文化意蕴来。尤其是在“诗经学”研究中,通过历史语境的重建来追问历史的真相就显得越发必要。然而,离开历史文化语境的架空立论曾经却是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清儒皮锡瑞有言:“后世说经有二弊:一以世俗之见测古圣贤;一以民间之事律古天子诸侯。各经皆有然,而《诗》为尤甚。……后儒不知诗人作诗之意、圣人编诗之旨,每以后世委巷之见,推测古事,妄议古人。故于近人情而实非者,误信所不当信;不近人情而实是者,误疑所不当疑。”[14]由此不难想象,对于历史文本的研究,我们若是脱离具体的文化语境,缺乏“关联性”的比较思维,不去借助互文性的文本将对象置于时代的“坐标体系”中去,我们就很难追问到历史的真相。
《庄子·天下》篇是我国最早的一篇反映学术思想的珍贵文献,其中在论述到“道术”与“方术”相分离时,有云:“天下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15]现在,暂且不去考证《天下》篇是否出于庄子之手,我们来分析“道术”与“方术”究竟是指代什么意思?“道术将为天下裂”这一“裂”字又该如何理解?是“分割”、“分裂”的意思呢,还是“破坏”的意思?要想回答好这一个问题,仅仅回到文本是很难得出正确答案的。首先,仅从文本上下文来看,我们似乎读出:世间的万事万物过去都源于一个统一的混沌的整体,那就是道,随着天下大乱,贤王不显,道德分岐,把古人完美的道德弄得支离破碎,很少能具备天地的完美,相称于神明的容貌。所以,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抑郁而不发挥,天下的人各尽所欲而自为方术。因此,有王官之学、官吏制度,有百家之学,并且百家各行其道而不回头。后世的学者,不幸不能见到天地的纯真和古人的全貌,道术将被天下人割裂,真是可悲啊。从中我们似乎得出这样一个简单的结论:“道术”与“法术”成为了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这就造成了对文本的不合理的误读。而要正确合理地真正理解这种关系,我们就不能不回归到春秋战国时代的历史文化语境中,结合先秦的各种典籍文献,通过“互文本”关系,揭示其真正的内涵。下面我们就通过重建历史语境的方法,简单地对《庄子·天下》篇重新进行“文化诗学”的解读。
我们知道,春秋战国时期,王室衰微,在礼崩乐坏的局面下,诸侯国间战争、征伐频仍。在这场社会大变革、大动荡的局面下,士的阶层也应运而生。他们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地位虽然较低,但多有学问。由于出身不同,立场不同,因而在解决社会现实问题时,其政治主张也不同,因此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文中庄子所代表的正是道家的立场,道家追求的人生理想是“逍遥游”式的“绝对自由”。这种近乎无政府主义的放弃任何形式统治的理想,乃是庄子追求的“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的混沌世界。而现实却是“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这种礼崩乐坏的局面严重地破灭了庄子心中乌托邦式的自由美好的理想,所以他也感慨后世的学者,不能再见到天地的纯真和古人的全貌。在《应帝王》、《天地》、《天道》等文献记载中,同样可以明显地感知到庄子的这种原始混沌的自由政治理想,“天地虽大,其化均也;万物虽多,其治一也;人卒虽众,其主君也。君原于德而成于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无为也,天德而已矣。……以道观言而天下之君正,以道观分而君臣之义明,以道观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泛观而万物者应备……故曰,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记》曰:‘通于一而万事毕,无心得而鬼神服。’”[15]这里既讲“无为”,又讲“人卒虽众,其主君也”,但君臣万物,都应该顺应于一个统一的“道”,只有这样,才能“通于一而万事毕,无心得而鬼神服”,天下人人各守其职、各得其份。可见,在《庄子·天下》篇中,“道术”也应该是一种混沌的不可言喻的美好理想,是一种天下一统、君臣各守其职、人人自由洒脱的一种社会秩序的美好愿望。而这“破”也就应该理解为破灭,就是指这种道术也随着社会大乱而破灭了。
所以,通过这种在“文本、历史、文化语境”之间反复穿行的方法,我们就能更好地接近《天下》篇所要表达的真正内涵,也更能逼近历史的原貌,揭开文学文本尘封于历史遗迹中的神秘面纱。
(二)“文化诗学”是文化的文学性研究,是文化的诗学,即应该研究文化中的文本,研究当下日常生活中各种鲜活的具有文学性的文化艺术形态,关注现实。当下的文学在文化研究的冲击之下似乎正处于一种进退两难的矛盾境地。一方面要坚决护卫文学的永恒的神圣家园,一方面又要关注现实,而现实生活却总是与各种文化现象紧密关联。即使是我们所谓的“纯文学”作品,在当下这种高度发展的媒介语境中也难于“独善其身”,也是在不为人所注意的情况下经过编辑,出版社的反复包装、制作,各种插图、漫画、艺照渗入其中,一方面规训着人们对待文学的认知,一方面企图追逐更高的市场营业总额。④如此种种。毋庸置疑的是,传统印刷文化语境中单纯的文学研究在当下这种“语—图”关系复杂的视觉文化语境中已经是寸步难行了,很难建立起一套合法的行之有效的文学话语批评体系。
为应对社会文化发展带来的新挑战,文学理论家们开始思考“重划文学疆界”的合法性可能。陶东风教授曾极力主张“日常生活审美化”研究,他希望能通过拓展文学的疆界范围达到对各种新兴文化现象的批判。在其发表的一系列论文中,陶教授用跨学科的方法将研究视野伸入到广告、时尚、酒吧、博客、网络等大众日常生活领域,令人耳目一新。他指出,“审美化的意义在于打破艺术(审美)与日常生活的界限,日常生活审美化的学术关注并不意味着对它价值上的认可”,因此他认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化研究“大可不必把它排斥在美学文艺学研究的大门之外”。[16]学者欧阳友权将文学研究的视角伸向了时下极其活跃的网络现象——微博客(Micro-blogging)的研究,他认为:“在网络媒体的传播力日渐强大的今天,文学没有像希利斯·米勒所预言的那样被技术传媒引向终结,而是通过改变自身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把生存的空间向数字化生成的新边界延伸,微博客文学便是其中之一。”[17]
我一直认为,“文化诗学”既要关注纯文学的文本,也应该关注具有文学性的各种文学艺术形态,包括古典的“有意味的形式”的各种原始图腾,当下具有诗意审美的短信、博客、微博等等具有文学审美性的新兴艺术形态。
我们来分析下面这个句子:
……一生教书育人,两眼炯炯有神,三尺讲台情深,四海学子满门,五洲驾驭风云,六合天地爱心,七仙向往凡尘,八面玲珑机敏,九霄云外星辰,十分磊落光明,百尺竿头奋进,千秋大业兴盛,万古流芳美名,亿众爱戴尊敬,兆祥中华复兴,极致境界追寻。
这是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文学字眼呢?这是不是诗情画意的感情表达呢?这是不是就是我们所从事的美好的文学研究事业呢?回答者纵然有千百万个人,我敢保证99%的人会赞同我们的观点:那就是文学,因为那些句子都是用非常细腻的笔法,用饱含深情的基调抒写出了自己对于老师的赞美。而这些句子正是刊登在《中国教师报》上的2011年教师节“感念师恩”主题活动祝福短语征集评选的获奖短信。
文化作为一种诗学的对象(文化的诗学),与诗进入文化观念(诗的文化学)共构成了一个互释、互渗(participation)的空间场域。与其说文化与文本的交融赋予了文化以文本的诗学审美属性,还不如说文化自身呈现出诗意的形态。因为人在创造文化的活动中必然要把人创造成“文化的人”,而人的哲学又“必然地同时就是一种科学哲学,必然地同时就是一种艺术哲学、语言哲学、神话哲学……一句话,人的哲学归根结底不能不是一种人类文化哲学”。[18]文化作为一种活动的创造,其本身就已经涵盖了诗的阐释,因此,诗的阐释可以看成是文化的本质属性之一,也是文化的阐释模式之一。正是在日常生存与本真的存在中,栖居着历史文化的创造中所蕴含的人类的诗意的呈现。海德格尔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文化诗学模式的阐释路径。在《艺术作品的本源》中,海德格尔说到:“艺术作品是人人熟悉的。在公共场所,在教堂和住宅里,我们可以见到建筑作品和雕塑作品。在博物馆和展览馆里,安放着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的艺术作品。如果我们根据这些作品的未经触及的现实性去看待它们,同时又不至于自欺欺人的话,那就显而易见:这些作品与通常事物一样,也是自然存在的。一幅画挂在墙上,就像一枝猎枪或者一顶帽子挂在墙上。一副油画,比如凡·高那幅描绘一双农鞋的油画,就从一个画展转到另一个画展。人们运送作品,犹如从鲁尔区运送煤炭,从黑森林运送木材。在战役期间,士兵们把荷尔德林的赞美诗与清洁用具放在背包里。贝多芬的四重奏存放在出版社仓库里,与地窖里的马铃薯无异。”[19]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中教导我们说:“囿于粗陋的实际需要的感觉只具有有限的意义。对于一个忍饥挨饿的人来说并不存在人的食物形式,而只有作为食物的抽象存在;食物同样也可能具有最粗糙的形式,而且不能说这种饮食与动物的饮食有什么不同。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20]我认为,在此,海德格尔与马克思都同样注意到了一个“审美认识”的问题。美其实就在日常的诗意存在中,在本真的体验中,所谓艺术,所谓审美,所谓诗意,不就是人的超脱世俗后本真的静观、默察以及人与物、心与自然之间的沟通吗?美,其实就是客观事物或社会生活中符合人的生活理想的综合反映,就是人对日常现实生活所作出的审美的认识。我想著名的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能够更好地给予我理论的支撑,他在《“慢慢走,欣赏啊!”——人生的艺术化》一文中指出:“人生本来就是一种较广义的艺术。每个人的生命史就是他自己的作品。这种作品可以是艺术的,也可以不是艺术的,正如同是一种顽石,这个人能把它雕成一座伟大的雕像,而另一个人却不能使它‘成器’,分别全在性情与修养。知道生活的人就是艺术家,他的生活就是艺术作品。”[21]
“人生的艺术化”不正是我们这些被机器笼罩着的现代异化人类所苦苦追寻的诗意吗?诗意存在于文学文本的虚构世界中,也同样存在于日常的文化生活中。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灿烂文明沉积出了华夏灿烂的文化,作为世界最古老的东方古国,造就了无数的经典作品,陈列于文学艺术的展堂之上,令人百读不厌。然而,正如胡适之先生所言“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诗经”时代有“诗经”时代的文学,唐代有唐代自己傲人的诗歌,“五四”也有“五四”时代特有的文学,处于社会主义的今天,在走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上,也有符合我们当今时代口味的文学艺术,无论经典抑或俗套,它就是我们当下所特有的时代产物,我们不应分高下、分贵贱,盲目排等级、划界线,我们需要敞开胸怀,用母亲般特有的爱惜去培养它、养育它,因为总有一天,在历史的书写中,它们不可能“缺场”。
所以,我赞成童庆炳先生所言,“文化诗学”应该具备一种开放的精神、一种包容的情怀,用“海纳百川,有融乃大”的批评精神去解读一切具有诗情画意的文学艺术形态。
注释:
①在文化诗学学理建构上,童庆炳、刘庆璋、蒋述卓等教授都提出了自己关于“文化诗学”的构想,这几位早期文化诗学的理论开拓者,尽管在思考的出发点和向度上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学术观点的核心仍基本一致,如:他们均主张文化和历史语境中文本意义的追问;重视文学与文化各扇面间的互涵互构研究;倡导“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的双向贯通;同时主张文化诗学的审美性前提,倡导现实人文关怀,批判社会文化中庸俗恶劣的反文化反诗意的东西;通过开辟文化诗学视野,找到文艺理论发展的新方向,力求建构起一门文学新论来。
②在文化诗学批评实践上,学界主要以林继中、顾祖钊、李春青等教授为代表,他们均采用文化诗学的方法,在实践中寻求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希冀在实践中激活传统。其文化诗学的实践代表著作主要有:林继中的《文化建构文学史纲(魏晋-北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李春青的《诗与意识形态:西周至两汉诗歌功能的演变与中国诗学观念的生成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顾祖钊的《华夏原始文化与三元文学观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③这里提到的文化研究的“介入”性功能和对权力关系的探讨,在批评的落脚点上类似于西方的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其领军代表斯蒂芬·格林布莱特(Stephen Greenblatt)强调文化诗学的“文化的政治学属性”,文学是“论证意识形态、社会心理、权利斗争、民族传统、文化差异的标本”,通过文本与历史的溯源,旨在挖掘文本中蕴含的复杂政治权利关系,揭示深埋于文本之内的“社会权利运作关系”。当然“文化研究”与“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的差别巨大,这里仅仅是从批评的指向层面上而言具有某些相似性。在此例举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阐明“中国文化诗学”与西方“新历史主义文化诗学”存在的根本差异。
④关于这一点,尼尔·波兹曼(Neil Postman)有着精辟入里的见解,他认为媒介就像是一种隐喻,用一种隐蔽但有力的暗示来定义现实世界,这种媒介——隐喻将世界进行着分类、排序、建构、放大、缩小、着色,并且证明一切存在的理由;媒介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以不为人所注意的方式介入,指导着我们了解事物。可参阅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及马歇尔·麦克卢汉的《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
[1]阿雷恩·鲍尔德温,等.文化研究导论[M].陶东风,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5.
[2]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452.
[3]雷蒙德·威廉斯.现代主义的政治——反对新国派[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60.
[4]陆扬.文化研究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59.
[5]赵勇.透视大众文化[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4:15.
[6]童庆炳.“文化诗学”作为文学理论新构想[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41-45.
[7]童庆炳.美学与当代文化讲演录[M].桂林:广西师大出版社,2007:223.
[8]刘庆璋.文化诗学学理特色初探——兼及我国第一次文化诗学学术研讨会[J].文史哲,2001(3):60-62.
[9]蒋述卓.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
[10]林继中.文化诗学刍议[J].文史哲,2001(3):57-59.
[11]童庆炳.文化诗学:宏观视野与微观视野的结合[J].甘肃社会科学,2008(6):132-135.
[12]罗纲,刘象愚.文化研究读本[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
[13]李春青.文化诗学视野中的古代文论研究[J].文学评论,2001(6):66-68.
[14]皮锡瑞.经学通论·诗经通论[M].北京:中华书局,1954:20.
[15]郭庆藩.庄子集释[M].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4:1065-1069.
[16]陶东风.日常生活审美化与文艺社会学的重建[J].文艺研究,2004(1):15-19.
[17]阳友权,吴英文.微博客:网络传播的“软文学”[J].文艺理论研究,2010(4):15-19.
[18]恩斯特·卡西尔.人论[M].甘阳,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7.
[19]海德格尔.林中路[M].孙周兴,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3.
[20]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87.
[21]朱光潜.谈美[M].北京:中华书局,2010: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