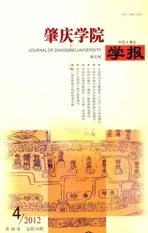论荀子对孟子“性善论”的批判
2012-01-28高春海
高春海
(肇庆学院 政法学院,广东 肇庆 526061)
从《荀子·性恶》篇中可以看出,荀子是采取破立结合的方式建立自己的性恶论的。所谓破是指批判孟子的“性善论”,力图证明其错误;所谓立是指利用各种证据从正面证明“性恶论”的成立。学界在研究荀子“性恶论”时往往把注意力放在了“立”的这一面,而较少论及荀子对孟子“性善论”的批判。徐复观、路德斌、李亚彬等人在各自的研究成果中都曾涉及到荀子对孟子 “性善论”的批判①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0-146页;路德斌:《荀子“性恶”论原义》,《东岳论丛》2004年第1期;李亚彬:《道德哲学之维》,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48-52页。。但由于论述主旨的原因他们均未就此话题展开论述。本文尝试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考察荀子对孟子“性善论”的批判中存在的问题并探究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
一、可行性之争
在《荀子》三十二篇中,荀子只在《性恶》一篇中谈及了孟子的“性善论”,而且是把它作为批判的靶子。荀子对孟子“性善论”批判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围绕着“性善论”与“性恶论”的可行性展开的。《荀子·性恶》载:“孟子曰:‘人之性善。’曰:是不然。凡古今天下之所谓善者,正理平治也;所谓恶者,偏险悖乱也。是善恶之分也已。今诚以人之性固正理平治邪,则有恶用圣王、恶用礼义矣哉?虽有圣王礼义,将曷加于正理平治也哉?今不然,人之性恶。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是圣王之治而礼义之化也。今当试去君上之势,无礼义之化,去法正之治,无刑罚之禁,倚而观天下民人之相与也;若是,则夫强者害弱而夺之,众者暴寡而哗之,天下之悖乱而相亡不待顷矣。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1]505-506荀子认为“善”是指人们的行为符合伦理规范,合乎国家治理的要求;“恶”是指人们的行为偏离伦理规范,违反了国家治理的要求。在荀子的思想中礼义主要是指伦理规范,圣王是治理国家的能手。在他看来,如果孟子的“性善论”成立的话,礼义、圣王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荀子显然把孟子的“性善论”理解为人天生具有完善的美德,没有作恶的可能。这样完美的人当然不需要礼义的规范和圣王的治理。如果孟子的“性善论”果真是荀子理解的那样,荀子的批判自然是成立的。因为众所周知的现实是人天生不具备完美的品德,人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也少不了出现违反道德的情况,严重时还会违法犯罪。因此社会总少不了礼义的教化、政府的治理以及刑法的震慑。如果离开它们,社会的确会出现荀子所说的以强凌弱、天下混乱的局面。而荀子“性恶论”的登场则很好地解释了伦理规范、政治治理的存在必要。因为荀子的“人性论”就是承认人天生有为恶的趋向,圣王、礼义乃至刑法的存在正是为了矫正人性之恶。到此自然可以顺理成章地推出荀子期望中的结论:孟子的“性善论”只能“坐而言之”,但在现实中不具有可行性。性恶论则极具可行性。
问题是孟子的“性善论”果真是荀子理解的那样简单吗?这就需要我们对孟子“性善论”做一个简要的探讨。孟子的思想体系是建立在“性善论”的基础上。这种“人性论”肯定是孟子经过认真思考建立起来的。因此他的“性善论”决不会轻易被人驳倒。在《公孙丑》中,孟子集中论述了他的性善论:“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2]79-80孟子从人们看到小孩子将要掉入井里时都会产生救人的念头这个事例出发得出人们天生都有善性。这善性就是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孟子又进一步把它们归结为仁、义、礼、智四端。这段论述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那个端字。端只是代表一种可能,一种萌芽状态或者说未完成的状态。孟子讲人人天生皆有四端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方面是指人们天生有成为善人的可能,另一方面暗示人们还要借助于后天的努力,才能把这种可能变为现实。孟子在《公孙丑》中说:“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2]80孟子这里说得很明确,人们仅靠天生的善端还不能成为品德完美的善人,要想成为善人必须经过后天的一番努力。因此,荀子把孟子“性善论”理解为人天生就具有完善的品德是错误的,他把善之可能当成了善之实现。
孟子在坚持“性善论”的同时没有排除人们为恶的可能。这从他与告子的辩论可以看出。《孟子·告子》载:“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2]254孟子认为人性向善就好比水势就下一样。但是水受外力的作用会高过人的额头甚至被引上高山。这就是说人也可能受外界环境的影响而做出不善的事情。主张人性善的孟子同样认为人有作恶的可能。自然,孟子不可能因主张“性善论”就否定了礼义、刑法、圣王的存在必要。这样就得不出荀子在《性恶》篇中期待的结论:“性善,则去圣王、息礼义矣;性恶,则与圣王、贵礼义矣。”[1]507
二、顺性逆性之争
孟子主张人性善,因此他认为人们行善是顺人性而为。《孟子·告子》载:“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 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 。’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 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 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2]253告子认为把人性等同于仁义就好比把作为原材料的杞柳当成了制成品的桮棬。孟子的回应是围绕着顺性和逆性展开的。在孟子看来问题关键在于桮棬 是顺着杞柳之性做成的还是逆着杞柳之性做成的。孟子认为告子无疑是主张桮棬是逆着杞柳之性做成的,进一步讲,他认为告子主张人们行善是逆人性而为。这正是孟子极力反对的观点。孟子认为人之为善就好比水势就下一样自然,为善是顺应了人天生的善性。孟子举例:当人们看见小孩将要掉入井里时就自然会产生恻隐之心,要伸出手去帮一把。这说明行善是顺人性而为。
荀子对孟子这个观点进行了批判,他认为人们行善是逆人性而为。荀子在《性恶》中说:“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今人饥,见长而不敢先食者,将有所让也;劳而不敢求息者,将有所代也。夫子之让乎父,弟之让乎兄;子之代乎父,弟之代乎兄;此二行者,皆反于性而悖于情也,然而孝子之道、礼义之文理也。故顺情性则不辞让矣,辞让则悖于情性矣。用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1]502荀子说人的本性就是饿了要吃饭,冷了要取暖,累了要休息。当食物出现在同样饥饿的长辈晚辈面前时,晚辈如果顺着自然本性而行就会先行进食,而不会把食物让给长辈;当休息的机会出现在同样劳累的长辈晚辈面前时,晚辈如果顺着自然本性而行就会先行休息,而不会顾及长辈了。晚辈之所以有礼让长辈的举动正是因为他们克服了“饥而欲饱”“劳而欲休”的本性。由此可见,辞让之类的善行是逆人性而行,而不是孟子所说的顺人性而行。
如此看来,荀子和孟子在为善是顺性还是逆性的问题上形成了尖锐的对立,而且都有各自的依据。不过,认真思考孟荀双方的立场就会发现他们的对立源于对人性的不同界定。在 《性恶》中,荀子说:“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又说:“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佚,是皆生于人之情性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1]503人天生就有耳目之欲。在荀子看来,这些生理欲求都是属于人性的范畴。孟子当然也知道人的这些生理欲求。但与荀子不同的是他不把这些内容纳入人性的范畴。孟子在《尽心》中说:“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2]333对于耳目之欲,孟子认为君子不应将之纳入人性的范畴,原因在于这些生理欲求能否实现有待命运的安排,不能完全由个人做主。其实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他和荀子一样认为这些生理欲求会诱发恶果。这一点可从《告子》中的一段对话中看出:“公都子问曰:‘钧是人也,或为大人,或为小人,何也?’孟子曰:‘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曰:‘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其小体,何也?’曰:‘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此天之所与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此为大人而已矣。’”[2]270孟子认为耳目不会思考,人们如果不用心思考,就会被耳目之欲所误导,成为小人。如果孟子把生理欲求纳入人性的范畴,那么他就要承认行善会和人性发生冲突。因为人们在行善时确实要克服那些不适当的生理欲求。孟子为了保证行善是顺性而为,就把耳目之欲彻底从人性的范畴中清除出去。他只从心上论性,而且认为心是全善之物。孟子在《告子》中提出:“仁,人心也”。[2]267又在《尽心》中说:“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2]309经过孟子的理论构建,人性与恶无缘,人性是善的,自然得出结论:人们行善就是顺人性而为。到了荀子那里,生理欲求被纳入了人性的范畴,人们为善就会和人性相违逆。
因此,我们可以说荀子与孟子产生分歧的原因在于对人性范畴的理解不同。不过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孟子把生理欲求从人性中清除出去的做法是否恰当。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种观点认为孟子的“人性论”立足于人禽之别,突出了人之为人的特征,而荀子的“人性论”则混淆了人禽之别,因此孟子要高于“荀子一筹”[3]。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荀子并没有忽视人禽之别。荀子在《王制》中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1]162孟子认为人先天具有不同于动物的道德属性,而荀子则认为人只有在后天经过学习,懂得了礼义,才能与动物划清界线。二是荀子将与动物类似的生理欲求纳入人性的做法更符合实情。恩格斯在谈到人性问题时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4]承认人与动物有共同的自然属性并不会混淆人禽之别。
三、性伪之争
荀子对孟子“性善论”的一个批判是围绕着“性”、“伪”的关系展开的。在荀子看来,孟子没有把属于先天范畴的“性”与属于后天范畴的“伪”区分开。荀子在《性恶》中指出孟子“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见,耳可以听。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目明而耳聪,不可学明矣。”[1]500在荀子看来“性”是指人先天具有的功能,根本不需要后天的学习和努力就能自然获得,这些内容包括眼睛可以用来看,耳朵可以用来听。“伪”是指人先天不具备,需要后天学习、努力才能掌握的内容,如礼义需要人学习才能掌握。荀子认为人性恶,只有经过后天的礼义教化人们才能成为善人。他在《性恶》中说:“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1]498在荀子看来,人们先天的本性是恶的,善作为一种美德是人们经过后天改造才能获得的,而孟子偏偏要把人先天的本性说成是善的。因此荀子认为孟子不懂“性”“伪”之分,不懂先天后天的区别。
在人性的把握上,孟子的审视角度与荀子不同。他是从人禽之别的角度谈论人性,并且认为人性就是指人天生具有善端。而荀子则把人禽相同的方面纳入了人性范畴,并认为人天生具有为恶的趋向。“伪”字在《孟子》一书中共出现了四次,但均无“人为”的意思。在《孟子·滕文公上》中“伪”字出现了两次:“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2]126这两处“伪”字均解释为弄虚作假。另外,“伪”字还在《孟子·万章上》中出现了两次:“然则舜伪喜者与?”“故诚信而喜之,奚伪焉?”[2]210这两处“伪”字都解释为“假装”。荀子把“伪”字定义为后天的人为的结果,这种做法在古书中十分罕见。这就很容易引起后人的误解。因此,我们只能说按照荀子自己制定的标准,他对孟子的批判才能成立。但荀子制定的标准从来没有得到公认。
在“人性论”的发展历程中,从来没有一个公认的标准。因此关于人性的争论从来没有停息过。思想家们都有各自审视人性的独特视角和标准,他们都是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和特定目标出发提出各自的人性论。客观地讲,思想家们都从各自的角度对人性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孟子和荀子在“人性论”上的争论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道理。
四、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荀子在批判孟子的“性善论”时确实存在不少误解和偏差。这种情况产生的一种可能是他没有全面了解《孟子》一书中关于“性善论”的论述。徐复观就推断荀子“不曾看到后来流行的《孟子》一书,而只是在稷下时,从以阴阳家为主的稷下先生们的口中,听到有关孟子的传说”[5]。考虑到当时的文化传播条件等因素,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可以设想,荀子只是听说过一些关于“性善论”的只言片语,就展开了对孟子“性善论”的批判。
不过,我们也应该考虑荀子在批判孟子“性善论”时是否带有非学理的因素。战国正是百家争鸣的时代,诸子各持己见,都力图驳倒自己的对手。细观诸子的著作可以看到一种奇特的现象:在诸子各自的书中,他们批驳的对手都成了输家。在《墨子》中,儒家总是被墨家驳倒;在《庄子》中,儒家不敌道家人物;在《孟子》中,墨家又被儒家的道理说服。再进一步看,诸子书中所批判的观点往往都被简单化甚至被严重歪曲。经过这种有意的处理,诸子在各自的书中都轻而易举地驳倒了对手,从而保证了自己的绝对胜出。荀子对孟子“性善论”的批判也不能说完全没有这种嫌疑。这种做法当然不可能真正驳倒对手。
荀子在《正名》篇中曾提出:“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辨”。[1]486但是做起来确实很难。客观地讲,诸子的观点都有自己的立论根据,这正如荀子在《非十二子》篇中批判论敌时所说的“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1]84。自然,诸子的观点都有各自的价值。
[1]张觉.荀子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2]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
[3]刘鄂培.孟子大传[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161.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42.
[5]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