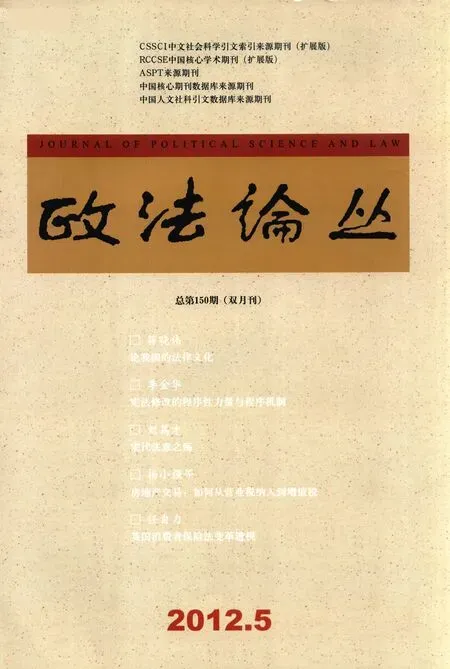论伊斯兰法的石刑
2012-01-28刘文静
刘文静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北京100872)
石刑(stoning),是用乱石将罪犯砸死的一种刑罚,是人类刑罚史上最残忍的酷刑之一,也是现存的最古老的刑罚。早在穆罕默德时代,伊斯兰法就有关于石刑的规定。作为对通奸行为的刑罚,石刑目前仍在少数几个伊斯兰国家适用,如伊朗、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等。2010年,一位名叫萨基内·穆罕默迪·阿什蒂亚尼的伊朗妇女因通奸罪,被伊朗法院判处了石刑。这一事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伊朗法院及当局遭到了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在现代文明与法制发达的今天,野蛮残酷的石刑仍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一些伊斯兰国家的法律中。石刑,这一让人谈之色变闻之胆寒的酷刑,为何能在穆罕默德时代扎根,为何延续至文明发达的21世纪?它的生命力究竟存在何处?
一、早期伊斯兰法与石刑
历史上,石刑在中东及巴勒斯坦地区广泛适用。我们无法查明石刑作为一种刑罚产生的确切时间,但关于石刑的文字记载却最早出现在《旧约全书》(以下简称《旧约》)和《犹太法典》中。《旧约》有这样的记载:摩西曾组织众人用乱石砸死了一个违反安息日规定的男子。①石刑在伊斯兰国家有着久远的传统,相传先知穆罕默德因其布道训教数次被人威胁,最后用乱石砸死。
在早期人类社会,法律与道德、宗教密不可分,法律与刑罚是道德伦理、宗教教义获得遵行的有力保障。法律普遍将通奸行为作为犯罪而予以严厉的惩罚。《旧约》和《犹太法典》详细规定了石刑的执行方法,包括对男人和女人行刑方式的区别以及何种情况下可对被惩罚者予以豁免。②伊斯兰法依据《古兰经》的规定,即“淫妇和奸夫,你们应当各打一百鞭”(24:2),对通奸的男女处以一百鞭的刑罚。后来,先知穆罕默德参照犹太法律的规定,声明对通奸行为处以石刑。据圣训记载,一对被控通奸的犹太男女被带到穆罕默德面前,穆罕默德查明,犹太法律对通奸罪判处石刑,遂据此提出对这二人施以石刑。一次属人法的适用,使穆罕默德深感犹太法律对通奸恶行处罚之得力。为重申伊斯兰教义对家庭、道德与荣誉的重视与维护,“先知降谕,一名已婚男性与一名已婚女性通奸,他们将被鞭笞一百下,并以石刑处死。”圣训在伊斯兰法中是仅次于《古兰经》的法律渊源,对通奸处以石刑的规定正式出现在伊斯兰法律中。后世沙里阿法院在裁判通奸罪时,一般直接援引圣训的规定。
伊斯兰法对通奸这种属于道德层面的问题处以最严厉的石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古代社会均把道德或宗教教义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一种手段,而伊斯兰教本身异于其他宗教的一个特点,就是强调家族荣誉等规定,使得伊斯兰法的道德法特征更为明显。《古兰经》是对穆斯林日常生活的规训,而圣训记录穆罕默德的生活言行。《古兰经》和圣训对教徒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做了细致的规定,严格训导教徒做道德高尚的纯洁穆斯林。从其内容来看,目的在于规范穆斯林与真主之间的理想关系。这种宗教伦理性质的法根本宗旨不是要回答合法或非法,而是以宗教道德为尺度,规定善恶、是非、美丑的标准。[1]P16而家庭,作为最基本的社会构成单位,与社会秩序的稳定程度息息相关。通奸行为严重破坏了稳定的两性关系和家庭结构,势必对社会秩序的稳固构成威胁;其次,传统的伊斯兰法以保护宗族、家庭与个人名誉为己任。穆罕默德认为通奸同酗酒、偷窃、抢劫等恶行一样,均是对真主安拉旨意的违抗,应当对其施以严厉的刑罚;第三,通奸行为被认为侵犯了伊斯兰法律所维护的一些最基本的价值:保护宗族、家庭荣誉和财产。在宗族血缘为纽带的部落社会,知道孩子属于谁非常重要。这也许能帮助解释通奸罪行为何适用石刑而不是其他刑罚。对待违背整个部族认同规则的人,自然应该由众人行刑。③
关于通奸罪的成立,《古兰经》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凡告发贞洁的妇女而不能举出四个男子为见证者,你们应当把每个人打八十鞭并且永远不可接受他们的见证。这等人是罪人”。(24:4)根据《古兰经》的规定,在四位亲眼目睹了通奸行为的成年男性穆斯林作证的情况下,才可对被控通奸的人定罪。这一近乎严苛的举证要求,实际上使得通奸罪很难成立。这一证据要件,引发了人们的质疑,有人甚至说,如果通奸是罪,那么四人目睹通奸却不制止,岂不是更大的罪?亦有学者认为,伊斯兰法的这种规定,其直接目的在于禁止公共场合下的性行为,而非授权官员查探隐私。[2]《古兰经》明确规定了对诬告通奸行为处以八十鞭的刑罚。在伊斯兰法律中,诬告通奸罪与通奸罪均位于六种最严重的罪行之列。在宗教社会,以道德伦理为核心的普遍价值观念支配着生活的方方面面。通奸的男女会使家族蒙羞而因此众叛亲离,被世人唾弃。针对诬告通奸行为的严刑峻法,一方面出于对穆斯林基本权利的保护,另一方面也大大减少了对通奸行为的指控。
二、伊斯兰法世俗化改革与石刑
经历了几个世纪的变迁,至19世纪,昔日强大繁荣的奥斯曼帝国已是气数将尽。国内统治阶层腐败不堪,民怨四起,同时,西方势力借机渗透,在帝国境内有着强大的势力。内忧外患的奥斯曼帝国面临着四分五裂的困境。此时,统治当局为挽救颓势,在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开展了规模浩大的改革运动。其中,以1839~1876年的“坦志麦特”改革最为著名。近代伊斯兰法律亦以此为标志开始了历时百年、时断时续的世俗化改革。
奥斯曼帝国在伊斯兰法改革过程中大量移植了西方的法律制度。在刑法领域,于1858年仿照法国1810年《刑法典》,制定了奥斯曼帝国《刑法典》,基本废弃了传统伊斯兰刑法的原则和规定。在法律改革的浪潮下,对通奸罪判处石刑的规定消失在人们的生活中。
奥斯曼帝国解体后,境内各个国家沦为英、法等国家的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在自强的强烈动机以及殖民国家的积极推动下,这些国家的伊斯兰法世俗化进程并未终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土耳其在凯末尔领导下,开始了全面彻底的法律改革,几乎废止了伊斯兰法的全部内容。土耳其大量引进了西方的法律制度,1926年以意大利《刑法》为蓝本,颁布了土耳其《刑法典》。同时,土耳其废除了沙里阿法院系统。至二战结束时,土耳其建立起了完全世俗化的法律体系和法院系统。在埃及、伊朗、叙利亚、利比亚等传统的伊斯兰国家,伊斯兰法世俗化改革也在稳步推进。除婚姻家庭领域外,传统伊斯兰法规制的民事、刑事领域都几乎被世俗法律占领。伊朗在20世纪初,参照西方法律制度大规模修订法律。1912年,伊朗效仿法国《刑法》典颁布了刑法典,这部法典以法国的刑法概念和制度代替了传统的伊斯兰刑法的概念和制度。1926年,伊朗以新的刑法典取代了1912年刑法典,这部新法典仍然照搬了西方刑法典的规定,没有保留任何传统伊斯兰刑法的痕迹。埃及的改革是在继承传统伊斯兰法原则和对某些具体制度择优处理的基础上,在民法、刑法等领域引进西方的法律制度,如1937年埃及参照意大利《刑法》,制定了《刑法典》,新的《刑法典》仍然保留了传统伊斯兰法的规定。此外,埃及废除了混合法院以及领事裁判权制度,限制沙里阿法院的管辖权,并最终于1955年废除了沙里阿法院,司法权收归世俗法院所有。阿拉伯半岛上的国家,如沙特阿拉伯,由于其是伊斯兰教的发源地,传统宗教势力强大,西方势力对其影响甚微,伊斯兰法长期适用于当地穆斯林社会,对西方法律制度的借鉴、吸收较少,主要存在于商事、金融领域。北非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国也进行了仿照西方法律制度的世俗化改革。摩洛哥于1954年依照法国刑法典制订了一部《刑事法典》,这部法典除保留了传统伊斯兰刑法中的通奸罪之外,其余的规定皆被弃用。阿尔及利亚则将法国的刑法典和民法典作为国内法直接适用。
19世纪直至20世纪60年代,伊斯兰世界进行的法律世俗化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场持续百余年的运动,是伊斯兰国家应对挑战,提高国力的必然选择。在现代法律制度的冲击下,传统伊斯兰法走向了式微。伊斯兰国家法律世俗化改革主要以移植西方国家法律体系,废除传统伊斯兰法为内容。关于伊斯兰国家的法律移植模式,有学者将其分为替代性移植模式和补充性移植模式。前者是指用移植的外来法律全面取代本国相应的固有法,后者是指以移植而来的外来法律补充固有法律之不足。即,这种法律移植模式,并不以外来法全面取代固有法,而只是以移植的方式借用某些外来法的资源,同时对固有法作一定程度的修改,以实现二者之间的相互妥协于融合。[3]依照此种分类方法,以土耳其为代表的彻底改革派当属前一类。在安拉庇佑的土地上,把按照安拉旨意形成的伊斯兰教法连根拔起,建立起由西方法律复制品组成的全新法律体系。除土耳其之外,替代性法律移植模式也出现于其他一些伊斯兰国家的特定法律部门中,主要是刑法、商法、民法和程序法领域。[3]民商法领域的改革无疑均是因为传统的伊斯兰法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无法提供相应的规制和法律救济,且日益成为商品交易发展的桎梏。而刑法领域,受西方现代化和理性化的影响,西式的刑法典逐渐取代了传统的伊斯兰法。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不处罚,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检察机关行使犯罪的公诉权,正当程序原则等开始为阿拉伯国家所继受。自19世纪西方国家入侵中东地区,伊斯兰刑法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大部分国家已转而实施源自西方的现代刑法制度。[4]P198古老的伊斯兰刑法在现代人权思想和女权运动的冲击下,已是千疮百孔。虽然摩洛哥、埃及、利比亚等国家依然保留着传统刑法规定的通奸罪,但在各国刑法逐渐西化以及现代诉讼制度建立的背景下,石刑在伊斯兰社会没有了适用的土壤。
三、伊斯兰法的复兴与石刑
经过百余年世俗化法律改革的洗礼,许多伊斯兰国家仿照西方模式建立了新的法律体系。20世纪60年代,规模浩大的伊斯兰革命席卷了许多伊斯兰国家,推翻旧政权之后,革命政权均宣布废除依照西方模式建立的世俗化法律体系,恢复适用传统的伊斯兰法,这一转变被称作“伊斯兰法复兴运动”。“伊斯兰法复兴运动”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在这场传统法律的复兴运动中,首当其冲的是利比亚,紧随其后的是巴基斯坦、伊朗和苏丹等国。[5]P352
卡扎菲领导利比亚革命后,于1971年正式宣布恢复伊斯兰法,传统伊斯兰法的主要制度又重新取代了世俗化法律。1977~1979年,霍梅尼在伊朗发动了“伊斯兰革命”,推翻了旧政权,建立了“伊斯兰政权”。由此拉开了轰轰烈烈的“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序幕。这场旨在恢复传统伊斯兰教法、建立伊斯兰世界新秩序的运动迅速席卷了巴基斯坦、约旦、埃及以及苏丹等国家。这些国家纷纷抛弃已按西方模式建立的世俗化法律体系,在民事、经济、刑法领域恢复了传统的伊斯兰法。
伊斯兰传统教法的卷土重来,绝不是偶然的,其深层的政治社会原因,值得人们思考。首先,法律世俗化的改革出现了许多弊端,并未给伊斯兰世界带来和平和富强。政府腐败、社会混乱,西方式的民主并未在这片土地扎根。对不熟悉现代法律的大多数民众而言,政府有名无实的议会制度、选举制度大多成了欺骗人们的幌子。而西方国家的不断盘剥,永无宁日的冲突与摩擦,使人们感到复兴奥斯曼帝国,重现往日的繁荣与强大已是南柯一梦。民众对现实的失望和对宗教衰落的茫然反而促成了伊斯兰传统价值观与西方价值观的彻底决裂。其次,面对伊斯兰世界的困境,主张通过恢复纯洁的伊斯兰教来振兴社会的原教旨主义迅速发展,得到了广大穆斯林的热烈支持。原教旨主义以反对西方和恢复伊斯兰教法立足并在伊斯兰世界获得大批民众的拥护。他们的主张迎合了穆斯林对按照西方制度建立的政权的不满以及对昔日良好社会秩序的渴望。再次,伊斯兰法复兴也承担了推翻旧政权、巩固新政权的历史使命。革命派在动员民众参加革命时,宣称建立伊斯兰新政权,重建伊斯兰世界新秩序。革命成功后,为迎合民意,巩固政权,则极端地废除所有世俗化法律,全面恢复伊斯兰教法。
作为伊斯兰教法的主要内容,传统刑法在轰轰烈烈的伊斯兰法复兴运动中,又重新获得了生命力。传统刑法视为重罪的通奸罪也堂而皇之出现在了新的刑法典中。而断手、鞭刑、石刑等古老的刑罚措施又被启用。巴基斯坦1979年的《通奸犯罪法》规定,凡合法婚姻以外的异性发生性行为即构成通奸罪,对未婚私通者鞭笞一百;对已婚通奸者乱石砸死。伊朗《犯罪惩罚法》规定,对未婚私通,打一百鞭,对年长已婚者通奸,打100鞭,然后乱石砸死。伊朗《犯罪惩罚法》对石刑这种刑罚,定义为“故意造成(被行刑者)剧烈疼痛致其死亡”的刑罚。[6]关于如何行刑,亦有着详尽的规定,其第102条规定:“男性受刑者应被埋至腰部,女性受刑者应被埋至胸部。”第104条甚至规定了石刑所用石块的大小:“不应太大,以至于一两下就可以致人于死地;也不应太小,以至于称不上石头。”同时按照传统伊斯兰教法的规定,伊朗刑法中对认定通奸罪提出了十分严格的证据要求:必须有4名男性(或3名男性以及两名女性)亲眼目睹性交过程,通奸罪才能成立。但是,伊朗刑法也允许法官采用心证,这为地方法官的草率判决提供了依据。[7]
在伊斯兰法复兴运动中,尽管一些伊斯兰国家宣称在民事、商事、刑事等各领域都恢复适用传统伊斯兰法,但恢复传统罪行及刑罚显然成为复兴传统教法的主要内容。关于通奸罪及石刑的重新启用,笔者认为有几个方面的原因:首先,伊斯兰法复兴运动宣称恢复纯粹的伊斯兰秩序,那么对古老的传统教法的重要内容,即通奸等重罪,自然应严格继承。于是,对通奸处以石刑的规定重见天日。其次,性自由被认为是西方社会的典型现象,对西方社会及其法律制度的不满情绪是支撑全面恢复伊斯兰教法的重要动力。尤其在原教旨主义的宣扬下,对社会道德堕落、家庭秩序破裂的严重失望使得人们把恶果归咎于西方法律制度的缺陷,也更激起了人们对缔造纯洁穆斯林社会的古老伊斯兰教法的向往。再次,随着20世纪中叶伊斯兰革命的兴起,石刑、断肢刑等残酷刑罚的恢复使用与伊斯兰新政权的建立有着密切的联系。④通过革命建立的伊斯兰新政权,始终标榜其是穆罕默德忠实追随者,是伊斯兰教法的忠实维护者,正因如此,在革命中获得了民众的支持。毋庸置疑,迎合民众心理诉求,恢复最原始伊斯兰教法的做法对巩固新政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四、石刑在现代社会
目前,仍存在石刑的国家包括伊朗、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阿富汗、伊拉克、苏丹、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尼日利亚。2010年的阿什蒂亚尼事件将伊朗当局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传统伊斯兰法成为众矢之的,而所谓重建伊斯兰新秩序的伊斯兰法复兴运动遭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
反刑罚国际委员会的负责人Farshad Hoseini通过媒体报道及人权组织的报告,统计出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在伊朗,至少有150人因犯通奸罪被执行石刑。同时在诸多的报道中,他发现一个问题,那就是,要想知道被执行石刑人员的真实姓名是极其困难的,原因就在于当局对这种消息实行严密封锁。他补充说,石刑在伊朗是当局用以控制社会的一种野蛮的工具。石刑的大多数受害人都是妇女。在宗教社会里,石刑是压制妇女的工具。在执行石刑时,行刑者们会没收围观者的手机及其他录音录像设备,以防止外界知道整个行刑过程。反石刑国际委员会的一位成员Ahmad Fatemi说,石刑的目的在于制造恐慌。他分析说,秘密施行石刑不会给当局带来不必要的尴尬。[8]
在人权发展、法治发达的今天,阿什蒂亚尼事件震惊了整个国际社会,也带给了我们无尽的思考。从一个罪名及刑罚的演变足以窥见整个法律体系变迁的历程。在伊斯兰社会,传统教法对通奸判处石刑的规定从穆罕默德时代产生,随着法律世俗化改革而消亡,又在伊斯兰法复兴运动中重新得以适用。法律改革与地缘政治及宗教文化的紧密关联让现代伊斯兰法前途未卜。而通奸罪与石刑在法律变革的起伏中也扑朔迷离。
首先,伊斯兰法仍然受到原教旨主义的强烈影响。原教旨主义以建立传统的伊斯兰社会为己任,其首要维护宗教的神圣性,矢志不渝地按照伊斯兰教的宗旨和原则来管理社会。按照伊斯兰教义,妇女从属于男人,且应当受到严格的控制。且通奸罪作为传统伊斯兰教法的重罪之一,恢复适用也是复兴伊斯兰法的应有之义。
其次,西方国家以人权为名,长期以来对仍施行石刑的伊斯兰国家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在当今西方国家与伊斯兰国家冲突不断的情况下,一些适用石刑的国家,虽然面临国际社会的舆论压力,但从政治角度出发,正可以此为契机表明与西方敌对的决心以及显示自身强硬的态度。如伊朗法院不顾国内外抗议的声音,仍以多数表决对萨基内·穆罕默迪·阿什蒂亚尼以通奸罪判处石刑,而伊朗政府也以反对干预其内政为由,在此问题上表现出了强硬的立场。
第三,从判决与执行的情况来看,石刑一般出现在偏远地区。在偏远的地区,人们依旧保留着最虔诚的宗教信仰,法官也恪守着执行安拉指令,惩罚有违教义的行为,他们仍然可以凭借自由裁量权适用石刑。经济的不发达,传统势力的强大,各种观念的滞后以及自身权利意识的不觉醒使得被指控通奸罪的人往往无力争辩或者不能获得有效的辩护。
事实上,石刑之所以在伊朗顽固存在,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犯罪惩罚法》允许法官根据自由心证来判决通奸罪。虽然《犯罪惩罚法》对通奸罪规定了严格的证据条件,即在四名亲眼目睹通奸行为的成年男子指证的情况下,通奸罪名才成立。但是,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之下,如果法官认为通奸行为发生了,那么他就能裁判被告有罪。反刑罚国际委员会调查认为,在伊朗,每年根据法官的自由裁量被判处石刑的人在1~12人之间。[8]让石刑最终消失,任重而道远。
结语
社会的发展变化必然引起法律适用条件的变化,因此,法律改革成为不可回避的话题。倘若法律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则会成为严重阻碍社会发展的桎梏。就传统法律而言,更是如此。根据社会条件的变化主动改革法律,不断赋予传统法律以新的精神和新的意蕴,传统法可能获得新的生机,保持长盛不衰的活力。否则,该法律就可能被社会发展的潮流所淘汰。[5]P398在当今社会,伊斯兰国家的法律变革因其自身特性而困难重重。宗教意识、法律文化、政治形态等因素与法律改革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传统法律原则与现代法律精神的背离与融合共生。一项法律改革甚至一个罪名和刑罚的变化都牵涉到多种因素的作用和多种社会力量的角逐。
就现实情况来说,伊斯兰国家“政教合一”的传统使得伊斯兰教法被赋予了浓厚的政治特性。西方国家与中东国家的不断冲突以及西方社会对伊斯兰法违背人权的抨击,都使得伊斯兰国家对西方国家的法律有着强烈的抵触心理。规避西方社会的法律体系,固守传统教法,拒绝承认西方的人权观成为一些伊斯兰国家反击西方社会的方式之一。然而,在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时代,保障人权、法治文明仍然是法律发展的潮流。在伊斯兰国家,如何定位传统教法在社会中的角色,并使其与现代人权和宪法相契合是伊斯兰法改革的首要前提。单纯地否定西方国家的法律与完全忽略传统伊斯兰传统教法绝不是有效的解决方案。只有充分考虑《古兰经》和圣训的历史背景,以从内部对伊斯兰法律进行现代化法律解释的方法来指导法律改革,才可能探索达成这种契合的路径。[9]就伊斯兰法的变革而言,更应着眼于法律实质而非形式。我们应当找寻法律原则的起源,而细节则应由周围环境来决定。一项法律无须是中世纪或阿拉伯的才是伊斯兰的。事实上,相比于先知穆罕默德时代,伊斯兰国家应该有更好的法律。目前,一些伊斯兰国家对传统教法也进行了一些改革,例如一些明显违背人权的法律规定,如石刑、断手等酷刑,虽然仍未废止,但是逐渐减少其适用成为一种趋势。
笔者认为,一些伊斯兰国家的法律仍不废止石刑等酷刑的规定,与法律所固有的象征性作用有关。我们可以把法律的功能分为两种,一种是象征性的功能,一种是实质性的功能。象征性的功能包含着这样的价值目标,即再次确认已获普遍承认的观念以及明示对某一社会问题已采取了相应处理措施。[10]象征性的法律很少甚至并不适用于法律实践,但其存在宣示了社会认可的某种价值取向,使社会公众有归属感和安全感。法律中一些不常适用的有关惩罚违背教义或道德行为的条款,恰恰体现了法律的象征性作用。在伊斯兰社会,象征性的法律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伊斯兰法对通奸行为处以石刑的规定,在先知圣训中确定,直至伊斯兰法复兴运动时被写入一些国家的刑事法典。它以法律的形式向全体穆斯林昭示,通奸的行为不仅违背安拉的旨意,而且会受到严厉惩罚。它训诫全体穆斯林应重视家庭及稳固的两性关系,维护家族及个人的荣誉。在伊斯兰法复兴运动中,利比亚、巴基斯坦、伊朗等国全面恢复了传统教法的严法酷刑,实际则很少执行。关于通奸罪,已有的数据资料显示,其适用范围非常有限,往往出现在偏远的保守的地区。而法院裁判通奸罪行的案件比较罕见,大多数通奸者并未受到指控和惩罚。
在一些伊斯兰国家的法律世俗化改革中,完全抛弃传统教法,复制西方法律制度的失败,为恢复传统伊斯兰教法提供了最好的契机与口实。所以,在伊斯兰法复兴运动中重拾最原始最古老最传统的伊斯兰教法,无疑为新政权的稳固上了一道保险杠,给渴望重拾伊斯兰帝国复兴信心的穆斯林民众打了一剂强心针。历史的车轮已裹挟着伊斯兰世界步入了现代文明社会,虽然用传统教法来重建新秩序的目标显得遥不可及,而让传统教法的象征性作用来宣扬伊斯兰法的基本精神与价值追求未必不是权宜之策。
注释:
①Crime(Sex)and Punishment(Stoning),The New York Times,August 22,2010.http://www.nytimes.com/2010/08/22/weekinreview/22worth.html?_r=1&ref=sakinehmohammadiashtiani,最后浏览日期2010年12月30日。
②See Irene Merker Rosenberg,Yale L.Rosenberg,Of God's Mercy and the Four Biblical Methods of Capital Punishment:Stoning,Burning,Beheading,and Strangulation,78 Tul.L.Rev.1169(2004).
③See Courtney W.Howland,The Challenge of Religious Fundamentalism to the Liberty and Equality Rights of Women:An Analysis under the U-nited Nations Charter,35 Colum.J.Transnat'l L.271,307-13(1997).
④See,e.g.,William A.Schabas,Islam and the Death Penalty,9 Wm.&Mary Bill Rts.J.223,234(2000).
[1]吴云贵.伊斯兰教法概略[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2]Liaquat Ali Khan.Jurodynamics Of Islamic Law[J].231Rutgers Law Review.259-60(2009).
[3]黄金兰.法律移植与法律文化变迁——以伊斯兰法文化变迁为例[J].比较法研究,2007,5.
[4]米健等.当今与未来世界法律体系[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0.
[5]高鸿钧.伊斯兰法:传统与现代化[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
[6]Shannon V.Barrow.Nigerian Justice:Death-by-Stoning Sentence Reveals Empty Promises to the State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J].17 Emory Int'l L.Rev.1203(2003).
[7]贾士麟.消灭石刑:以生命的名义[J].报刊荟萃,2010,9.
[8]Michael Higgins and Adam McDowell.Iran's Stone-Age Justice System;The Plight of A Woman Condemned for Adultery Has Focused the World's Attention on a Barbaric Death Sentence Enshrined in Tehran's penal code[N].National Post(f/k/a The Financial Post)(Canada),November 20,2010 Saturday.
[9]Reza Aslan.The Problem of Stoning in the Islamic Penal Code:An Argument for Reform[J].3 UCLA J.Islamic&Near E.L.93-98(2003).
[10]Bonnie S.Fisher,Jenniefer L.Hartman,Francis T.Cullen and Michael G.Turner.Making Campuses Safer for Students:The Clery Act As A Symbolic Legal Reform[J].32 Stetson L.Rev.61(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