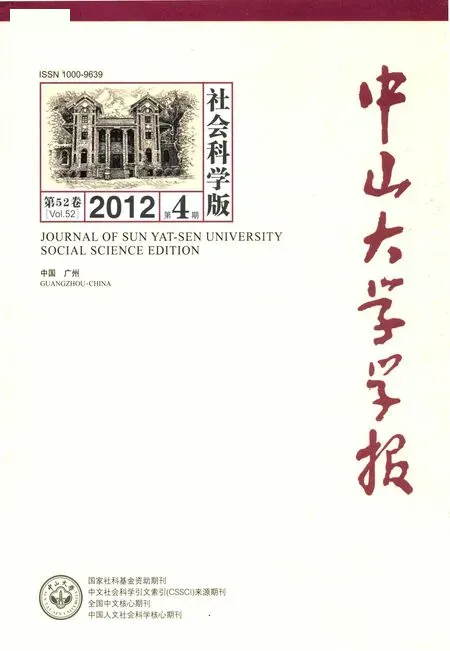“以数立言”与九言诗之兴*
——谢庄《宋明堂歌》文体新变考论
2012-01-24李晓红
李晓红
九言诗是古代诗歌中颇为特别的一体。它在汉魏时期出现后①前人有举《诗经·大雅·泂酌》“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夏书·五子之歌》“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诗九言,实皆偶见九言句,不可认同为九言诗。今可见最早通篇九言之作,乃翻译于东汉建安年间的佛经《修行本起经》九言偈颂。详参孙尚勇:《九言诗考》,《聊城大学学报》2005年第6期。,一直不受重视②南朝梁任昉《文章缘起》标举诗九言创始于魏高贵乡公曹髦(241—260),明代龚黄《六岳登临志》卷4《西岳华山》言魏道士王晖有九字诗,皆已佚。:历代文人曾指出其句式节奏“伤于大缓”③[日]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南·定位》,《文镜秘府论汇校汇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493页。、“不协金石”④颜延之:《庭诰》,《太平御览》卷586,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640页。、“不入歌谣之章”⑤挚虞:《文章流别论》,《太平御览》卷586,第2639页。的传播局限,以及其句式“长则意多冗,字多懈,其于文也亦难”⑥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全校本)》卷21《古人不用长句成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189页。、“牵于铺言足数,亦不能工”⑦张耒:《明道杂志》,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5页。、“最难自然协律”⑧陆以湉撰,崔凡芝点校:《冷庐杂识》卷5《九言诗》,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68页。之创作困难,导致“世希为之”①挚虞:《文章流别论》,《太平御览》卷586,第2639页。、“无用为全章”②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栾保群、吕宗力校点:《日知录集释(全校本)》,第1189页。、“九言不见”③颜延之:《庭诰》,《太平御览》卷586,第2640页。的存在状态。
在整体上趋于低迷的发展状况中,有两个时期出现例外:一是南北朝,一是清代。我们初步统计《中国基本古籍库》所收录文献中出现的通篇九言作品,一共得到110首:南北朝百余年间④若从刘宋武帝永初元年(420)算起至隋文帝灭陈(589),南北朝历史长约170年,但是九言乐府诗创始于谢庄《宋明堂·歌白帝辞》,作年在孝武帝孝建二年(455)后,至周庾信《周五声调曲·宫调曲四首》而止。持续时间实仅百余年。详见后文。存有8首,隋唐五代未见存作,两宋存2首,元代存1首,明代存11首,清代存88首。尽管存在文献亡佚、失收及统计偶然失漏等客观因素,但作为观察历代九言诗创作基本趋势的依据,这一统计数字当仍有合理处。此中年代较近的隋唐宋元时代罕见九言诗,而年代较远的南北朝留有8首完整九言诗作,不能不说是很特殊的;而与明代时代相接的清代,留存九言诗作是明代的8倍,也很引人注目。
有意思的是,南北朝与清代九言诗创作的勃兴现象,都与一种独特的诗歌创作方式——“以数立言”有关。下文拟对这种诗歌创作方式之始末及其对九言诗创作的具体影响展开探讨。
一、谢庄《宋明堂歌》五帝歌辞“以数立言”之体式创制
沈约(441—513)《宋书·礼志》载: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四月诏“经始明堂”,“六年正月,南郊还,世祖亲奉明堂,祠祀五时之帝,以文皇帝配,是用郑玄议也”⑤沈约:《宋书》卷16,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434页。,使谢庄(421—466)造明堂歌辞。《宋书·乐志》著录谢庄《宋明堂歌》:
《迎神歌诗》。依汉郊祀迎神,三言,四句一转韵。
《登歌词》。旧四言。
《歌太祖文皇帝词》。依《周颂》体。
《歌青帝词》。三言,依木数。
《歌赤帝辞》。七言,依火数。
《歌黄帝辞》。五言,依土数。
《歌白帝辞》。九言,依金数。
《歌黑帝辞》。六言,依水数。
《送神歌辞》。汉郊祀送神,亦三言。
右天郊飨神歌。⑥沈约:《宋书》卷20,第569—571页。
末句表明此套歌辞也应用于郊祀礼典。此中各篇都有体式说明,这在《宋书·乐志》中很罕见⑦沈约:《宋书·乐志》所录郊庙歌辞仅此一组有体式说明,其他歌辞也仅缪袭《魏鼓吹曲十二篇》、韦昭《吴鼓吹曲十二篇》二组有体式说明。,凸显此套歌辞体式之独特:“迎、送神歌”依汉代郊祀迎、送神歌辞体式,《歌太祖文皇帝词》依《周颂》体,《登歌词》用“旧四言”,都是依循旧制;但祭祀五帝的歌辞却不言依旧制,转称依“水、火、木、金、土”数立言⑧前揭孙尚勇《九言诗考》一文曾指出谢庄创立以五行数制作郊庙歌辞的传统,但认为其对后世诗歌影响不大,与本文视角不同,可参。,且在“依金数”名义下运用了前人认为“不协金石”、“不入歌谣之章”的九言体造作《歌白帝辞》:
百川如镜天地爽且明,云冲气举德盛在素精。
木叶初下洞庭始扬波,夜光彻地飜霜照悬河。
庶类收成岁功行欲宁,浃地奉渥罄宇承秋灵。①沈约:《宋书》卷20,第570页。按点校本原断为四五杂言体,此据其体式说明“《歌白帝辞》。九言,依金数”改断为九言体。
对于这种体式创制现象,萧子显(487—537)《南齐书·乐志》曾展开探讨:
明堂歌辞,祠五帝。汉郊祀歌皆四言,宋孝武使谢庄造辞,庄依五行数,木数用三,火数用七,土数用五,金数用九,水数用六。案《鸿范》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月令》木数八,火数七,土数五,金数九,水数六……若依《鸿范》木数用三,则应水一火二金四也;若依《月令》金九水六,则应木八火七也。当以《鸿范》一二之数,言不成文,故有取舍,而使两义并违,未详以数立言为何依据也。②萧子显:《南齐书》卷11,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172页。
从中可见《宋明堂歌》五帝歌辞“以数立言”有如下几个独特之处:
其一,汉代祭祀五帝歌辞皆是四言体③杨宁曰:“汉人《郊祀乐歌》,享五帝用成数,则‘金天白帝’九言,‘太昊青帝’八言。”(《日知录集释》卷21引,第1190页)似以汉乐府五帝歌辞即有“以数立言”之例,且有八言、九言之作。按前引挚虞称九言“不入歌谣之章”、颜延之称九言“不协金石”,皆以乐府歌谣不用九言。今存汉乐府歌诗也无九言者,杨宁之说疑误。,谢庄不依旧制,转依五行数立言造作新的歌辞体式。按《周礼》已有“祀五帝”之说④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2,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版,第649页。,西汉武帝举行过祀五帝礼典,司马相如等所造郊祀歌诗十九章中《帝临》、《青阳》、《朱明》、《西颢》、《玄冥》⑤歌辞见班固:《汉书》卷22《礼乐志》,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054—1057页。即汉代祀五帝之辞⑥详参顾颉刚:《汉代学术史略》第18章《祀典的改定和月令的实行》,《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顾颉刚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87—88页;王福利:《汉郊祀歌中“邹子乐”的含义及其相关问题》,《乐府学》第3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年,第95页;郭思韵:《汉郊祀歌的“邹子乐”与东汉两用〈朱明〉小议——兼论与〈帝临〉之关系》,《中国典籍与文化》2011年第3期。。东汉以来祭祀五帝礼典继续发展⑦详参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第4章《吉礼》“祀天帝·大飨明堂”,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90页;张一兵:《明堂制度源流考·秦汉明堂制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03—104、129—130页。,这些歌辞一直沿用⑧详参郭茂倩:《乐府诗集》卷1《郊庙歌辞》序,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1—2页。。谢庄对此并不陌生,《宋明堂歌》中“迎、送神歌”的文体即依汉旧制,惟独祭祀五帝歌辞不用旧制,显然是特意的体式新变。
其二,谢庄所依五行数与《鸿范》、《月令》之五行数系统不全相合:除《歌黄帝辞》依土数五与《月令》、《鸿范》土数合外,《歌青帝辞》依木数三,与《月令》木数八相违;《歌赤帝辞》依火数七,《歌白帝辞》依金数九,《歌黑帝辞》依水数六,与《鸿范》火二、金四、水一之数相违。
其三,萧子显推断谢庄所依五行数是在《鸿范》、《月令》中依违取舍而来:《歌白帝辞》、《歌黑帝辞》取《月令》水六、火七之数。因为《鸿范》水一、火二,立言将成一言句、二言句,“言不成文”,故舍之。但按此逻辑,还存在难以解释之处:从《鸿范》金数四、《月令》金数九看,“依金数”之《歌白帝辞》,有四言体、九言体可选用。按四言体《诗经》常用,汉郊祀五帝歌辞皆用四言,晋代以来更有“雅音之韵,四言为言(一作‘正’)”⑨挚虞:《文章流别论》,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56,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年,第1018页。之观念;而九言体却是“世希为之”乃至“不见”的陌生文体,且“声度阐诞,不协金石”。无论从《宋明堂歌》这样的“雅音之韵”考虑,还是从“成文”便利考虑,都当以四言为优选。谢庄却弃四言而取九言,在郊祀礼典这样的庄重场合使用既往认为“不入歌谣之章”的九言体作歌辞,显然是一种特意而大胆的创制。
二、“以数立言”造作祭祀五帝歌辞的原因与寓意
谢庄《宋明堂歌》为何会有如此特意的体式创制?前人有过探讨。萧子显称“不详以数立言何据”。宋代陈旸则直接批评道:“凡此率皆傅会五行之数而强合之,岂感物吟志、本于自然之意哉。”①陈旸:《乐书》卷160《乐图论·俗部》“歌·诗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211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740页上栏。后王质曾加以辩解,他通过论证《诗经·颂》之句式皆一、二、三、四、五言,乃取数于《鸿范》五行,提出:“九畴初五行,万事无不由之而出,谢庄亦有所自来也。”②王质:《诗总闻》卷19《闻颂三》,《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2册,第714—715页。但今可见两晋南北朝文献多有语及《诗经》六言、七言句式,似无以《诗经》句式取数于五行之说。笔者以为,谢庄“以数立言”之创制,主要是传统的祭祀礼仪规范、魏晋以来礼仪歌辞文体观念、宋孝武帝朝制礼作乐的风气与谢庄自身礼乐文化取向的选择结果。
(一)“以数立言”与“礼神者必象其类”的祭祀礼仪
如前所述,《宋明堂歌》是因应宋孝武帝“亲奉明堂,祠祀五时之帝”礼典需求所制的礼乐歌辞,寄寓礼典的礼仪内涵,“以数立言”造作祭祀五帝歌辞,乃是表现礼仪的需要。
这从《宋明堂歌》祭祀五帝歌辞体式与汉郊祀五帝歌辞的体式区别中可以见出。汉郊祀歌五帝辞是纯然划一的四言体,而谢庄所造作歌五帝辞各篇皆独具形式:《歌青帝》三言、《歌赤帝》七言、《歌黄帝》五言、《歌白帝》九言、《歌黑帝》六言。诸篇在句式字数上与所歌咏对象的五行数相同,表现出祭祀歌辞的文体样式与祭祀对象一一对应的关系。这其实是一种源自《周礼》的祭祀礼仪,如《周礼·春官·大宗伯》载:
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皆有牲币,各放其器之色。③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18,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762页。
其祭祀所用礼器,皆具有与其祭祀对象身份、性状的对应性。如天色苍而圆,“礼天”的“苍璧”即是玉色苍且形“圜象天”的;地色黄而方,“礼地”的“黄琮”即是玉色黄而形“八方象地”的④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18,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762页。。这种祭祀礼器选用原则⑤这样明确的祭物与祭祀对象匹配的意识形成于何时,目前尚无确论。夏鼐提出:“《周礼》是战国晚年的一部托古著作。我以为这书中关于六瑞中各种玉器的定名和用途,是编撰者将先秦古籍记载和口头流传的玉器名称和他们的用途搜集在一起;再在有些器名前加上形容词成为专名;然后把它们分配到礼仪中的各种用途上。这些用途,有的可能有根据,有的是依据字义和儒家理想,硬派用途。这样他们便把器名和用途,增减排比,使之系统化了。”《商代玉器的分类、定名和用途》,《考古》1983年第5期。,郑玄概括为“礼神者必象其类”⑥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18,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762页。。
祭祀礼典确定礼器的依据是“象其类”,用于祭祀礼典上的歌辞,本质上是一种“礼器”,也应讲求“象其类”。宋孝武帝朝祭祀五帝礼典“是用郑玄议也”。按郑注“五帝”:“苍曰灵威仰,大昊食焉;赤曰赤熛怒,炎帝食焉;黄曰含枢纽,黄帝食焉;白曰白招拒,少昊食焉;黑曰汁光纪,颛顼食焉。黄帝亦于南郊。”⑦郑玄注,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卷19《春官·小宗伯》“兆五帝于四郊”注,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766页。采纳的是汉代纬谶学说之五帝观念,认为五帝依着五行的方位、颜色和季候而各有不同⑧详见周予同:《纬谶中的“皇”与“帝”》三《“五天帝”与“五人帝”》,朱维铮编:《周予同经学史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91—292页。。五行各有其数,五帝当然也随之各具不同的数字属性,谢庄作祭祀五帝歌辞各篇句式字数因而相应不同。换言之,谢庄是因应“礼神者必象其类”的礼仪需求才选择依五帝之五行数立言造辞的。
但如萧子显所言,五行数有不同的系统。《鸿范》:“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月令》:“木数八,火数七,土数五,金数九,水数六。”谢庄《歌白帝辞》依金数,若从“成文”的角度考虑,应选择《鸿范》金数四,排除《月令》金数九,才可避免“牵于铺言足数,亦不能工”的九言体式。为何谢庄却取“金数九”而舍“金数四”?
笔者以为,谢庄《歌白帝辞》依金数九立言,不依金数四,仍是因应白帝身份的一种礼仪创制。不仅《歌白帝辞》,整组祭祀五帝歌辞,所选用的五行数,皆是祭祀对象的身份象征。谢庄“依五行数,木数用三,火数用七,土数用五,金数用九,水数用六”,象征了五帝在五时的生成之功。按汉董仲舒言:“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①苏舆:《春秋繁露义证》卷10《五行对》,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314页。而五帝居五时,青帝在春,主生;赤帝在夏,主长;黄帝在季夏,主养;白帝在秋,主收;黑帝在冬,主藏。《南齐书·乐志》谢朓《雩祭歌》五帝歌辞体式说明曰:
《歌青帝》木生数三。
《歌赤帝》火成数七。
《歌黄帝》土成数五。
《歌白帝》金成数九。
《歌黑帝》水成数六。
谢朓所用之数“一依谢庄”②萧子显:《南齐书》卷11,第172页。。此中仅《歌青帝》用生数,表明青帝主生,而赤帝、黄帝、白帝、黑帝非主生者,皆用成数。可见谢庄选用五行数,非为简单求“成文之便”而从《鸿范》、《月令》五行数中随意取舍,而是与五帝身份密切对应的礼仪表征。《歌白帝辞》依金数九,不取金数四,是因为四乃生数,不合白帝在秋天主万物收成之身份。
谢庄《宋明堂歌》祭祀五帝歌辞体式所依五行数分辨生数与成数,其思路实也源自“用郑玄议”。郑玄经注分辨五行之生数、成数,其注《礼记·月令》“孟春之月……其数八”曰:“数者,五行佐天地生物成物之次也……木生数三,成数八,但言八者,举其成数。”③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1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354页上栏。又注“中央土……其帝黄帝……其数五”曰:“中央土火休而盛德在土也……土生数五,成数十。但言五者,土以生为本。”④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卷16,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372页中栏。皆是其例。值得一提的是,谢氏《歌黄帝》依“土成数五”,与郑注“土生数五,成数十”之说不同,表现出《黄帝内经素问》“土生数五,成数亦五”⑤《黄帝内经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有“土常以生”之说,唐王冰次注:“数谓五常化行之数也,水数一,火数二,木数三,金数四,土数五。成数谓水数六,火数七,木数八,金数九,土数五也。故曰‘土常以生’也。”(王冰:《重广补注黄帝内经素问》卷21,《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733册,第269页下栏)的观念。此或为郑注《月令》“土以生为本”之说采纳《素问》“土常以生”学说,在进入南朝后《素问》五行观念进一步渗透到经学中的表现⑥南朝儒学存在“金木水火得土而成”之观念。孔颖达《礼记注疏》卷14《月令》载:“皇氏(侃)用先儒之义,以为金木水火得土而成,以水数一得土数五故六也,火数二得土数五为成数七,木数三得土数五为成数八,又金数四得土数五为成数九。此非郑义,今所不取。”尽管孔颖达以为此非郑玄义,然而皇侃持此说,说明其时经学观念如此。宋代沈括尚以此说有理,详参《梦溪笔谈》卷7。。
要之,谢庄“以数立言”造作祭祀“五时之帝”的歌辞,乃至选用金数九立言造作九言体《歌白帝辞》,皆是“用郑玄议也”的礼典礼仪需要:依五时之帝所居季节物候,选定相应的五行生数、成数立言,作成一套与汉郊祀歌整齐划一四言体式迥异的、能在文体样式上“象”五帝之“类”的祭祀五帝歌辞新体式。这是郑注《周礼》“礼神者必象其类”的祭祀礼仪规范在祭祀歌诗外在文体样式上的表征,故而与其说它是一种文体样式的新创,毋宁说是一种祭祀礼仪的创制。
(二)魏晋文章体式观念与传统礼典歌诗文体礼仪的互动
礼典歌诗在中国古代有悠久传统,礼典礼仪要求“歌诗必类”①杜预注《左传·襄公十六年》“歌诗必类”曰:“歌古诗,当使各从义类。”见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卷33,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1963页上栏。。《宋明堂歌》中“以数立言”的五帝歌辞,还是魏晋以来文体观念与礼典歌诗礼仪的内在互动的一种结果。
魏晋以前的歌诗文体之“类”,注重文辞内容之“义类”,指歌诗在文辞内容上“必须能准确明白地表达出赋诗之人的思想感情,同时,这一思想感情又必须符合当时的场合、气氛、双方的身份以及谈话的主旨等等”②陈绂:《“断章赋诗”与“歌诗必类”——浅析〈左传〉赋诗的特点》,《文史知识》1995年第1期。。从先秦时代燕飨、外交仪式上用诗,到汉魏时期的郊庙乐府,都主要讲究歌辞内容,对歌辞外在的文体样式不甚注意。如汉郊祀歌五帝辞《青阳》、《朱明》、《帝临》、《西皓》、《玄冥》都是四言体,外在文体样式上看不出与歌颂对象有何相“类”性;但内容上则“各从义类”,如《青阳》描绘青帝所在春季的物候;《朱明》描绘赤帝所在夏季的物候,皆表现出歌辞与所祭祀对象的“象类”关系。可以说,依照文辞内容来判断歌诗是否“象其类”、“得事体”,是其时礼典歌诗的评判标准。汉人言及一般文章的“文体”,也往往指其内容义理,如曾与郑玄同时代的卢植评郦炎“著述十余箱,文体思奥,烂有文章”③虞世南编撰:《北堂书钞》卷99“箴缕百家”条注引卢植《郦文胜诔》语,北京:中国书店,1989年,第377页上栏。,所谓“文体思奥”即指所著文章内容切实、义理深奥。
魏晋之际,歌诗的外在文体样式日益为人所注意。如西晋泰始五年(269)尚书奏使傅玄、荀勖、张华各造乐歌诗,张华(232—300)表曰:“按魏上寿食举诗及汉氏所施用,其文句长短不齐,未皆合古。”④沈约:《宋书》卷19《乐志》,第539页。荀勖(217?—288)则曰:“魏氏哥诗,或二言,或三言,或四言,或五言,与古诗不类。”⑤沈约:《宋书》卷19《乐志》,第539页。皆是针对礼典歌辞外在文体样式的批评,可见外在的文体样式已成为评判歌诗之象不象“类”的重要依据。时人区判歌诗类别,也有以诗之句式字数为区分标准者。如挚虞(?—311)《文章流别论》称:“诗之流也,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九言。古诗率以四言为体。”⑥挚虞:《文章流别论》,欧阳询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56,第1018页。刘义庆《世说新语》载谢安(320—385)问王子猷“云何七言诗”,子猷答曰:“昂昂若千里之驹,泛泛若水中之鳬。”⑦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973页。皆是以句式字数区判诗体类别,这使得歌诗的外在文体样式与数建立了联系。
《宋明堂歌》五帝歌辞各篇句式字数一一对应其歌颂对象的五行数,可谓是以句式字数区判歌诗之“类”的观念产物。中国古代的礼典礼仪一贯讲究用数,有所谓“礼数”之说。礼数有其象征性,如前文所论用五行数象征五帝的身份。因此无论是礼器,还是礼节,都有一定数的规定。只有行礼者的礼数与其名位及欲表现的礼意相符,才能恰当地揭示礼的形式及其内容之间的显现与被显现关系⑧详参梅珍生:《论礼数与礼意的统一》,《中国地质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这在明堂制度中表现得尤其明显。郑玄以周人明堂五室,合于五行之数,周礼依数以为之室⑨参看魏收:《魏书》卷69《袁翻传》“明堂议”,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1537页。。蔡邕《明堂月令论》称“其制度之数,各有所依”,如“堂方伯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圜屋径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⑩蔡邕:《蔡中郎集》卷10,《四部丛刊》本。。总之,“依数”是明堂制礼的一个原则。《宋明堂歌》五帝歌辞“以数立言”,是明堂“制度之数,各有所依”的自然延伸。
汉郊祀五帝歌辞皆用四言,仅通过歌辞内容表现与祭祀对象的对应关系,歌辞体式未被视为区别文类的标准。《宋明堂歌》五帝歌辞各篇均以独特文体样式象征五帝身份,显示出歌辞外在样式也具有礼仪意义,折射出文体样式在时人眼中已具独特地位。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所谓“魏晋文学自觉”,不仅仅是“文学性”、“抒情性”的自觉⑪王南:《“文学性”与“文学自觉说”》,《文艺研究》2010年第9期。,还有文章体式的自觉。人们从单一关注文章的内容,到关注文章的外在文体样式,一步步丰富文章的文体观念。这种文体观念的发展,反过来促成祭祀歌诗的文体/礼仪变革,即文章的外在体式也参与到“国之大事”——“祀”①《左传·成十三年》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宋书·礼志》也加以标举,见沈约:《宋书》卷16,第419页。之礼典中来,可谓文体自觉后的“文章经国之大业”②曹丕《典论·论文》语,萧统:《文选》第6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点校本,第2271页。。
(三)“以数立言”造作五帝歌辞与宋孝武帝朝礼乐制度的“复古与创新”
传统“礼神者必象其类”祭祀礼仪、“制度之数,各有所依”的明堂礼制及挚虞以诗句字数区别诗体类别的观念,是促成谢庄“以数立言”造作五帝歌辞的理论背景。但此背景至迟在挚虞生活的时代已成立,发挥作用却是在挚虞逝世后近一百五十年的刘宋孝武帝朝③虽然晋初明堂及南郊除五帝之位(沈约:《宋书》卷16《礼志》;房玄龄等:《晋书》卷19挚虞“庚午诏书”)不需考虑造作祭祀五帝歌辞,但太康十年(289)“复明堂及南郊五帝位”(沈约:《宋书·礼志》)也未见“以数立言”的歌辞。。这说明谢庄“以数立言”造作祭祀五帝歌辞,还是当朝制礼作乐的选择。在谢庄之前,由于《诗经》、汉郊祀歌等四言经典体式的影响,荀勖“造晋哥,皆为四言”④沈约:《宋书》卷19《乐志》,第539 页。,谢庄特意改易汉郊祀歌四言旧制,与宋孝武帝朝制礼作乐“复古与创新”的选择相关⑤借用阎步克评宋明帝朝冕服制之语,详参氏著:《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第7章《南朝冕服的复古与创新》,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
刘宋孝武帝朝从一开始便有“复古与创新”的制礼之举。《宋书·礼志》载孝建元年(454)朝议平刘义宣、臧质之乱的出入礼。按此前宋文帝时礼典旧例,出时告二郊、庙社,入时告庙社而不告二郊。孝武帝朝臣议入同告庙社、二郊。但入告二郊之礼为前例所无,时国子助教苏玮生提出:尽管《礼记》载天子巡狩“归,假于祖祢”,未言入告二郊,但《礼记》也载“诸侯适天子,告于祖,奠于祢,命祝史告于社稷宗庙山川,告用牲币,反亦如之”,又有郑玄说过“出入礼同”。苏玮生认为:“天子诸侯,虽事有小大,其礼略钧,告出告至,理不得殊……应推例求意……宜并用牲告南北二郊、太庙、太社。”宋孝武帝“诏可”⑥此议始末见沈约:《宋书》卷16,第426—427页。。此一决议,遵照郑玄所谓“出入礼同”之说,可谓“复古”;而创设《礼记》所无的天子巡狩入告二郊庙社之举,又属“创新”。
这种复古与创新,寄寓着宣告宋孝武帝朝政治合法性目的⑦杨英曾指出上古礼制一般是在即位后行告天礼,讨逆的礼仪只有献俘礼:“刘宋讨逆取胜后告天完全是凭藉经义的自创,这其中蕴含着自身行为合法,让天知晓的意义。”(《刘宋郊礼简考》,《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回顾与探索》,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398页)即推行前朝所无的讨逆归告天礼,与昭告孝武帝刘骏讨伐其叔父刘义宣合法性的政治目的有关。此盖孝武朝礼典革新的深层原因所在。,符合宋孝武帝的需要,易获得认可。如孝建二年(455)九月,荀万秋议“郊庙宜设备乐”。一向为孝武帝所倚重的权臣颜竣不赞同设乐,建平王刘宏则认为不妨设乐。颜竣的依据有《礼记·郊特牲》“扫地而祭,器用陶匏”甚为质素,未必设乐;《周礼·春官·宗伯》“奏黄钟,哥大吕,舞云门,以祀天神”之天神“又非天地”等,总之是“考之众经,郊祀有乐,未见明证”。刘宏从不同角度解读颜竣所据经典,称《礼记》所载只是说明郊天礼器质素,但“不害以乐降神”。《周礼》所言“天神”,即是天的别称,《周礼》载设乐祀天神,表明古有设乐祀昊天五帝⑧按郑玄注“天神”指“五帝及日月星辰也”,“五帝”是昊天在不同季节的身份别称;而魏王肃则认为五帝非天,昊天只有一个(郑、王不同说法见《礼记注疏·郊特牲》孔颖达疏)。颜竣持王肃说,认为《周礼》设乐所祀“天神”非天;刘宏持郑玄说,认为“天神”即指天。。结果群臣赞同刘宏之驳议,孝武帝诏可郊庙设乐⑨关于此一争论始末详见沈约:《宋书》卷19,第543—545页;本文前言《宋明堂歌》也用于天郊飨神,盖是在郊庙设乐礼议通过后的便用之。。这从郑注《周礼》设乐“祀天神”的角度看,是“复古”;从《礼记》郊天质素传统看,可谓“创新”。
谢庄“以数立言”造作《宋明堂歌》五帝歌辞,正是在孝武帝朝这种“复古与创新”的制礼作乐风气下形成的。《宋书·礼志》载宋孝武帝与其礼官们“详考姬典,经始明堂”,“依汉汶上图仪,设五帝位”,“用郑玄议”①沈约:《宋书》卷16,第 434 页。。在五帝歌辞的造作上,却不依汉五帝歌辞的四言体,转而依数立言,以至于用既往“不入歌谣之章”的九言体造《歌白帝辞》,可谓“创新”;然衡之以“礼神者必象其类”的祭祀礼仪、“歌诗必类”的歌诗礼仪、“制度之数,各有所依”的明堂礼制,又皆能相合,不无“着意遵古的明确意向”;其对五行生数、成数之别择,也堪称自出心裁而又“象数是遵”②沈约《宋书·礼志》载宋明帝泰始四年诏中语,见《宋书》卷18,第525页。。这种创意想必对宋明帝朝冕服制的“复古与创新”产生过导夫先路的作用③阎步克考察宋明帝时舆服制度,指出其源于《周礼》又超越了《周礼》,如冕制“象数是遵”,汉伏生《尚书大传》有五行五色思想,按照黄、黑、白、赤、青五种颜色,把服章分为五组五等,宋明帝则把“五采”用于皇帝冕缫的分等了,表现出“着意复古的明确意向”和“‘制度创新’的强烈欲望”(详参前揭《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第259—260页)。这与《宋明堂歌》体式创意颇近似。。
(四)九言体《歌白帝辞》的出现与陈郡谢氏之礼乐学养
“以数立言”造作《宋明堂歌》五帝歌辞,还与谢庄这一具体创作者有很大关系,这从其中《歌白帝辞》采用九言体一事上可约略推见。
从《歌白帝辞》出现的时间看,按宋孝武帝大明五年(461)四月诏“经始明堂”,《宋明堂歌》理应作于此时。但由于《宋明堂歌》同用于“天郊飨神”,按《通典·乐志》载:“孝武孝建二年(455),有司奏:‘前殿中曹郎荀万秋议,郊庙宜设乐。’……孝武又使谢庄造郊庙舞乐、明堂诸乐歌辞。”④杜佑:《通典》卷141,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标点本,第3600页。则祀五帝歌辞很可能是孝建二年郊庙设乐时所制⑤曹道衡、刘跃进《南北朝时期文学编年》系此篇作年在孝建元年(454),并考订曰:“《宋明堂歌九首》,见《通典》卷一四一。按《通典》作‘孝武建元元年’云云,误。当据《南齐书·乐志》作孝武帝孝建元年。”(《南北朝文学编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167页)今核中华书局点校本《通典》卷141,无“孝武建元元年”语,《南齐书·乐志》也仅载“宋孝武使谢庄造辞”,未确指孝建元年。不知曹、刘所说何据。。总之,无论是455年还是461年,都可谓与颜延之(384—456)论“《柏梁》以来,继作非一,纂所至七言而已。九言不见者,将由声度阐诞,不协金石”⑥颜延之:《庭诰》,《太平御览》卷586,第2640页。之说处在同一时期,表明时人已意识到九言体协律之难。谢庄自年少即以“别宫商,识清浊”闻知于世⑦范晔、王融、钟嵘皆曾嘉许之。详参王运熙:《谢庄作品简论》,《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其个人诗文创作甚为讲究音律美⑧详参徐明英、熊红菊:《谢庄诗歌律化初探——兼与刘跃进先生商榷》,《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第1期。,对九言体“声度阐诞”的音律弱点能够体会,其传世作品中未见有其他九言作品。九言体《歌白帝辞》的出现,设若仅是孝武帝及其礼官们的选择,谢庄只是应诏制辞,那么由他来创制既往“不入歌谣之章”的九言体乐歌,也说明了谢庄被公认在处理九言歌辞与金石器乐的协和问题上具有超越时辈乃至前人的能力。
而这一点,是谢庄及其家族陈郡谢氏所在意的。谢庄的先人谢尚(308—356)“善音乐,博综众艺”⑨房玄龄等:《晋书》卷79《谢尚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2069页。,曾在镇寿阳时组织“邺下乐人”为朝廷“具钟磬”(10)沈约:《宋书》卷 19《乐志》,第 540,540 页。,“雅乐始颇具”(11)房玄龄等:《晋书》卷23《乐志》,第698页。;谢安“性好音乐”(12)房玄龄等:《晋书》卷79,第2075页。,其辅政时,子侄谢玄、谢琰等破苻坚,获“乐工杨蜀等,闲练旧乐,于是四箱金石始备焉”(13)沈约:《宋书》卷 19《乐志》,第 540540 页。。可以说东晋乐府是谢尚、谢安主持创制完成的。又谢安辅政“时宫室毁坏,安欲缮之。尚书令王彪之等以外寇为谏,安不从,竟独决之”,盖宫室是《周礼》非常重视的礼制内容之一。谢安用漂来之梅木为梁,“画花于梁上以表瑞”①详参许嵩:《建康实录》卷9“烈宗孝武皇帝·(太元)三年(378)春正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标点本,第265—266页。,“宫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体辰极,而役无劳怨”②房玄龄等:《晋书》卷79,第2074,2075,2077页。,表现出其在传统礼制、谶纬符瑞方面的文化取向与知识积累。进入南朝,谢氏子弟虽然在武人政权中屡遭打击,但仍以其家世学养,占据文化上的优势地位。如刘裕在杀害依附其政敌刘毅的谢混(谢安之孙)后,“登坛日恨不得谢益寿奉玺绂……使后生不得见其风流”③房玄龄等:《晋书》卷79,第2074,2075,2077页。,结果仍以谢安的另一个孙子谢澹“持节奉册禅宋”④房玄龄等:《晋书》卷79,第20742075页。。可见初由武功起家、文化水平不高的统治者也倾慕陈郡谢氏的文化威仪,而谢氏子弟也正是通过职掌“奉玺绂”等礼制典章来表现与维护其文化上的尊崇地位。继承谢安文化遗产的谢庄⑤按谢庄父谢弘微十岁过继为谢峻子,谢峻乃谢安之孙、谢琰之子。《宋书·谢弘微传》:“弘微家素贫俭,而所继丰泰,唯受数千卷书、国吏数人而已。”(沈约:《宋书》卷58,第1590页)谢安、谢琰之礼乐文化遗产即随这“数千卷书”及熟悉谢安制礼风格的“国吏数人”传至谢庄。为宋孝武帝朝造郊庙舞乐、明堂诸乐歌辞,“以数立言”,用“不协金石”的九言体作《歌白帝辞》。其体式之新,所牵涉知识门类之广,堪称“辞必穷力而追新”⑥詹锳:《文心雕龙义证·明诗篇》,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08页。与“知识至上”⑦胡宝国:《知识至上的南朝学风》,《文史》2009年第4期。,透露出谢庄这样的一流高门士族子弟在南朝武人政权下努力维护其文化地位的姿态。
三、“以数立言”制辞方式的传播与九言诗创作之勃兴
谢庄“以数立言”造作的祭祀五帝歌辞,尽管是应宋孝武帝诏制,但并不是人们习惯所认为的“歌颂帝王功德,文辞板重枯燥”⑧王运熙:《谢庄作品简论》,《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之作。从前引《歌白帝辞》来看,虽是运用“声度阐诞,不协金石”的九言体,但通篇句句押韵,两句一转韵,声情绮靡,文辞优美动人。如“木叶初下洞庭始扬波”一句脱胎自《九歌·湘君》“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化用楚人祭祀湘君之辞,不仅切合其祭祀秋灵白帝之题旨,且使得本篇与楚歌的抒情传统获得沟通,营造出诗情;“夜光彻地飜霜照悬河”一句以夜光下飞霜悬河之景写秋月之明,足见以《月赋》脍炙人口的谢庄“工于写景”⑨王运熙:《谢庄作品简论》,《南阳师范学院报》2002年第3期。的创作特色。其他诸篇也都大致如此,不仅从内容到形式都做到“礼神者”“象其类”,而且具备魏晋以来所推崇的“诗赋欲丽”的艺术特质。这套乐府歌辞体现出谢庄在礼学和文学上的独到造诣,也代表了刘宋时代礼乐文化的新发展。它随着礼乐的传播对南北朝乐府歌诗乃至九言诗创作都产生了影响。
(一)“以数立言”与南北朝后期之礼典乐歌
萧齐的乐府制辞沿用“以数立言”。《南齐书·乐志》载:“(齐)建元初,诏黄门郎谢超宗造明堂夕牲等辞,并采用庄辞。建武二年,雩祭明堂,谢朓造辞,一依谢庄。”(10)萧子显:《南齐书》卷11,第172页。可见其时明堂、雩祭等礼典歌辞仍为谢氏子弟所制,谢超宗、谢朓皆沿谢庄旧制,“以数立言”造作祭祀五帝歌辞。如谢朓《雩祭歌·白帝歌》:
帝悦于兑执矩固司藏。百川收潦精景应徂商。嘉树离披榆关命宾鸟。夜月如霜秋风方嫋嫋。商阴肃杀万宝咸亦遒。劳哉望岁场功冀可收。
右《歌白帝》,金成数九。(11)萧子显:《南齐书》卷11,第177页。原点校本断为四五杂言,今依谢庄例改断为九言。
是同样“依金数九”、运用九言体造作的歌辞。
谢庄、谢超宗、谢朓接连为宋、齐朝廷制作礼乐,确立了“以数立言”造作祭祀五帝歌辞的新礼仪。作为“南朝前半期之文物制度”①参看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3—16,13,14—16页。之一,在北魏孝文帝汉化追求中被引进北朝。《隋书·音乐志》载:
(北)齐神武霸迹肇创……咸遵魏典……其后将有创革,尚乐典御祖珽自言,旧在洛下,晓知旧乐。上书曰:“……永熙中,录尚书长孙承业,共臣先人太常卿莹等,斟酌缮修,戎华兼采,至于钟律,焕然大备……今之创制,请以为准。”珽因采魏安丰王延明及信都芳等所著乐说,而定正声……武成之时,始定四郊、宗庙、三朝之乐……《五郊迎气乐辞》:青帝降神,奏《高明乐》辞:“岁云献,谷风归……”赤帝降神,奏《高明乐》辞:“婺女司旦,中吕宣。朱精御节,离景延……”黄帝降神,奏《高明乐》辞:“居中匝五运,乘衡毕四时……”白帝降神,奏《高明乐》辞:“风凉露降驰景飏寒精。山川摇落平秩在西成……”黑帝降神,奏《高明乐》辞:“虹藏雉化,告寒。冰壮地坼,年殚……”②魏征:《隋书》卷14,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点校本,第313—318页。
此中祖珽所造《北齐五郊迎气乐辞》之体式,与谢氏所造作宋齐祭祀五帝歌辞体式全同③梅鼎祚《古乐苑》卷3录北齐《五郊乐歌》题注称“此五歌亦如宋谢庄用五行数”(《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395册,第37页),是。。陈寅恪先生曾论“北齐仪注即南朝前期文物之蜕嬗”④参看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3—1613116页。,此套歌辞可作一证。祖珽之父祖莹曾与北魏太和十七年(萧齐永明十一年,493)由南齐北奔的王肃(464—501)同时立朝⑤魏收:《魏书》卷82,第1799 页。。王肃熟习南朝前期礼乐制度,受北魏孝文帝重用,有“朝仪国典咸自肃出”之说⑥参看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第3—1613116页。。祖莹好学博物,当从王肃处获悉宋齐礼乐信息。祖珽因得以传承“以数立言”的造辞方式,“依金数九”制成九言体《白帝高明乐辞》。
“以数立言”的制辞方式在以《周礼》立国的北周王朝也有所见。由萧梁入北的庾信(513—581)为北周造《周祀五帝歌》⑦歌辞见郭茂倩:《乐府诗集》卷4,第48—50页。:《青帝云门乐》三言、《赤帝云门乐》七言、《黄帝云门乐》五言、《黑帝云门乐》六言,皆同谢氏;惟《白帝云门乐》改用四言体,与谢氏《歌白帝》用九言体不同,但这套歌辞“以数立言”可以无疑。不仅如此,庾信为北周元正飨会大礼作《周五声调曲》⑧歌辞见郭茂倩:《乐府诗集》卷15,第211—216页。也“以数立言”,且纯依《月令》五行数,如其中歌咏民德的《角调曲》二首依照“角属木”、“木数八”立言,显然也是通过“以数立言”表现乐歌体式与歌咏对象对应的礼仪⑨庾信造《周祀五帝歌》、《周五声调曲》,所依之数皆未“一依谢庄”,此与其自身文化取向有关,因非关本文主旨,兹不赘。其依“木数八”立言创制的《角调曲》八言诗在诗体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详参拙文:《论八言诗及其相关问题》,《学术研究》2009年第9期。。而其中歌咏臣德的《商调曲四首》,依“商属金”、“金数九”立言,再次以九言体造歌诗。
(二)从九言乐歌到颂圣诗
从谢庄至庾信,南北朝乐府在“以数立言”制辞方式的名义下,创作了多篇九言乐府歌诗。在谢庄前,挚虞指出九言“不入歌谣之章,故世希为之”,颜延之已称“九言不见”。谢庄、谢朓等九言乐歌创制,客观上促成九言体式在南北朝文坛的创作实践与传播。从梁简文帝《玄圃纳凉诗》“夜月似秋霜”化用谢朓《歌白帝》“夜月如霜秋风方嫋嫋”一句看,这些用于祭祀礼典的九言乐歌对同时期的一般诗文创作也产生了影响。宋张耒言“尝读《沈休文集》中有九言诗”(10)张耒:《明道杂志》,第5页。,或为齐梁时人独立创作九言诗之例(11)南朝以来的诗体观念中,乐府歌辞与一般诗作稍有分别。如萧统《文选》在“诗”类中别立有“乐府”、“杂歌”、“杂诗”等子目。张耒论沈约集中九言诗,却未言及谢庄、谢朓、庾信等人之九言乐府歌辞;严羽《沧浪诗话》论诗体沿袭梁任昉《文章缘起》之说,诗九言与乐府别立。大约宋人仍持乐府与诗相别之观念。据中华书局1990点校本《张耒集》前言,张耒的诗文集在他生前已经行世,今存传钞本大体是按文体编排。四部丛刊影印旧钞本《张太史集》中“古乐府歌辞”与“古诗”别立,或可佐证张耒所言沈约集九言诗为一般诗作,非乐府歌辞。。梁任昉《文章缘起》举秦汉以来文章,标立“诗九言”(12)见陈元靓:《事林广记》后集卷7“辞章类”,《续修四库全书》第1218册,第354页上。一体;萧统《文选序》称“诗者……四言、五言,区以别矣。又少则三字,多则九言,各体互兴,分镳并驱”①萧统:《文选》第1册,第2页。,说明其时文坛已告别“九言不见”的状况。
萧梁乐府不再“以数立言”②《隋书·音乐志》载萧梁武帝“思弘古乐,自制定礼乐”,“辞并沈约所制”,其中祭祀五帝歌辞统一用四言体。这一方面是对《诗经》、汉郊祀歌四言经典体式的复归,一方面也与精通古礼的王谢高门在入梁以后门庭衰落有关。详参曹道衡:《中古文史丛稿·南朝文学史上的王谢二族》,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隋唐承梁制③隋唐礼仪别采梁礼及北齐仪注。详参前揭《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第13页。,不再“依金数九”立言作九言乐府歌诗。尽管如此,作为曾用于明堂礼、五郊祭祀礼、元正飨会大礼那样庄重的王朝礼典的歌辞,“以数立言”的乐府歌诗还是随历代乐书流传下来了。北宋宋祁(998—1061)作《大有年颂·秋颂》“九言,据金数”④宋祁:《景文集》卷34,《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88册,第293页。,可谓“以数立言”的回响⑤按《景文集·大有年颂》之前是《皇帝神武颂》,题注“案仁宗本纪乾兴元年六月诛雷允恭,七月贬丁谓,此篇当是祁未登第时所作”(《景文集》卷34,第290页),之后是《景灵宫颂》,题注“案《宋史》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作景灵宫,仁宗天圣二年奉真宗御容,此篇当是祁登第后所作”(《景文集》卷34,第293页)。《大有年颂》当作于宋祁未登第或初登第时,似非诏制,也未见用于乐府,当属宋祁之个人创作。。此后郭茂倩《乐府诗集》、陈仁子《文选补遗》都收入了谢庄、谢朓等作。明万历庚辰(1580)进士李之用编辑《诗家全体》,将谢庄、谢朓之《白帝歌》、庾信之《商调曲四首》从成套“以数立言”的礼典乐歌中单列出来,编入“九言诗”类⑥李之用辑:《诗家全体》卷8,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邵武府学刻本。,使这些九言乐府歌诗更广泛地为人所注意。清初张玉榖《古诗赏析》收录庾信《商调曲》并评曰:“五声中商声属臣,故通首皆切臣说。”⑦张玉榖著,许逸民点校:《古诗赏析》卷21,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510页。对之颇加赞赏。清蔡钧称:“李之用所辑《诗家全体》有庾开府八言诗、九言诗。”⑧蔡钧:《诗法指南》卷4,乾隆戊寅(1758)年序刊本。表明这些乐府九言歌诗已进入一般学诗者的视野。
清代康乾年间,“以数立言”所显示的“礼数”内涵,被借用到颂圣诗的创作上。其时文人“取诸九昭阳德”⑨陈廷敬编:《皇清文颖》卷65《九言诗》,《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450册,第520页。、“乾元用九”(10)董诰:《皇清文颖续编》卷78,《续修四库全书》第1667册,第218页。象征皇帝身份,并依以立言作九言诗颂圣,思路与谢庄等“依金数”造作《歌白帝辞》同出一辙。这种九言颂圣诗颇得皇帝欢心。如沈树本献给康熙帝《万寿恭纪九言诗百句》后,获“召见,奏对称旨。越八年,辛卯魁乡荐,壬辰以一甲第二人及第,授翰林院编修。是科会试中式。举人奉旨覆试,命交卷后各奏履历。公奏毕,上举南巡时献九言诗事,徧谕大臣,奖励有加”(11)卢见曾:《雅雨堂集》文集卷2《沈舟侖翁诗略序》,《续修四库全书》第1423册,第472页。。李钧简“幼端敏……初入词垣,有权要闻其才,欲私之,不与通,故蔽之十年。圣驾东廵,献弌东全韵九言诗,称旨立朝”(12)丁宿章:《湖北诗征传略·李钧简》,《续修四库全书》第1707册,第361页。,几乎是通过献九言颂圣诗改变了仕途命运。皇帝的激赏,引发了朝中文人创作九言诗的热情,当时有“秘阁早传三礼赋,艺林争诵九言诗”(13)钱陈群:《香树斋诗集》卷11《送朱玉阶编修省亲归里》中句,并有自注曰:“驾幸翰林院,玉阶作九言诗,颇为京都传诵。”《四库未收书辑刊》第9辑第18册,第272页。之说,表明九言颂圣诗已有近似汉大赋那样的皇家专宠地位。
入清之后九言诗创作出现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与九言颂圣诗的创作效用不无关联(14)在《四库全书》、《中国基本古籍库》两个数据库所见南北朝以后出现102首九言诗作中,确定作于沈树本献九言颂圣诗前的仅有21篇,超过八成的九言诗是康熙年间后出现的。尽管清代九言诗创作的兴盛有多方面的因素,但九言颂圣诗的影响不可小觑。。其时有创作九言组诗者,如朱景英《村居杂咏为西樵赋九言八首》。有分韵创作者,如赵文哲《九月朔日陶然亭迟所招客,适申拂珊廷尉,毛礼斋侍御,吴百药侍读,陆朗夫、张研庐、陈絙桥三农部,曹竹虚编修,程瀣亭吉士,毛敬思舍人,程鱼门、孙补山两同年携酒肴先在,遂同分赋得九言》。有用于唱和者,如陈廷庆《丙辰九日同徐惕庵农部大榕、陈古华太守廷庆、孔幼髯国博广林、陈无轩学博焯、何梦华上舍元锡登灵隐西峰,古华赋九言长歌,同人皆和之》。有作联句者,如张文虎《井眉居同坚香先生、姚铁琴伯舅之桐送张叔未丈廷济归新篁里九言联句,用朱椒堂侍郎为弼题八砖精舍韵》等等。这些创作实践,尽管可能是文人一时雅兴,但或不无训练九言诗创作技巧以为颂圣作准备的心思。事实上,清末的一般文人诗作中尚可见颂圣经验留下的印记。王韬(1828—1897)《至粤已逾一载,辱江南诸故人投书问讯,作九言一首寄黄六上舍,潘大、杨三两茂才》,其中“众乐升平悲我不得预,尚冀圣恩祝网开蛛蝥”显然未脱颂圣诗之迹,可谓以颂圣式的长篇抒写获罪于朝廷后客居香港的困顿生活与怀乡心境①详参罗婉薇:《读王韬九言长篇〈寄黄六上舍,潘大、杨三两茂才〉》,香港中国语文学会《文学论衡》第17期,2010年12月。。
因颂圣而兴起的多种九言诗创作实践,也使得文人驾驭九言体式的能力与九言体式自身的表达功能都得到提高。至少在王韬诗中,我们已看到九言长句诗在描摹日常光景上的能力:
南村杨梅北村之卢橘,香蕉黄橙不论钱可售。
紫绡红缯径寸之荔支,玉珧下酒风味欺蝤蛑。
粤西善鲊粤东尤善鲙,薄肌细理沃醪杂姜蒌。
……
贾胡居奇光怪炫列货,四重金碧多喜居层楼。
天下兵动江浙又涂炭,衣冠避宦经此盟海鸥。
吾闻五羊城中仙下遨,最好深宵风月珠江头。②王韬:《蘅华馆诗录》卷3,《续修四库全书》第1558册,第470—471页。
此中近于散文口语的长句诗,展现出作为殖民地的香港商贸之盛及与之比邻的羊城偏安市井生活,预示着九言诗体与现代社会生活对接的可能。五四新文学运动后,在探索现代新诗发展道路的过程中,诗人与诗论家林庚先生(1910—2006)提出发展九言诗使其成为新格律诗的方向③详参林庚:《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这种思路或与晚清九言诗的新风不无关联。
从“依金数九”立言造作《歌白帝辞》,到以“乾元用九”立言造作颂圣诗,古代九言诗经过一个从祭祀歌辞到颂圣诗之发展轨迹。“以数立言”的诗歌创作方式与其“礼数意义”,促使不协自然音律的九言长句诗体,得以一直在中国文化史上产生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