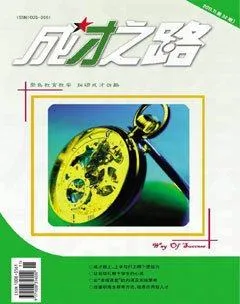凭什么成就卓越
2011-12-31张在军
成才之路 2011年32期
十、通向山外的路越来越远
1.做好平凡的事
湖北有位教师不远千里来到我工作的学校,他要亲眼看看我这“东方之子”是在一所怎样的学校里工作的。
那是初秋的傍晚,太阳快落山了,孩子们打扫好卫生,三三两两小鸟归巢般回家了。我一个人正在办公室里改作业。他来了,自我介绍叫陈功,在荆门一所中学当教师。和我差不多的年龄,个子稍高我一点,一口湖北味的普通话,憨厚地笑着,露出一口洁白的牙齿。
相距千里之遥,却能坦诚交流,这也算五百年的缘分吧。
几天的交谈中,陈功告诉了我他此行的目的:
我任教的学校有20多位教师,自己从参加工作就很卖力,但校长好像对我特别有成见。分配班级,从不把我看好的重点班级交给我,而是分给我一些微不足道的工作。班级也总给我一个不起眼儿的。我爱好文学,也有作文辅导方面的经验,学校成立文学社,辅导员总该让我干吧,校长却把这差事分配给了一个刚参加工作的黄毛丫头。这不是存心和我过不去吗?你不器重我,我也懒得为你卖命了,两年多了,我带的班级没一个给他露脸的,这样的校长,鬼才为他卖命呢。苦闷中,我看到了《中国教育报》上介绍你的《蒙山沂水铸师魂》的文章,就请了假跑你这里来了。
了解到他的来意后,我想了很多。总觉怀才不遇,总感到不被上司器重,总觉被埋没了,恐怕是很多青年人参加工作后的共同感觉。应该说,刚参加工作,绝大多数青年人是敬业的,没有几个人刚踏上工作岗位就破罐子破摔的。怎样解开陈功老师的心头疙瘩,让他重新焕发出工作的热情呢?我思索着。
一天下午给学生上完课后我把陈功约到了办公室,拿出达·芬奇的一幅名画,问他,你知道这是谁画的吗?陈功看了一眼说:当然知道了,意大利的著名画家达·芬奇画的《最后的晚餐》啊。我问他那你知道这幅画是怎么画出来的吗?陈功摇摇头说不知道。
我开始和他聊这幅画的来历。世人大多知道达·芬奇一生成就辉煌,其实他的前半生一直遭遇坎坷,怀才不遇。30岁那年他投奔到米兰的一位公爵的门下,希望这位公爵能给他创造一些成名成功的机会。可是,他去了几年还是一直默默无闻,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做。他的画也没有得到公爵的赏识。但是达·芬奇自己没有丧失信心,始终在自己简陋的画室里执著地画着。
转眼间,他在公爵家待到第三个年头了。一天早晨,公爵来找他,让他去给圣玛丽亚修道院的一个饭厅画一幅装饰画。这是一件无足轻重的活计,一个普通的三流画家就可以完成,因为谁都觉得实在没有必要在一个饭厅的墙壁上下真工夫。
但是,达·芬奇却不这样认为。从老师让他反复画一只鸡蛋以来,他就没有敷衍了事地画过一幅画。即使是平时练习也是如此。这次也是一样,达·芬奇倾尽了自己所有的才华,日夜站在脚手架上努力地画啊画。
两个月以后,饭厅的装饰画画完了。很有鉴赏水平的公爵立刻意识到这是一幅不可多得的杰作。他立刻找来了米兰的著名画家,请他们看看达·芬奇的这幅作品。所有前来的画家无不对画作严峻的构思和大胆的用色感到惊奇。
是的,世界上不朽的名画《最后的晚餐》诞生了。
名不见经传的圣玛丽亚修道院因此而声名鹊起,从来也没有什么名气的达·芬奇也因此名垂青史。
陈功很憨厚地笑了。
他挠挠满头的乱发说,和你在一起的这一星期里,我理解了什么叫做伟大。你教了三个年级,光备课就有十几本,语文、数学、体育、音乐、美术、劳技,所有的课都是你一个人教,我看了你所有的备课,几乎都是一丝不苟,孩子们作业也批改得那么完美。今早晨升国旗时,那位小旗手的褂子的领角翻了,你悄声地给他正过来。昨天下午锁教室门时,一提门,我也听到了一声轻微的“咣当”声,这声音轻微的完全可以忽略,你却在每块门玻璃上都用手敲了一遍,直到找出那块被风吹动了的玻璃,然后拿钉子钉牢。这几个小细节深深触动了我的心灵。我理解了什么叫不平凡,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就是不平凡啊……
我也笑了,说生活中的很多人之所以一事无成,是因为他们总是把那些发生在身边的日常细微的小事看得无足轻重,总以为在未来的某一天会有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等待着自己去完成。事实上呢?那样的大事仅仅局限于极个别的人和极个别的时刻。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那样的机会几乎是没有的。人生如同一条小溪,一块块碎石激起的朵朵浪花,构成了一生的风景。我们的生活中,时刻发生着的,都是那些很不起眼儿的小事情,正是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情构成了我们的人生。
阻止我们前行的,不是前面的那块巨石和那座高山,而是我们鞋里的那颗小沙粒。人生中的小事情,它们不仅仅会使你的人生丰富而精彩,还会在某一个不经意的时刻,使你走向伟大和崇高。
2.小村上电视
西棋盘学校的知名度越来越高,一批批的记者不远千里百里,翻过层叠的大山,来到我的学校。学校卫生得每日清扫,参观学习采访调研的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了。孩子们每天也都穿戴整齐,衣服无论新旧,都洗得干干净净。记者们来一趟不容易,总想把要了解的东西了解透彻,便挨个学生访、逐个学生问。一来二去,孩子们的即兴发言水平、接受采访水平、待人接物礼仪水平逐渐高起来了。记者们交口称赞说,除了穿戴破旧以外,西棋盘的孩子举手投足比城里娃还胜一筹。
深秋的一天,一行电视记者来到了西棋盘。县里陪同的同志指着一男一女介绍说,这二位是省电视台的记者,来专题报道你的。接过二位递来的名片看了看,女的叫祝丽华,男的叫李海明,都是文艺部的。介绍完坐下,祝丽华说,我们去临沂采访,从团地委的沂蒙长青基金奖获奖材料中了解到了你的情况,又去地区教育局采访了几个局长,觉得你的事迹很感人。你高考落榜,也曾做过无数的大学梦、成功梦,在山区教坛的三尺讲台上跋涉着你的无悔人生,书写着你的青春年华。我们觉得用电视散文的形式表现你的人生历程比较好。李海明随手递给我一个电视脚本,《沂蒙交响诗——赤诚》。事迹如何表现,画面如何拍摄,本子上都设计好了。
听说来了拍电视的,村人都呼呼啦啦赶来了。一眼就能看出,村人大都洗了脸、换了新衣。常会叔提来了茶具热水,为记者们倒上,便吆三喝四地用烟袋赶着光腚山娃。记者稍事休息,李海明便肩扛机器开始干活。先拍了我上课、办公、和娃们做游戏的镜头,便走出校园到村里去拍环境。村人不甘落后,大呼小叫看耍猴一般跟在他俩身后。祝丽华回头笑微微地说一声,乡亲们别靠得太近,鸡飞狗跳的镜头不雅。前边村人立时停住,后边没听见仍在急赶,几十口子人嗷地挤成了一团。前边的顶不住,几个趔趄险些趴倒,后边仍在挤,就挤出一片嘻嘻哈哈的笑骂。
那边李海明对着民房、小巷、绿树推拉摇移,这边祝丽华从人群里挑选接受采访的家长。村人一听,哄地往后退去,那边常会叔一边说着看这个没文化熊样,谁也别跑。祝丽华便笑说书记就先带头吧,常会说带头就带头,昂首挺胸赴刑场就义般走了过来,祝丽华又笑着点了3个家长的将。李海明走回来,镜头又对向了家长,对着谁,谁的嘴唇就猛一阵哆嗦,浑身一阵抽搐。于是祝丽华一遍遍启发,引导,大半天工夫完成4个大人的采访。
午饭是常会叔张罗的,学校院子里的大柿子树下,并排放了两张大八仙桌,幕天席地,每桌上有六大盘、四大盆。一盘油炸花生米;一盘腌香椿芽;一盘油炸山蝎;一盘蒜泥拌蚂蚱菜;一盘腌花椒;一盘辣椒面拌山芹菜。一盆煮山鸡蛋;一盆青椒炒山鸡肉;一盆全羊汤;一盆面叶绿豆汤。
常会一边吆喝大家入座一边介绍,没有什么好招待的,都是自己产的纯绿色食品,鸡是自己养的,吃草种中药种山蝎子喝山泉水长起来的,蛋是俺自己下的。
众人入席。
悠悠白云从校园上空飘过,阵阵秋风吹得头顶柿子树上的树叶一阵刷刷拉拉。
饭后稍息,祝丽华、李海明擦擦汗又开始干活。又拍摄了小鸟归巢,夕阳西下,牧牛回村,孩娃放学。当晚霞的最后一抹余辉消失在地平线上的时候,拍摄工作结束了。村人送挚友贵客一样把记者送上车,直送得祝丽华、李海明下吉普车,挥手告别三四次。
村里没有电,自然也没有电视机。片子什么时间播似乎与村人无关。但有一天,村里传出一条爆炸性新闻,坤明买回一台电视机。这小子疯了?众人呼啦涌到他家,可不?在天井里的磨盘上放着一台破旧的14英寸电视机,旁边还放着一个拖拉机上的蓄电瓶。拍咱村的电视咱看不到,还不遗憾。坤明说,我用刚卖几麻袋瓜干的钱,去镇上买来了这套设备。
坤明边说边接电线,不一会儿,一群模模糊糊的人嘶哑着嗓子出现在电视机里了。
国庆节的前夜,是祝丽华、李海明说的播放《赤诚》的日子。坤明买电视机收播西棋盘电视片子的消息早已一传十十传百传遍了三村六庄。不到天黑,坤明家的天井里、墙头上、大树上就挤满了看新鲜的人。
老人们回忆说,村里第一次放电影也就这么多人。
为防备电不够用,坤明去镇上充了一整天电,搭上了一条大鸡烟两瓶白干酒。常会说可别到10点播放咱们时正好没电了,先关了吧。众人齐嚷关掉、关掉、快关掉。坤明只得关掉。有人去大队拿来气灯点上,院子里立时亮堂起来。还有几个小时呢,长夜难捱,大家东扯葫芦西扯瓢,扯了一会,小娃们出去玩叼小鸡藏猫猫。
李秀文呢,说段书吧。常会提议。说就说吧,李秀文清清嗓子开了腔。“闲言少叙书归正,拉开当年开正风,想听文的西厢记,要听武的有罗成……”几句传统的书前套辞说罢,李秀文演讲《兴唐传》开始。
这里三个回合刚说完,有人说开机子吧,10点了。坤明打开了电视机,电视里正说广告,众人看着、聊着、畅想着,什么时候家家有一台电视机,放在床头想看什么有什么该多好。
优美的“沂蒙山小调”的旋律响起来了。熟悉的山崮,熟悉的街巷,熟悉的校园,熟悉的村人从电视机里出现了。有人问常会,平时在社员大会上你一套一套的,这回在电视里讲话,怎么浑身哆嗦脑血栓呀你?
常会说,站着说话不腰疼,那天让机器对着你,你怎么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三个人逮都逮不住,野兔子听枪响一样跑没影了。
村人一阵欢笑接着一阵欢笑。
之后的好多天,三村六庄都谈论着西棋盘上电视的事。和西棋盘人见面,问的也多是你上没上去?村人便说,上了上了,大树根下蹲那儿抽烟呢,你没看见我?
后来西棋盘上电视的机会多了,中组部党员电教中心来了,“东方时空”来了,中宣部《使命》摄制组来了……,但远远没有了第一次的热闹和新鲜。
若干年以后,与已经是总编辑的祝丽华老师谈起西棋盘第一次上电视的情景,祝丽华两眼都湿润了。西棋盘之行是我难忘的一次采访。祝丽华说,那朴实的午饭,那朴实的村人都使我终生难忘,多少次梦回西棋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