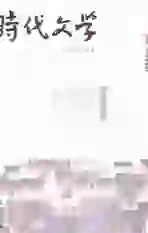太羹有味是诗书
2011-12-29陈靖
时代文学·上半月 2011年2期
摘要:本文探讨了张旭书法和诗歌的共性。指出其诗歌和书法都是心迹的宣泄,是自然美的体现和对意象关的追求。其诗歌和书法都是其人格的写照。
关键词:诗歌;书法;自然美;意象美;诗书如人
张旭是盛唐杰出的书法家,其楷书“唐人正书,无能出其右者”Ⅲ;其草书代表了盛唐书法的最高成就。唐文宗时,诏以李白的诗歌,裴雯的剑舞,张旭的草书并称唐代三绝。张旭又是杰出的诗人,他“文辞俊秀,名于上京”。与贺知章、毛融、张若虚一起被誉为吴中四杰。其诗歌与书法相映生辉,既展现出大唐王朝蓬勃向上的万千气象,也抒写出诗人、书法家纵横不群的奔放激情,显现着诗人、书法家任意挥洒的磅礴气势,凸现出浪漫主义意向的艺术魅力。
《全唐诗》里收录了张旭的六首绝句,都是绝妙好诗。然而历史记住张旭更多的是“颠张”,是其“酒中仙”的狂逸个性,是“性善书,不治它技”的书法家。对其郁郁的文采,浪漫的诗风却鲜有提及。其实,他的诗和他的草书一样充满了烟雨迷离、舒卷云烟的氤氲气息;意境的美妙,气韵的流溢,胸襟的舒卷,是其诗鲜明的艺术特色。
为进一步了解张旭的诗歌艺术。我们不妨将其草书和诗歌相结合进行具体的分析。这样做,一是因为中国的诗书画在古代不仅在理论上互通互补,在创作上相互交融,彼此借鉴,彼此渗透;二是因为这样做,既可以鲜明地揭示张旭的诗歌特色,也有助于在深层次上认识和了解张旭书法。
一、张旭诗歌和书法都是心迹的宣泄,自然美的体悟
书法作为人类物质和精神追求的艺术表现,其本质内容则是来自于人的心灵倾诉。“夫书者,心之迹也,故有诸中而形诸外,得于心而应于手。”张旭草书,内得心源,外师造化。他把书法艺术作为表情手段,通过这种艺术手段他把“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发之。”因而张旭的草书是发乎情的生命本能的宣泄。唐书法家蔡希综云:“(张旭)乘兴之后,方肆其笔,或施于壁,或札于屏,则群象自由,有若飞动,议者以为张公亦小王(献之)之再出。”由此可见,他的草书迥异于“不激不厉”的大王书风,而取法“纵逸不羁”的王献之。这种书法风格更有有利于其心性的宣泄。其草书如《肚痛帖》,线条筋力弥满,给人以活泼飞动的美感。同时,由于字字之间运用了隐与活、粗与细、大与小等多种形式的对比。造成空间布局上节奏的张弛、快慢的变化。
书法艺术是中国人的精神诉求。自然美贯穿书法活动的始终,笔法、结构、章法、创作模式、书法鉴赏无不体现“书道自然”这一总的要求和内在规律。中国古代书论中有大量对书法自然美的描写,如晋卫夫人在《笔阵图》中所讲:横画如千里阵云,竖画若万岁枯藤,点画如高峰坠石。东汉蔡邕日:“为书之体,须入其形,若坐若行,若飞若动……纵横有可象者,方得谓之书矣。”怀素也说:“吾观夏运多奇峰,辄常师之,其痛快处如飞鸟入林,惊蛇入草。”这些书法理论都是书法家返归自然、师法自然,对自然体察的总结,审美之升华,同时也是对书法自然美的形象描绘。
张旭的草书是发乎情的生命本能的宣泄,又是对自然美的体悟。他外是造化,以自然为师,他完全游目于自然而与自然运化一致。游心于自然而与自然大化同流,他“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他见公主担夫争道得其形,见公孙氏舞剑器而得其神,当他把这种对大自然的“体察”化之于书法时,这就出现了他书法中那种有生命的形象。这些形象是通过他的情感所体会的,是“可喜可愕”的;他在表达自己的情感中同时反映出或暗示着自然界的各种形象。或借着这些形象的概括来暗示着他自己对这些形象的情感,“这些形象在他的书法不是对事物的刻画,而是情景交融的意境,像中国画,更像音乐,像舞蹈,像优美的建筑”。正是以造化为师。使张旭的草书意韵起群,不同凡响。
张旭的诗歌同样是心迹的宣泄,自然美的体悟。张旭虽处大唐盛世,却终生沉沦下潦,仅当过官小职卑的常熟尉和金吾长史。但他仍傲世自高,为了追求精神的解放,个性的自由,他优游林泉,留连山水,并将壮猷伟气,一寓于简牍间。他的六首诗全是写景诗,这一方面是其寄情山水的生活的反映,却也是同他的书法创作密切相关。这些诗。把人们带进了月夜清溪,江山烟云;听薄暮劳歌,鱼舟问答。诗人挥动一支写意传神的妙笔,勾勒出一副副形象生动鲜明,意境美妙的风景画卷。这画中的山水景象奇伟空阔,充溢着自然美和豪放飘逸的情致,尤如作者那一副副体势飞动,笔意连绵,雄劲而潇洒的草书。自然景物寓于胸中,酣醉不平,有感而发。或诗或书。无涯无际的联想,诗歌的流畅俊逸与书法的畅神飘逸相互辉映,共同体现着张旭的浪漫主义艺术特色。
二、张旭的诗歌和书法都体现了作者对意象美的追求
书法不象绘画那样具体,直接地描摹事物。因此书法的美,近乎一种抽象的朦胧的美。书法艺术是意象的艺术,好的作品如海上蓬莱,月中桂子,给欣赏者以莫名的享受。“花看半开,酒饮微醉”,妙就妙在“半”字;“隔帘看花”,妙就妙在“隔”字,它隐约着神秘,泛透着玄妙。书法“囊括万物,裁成一相”,而这一相乃是无形,这一相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对应点,但它蕴涵在万物中,它曲折,间接,形而上地反映现实。张旭的草书打破了魏晋拘谨的草书风格,在笔法上大胆突破,似非而是:在结构上,将上下两字的笔画紧密相连,有时候两个字看起来像一个字:在布局上疏密悬殊很大。他一反传统的书写速度,采用大写意抒情的方式,他的书法完全打破了传统书法的秩序,作品变得朦胧,飘忽,迷远。张旭的诗也受到书法的意象和“裁成一相”的影响,即多用虚笔,间接、曲折,“无画处皆成妙境”。《山中留客》仅第一句“山光物态弄春晖”用写景之笔勾勒出全景,其余三句,在挽留客人的劝说之词中,巧妙地虚写出更令人神往的深山空翠。再看《春游值雨》,“欲寻轩槛列金尊”四句诗写出了阴雨晴的变化,但只是用浓墨渲染晚来江上烟云低垂的昏暗之景,而把夜雨和晚晴置于设想和期待的“须倩”和“却待”之中。《柳》和《春草》也都用了这种虚笔写景的手法。这样,他笔下的山水人物形象若有若无,似真似幻,亦真亦动,反而更有助于反映那种迷茫幽远的境界。
张旭被杜甫称为酒中八仙之一,《酒中八仙歌》对其形象的描写颇具个性,“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落拓不羁的外形,凸现着鄙视利禄、专心艺苑的品性。其书常以酒为媒介,“每醉后呼叫狂走,索笔挥洒,变化无穷,若有神助”㈣,这是一种“礼岂为我设”的天放,他完全进入到了如醉如痴的忘我境界。在这种心态下,“书家的下意识、潜意识、梦、联想、幻觉、示现……各种在冷静状态下不会出现的美的意念都出现了,书家简直有点轻躁狂、神经质了。这时所产生的书法作品已不是初级的意象所能解说,它已是‘不可说’的心象、心画了”,因而张旭的书法作品充满状若断而反连的云烟之象,烟霏露结,飘忽朦胧。法国人勒内·艾蒂安布尔说:“无论是中国书法或阿拉伯书法,甚至最抽象的书法都有其意义,一个字若不是表示某种宗教或道德观念,就是显示一种诗的意象。”㈣张旭草书的线条流出了万象之美,也流出了人心之美。张旭是一个天才的艺术家,创造了这条线(一画),使万象得以在自由自在的感觉里表现自己,同时他又赋予这万象以节奏旋律,他让自然万象充盈着意象之美,这是需要何等石破天惊的力量。张旭的草书正是这种意象美的体现。
张旭的诗同样布满了迷离的烟雨和空蒙的云雾,很少有艳丽的色彩。例如,在《桃花溪》开篇便是一座飞桥隐现于飘渺云烟之中;《山中留客》“山光物态弄春晖”虽然先展现了和煦阳光下的明媚春山,但紧接着飘来几缕轻阴,最后更把人引向云封雾锁的高山深谷“入云深处亦沾衣”。他咏春柳,不同于诗人贺知章,贺以“碧玉妆成一树高”点染春柳鲜明悦目的碧绿之色:而他的诗却是“濯濯烟柳拂地垂”,着重表现柳条笼烟裹雾的风韵。总之。他的诗中画是典型的山水画,不给景物敷采设色。张旭不是画家,他对于色彩的捕捉不是那么敏感,对色彩的刻画不是那么细腻、不是那么微妙,但张旭又是一位高明的画家。他太喜欢水墨黑白这种独特的视角形式,以致仅凭挥笔运墨就能勾勒出大自然的奇幻妙境以及天地造化之象。
三、书如其人,诗如其人
张旭的诗歌和书法共同宣示了作者狂放的个性。浪漫的气质,纵横的才情,俊逸的风采。六首绝句,都跃现出诗人寻幽探胜的身影,清狂洒脱的神态。《山中留客》中诗人殷勤留客的话语,也倾吐出他对这深幽雄秀气象无穷的云山非常爱恋。《桃花溪》里,他问渔人的话又是多么的天真有趣,“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这两句话。既表现出他对桃花园的急切向往,又透露出他感到这理想天地渺茫难求的怅惘心情。又如,在《清溪泛舟》中,“旅人倚征棹,薄暮起劳歌。笑揽请溪月,清辉不在多”,在这里作者豪兴勃发,朗声大笑。手掬清波,欲揽溪中明月,何其狂放潇洒!杜甫赞张旭草书“俊拔为之主”、“逸气感清识”(《殿中扬监示张旭草书图》)。苏轼赞:“张长史草书倜然天放,略有点画处而意态自足,号称神逸。”悯明代书法家丰道生赞其字:“行笔如从空掷下,俊逸流畅,焕乎天光,若非人力所为。”这些评语,不也是其人其诗的绝妙写照吗?
“太羹有味是诗书”。它说明了有味的太羹是“诗书”。欣赏张旭的草书,品味其诗歌,不正是一场视觉上的饕餮盛宴吗?
参考文献:
[1]黄庭坚,屠友祥校注,山谷题跋[M],上海:上海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