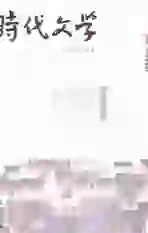论《红楼梦》中的戏曲及曹雪芹的文学观念和悲剧精神
2011-12-29高永江
时代文学·上半月 2011年2期
著名汉学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浦安迪(Andrew Plaks)在他具有开拓性的著述《红楼梦中的原型与寓言》(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the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中指出:“《红楼梦》的全部书页中包含了各种文学样式(诗歌、戏剧、古文、方言小说等等)和文学体裁(诗、词、骚、赋等等)。全书的中心关键是专注于对传统思想家引发的思考(老子、庄子、孔子、孟子和禅宗)”几百年来人们对《红楼梦》中所涉及到的各种文学样式的研究论述举不胜举,但对于戏曲的关注却不多,只有在少量的论著见其谈论,而且多是对其中的戏剧现象加以研究,最多论及戏剧在小说中的作用,缺乏对《红楼梦》作者通过戏剧所表现出的文学观念的系统论述,以及其价值与意义的充分认识,现将提出研讨感觉很有必要。
《红楼梦》中戏曲出现虽不象诗词那样多,但在一部小说作品中出现这么多的戏曲剧目和戏剧活动古往今来还是少见的。小说中一共演戏十一次,包括了家庭中的过年过节,生日聚会,打醮酬神,游玩娱乐,重大事件(如元春省亲)等等,还有小说里的人物在各种日常生活中提到看过听过的戏曲曲目,一共有三十几部戏,其中有《西厢记》、《琵琶记》、《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长生殿》等优秀剧目。其中有杂剧、昆曲、弋阳腔、各种地方戏等多种戏剧样式。这不仅真实反映了当时贵族家庭的生活画面,以及戏剧活动在清代的频繁盛大状况,更重要的是透露出小说作者通过戏剧所要表达的文学观念和美学思想。
首先,《红楼梦》借用中国古典戏曲表达“情至”的文学观念和悲剧精神。众所周知,《红楼梦》借用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学中的比喻、象征、典故、诗、词、赋、空间意识、文的结构,而借用最多的是两部有永久魅力的浪漫剧本一王实甫的《西厢记》和汤显祖的《牡丹亭》,在小说第十一回,十八回,三十五回,四十回,四十二回,四十九回,五十二回,五十四回,六十二回。六十三回等多次提到两部戏的曲目。并将这两部戏曲名作为二十三回的回目“西厢记妙词通戏语,牡丹亭艳曲惊芳心”,而且描写得极细致,写出了林黛玉聆听《牡丹亭》曲文达至共鸣的全过程。背景是众姐妹和宝玉已奉元春之命,搬人大观园,都是年轻女孩儿,就一个男性贾宝玉。大家“坐卧不避。嬉笑无心”。结果静中生动,宝玉忽然有一天不自在起来。于是便读起了《西厢记》,“正看到‘落红成阵’,只见一阵风过,把树头上桃花吹下一大半来。落得满身满树满地皆是。”。黛玉看到也读,而且读得“余香满口”。两个人“连饭也不想吃了”。而后二人在对话中又不时引用《西厢记》里的曲文“我就是那个多愁多病的身,你就是那倾国倾城的貌。”“原来也是个银样鑞枪头。”春日时节,沐浴在纷纷飘落的花瓣里,俊男靓女坐在桃花树下共读《西厢记》。
正在这时袭人来找,说老太太唤宝玉有事。林黛玉一个人闷闷地回潇湘馆,路过梨香院,恰好里面正在排练《牡丹亭》。“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两句曲文传人黛玉耳朵,她“感慨缠绵”。她听到“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不由得“点头自叹”。又听到“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两句,黛玉“不觉心动神摇”。而听到“你在幽闺自怜”等句,她已经“如醉如痴,站立不住”,一蹲身坐在一块山子石上,反复细嚼“如花美眷,似水流年”八个字的滋味。这时黛玉又联想起唐人诗句“水流花谢两无情”以及刚刚读到的《西厢记》里的“花落水流红,闲愁万种”。最后她“不觉心痛神痴,眼中落泪”。《红楼梦》里这段情节是描写艺术欣赏达到共鸣境界的绝妙文字,起因、渊源、影响,主要来自《西厢记》和《牡丹亭》的艺术感染作用。在以后的章回中都多次引用两部戏曲的曲文。如26回午睡时分,黛玉半躺在床上,低声细语吟诵《西厢记》中的一段诗行。这段有名的诗行是崔莺莺的内心独自,抱怨春风吹开了花朵,却没有给女主人带来爱情,以至于女主人只好“每日家情思睡昏昏”。当宝玉走进黛玉的住宅时,就像张生撞见崔莺莺暗吐私情一样,正好听到这句话,宝玉立即对黛玉的丫环紫鹃引用《西厢记》中的一句诗,模仿张生对莺莺的丫头红娘说:“若共你多情小姐同鸳帐,怎舍得(你)叠被铺床?”可见《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对《西厢记》和《牡丹亭》别具特识。为何这样,不难看出。《西厢记》和《牡丹亭》两部剧作都十分强调“65b7f8d113cd7c1e54f91de191d72406情”,有中国古典式爱情的表达模式,花园、美景、才子、佳人、邂逅、情爱、婚配等。的确,这些都对曹雪芹产生影响,并把它们运用到《红楼梦》里。对“情”的描绘,是明末清初文学作品的一个共同特色。在明代,产生许多这样的作品。《毛诗序》把情引入诗论,以情感人。揭示了诗歌的抒情性质以及诗作为读者的情感特征,而抒情性是中国古典戏曲的主要特征,有“诗剧”的美誉。汤显祖认为戏剧是最能表“情”的方式,并以戏剧创作实践他的“主情说”,提出“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的戏剧主张,构成了他的戏剧观。汤显祖阐明了情、梦、戏之间的关系:“情”在戏剧中占有中心位置。包括有复杂的生活内容和积极的人生意义;“情”通过“梦”表现出来,而“梦”又通过“戏”反映出来。简言之,戏是梦在情的反映。也就是说。戏剧是通过梦幻的表现形式来反映人世间现实中人们的善恶是非及思想感情的。《牡丹亭》通过杜丽娘的故事,表达“情不知何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者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牡丹亭记题词》),杜丽娘这一艺术形象就是情感的化身,“至情”的写意。而王实甫倾注在张生和莺莺身上的满腔热情则使这两个艺术形象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明清作家心目中的才子佳人模式。明清这种文学现象的文化背景可在王阳明的“良知说”和李贽的“童心说”中找其哲学原理和思想根源。曹雪芹深受他们的影响,更是对《西厢记》和《牡丹亭》两部戏的热爱与觉悟,“披阅十载,增删五次”发出“开辟鸿蒙。谁为情种?都只为风月情浓。趁着这奈何天,伤怀旧,寂寥时,试遣愚衷。因此上,演出这悲金悼红的《红楼梦》。”(《红楼梦·引子》)的悲声,道出情的复杂,表达他的“情至”观。并借两主人公对两出戏的喜爱,产生的共鸣,引起他们的青春觉醒,揭开了他们蕴藏的爱情的心扉,启发了他们要求摆脱封建礼教桎梏的愿望。可见,《红楼梦》里,《西厢记》《牡丹亭》正好成了宝黛爱情的催化剂。从此,他俩的爱情,由“两小无猜”阶段,飞跃到真挚恋爱阶段。表现出共同志趣,心与心的沟通、交流、感应、体察与品味,既是深情款款的恋人,又是心灵相通的挚友,既是志同道合的知己,又是生死相依的伴侣。相互了解,相互关怀,从而培育出纯洁真挚的爱情。曹雪芹既有传承,更有创新。超越了《西厢记》与《牡丹亭》的一见钟情,郎才女貌,浅层次的爱情模式,开创了一个爱情的新世界,在文学天地中创设出至今让人向往的爱情的最高境界。更难能可贵的是突破了“有情人终成眷属”理想的爱情归属,不以《西厢记》和《牡丹亭》妥协的“大团圆”的结局,而以极其冷峻的笔触写出美好的爱情与现实的矛盾、冲突、对立,表达出真正的爱情也许是永远无法结合在一起的,只不过是一种空幻。宝黛他们注定要经受折磨,感受苦痛。写出爱情与婚姻的分离。情爱与性爱的分离。曹雪芹用细腻的笔墨写出宝黛爱情的苦痛:个人的追求与家庭社会的矛盾;金玉良缘与木石前盟的纠葛:性格与处境不容,“还泪”的传说写出痛苦辛酸的经历,最后黛玉死去宝玉出家的悲剧结局,表现了前所未有的爱情复杂性和悲剧性。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既写了有爱情却不能结合的“痛”,又写了有情爱而不能实现性爱的“苦”,还有大量的既无情爱又无性爱的“悲”。这是曹雪芹对“情”认识与发展,又是他美学思想的呈现,摒弃老套,是对中国古典悲剧的贡献。有其进步与震撼,但也有倒退与遗憾。《西厢记》,特别是《牡丹亭》以美的形式表演出两性间的性爱,表现出爱情与亲情、友情的不同之处,惊世骇俗,表现了汤显祖的胆识与先进。而之后的曹雪芹却把情爱与性爱分离,小说中涉及的人物都是如此,情爱与性爱始终是对立的,不相容的。有情爱无性爱,宝黛如是;有性爱无情爱,贾珍、薛蟠之流如是;既有情爱又有性爱的,最终走向死亡,司棋和潘又安如是。这必然导致爱情的悲剧,而这样美好的感情最终走向毁灭,必然带来幻灭感。
然而《红楼梦》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又不纯粹是爱情婚姻悲剧——众女子的普遍悲剧——所谓“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所能包容得了的:宝玉摒弃了为封建统治建功立业的人生道路,却在严酷的现实中找不到出路而产生的幻灭情绪:蔑视以三纲五常为封建统治法典的人伦准则,却找不到新的人生真谛而产生的精神苦闷;以及贾宝玉对人与自然生死幻灭变化的哲理思考,都表现出曹雪芹最深刻的悲剧精神。
其次,《红楼梦》借用中国古典戏曲表达神仙道化思想,“色空”的观念和悲剧精神。曹雪芹在《红楼梦》中利用各种方式表达佛道思想。有佛典中的用语“绛珠仙子”“神瑛侍者”;有人物塑造甄士隐学道、妙玉女道士;有道场法事打醮清虚观。有作品人物直接感叹“人生如梦,世事无常”甚至通过作者自白,提出“因空见色,由色生情,传情人色,自色悟空”等等。其中最直接鲜明表达的不过于一僧一道点化甄士隐的《好了歌》和《红楼梦曲收尾·飞鸟各投林》。
而利用汤显祖的传奇戏曲《邯郸记》和《南柯记》,把他们天衣无缝嵌入小说中,表达神仙道化思想,则是《红楼梦》巧妙之处。小说第十八回元春省亲点了四出戏,其中《仙缘》一出是汤显祖的传奇剧《邯郸记》的第四出。《仙缘》是写卢生在梦中经历高官厚禄。但也蒙受诬告流放,结局虽重享荣华富贵,只是黄粱一梦。梦醒时由八仙中的吕洞宾带他到仙境遨游,遇到七位神仙点破他世上的荣华富贵、权位势力、高楼大厦、儿女私情,没有一件靠得住的,这七位神仙,每人向卢生唱一段“浪淘沙”曲来点化卢生,每一段唱完,卢生唱一句“我是个痴人”。
我们再来回味一下《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中一僧一道点化甄士隐的《好了歌》:
这二者对照,彼此的继承关系是十分明显的。“惟有功名忘不了!”等四句,说的是功名,即对应于曹国舅唱的后半曲及铁拐李、蓝采和、韩湘子所唱;“只有金银忘不了!”等四句,说的是金钱,即对应于曹国舅唱的前半曲;“只有娇妻忘不了!”等四句,说的是娇妻,对应于汉钟离所唱:“只有儿孙忘不了!”等四句,说的是儿孙,对应于何仙姑所唱。二者如出一辙,都是赞颂神仙好,“不学仙真是蠢”,劝世人断绝功名富贵之念,家室儿女之情,及早悟道学仙,跳出红尘。这一切加浓作品的出世思想。
再如第二十九回,清虚观打醮演戏,神前拈的三个剧目,就有汤显祖的传奇《南柯梦》。此戏写淳于棼梦人槐安国,始而飞黄腾达,极富极贵,终而家破势败,一切皆空。淳于棼醒而大悟“人间君臣眷属与蝼蚁何殊。一切苦乐兴亡与南柯无二。等是梦境”。一出“人生如梦”的大戏表现出浓重的幻灭感“万事无常”、“诸色皆空”。这类神仙道化思想,与《红楼梦》整个小说里表现出的佛道思想是一样的,也就是曹雪芹从他的人生经历中所得到人生观,也是《红楼梦》的深刻思想内涵。
但这样的“色空”观念,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为“色即空”的消极避世,出世思想表现,陷入悲观主义泥淖。他有更深层次的哲学思考和悲剧意蕴的体现。《红楼梦》是一部凝聚了作者十年心血写出的“字字看来皆是血”的真情表达,并把这真诚感情寄予小说人物之中,可谓达到双重性真实的契合。自我真实的生命体验,笔下人物真实的情感经历,人生遭际,这些都不是简单的用一个空字就能抹去的。这些真实鲜活的存在时时刻刻撞击着他的心扉,我们在字里行间都能强烈的感受到他的恋惜之情,对情的痴迷,对一切他认为值得为之掬一把同情之泪的人、事、景、物。甚至衰败的贵族家庭的惋惜,但他又无回天之力,就如笔下的宝玉,无法避免爱情的,婚姻的,女儿的,家庭的,社会的,人生的、自然的一切悲剧。这种生活现实的必然与个人愿望之间的深刻矛盾,痛苦的折磨他和他笔下的人物,他们需要寻找一种心理的麻醉剂,通过麻醉来获得心理平衡,于是只好乞求传统的佛、道文化,笔下人物出家,他“色空”观念的表达,正是这一诉求的实践。“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有恩的,死里逃生;无情的,分明报应;欠命的,命已还;欠泪的,泪已尽。冤冤相报实非轻,分离聚合皆前定。欲知命短间前生,老来富贵也真侥幸。看破FrHb5Uf3qK/Fr0XYuUpR9bLUH+iBW52c9wCRptXJ0JM=的,遁入空门;痴迷的,枉送了性命。好一似食尽鸟投林,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红楼梦收尾?飞鸟各投林》)。这样必然出现现实与虚幻,感情与理性的矛盾冲突,在这矛盾冲突中,人生的酸甜苦辣,世态的冷暖炎凉,都会以一种异常的形式放大起来,进而深化成为一种面对冷酷的现实而“大无可如何”的悲剧意蕴。《红楼梦》超越了《邯郸记》和《南柯记》这些传奇戏剧,就在于《红楼梦》的艺术魅力来自小说本身所展示的现实生活内容。而不仅仅是梦境、太虚幻境等虚幻的场景。这种现实内容所产生的强大逻辑力量,必然对色空观、宿命论产生强大的冲击,而色空观、宿命论又在作家生花的妙笔下,强行向这种现实的逻辑进行渗透,二者往复交错,纠结而又抵牾,抵牾而又显得了无痕迹。这种描写,客观上有利于强化小说的悲剧意识,因为现实的欢愉与苦闷、追求与幻灭,虽然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描写,但如果缺乏哲理性的人生探索,就容易流于浅俗;而“色”“空”这类将人生归结为虚无的思考,如果没有坚实而有艺术魅力的现实生活描写来抵制影响,抑制它的恶性膨胀,全书难免坠入虚空的因缘说法。失去其生动丰富的历史容量和厚重宏大之感,悲剧意识也必然减弱甚至丧失殆尽。
从以上看出,《红楼梦》中出现的戏曲,并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之笔,他既是全书情节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许多专家学者多有论述,这里不累述),又是诗意的表达,意境的追求的精妙辞章(如第二十三回),还是作者借以丰富他所反映的社会生活,有助于深刻揭示“红楼”由盛而衰的历史命运,更是对中国古典戏剧思想的继承与发展,形成自己的文学观念和美学思想,把中国古典小说创作推向一个难以逾越的顶峰,使中国古典悲剧精神更加丰富、完善与成熟。
注释:
①浦安迪(Andrew H,P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