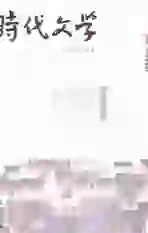沉沦与消解
2011-12-29曹卫军
时代文学·上半月 2011年2期
摘要:陀思妥耶夫斯基是一位肯定生命存在意义的作家,面对俄国19世纪新旧交替的社会转型期所呈现出的混乱、黑暗、病态的状况,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触及死亡并沉思这一永恒的话题。陀氏在作品中大量描绘死亡,一方面展现了传统文学中所表现的个体生命的终结,反映了他对人类生存的最深远的关切;另一方面从更高的层次上体现了陀氏对死亡的深刻认识,即一种更高意义上的超越肉体消亡的死亡观。表现为俄罗斯传统文明和文化的衰颓、信仰和精神的危机、人格的分裂、自我的丧失等,他笔下的主人公们面对死亡,不时发出生命空无、世界无意义的沉重叹息,这使陀氏的死亡现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现代主义的深刻含义。
关键词: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创作;死亡意识;现代观照
一
死亡是人类存在中不能摆脱的宿命,从古至今引发人们对其关注和思考,并成为文学发展中一个重要母题。但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人们对死亡的关注是变幻不定的,传统文学在表现死亡时,展现的是一个坚强的个体对社会人生的不屈抗争和探寻,而死亡最终都不外乎一个结果。即一个有形的个体的消失或一段生命的终结。正如伊壁鸠鲁所说:“当我们存在时,死亡对于我们还没有来,而当死亡时,我们已经不存在了。”
但在20世纪,由于上帝的死亡、传统理性的坍塌、两次世界大战的恶果、疯狂的经济竞争、性自由、拜金主义等导致了社会阶级的分裂、家庭结构的分裂和人格精神的分裂。人类在过去数千年中创造的精神文明毁于一旦,西方社会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社会生态危机。人们的社会情感随之濒于死亡。面对人类命运的种种困境,哲学家们自认为对人类有价值的理论、观念和变革手段显得苍白而无用。这种现实状况表现于文学,一方面引发了作家们面对现实和未来的绝望感,使现代主义文学笼罩着浓厚的死亡意象,另一方面,作家们对死亡的思考也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对肉体存在的否定而走向多层面,以其独特的方式在生命存在中获得了新的肯定。在现代主义作家笔下,死亡或是西方现代社会即将走向崩溃的趋势;或是西方历史沉淀了几千年的文明和文化趋于衰颓的景象;或是许多作家所展示的信仰危机、精神沉沦、道德颓丧的迷茫与空虚;或是人格分裂、自我丧失、人性失落的痛苦与绝望……现代主义作家对死亡的思考已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肉体消亡”,在一个文化缺失、文明颓废的时代里,死亡绝不是一个“从外面来到人身上的外在现象,或者说,只是人们在生命历程中突然遇到的一次偶然事件……而是人刚一存在就承担起的生存方式”它使人们以独特的方式从超越传统的视角感受着生命存在的深层含义。
陀思妥耶夫斯基生活在俄国19世纪新旧交替的社会转型期,由于命运之路异常坎坷,终生与疾病、贫困和灾难为伍,假死刑、苦役和流放、癫痫病等一次次将他置于生存的悬崖危境,心灵和肉体的痛苦给精神带来了饱经忧患的生存体验,这使他的作品不可避免地触及死亡并沉思这一永恒的话题。别尔嘉耶夫说过:“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完全是末日论式的,它只是对终极的东西感兴趣,只是面对终点。”的确,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充斥着各种各样关于死亡的描写:《死屋手记》中的苦役犯之死;《少年》中的自杀事件;《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的自杀;《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弑父;《穷人》中的大学生之死;《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中的尼丽之死;《罪与罚》中拉斯柯尔尼科夫在流放时所做的瘟疫大流行的可怕图景……陀氏连篇累牍地描绘死亡。一方面展现了传统文学中所表现的个体生命的终结。反映了他对人类生存的最深远的关切;另一方面从更高的层次上体现了陀氏对死亡的深刻认识。即一种更高意义上的超越肉体消亡的死亡观。这使得陀氏在表现死亡这一主题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现代主义的深刻含义。
二
西方哲学一向视死亡为一种“非存在”的状态。“非存在”作为一个否定性的概念,有两层含义:要么排斥在“存在”之外,要么被作为“存在”内的否定因素而加以克服。现代主义文学对死亡的思考正是对第二层含义的形象化阐释,海德格尔在谈到死亡时说,作为生存的终结的死亡并不是只在生命终结的将来才发生。而是贯穿于存在的全过程,人的存在实际上是一种“朝向死亡的存在”,死亡的本质并不是不存在了,而是一种虚无。也就是说,死亡不再是一种否定的方式,而是人的生存中一种不可超越的绝对的可能性,其中包含着深刻的生命存在意义。
陀氏所处的时代特征是俄国农奴制改革前后。封建贵族秩序被打破,新的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以排斥一切的力量冲击着旧有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旧贵族社会处于一种分崩离析的衰颓状态,整个俄国弥漫着一种末日来临的恐惧,这是陀氏死亡意识的一种表现形式。在陀氏笔下,许多旧贵族家庭的解体就是这种死亡观的具体表现:《白痴》中的伊沃尔金一家常常吵闹不休,父子相互仇恨,儿子鄙视母亲,兄弟姐妹之间相互厌恶,并最终导致了家族的解体。《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父子两代同争一个女人,为了财产大打出手,甚至以死相拼,面对熟睡中的父亲,长子德米特里“厌恶增长到了无法忍耐的地步。……他突然从口袋里拿出铜锤来……”老二伊凡也因对父亲怀恨在心,成了精神上的杀父凶手:而私生子斯麦尔加科夫更是出于对自己屈辱地位的反抗以及一己之利的满足,最终在疯狂中完成了杀父的行动……在这些家庭中,亲人之间充满了冷漠、猜忌、仇恨,旧贵族家庭表面上的优雅、荣耀、温情脉脉以及那种血缘亲情已荡然无存,旧有的道德体系在以个人为中心的资本主义文明冲击下也无力挽救旧贵族日薄西山的衰亡颓势,而旧贵族家庭的解体也预示着旧有的贵族制度的灭亡。陀氏通过一个个家庭的解体,象征性地展示出一个时代、一种传统、一种生活方式的终结,其中的死亡倾向再明显不过。在《白痴》中,他借列别杰夫之口比喻俄国社会就像是一匹灰色的马,而“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再后面便是地狱……”体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绝望感。这种绝望感体现在作品中,就是陀氏对当时的俄国社会所面临的信仰危机的痛心疾首,无论是前期作品还是后期作品,贯穿始终的一个声音就是“上帝是否存在?”
上帝的缺失是陀氏敏感于旧贵族社会的崩溃所导致的普遍存在的信仰丧失现状的深沉叩问。而伴随着这样的叩问,是不是“什么都可以去做”也成了人们现实生活中必然要面对的问题。这事实上是陀氏在信仰丧失之后对人的道德危机的深沉忧思。按照陀氏的逻辑,人的存在由于失去了信仰,道德秩序也将全面崩溃,而失去了道德约束的人的存在必然是虽生犹死的。正如陀氏在《卡拉马佐夫兄弟》中所言:“我的痛苦是……没有信仰”而这正是陀氏作品中死亡意识的又一种表现形式,即存在的无意义。
“断言存在的无意义,其心理学原因在于绝望和苦闷。”而社会根源是存在过程中无法排遣的痛苦。陀氏作品中的所有主人公,一方面相信他们能过上美好的生活,同时又一辈子都在受苦受难,而实际上这些罪差不多又都白受了,这不仅会产生老卡拉马佐夫所提出的问题:“是谁这么拿人开玩笑?”而且会直接导致出存在毫无意义的思想。伊凡对生命意义和人们必须生存其中的世界秩序产生了深深的怀疑,迷悯中的他陷入痛苦而无法自拔的梦魇中,他的幻影对他说:“你只要想想我们现在的大地……衰亡,冷却,破裂,粉碎……真是难堪到极点的乏味事。……”陀氏作品中所表现的信仰危机、精神沉沦等,传递出一种濒临末日般的幻灭感和危机感,也使陀氏的作品中散发的死亡气息具有现代主义的明显特征。
三
旧制度崩溃了,信仰没有了。人类就会因普遍的有肉无灵、有欲无情、精神缺失而迅速走向自我灭绝。于是,人格的分裂、人性的灭绝、自我的丧失也成了陀氏表现的一个重要主题,这种因存在的某种丧失或缺失而导致的死亡意识在现代主义文学中大量存在,而这一点也构成了陀氏作品死亡意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人是什么,我是谁,这是以人为本的西方哲学和文学共同关注的焦点。哲学史上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到二十世纪的恩斯特·卡西尔等,关于人的探寻从未间断过,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将人的存在只是看作是一种表面的现象,在传统文学中,形形色色的人物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的方式经历着矛盾冲突,但这种冲突只是由于外在于他们的某种环境、或由他人的某种欲望所导致。而弗洛伊德“潜意识”理论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人类更加深邃的内在隐秘,看到了人因“本我”与“超我”激烈交战而导致的内心分裂的痛苦。而陀氏的创作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具有了现代主义的内涵,尤其是他对人因内心的深刻矛盾所导致的人格分裂有着独特的理解,他认为,人置身于某种社会条件下,社会道德信念与满足自我需求的本能不相容,而又找不到精神支点以获得心灵的慰藉,因而人性分裂、摇摆,以求平衡。其典型表现就是两重人格。
《孪生兄弟》中的戈里奥特金由于悲苦的境况使他无法像正常人一样挺起胸膛做人,于是在内心裂变出另一个新的戈里奥特金,进行了一场“白日梦”式的野心的挣扎。但是,要想爬上去,就必须趋炎附势。出卖良心。可这一切和原来那个戈里奥特金的善良本性完全背道而驰,这样,两种尖锐对立、水火不容的气质在戈里奥特金身上纠缠、斗争着,同一个戈里奥特金被作家一分为二,善我与恶我激烈地战斗、融和、分裂……从而形象地展示了人在社会重压下内心的挣扎、喘息和灵魂的扭曲。《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每一个人物,都体现着这种人性的复杂与矛盾,感受着灵魂撕扯的痛苦与煎熬。德米特里就是一个“残酷而淫荡的蜘蛛灵魂”和高贵的冲动相结合的人,一方面罪恶多端、放荡不羁,一方面却是神圣的新道德的化身,“一种新的人性的最圣洁、最敏锐和最真诚的预言家”:而伊凡更是一个人格分裂的典型:一方面,他摈弃道德原则,不分善恶是非,鼓吹“一切皆可妄为”;另一方面他又崇尚理智,同情人类苦难,否定不平等的社会,为了儿童们遭受的苦难责难上帝,富有人道主义精神……作品中的每一个人都在两个对立的深渊中挣扎,一方面是高尚的理想,另一方面却是极为卑鄙可恶的堕落。
在陀氏的作品中,这种分裂的“自我意识”使主人公在感受世界和感受自身的过程中往往产生对自我的疑惑,这又导致了人的精神世界的消解,表现在创作中便是出现了大量丧失自我的典型。《地下室手记》中的“地下室人”形象就是一个自我迷失,无人格的典型。他没有健康、崇高的精神世界和生活理想,也体验不到人之为人的崇高价值。于是他放弃了对于人和世界的希望,蛰居在一方小小的角落里,在绝望中享受自辱自虐、自轻自贱的快感。他常常躲在地下室里,想“别人如何想他……可能对他做出何种定义和评价,并猜测他们评价他时所用的口气和感觉,想象别人可能会用的字眼。他甚至停下自己的话,来插入想象中他人的回答。”他在现实的存在中找不到自我的定位,只有“通过一面他人意识的镜子,注视自己,注视着自己的形象在所有这些镜子里的折射影子。”甚至在有些时候,希望别人把他扔出去以证明别人对他存在的承认……由此我们看出,“地下室人”其实是丧失了人的真正价值的、无人格的畸形的人。而陀氏作品中的其它一些人也常常因自我人格的迷失而痛苦:把自己关在个人小天地里并沉湎于孤独思考的拉斯柯尼科夫说:“我是虱子”、“人是虱子”;德米特里也说:“我就是那只昆虫……我们卡拉马佐夫家的人全是这样的,就是在你这天使的身上也有这样的昆虫。”《群魔》中的斯塔夫罗金甚至说:“我知道我应该自杀,应该把自己当作一个卑鄙的虫豸那样从地球上清除掉……”
陀氏比同时代的任何作家都更敏锐地感到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弊端对人的存在所造成的威胁。生活在病态的、不和谐的社会环境下,人正常的、美好的感情会越出正常的范围,人与自我的丧失就成为了不可避免的人的结局。在陀氏看来,“人们孤零零地在世界上——苦就苦在这里!……一切都死了,到处都是死人……这就是世界。”
四
陀氏是一位“病态”的天才,终其一生,死亡问题总是在困扰着他的心灵,但陀氏更是一位肯定生命存在意义的作家。他以自己的文学创作展现了他对死亡的深刻理解,并苦苦思考着人的生存处境,其目的是想寻求一条解救人类苦难和困境的理想途径,但陀氏所处的俄罗斯,是一个大变动、大转折、骚动不宁的时代,整个社会呈现出矛盾与混乱的景象,危机四伏,他常常感到现实途径的困惑与迷茫。于是他把目光投向了现实之外,他曾说:“在这样的时刻,谁都会像一棵枯萎的小草一样渴望信仰”,他还说:“如果有谁向我证明,基督脱离了真理,并且的确是真理也脱离了基督,那我宁愿与基督而不是与真理在一起”。因此,陀氏在寻求人类拯救时,发现了宗教。而这一点也使陀氏对死亡的思考具有了现代主义的某些特征。
在现代主义文学中。许多作家在观照和思考死亡的多层面意义的同时,都在苦苦地探寻人的出路,寻找着拯救自我的途径,他们把目光投向了宗教,艾略特的《荒原》以荒原上空雷霆的回声喻上帝,表现出强烈的宗教期待;叶芝在《基督重临》中以“无疑基督就将重临”来呼唤一种新的秩序;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用耶稣受难前对弟子的忠告“你们要彼此相爱”为原型告诫世人,一个缺乏爱的世界是没有存在的可能的;贝克特在《等待戈多》中以苦苦地等待一个赋予人的存在以意义的上帝,传达出失去信仰的现代人的痛苦与绝望;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让布恩地亚家族的后代在堕落与纷争中不断怀想马孔多最初的美好状态,表明乐园式的过去必将成为永不复返的往事……这些作品在表现西方社会面对死亡的无奈和绝望时都发出了宗教回归的呼吁,他们认识到现代人的困境在于“存在性的焦虑”,在他们看来,只有宗教的终极关怀,才是处境空虚、生存下去的勇气已到了山穷水尽却依然渴望出路的人的一种拯救。“重新开始,重建慈悲之城”,是现代主义作家对宗教的共同呼声。
对于陀氏而言。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发展始终伴随着浓郁的宗教氛围,基督教的原罪意识和《使徒行传》、《福音书》所宣传的慈爱、忍耐、友善等宗教思想,从小就深埋于他的意识深处。这使得他在创作中关于人的思考基本上是一种宗教式的思考。面对当时的俄罗斯这样一个到处充斥着罪犯、投机商、精神病人、赌徒、酒鬼、“偶合家庭”等疯狂、冷酷、病态、丑恶、黑暗的世界,他认为人类已滑入一个最黑暗的时期。人的存在完全失去了应有的美好状态,对现实社会给予反抗是徒劳的,所以他选择了一条皈依之路,希望能够在宗教中找到社会罪恶的根源和人类苦难的解救之路。他认为宗教能使大家一起共同走向美好的未来,基督就是人类在苦难之中的希望,是人类在痛苦徘徊时对彼岸世界的向往。所以,他主张人们皈依宗教,并深信宗教是对恶的惩罚,是对人类苦难的拯救。这一点,陀氏和现代主义也是殊途同归的。
参考文献:
[1]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编译:《古希腊罗马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第366页。
[2]李永平:里尔克后期诗歌中关于死亡的思考,《外国文学评论》,2002年第2期第10页。
[3]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第198页。
[4]易丹:《断裂的世纪》,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45页。
[5][7][9][14]《卡拉马佐夫兄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592页、第73页、第975页、第153-154页。
[6]《白痴》,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243页。
[8][德]赖因哈德·劳特:《陀思妥耶夫斯基哲学》。沈真等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23页。
[10]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世界文学》编委会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上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73页。
[11][12]巴赫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问题》,北京:三联书店,1988年,第52页、第53页。
[13]《罪与罚》,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556-557页。
[15]《群魔》,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第894页。
[16]《陀思妥耶夫斯基中短篇小说选》(下),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第644页。
[17]陀思妥耶夫斯基:《1854年1月末至2月20日致冯维辛娜的信》,《俄国语言文学研究》(文学卷)第一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447页。
[18]孙彩霞:《西方现代派文学与(圣经)》,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第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