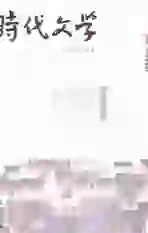庚寅短章(18首)
2011-12-29张庆岭
时代文学·上半月 2011年2期
作者简介:张庆岭男,山东齐河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小拇指》诗刊主编。
创作谈:
诗,不是表达,表现,再现,更不是思辨;诗,只是呈现,只是把自己亮到那里,把衣服脱掉。赤身裸体,然后把灵魂剖开。就这样,只是这样。一首诗的完成是二重奏,即诗人一重,读诗人一重,二者各占百分之五十,谁也不能少,谁也不能多。诗不是小说,不是散文,不是戏剧,更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普通文章。小说,散文,戏剧。以及普通意义上的文章,都是一重奏,作者写出来,就完成了,读者去读,只是听作者给你个交待,交待完了也就没了,喜怒哀乐直接产生,而诗却不行,她非要读者的继续制造而不能完成。非要读者继诗人开成的诗花结成读诗人的诗果而不能完成。
诗,要靠感觉。世界从来不缺少诗,我们也不缺少诗的创造力,我们缺少的只是对诗的感觉:对生活中的诗,对书面上的诗,还有对心中的诗。天涯何处无芳草?但,我们看不到。感觉,是一种能力,是一种读诗、写诗所必须的对于诗人是要命的缺了什么也不能缺了它的能力。感觉,让我们对一首好诗拍案叫绝;感觉,让我们把金子从一堆沙子中分离出来;感觉,会让我们发现那颗被黑夜千裹万裹的星星;感觉,能让我们在千军万马中取上将首级;感觉,可以教会我们洞察一切……感觉。就是我们心中的诗呵!一句话,所谓诗人,就是对诗有特别感觉的人。
诗,要“深深的,浅浅的”。我曾这样打过一个比方:说她就像一个绝美的裸体,只披一件透明的轻纱。那件轻纱,就是她的语言——要浅,浅到明白如话。我们可以透过轻纱,看到你所想看到的许多东西。想到你所想到的许多东西,这就是她的内涵——要深,深到一层意思后面还有一层意思,甚至深到深不可测。也就是当你真正地进入诗之后,那件轻纱,那些浅浅的语言,就已经没了,化掉了,这就是我所谓语言的“浅”,而她的内涵却让你一次次惊魂地愉悦,这就是我说的“深”。拿两句诗来作证——“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你们说,它该有多么明白,而它又该有多么深刻!
……
路灯
生活睡了
连生活摘下的面具——城市都睡了
唯有路灯
醒着
它在等那些一直都在为别人
打造面具的人等他们下班等他们
回到住处回到12个小时
之外
它一定要送给他们一小片温暖
它知道身处黑夜的人
最需要
什么
牛二小儿卖粮
两万斤小麦一个大拖挂
就装了 牛二小儿坐在拖挂上
任迎面的风铆足了劲儿吹他
风 知道他的心是热的 他
一年的希望是热的
风 更知道 牛二小儿 即将
到手的票子也是热的
收粮的老板走过来
牛二小儿明白——财神爷来了
脸上便堆满了小山一样的谦恭
老板把长长的手伸进粮车里
好一会儿才抓出一小把麦粒子
老板把麦粒子放到嘴里嘎、嘎、嘎地咬
好像要咬出藏在牛二小儿身上的水分
牛二小儿把香烟和笑一股脑儿递上去
老板一边“吐吐吐……”
一边刮北风一样高喊:
“三级 三级 三级……”
九月的天 牛二小儿
就冻在了那里
回家
专走田间小路
顺着儿时蛐蛐的叫声
在七拐八拐羊肠子一样的高粱地
玉米地、棉花地缝儿里
走失城市综合征
一群孩子正在豆子地里捉蝈蝈
他们把亲切的乡音捧在手上
目不转睛地打量着眼前的陌生
然后 若有所悟 转眼 又像一群
小麻雀飞得无踪无影
城里的星期天够不着乡下
满地的庄稼就比着个儿生长
立秋说到就到 连路边的小草都知道
致富不是小事——谁敢给
过日子开玩笑……
再拐过一片桑林就看见家里的老屋了
门前的大柳树下 是否还站着
母亲的张望? 心中一阵嘀咕——
可要拄好拐杖呵娘! 千万小心 别让
八十岁的咳嗽跌倒
数数故乡六十年
这六十年 能够如数家珍的
就两样东西
从第一年开始 我就数到了饥饿
一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十年
一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十年
一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十年
一年 二年 三年 四年 五年……十年
数着数着我终于
数到了温饱
数着数着我就发现
故乡竟被这两样东西
追着跑起来了
冷板凳
我知道 现在它和我一样
在这座城市里无倚无靠
我更知道 它的一条腿 似乎
在早些年就被命运咬伤过 到
现在还有点儿瘸
不时地痛
但是 我还是看了它一眼 然后
就实实在在地坐在了它上面
生活太累了
我必须明白:只有坐稳了它
才有可能让它和我
还有这座城市
变热
大风刮了一天
大风刮了一天
大风不满意自己的处境
它要从一天里跑出去
将自由扩张一倍
大风如一头疯掉的猛兽 张开利爪
一边狂奔 一边吼叫 它
撕抓着自己的内心——
一些树叶、枯枝被抓下来
一些轻浮之物扬上半空
它要抛弃自己的
浮躁与虚妄
大风刮了整整一天
傍晚时分渐渐安静下来……
第二天清晨 隔着时间的栅栏我
看见大风正趴在昨日的院里
温柔如一只小猫
它睡着了
怀念
登上纽约的凯伦大厦
我不想再怀念任何人 比如脚下的
华盛顿、马克·吐温以及那个写《致船长》的
惠特曼 我要从此学会怀念自己
学会怀念我逝去的三颗牙齿、剪掉或脱落的
头发 以及永不回返的童年
我要像怀念太平洋的每一滴水
亚洲大陆的每一寸土地那样
怀念它们 我要将我剩下来的身体
还没来得及打法的岁月 都
变成千千万万个汉字 再用
家乡的方言 一个一个
将他们喊出
酒后
都走了
狼藉的杯盘、东倒西歪的空酒瓶子
没有走 它们还在继续等待
一场酒事的峰回路转
坐在老大位子上的那个人的手势
话语的回声、身体的气味 也没有走
由于不断向杯子里倾倒着重量级
话题 满屋子的灯光
默默地有增无减
六张嘴制造的烟雾、狂妄、伤感、抱负
不亚于一场难以消散的热带风暴
从醉意里脱口而出的那只手 再快
也抓不住一只酒杯决心撞击
命运的清脆声……
十分钟后 与此无关的一双手
推门进来收拾残局 然后 于黑暗中
领着十年后的回忆出去
古井的执著
先把头低下去
然后把身子低下去
最后把一生低下去 世上没有谁
像他这样执著地低至脚下
直到低进大地
直到低成虚无
低成深刻
低成清澈
现在它已经低进了历史
母亲的顶针儿
顶一下缝一针
再顶一下再缝一针……
在童年漫长的冬夜里 母亲
用一枚顶针儿为我缝制了多少温暖
母亲一辈子没戴过戒指
顶针儿就是她的戒指
春阳时 秋风里 油灯旁
母亲缝补着清贫缝补着 我们
兄妹五人的幸福 更大的幸福
便从顶针儿的坑眼儿里漾出来
一直漾满母亲的一生
母亲有力的中指借用一枚顶针儿把
对我们一家人的爱打理得
利利索索
大湾塘上的簸箕石
一年四季村中的婶子大娘姑姑姐姐们
都来这里洗衣 她们雁儿一样一字儿摆开
洗各自的心事 其实农人的衣裳
并不脏 汗臭味儿泥土味儿辛苦味儿
一洗就没了 她们来洗衣大多是
为了来说说话 把自己听来的新闻、趣事
邻村的蹊跷,个人心中的忧愁、烦恼……
随着哗哗哗的洗衣声全倒进河里
一到盛夏晚上这里就更热闹了
几乎大姑娘小媳妇全都跑来洗澡
白白滑滑的石头上攒动着一片
白白滑滑的青春
夜幕下或月色下全是女人的大胆与泼辣
戏水声、嬉闹声将大湾塘上的簸箕石
陷落进一片纯朴之中
洗衣少女
怎么看那条小河都是从
她的一双大眼睛里流出来的
欢快的洗衣声 甩出一道道彩练 让
那么多星子溅上天空
把青春从左手移到右手
少女就有了双倍的美
河水的绿、天空的蓝、胳膊的白
让身后的城市哑口无言
鱼儿是世界的左眼
心跳是世界的右眼
它们谁都一动不动 世界
也没有办法
感知一粒灰尘
它 怎么就那么小 小到
绝对不值得你说——微不足道
小到 让我的惊讶一下子
失去了控制
我是借阳光的眼睛才发现它的
不 不仅仅是 还要加上 七分敬畏
三分想象 以及
哲学与美
它 悬浮在那里
就像一枚太阳悬浮在太空里一样
就像一个问题悬浮在一个人的脑海里一样
它 悬浮在那里 把心中巨大的平静
想了又想……
它 什么都不想干 只是
紧紧地抱着自己的小
让我的大一下子消失
多想登一次黄鹤楼
不是现在也不是民国
更不是病入膏肓的大清朝
而是一步一步回到开元盛世
真不知道走多少路才能到达唐朝
做多少诗学准备才能在一首诗里邂逅崔灏
登上楼顶我把一脑子的简化汉字
全倒出来让它变成一行行
空悠悠的白云 我想
这一次该轮到汉阳纸贵了吧
可 我错了 分明看见
大地安静成一张白纸
上面只写出两行字:
夜不闭户
路不拾遗
两个放蜂人
每年初夏他们就
带上庞大的蜂群把日子
从南方搬到北方
一对夫妇一个双目失明
另一个左腿有严重残疾
梨花开了 槐花开了 过不了多久
大平原上的枣花也会开
他们脸上的笑容也会开
有嗡嗡嗡的蜂语有铺天盖地的光明就不怕
平平仄仄的人生既不工整也不对仗
用不着修补残缺的命运 但他们必须
把幸福弄短再把苦难弄长
收拾完一天的活计倒头便睡
期盼一下子撞上
对方的梦
在德州地摊儿吃早餐
这是北方平民规模庞大的早餐
一排排脏兮兮的矮桌子
忽地就能把自己伸出两米多长
歪歪斜斜的饭价表站在木牌子上
正在向你 点头 微笑 问候
大火烧一块 窝窝头五毛 肉夹馍两块五
满满一碗老豆腐一块二……
在这里掏出又装进口袋里的每一分钱
全都深呼吸一样的纯洁
汗水一样的干净
面对面坐下的不全是本地口音
男人 女人 大人 孩子 丑的 俊的
穿着随意 打扮时髦 笑或者不笑
熟识的也罢 陌生的也好 现在大家
围坐成了一家人 谁也不把
饥饿与吃相藏着掖着
刚下夜班的小姐与就要上早班的建筑工
还有那位诗人 一个网络写手 和
一位半工半读的大学生现在大家一起
坐在同一张桌子上 他们的目光
在轻轻地游走 擦肩而过 或者
浮光掠影地碰撞 但谁也没能
找到久违的故乡
故乡土屋
一眼看上去 还是那副
站着跟蹲着一样憋屈的老实相
土坯 土墙 土底脚 土屋顶……
从上到下 土成一个
浑厚的汉字
窗上的剪纸 早已
让时间撕成了碎片 两扇
木讷了一辈子的屋门大张着没有牙的嘴
风出出进进 多像一位
来去随意的邻居
灶前飘着炊烟
炕上睡着我的童年 院子里
传出一声声潮湿的狗叫
觅食的母鸡带着一群子女 将
满地的饥饿啄乱……
可以百分之百地断定
母亲去村东头借粮还没有回来
她已无力精打细算 只好放开手脚
任锅里煮着的野菜 将
清汤清水的委屈千百遍地
大口大口吞咽
暴雨
天空原本那个蓝啊 蓝得
几乎就要掉下来
秋风在擦 白云在擦
劝是劝不住的
我怀疑那场暴雨
是从蓝的深处降下来的
乌云只不过是一点儿点儿由头儿
准确地引发了这个世界
根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