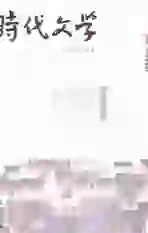诗意的故乡
2011-12-29陈德均
时代文学·上半月 2011年2期
陈德均,男,本科学历,中共党员,1963年5月10日出生,1982年7月师范学校毕业后在中学任教15年,1997年9月调入禹城市教育局从事教学研究和教育科研工作至今。先后被评为禹城市十佳园丁、德州市教学能手和山东省教育科研先进个人,所写论文多次获奖或编入省级出版社出版的文集中。自幼热爱文学。2010年开始尝试散文写作,2010年6月发表第一篇散文作品,迄今已在《鲁北文学》等文学刊物上发表散文作品五篇。
1
我的故乡地处鲁西北平原。从济南往西100多华里,有个不足400人的小村,便是我的出生地。小村何年何月建立,不太清楚。传说我们祖先原本不在山东,是明朝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底下迁移而来。迁移的原因,有的说瘟疫,有的说洪水,有的说战争,到底为什么,没去考证。其实,所谓的故乡原本都是他乡。这是余秋雨先生说的。从朱元璋时期到现在,这片土地上已延续了若干代,骨子里、血液中,早已被齐风鲁俗同化,成为地地道道的山东人。
山东人和全国人一样,有优点也有不足。传统山东人有敦厚尚礼、豪爽侠义、勤劳正直、顾全大局的一面,也有好走直道、谨慎保守的一面。山东古代出过不少名人,近代以来步伐一度落伍,改革开放后又见起色。比较而言。鲁西和胶东仍有不小差距。
我的故乡属内陆性温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冬季不太冷,夏天不太热,春秋相对稍短。春天多东南风和西南风,雨量很少,有“春雨贵如油”之说,属较干旱地区,秋天多吹西北风和东北风,有时偶有扬沙天气,夏天雨量较大,多急雨。常打雷,但往往一阵风后即能放晴。也有连续几日阴雨连绵的时候,但不多。有时一阵大雨后可以看到艳丽的彩虹。
小时候,村里的房子都由土坯垒成,墙面糊一层黄泥。土坯下面由五层或七层的红砖支撑房体,房梁一般由榆木充当,檩条大多为柳木,一般为五根,也有七根的,檩条上方横着一根根半米长的椽子。椽子上面是芦苇编成的房席,席上加一层厚厚的黄泥,便铺成了房顶。房顶几乎是平的。夏天可以铺张草席,在房顶上纳凉,清朗的夜空星光满天,南风徐徐吹来,凉爽而惬意。
那时的小村。一个家族往往相邻而居,大门口斜对着,共同朝向同一个胡同,春冬两闲时可以相互串门、聊天,逢年过节相互致意、祝福,同族问尽管也有吵闹。但很快就能握手言和,至今回想起来,那种浓郁的乡情氛围依然令人难忘。
2
小时候,村中共有三条街道,均为东西走向,街面不算平整,大雨过后常常泥泞不堪,单从审美角度看,实无美感可言。但院子西边那片枣林却是一道难得的风景。
那片枣林东西窄、南北长,比较开阔。抬眼望去,浓郁的树冠仿佛大片的绿云在空中悬浮着。枣树的树干黑中见紫,表面粗糙,木质坚硬,叶子呈椭圆型,大小与拇指差不多,枝条舒展,如龙爪向天,枝叶间多刺,形似大头针,稍稍有些弯曲。
每年农历六月是枣树开花的时期。枣花金黄色,呈五角形,比绿豆粒大不了多少。此时勤劳的蜜蜂会闻香而至,扇着翅膀在花叶间嗡嗡地不停忙碌。七月中旬枣子由青变红,八月上旬陆续成熟。成熟的鲜枣呈大红色,与鹌鹑蛋大小相当,形状也是椭圆型,表面光洁滑润,吃起来脆甜可口。
儿时有很多游戏,爬树比赛便是其中一种。有时候,我们玩腻了,便开始打赌,比赛爬树,看谁爬得又快又高。谁也不服输,争先恐后地往上爬,免不了被枣刺扎几回,也不敢叫苦,咧着小嘴强充好汉。
每年,一到枣子成熟季节,我们这些顽童总是不甘寂寞。常常跑到林子里偷枣吃。那时枣林的主人70岁上下,个子不高,秃顶,有些驼背,头上常裹一条白毛巾。我们总是趁他不在,捡起砖头瓦块朝树上乱投。然后爬在地上哄枪枣子。有时吃得正带劲儿,猛听到不远处一声断呵:“那是谁啊?给我站住!”吓得我们心惊胆战,撒腿就跑。一边跑一边听他不停地喊:“哪里跑?站住!”喊得越响跑得越快,不一会儿就从枣林里消失,躲进旁边的胡同里……
3
那时村东村西各有一个池塘。东边的池塘里长满了芦苇。春天池水少,芦笋尖尖地从池底钻出来,很快就没过膝盖、高出头顶。夏天雨水多,村里村外的水大多流进池里,芦苇本是水生植物。在水的滋润下更加密密麻麻、郁郁葱葱,彰显出生命活力。
秋天,芦苇渐渐吐出穗子,白白地招摇在顶上,在微风吹拂下,左右摇摆,远远望去,苇荡上方仿佛白白的流云在飘荡、舞动。到了深秋,苇穗熟了,苇絮带着种子,随风飘散,像春天的柳絮、冬日的雪花。秋天的池水不深,池中小堤开始显露,池塘被自然分为两块,中间稍高处有个很窄的缺口,一股细水流通南北。北面的池水渐渐浇了农田,南边的水位相对增高,缺口处水流变急,每到这时,我们常会握一把笊篱(漏勺),静静蹲在那里,专等逆水而上的小鱼,捉到的小鱼虽然大多三四寸,但兴致始终不减,常常一蹲就是半上午。
等到北边的水接近干涸,我们就和大人一起去池里摸鱼。伸开小手,小心翼翼地贴着池底轻摸。常常可以捉到卧在水底的鲫鱼。或是大家先把池水搅浑。把大点儿的鱼呛到水面,然后用自制的小网悄悄由下往上捞。那时我只有十岁左右,竟侥幸捞到一斤半的大鲤鱼,算是一种不小的收获。
冬天是芦苇收获的季节,池水变得越来越少,等水面结了冰,大人们便开始拿起镰刀和铁锨收割芦苇……芦苇的叶子窄、长、尖,苇杆犹如女性的小指那么粗,一节一节的,似细细的竹子。小时候没什么玩具,拔一颗芦苇,选节粗的,三削两削做成苇哨,可以高高兴兴吹上好几天。我十来岁时,田里缺少肥料,大队书记拍板,集全村之力铲掉苇根,深挖池泥肥田。田是肥了,但从此再也见不到那一池芦苇。
不过。事物都从两面看,此后我便看到了另一种风景:秋天的池水澄澈见底,池面平滑如镜。靠岸的水中,小鲢鱼自由自在地闲游。远处的岸上,成行的绿柳倒映在水中,呈现出一种对称的美。池的中央,几只白鹅安闲、优雅地慢游着,天蓝、水清、树绿、鹅白,一幅多么亮丽清新的美丽图画啊!突然,一群爱吵闹的鸭子嘎嘎叫着来到岸边,扑哧扑哧窜入水中,小鱼骤逝,树影被弄乱,鸭的身后平添了几道道浅浅的拖痕……
4
村西的那个池塘更大,塘坡更缓,池水也更深一些,那是我们夏日戏水的地方。七岁时,母亲看着我学游泳,到八九岁时已游得有模有样。小时的生活很艰苦,吃不好也穿不好,物质相当贫乏,那个池塘便成了我们的精神乐园:有时候,我们一块游到池中心,平均分成两组后,各退一段,开始泥水大战——先憋住气,深扎猛子,到池底捞一些紫泥,然后一边踩着水,一边使劲地向对方投去,看谁投得远、躲得快、藏得好。有时我们用手撩起水,把干硬的斜岸弄得又湿又滑,然后光着屁股,头上脚下斜躺在坡上,相互比赛着往下滑,看谁先滑到水里面。有时我们比赛游速,像一群水鸭子,扑啦扑啦鼓着劲儿往前窜,看谁先游到池对岸。
几年后,村西的池塘包给一家农户,里面种了莲藕,秋天虽可以看到满池的花红荷绿。偶尔还可以偷个莲蓬吃,但盛夏时节再也不能去那里游泳。此后每逢暑假,我们就转到村北的小河里戏水。小河深约三四米,宽大概七八米,河上有一个单孔平顶砖桥,河的两岸栽满了柳树,风一吹摇曳多姿。夏天烈日炎炎,大人们干完农活路过这里,常常坐在桥旁的树荫下乘凉,等凉快透了、闲聊够了再回家做饭。
那时村里没有电,吃过晚饭后我们无事可做。闷热难耐时,便约上伙伴来到村后,先从桥上跳入河中,舒舒服服泡泡温水澡,再相互嬉闹一番,然后从西往东,从东往西地游个痛快……
5
小时候,乡间的房子比较简陋,只从村里看算不得美观,但若技个角度,绕到外边去看,小村也别有一番风景。
初春,柳树的枝条最先发芽,树冠上淡淡的绿意,如烟似幻,散发着朦胧的诗意关。夏、秋季节,远看小村,只见树屋掩映、绿灰相间,袅袅的炊烟从树梢上、屋顶上徐徐上升,随后逐渐消散,俨然一幅有静有动、乡味浓郁的立体油画。孟浩然有诗云:“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我们这里看不到青山,但绿树绕村的景象却是真真切切的。冬天,当柳树、榆树、槐树一一落尽叶子,只剩了枝干,远远望去,黑色的枝条后是微灰泛黄的房舍与墙面,线面结合、简约素淡,好一幅生动传神的中国水墨画!故乡的田园也自有风光。春季到夏天,田野平坦,一览无余,万物苏生。秧苗吐绿,大地像一条巨型绿毯,散发着勃勃生机。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大豆圆,棉花白,玉米黄,瓜果飘香。秋天的天空湛蓝而高远——天如苍穹,笼盖四野。秋天的云是巧的,变幻无穷,如羊、如狮、如车、如船。有时一抬眼可以看到白白的、缓缓南行的人字型雁阵。树上蝉鸣鸟叫,岸边、田中蛙声不断,村里、村外犬吠牛哞。冬天的田野光秃秃的,似乎没什么好看,不过在我看来,大平原上空旷的原野也是一种独特的美,一种素净的、广阔的、单纯的、质感的美。
那时,我们常去离村五六里的田里干活儿,虽屡遭雨淋,也多次看到日升日落的景象。那艳阳夕照、彩霞满天的画面着实让人难忘:太阳越来越低、越来越大,天空越来越红,越来越绚烂。对此,萧红在《呼兰河传》里曾有过精彩的描绘:“天上的云从西边一直烧到东边,红彤彤的,好像是天空着了火……”火烧云(彩霞)不仅热烈美丽,本身还有预测天气的作用。当地农谚云:“云来接,阎王不得歇;火烧云,赶明儿(明天)晒死人”——我们这个地区,太阳将落时,地平线上如果突然涌来一片云,第二天不是阴天便是下雨:如果“彩霞满天”,第二天十有八九会阳光灿烂。我观察过多次,通常很准。
至今,我的脑海里仍时常浮现出这样的画面:夏日的傍晚,我们牵着牛,扛着锨,从西北农田里往家赶,背后是落日,身边是小河,眼前是炊烟袅袅,绿树葱葱,隐约露出灰白的房舍,村子里不时传来母亲呼唤儿女回家的声音,加上此起彼伏的马嘶、鸭叫、蝉鸣,共同弥漫成一曲乡村交响乐,在小村的上方萦绕、盘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