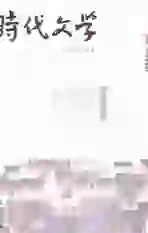拔顶芯
2011-12-29窦秀哲
时代文学·上半月 2011年2期
窦秀哲,男,1959年8月生于山东省临朐县五井镇南蒋村。1975年参加工作,任过教、打过铁、当过公社专职通讯员,第一学历,初中。恢复高考后。1979年考入原德州师专政治系。1981年分配到德州市报工作,先后当过记者、编辑,总编室主任。现供职于德州市人社局。其作品散见于省、市文学刊物。
20世纪70年代初。
那一年,我正上小学五年级。炎热的夏天来到了,劳作了一上午的人们,吃罢午饭,困得直打哈欠,两只眼皮似有千斤重,谁不想睡个午觉解解乏,可大槐树上的高音喇叭,拼命地唱着现代京剧:“九龙江上摆战场,相互支援情谊长……”没办法。大人们只好到田间地头。横七竖八地躺在地上睡觉。眼下玉米棒子已长得半人多高了,山上山下,一片望不到边的绿色海洋。就连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绿色清新的味道。俗话说,六月连阴吃饱饭。谁知这话对不对?一连三天的时断时续的阴雨天气,使正在快速生长的玉米棒子,大片大片地发生了虫灾。
这还了得!大队支书兼革委会主任豆树新大清早就在大喇叭上声嘶力竭地吆喝:“眼下玉米棒子发生了虫灾,将直接影响粮食跨纲要,要不赶快治虫,还有绝产的危险,要求全村男女老少总动员,老婆孩子齐上阵,打一场虫口夺粮的人民战争。”为灭虫,大队责令正在上课的学生放了一周的假。为此,俺村一至五年级的小学生,各队回各队,成立了学生灭虫队。各生产队由一名有文化、善领导的社员作为领队。我们二队,队长点名让已是三十冒头、平时喜欢扎堆于妇女。爱说俏皮话的窦秀堂当我们的领队。经过一番紧锣密鼓的准备,一场轰轰烈烈的灭虫歼灭战在全大队上下打响了。天不亮,在大喇叭的喊叫声中,人们就披星戴月。向着玉米地出发了。
社员们在泥沙中,按一定比例,拌上了一种叫六六六的农药,大家拿着各种瓢盆,盛上农药,逐棵往玉米芯上撒。闷热的天,大人小孩穿行在棒子地里,毛茸茸的玉米叶子,在人们的身上划出了一道道的血印子,有的还流出了血,但谁也没有叫苦喊累。大家有一个共同的心愿,就是赶快把这危害玉米生长的虫害治下去。我们二队的三十多个一至五年级的小学生,拿着盛满农药的瓢盆,不停地穿梭在玉米田里,你看一个个生龙活虎,干劲十足,还真有那么一股战天斗地意志坚的劲儿。
休息的时候到了,同学们都在地头坐下来用褂子擦汗。有的同学跑到附近的河里喝水。我看到眼前三队的玉米地里的虫害厉害,其玉米顶芯大都被虫子咬坏了,有的已枯萎了,有的正在枯萎,就起身到地里拔了两棵被虫咬坏的玉米项芯,并在虫口处放上了一点农药,心想,非杀死你这可恶的害虫不可!同学们看我这样做,也不约而同的涌进了地里,有的拔顶芯,有的撒农药。正在大家干的起劲的时候,秀堂从远处跑了过来。他站在地头大声喊:“这是三队的地,快回来!”我也跟着喊,“别浪费农药了,拔了顶芯就走。”于是“呼啦啦”一帮同学又回到了田边地头。有的同学议论:“这是三队的玉米棒子,你们操的哪门子心呢?”秀刚争辩说:“还不是集体的东西,都不管,谁管?”就是这一会儿的工夫,几十棵被虫咬的玉米,有的拔了顶芯,有的灌上了农药,虫害可能没什么问题了,谁知,却为以后的批斗埋下了深深的伏笔。
开学了,大家都陆续来到了学校。刚踏进校门,我就看到大队民兵连长陈传忠,抱着一些半干的玉米叶子,走进了老师的办公室。整个一上午,上了四节课,老师讲的什么,一点也未记住,倒记住了老师那张铁青的十分吓人的脸。我预感到这是不祥之兆,果然不出所料,中午放学时,老师把我们二队的七名同学留下了,这里面包括两位女同学。三名老师紧绷着脸,像赶羊似的,把我们赶到了一年级那间黑屋子、土台子的教室,然后,负责的老师秀善扔下了一句话:“在这里好好反省!”转身“咔嚓”锁上了门。秀善是大队指定的村小学的负责人,文革前完小毕业,据老人们讲。他虽只上了四年学,却是全村第一个大秀才。红白事儿,逢年过节的毛笔字,都是出自他的手,是村里村外颇有名气的大能人,但他好像长了什么吓人毛,全校的学生都怕他。“我们这七个人是怎么了?”“谁知道啊!”“管他呢。”“不让走,咱就在这里拉尿,去他娘的!”早晨饭,大家大都是喝的稀饭,没到中午就饿了,这时一人说饿,六人响应,但锁在屋内出不去怎么办?“唉——有了”,透过门缝看到了秀刚的妹妹秀响在院子里找秀刚。于是我们几个就嘴贴在门缝上大声喊道:“快过来,快过来,我们在这里呢。”听到喊声,秀响跑了过来,“你们怎么被锁在这里?”“你快回家给我们拿点吃的吧,饿坏了!”“中,你们等着。”于是好心的秀响回家给我们每人拿来了一个煎饼和一小块咸菜,饿极了的我们狼吞虎咽地一会儿就吃光了。下午上课铃响了,全校一百多名学生集中在五年级的大教室里,我们却被锁在一年级的黑屋子里,听到外面唱歌了,秀胜说,“人家唱歌咱唱样板戏”于是秀胜起了头,我们七人一起高声唱起了《红灯记》:“临行喝妈一碗酒,浑身是胆雄纠纠……”
“都别唱了,不知愁得慌?”秀善凶神恶煞地跑过来了,他气呼呼地说:“给我听好了,我宣布,把破坏庄稼分子窦秀刚揪上台来!”“啊,揪斗我们了!”被紧锁的门“哗啦”一下打开了,在秀善的指挥下,两名我们五年级的同学,一人反扭着秀刚一只胳膊,像大人揪四类分子一样,一路小跑揪到大教室的讲台上。大教室门口挤满了看热闹的男女老幼,看样子,他们都在议论着什么。紧接着把秀胜揪了出去,我是第三个被揪出去的,接下来是玉明、玉福,最后是秀静和玉环两名女同学。我们七人被揪到讲台上。靠着墙根排成了一串,秀善喝斥我们这些破坏庄稼的坏分子,要低头弯腰,老实认罪。
批判开始了,主持人是秀善。本次批斗会的发言人也是他,他例举了大量事实后说。“这次学生拔玉米顶芯,不是偶然的,是阶级斗争在生产劳动和学校的真实反映,其背后肯定有暗藏的阶级敌人,在扇阴风点鬼火。企图颠覆无产阶级政权,我们坚决不答应。”逐个批判开始了。万万没有想到,第一个出列被批的就是我自己。“窦秀哲你这个家伙,据大家检举,你是二队破坏庄稼的学生头头,你要低头认罪,老实交代问题。要从灵魂深处找根源,思想深处查原因……”
整整一下午的批斗会,在一片口号声中总算结束了。晚上回家生怕父母提及此事,未吃晚饭就睡下了,朦胧中我仿佛看到了历来和蔼可亲的父亲,不知啥时候换了一副冷峻严肃的面孔。
继学校批斗会后,大队一班人多次找我们二队被揪斗的七名同学交代问题,其中问得最多的是拔顶芯是谁教唆的?我把事情的经过讲了不知多少次,但大队一班人都说不行,不彻底,没触及到实质。没办法,大队让民兵连长陈传忠靠上,每天下午放学后让我交代问题,但问来问去,还是那个过程,于是,陈传忠也不耐烦了:“你再不老实交代,就交到公社去,让公安特派员处理。”我说,“就是交到省里中央也是这些事儿。”“小小年龄,像个老走资派,死不改悔,以后走着瞧。”一周后的一个有月亮的晚上,大队召开了批斗大会。大会一开始就觉得周边阴森森的,二三百号人鸦雀无声,会场四周,齐刷刷地站着二十几名荷枪实弹的基干民兵。当大队支书兼司仪豆树新宣布,“将二队破坏庄稼的阶级敌人窦秀堂揪上台来!”当时全场所有的人都瞪大了眼睛,只见两名背着大枪的基干民兵,一手反扭着秀堂的胳膊,一手拌着脖子,一阵猛跑后,将秀堂揪到了主席台。豆树新责令其跪下,早在一旁等候的工作人员,立刻给秀堂挂上了一块纸壳做的白牌子,上面写着:“破坏庄稼的坏分子窦秀堂”。刚才揪秀堂的民兵,迅速摘下了大枪并“哗啦”一下推上了子弹,黑洞洞的枪口对准了他的胸膛。“鉴于学校已召开了批斗会的原因,这次批斗会,学生就不再揪了。”豆树新清了清嗓子说,“这个、这个。窦秀哲是我大队小学五年级学生。这次拔顶芯虽数量不多,这个、这个,只有两棵,但却是二队学生中的出谋划策者。”话音未落,会场一片哗然。刹时,我觉得有千万条钢针在向我刺来,不知何时我们一起曾揪斗过的同学都站到了主席台上。“下面批判开始,首先由二队发言……”结果豆树新连喊了三声二队,没有一人回答,会场陷入了尴尬局面,一时间,人们议论四起。“没有发言的我发”,秀善说着,一个箭步跨上了主席台。从口袋里掏出了一摞子发言稿,清了清大嗓门。高声说道,“我怀着无比愤怒的心情,声讨窦秀堂带领学生破坏庄稼的滔天罪行。窦秀堂,你这个伪保甲长的儿子,一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反对社会主义,打着红旗反红旗。这次煽动学生搞破坏不是偶然的,是你长期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必然结果,我们要彻底批倒斗臭你。并且再踏上一只脚,让你永世不得翻身……”秀善措词强烈且充满火药味的发言,让在场的社员目瞪口呆,过去谁也不知道秀堂是伪保甲长的儿子,这时对他有成见的人幸灾乐祸了:“操,秀堂这个私孩子,平时装得人模狗样的,原来也是个鸡巴操的。”秀善批判完秀堂,把话锋一转,“我校这七名学生,之所以破坏庄稼,其根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在学校的反映,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争夺接班人的具体表现。就拿窦秀哲来说,本来是个好学生,可是他的舅父,解放前曾当过伪军,其姑夫是富农,这些人,人还在心不死,时刻梦想恢复他们失去的天堂,我们决不能掉以轻心。对阶级斗争要做到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
大队充满杀气的批斗会也是在一片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散了,但人们紧绷的阶级斗争的神经未松。最后对秀堂的处理是。戴上坏分子的帽子,交二队贫下中农监督改造,对我及六名同学的处理是,本年度不准推荐上初中且摘掉红小兵的胸章,视今后劳动学习表现优劣而定。事后。我们才知晓,大队和公社经联合调查,确认秀堂是这次学生破坏庄稼的幕后教唆人。据说,有人指证他到三队的地里指挥拔玉米顶芯。
批斗会后,我们几个像霜打的茄子,没有一个脸上有笑容。我想,完了,彻底的完蛋了。连上初中的机会都没有了,还谈什么理想啊?还是默默地学习、劳动,在农村下一辈子庄户吧。不到一个月的光景,秀堂死了,大人们说,他是得气鼓病死的,肚子胀得像小牛,其家人给他穿衣服时,费了好大劲,却怎么也系不上扣子。秀堂的老母亲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亲友哭诉:“俺那秀堂啊,你这个傻孩子啊,扔下老婆和一堆孩子走了,你可到了好处去了呀,再也不挨批斗了啊……”
转眼秋假来到了,学校一下又放了五十天的长假。当我们二队的学生掰玉米棒子,又来到了夏天拔顶芯的那块地时。目光一下被眼前的一切深深地吸引住了:被拔掉虫咬顶芯的玉米长出的棒子又粗又大又饱满。“我操煞你娘——瞎眼的王八蛋,把生虫的顶芯拔了有什么不好?狗日的还揪斗俺,不让俺吃饭,啥玩艺啊,我操……”秀刚在地头上拿镰刀指着那块地,一边擦眼泪一边骂,大家看到眼前的现象,谁心里也有数,但少说为佳,生怕再惹出是非来。这件事很快传到了公社,当天农技站就下来了一个戴眼镜的女技术员,她在那块地里仔仔细细地查看了大半天,临走时随便扔下了一句话:“歪打正着”。
“咳——”这歪打正着不要紧,害得我们有苦无处说有冤无处诉,用句当地的俗话说。可真“叹人”啊!
秋假开学后,不知是感动了上帝还是另有原因,我们七个被批斗的同学又重新发还了崭新的红小兵胸章,从此学校、社会不再提及那件批斗的事了,我也觉得如释重负。但还是害怕不能推荐上中学的事。快到寒假了,有一天,秀善从公社开会回来说,今年小学升初中改推荐为考试了,让我们抓紧准备考试,这下我放心了。一周后我村五年级的三十五名同学参加了全公社的升初中考试,幸运的是我们原本无缘上初中的七人,全在二十名之内,我竟以语文、算术、科学常识三个一百分的好成绩,名列榜首,成为当之无愧的第一名,其语文的作文,就是写了拔顶芯那件事儿,但没好意思写挨批斗的经过,所反映的是科学种田创高产这一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