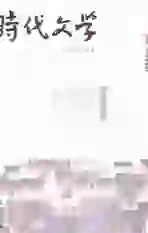散文二题
2011-12-29刘月新
时代文学·上半月 2011年2期
记忆深处的那些生灵
小时候,姥姥舅奶奶来家走亲戚,奶奶总是再三挽留让多住些日子,她们总是说,家里离不开,除了伺候一大家人吃饭,还喂着那么多生灵。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生灵”就是指的猪,羊,狗,猫一类动物。长大了才知道,但凡有生命的东西包括人、动物和植物都是生灵。既然有生命就该有生存的权利,最起码在生命上是应该享受平等的,但事实上并不都是这样。
少儿的天性中是最喜欢小动物的,而少儿的天性中又是最能毫无顾忌地戕害弱小生命的。这是少儿天性的悖论。我在这悖论中长大……
知了,知了
麦收已过,刚刚完成了“金蝉脱壳”使命的知了们,就忙不迭地在树上欢快地歌唱起来,整个农村因了它们的出现也似乎更加热闹。它们是在歌唱新生吧。如今蜷缩在城里的钢筋水泥格子里,很难再听到知了的叫声,每当想起这些,心里就会升起一种“猛兽被囚于笼”的悲哀,就觉得当年在故乡有知了相伴的日子更加珍贵,就越发怀念。一想到知了,就想起伙同弟弟们“火捉”知了的那一幕,那火如今还燎在心口上,生生地疼。
记得那年高考结束后,白天跟着母亲去责任田里干活,晚上就带着读小学的弟弟去村外树林里捉知了猴。树上的知了见到手电光亮,就像勇敢的飞蛾寻求光明一样扑棱棱飞到地上来,成了我们囊中的战利品。有一天我突发奇想,去树林“火捉”知了。我对自己这个新的创意竟然得意了好大一会儿。
晚上,我让弟弟约了胡同里的伙伴小柱和火蛋兄弟俩,我们四人抬着两大捆麦根(当时农村大部分还是拔麦子,用铡刀拦腰铡成两截,下半部分当柴烧),来到村西头的杨树林里。知了们在树上不知疲倦地高唱着,一声高过一声,浑然不知危险的到来。我们在树林里找那些比较宽阔的地面,把麦草一堆堆铺开,然后一一点燃,顿时,树林里火光冲天,麦草节燃烧时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我们四人拿着长棍挨个敲打着树干,在树上高唱着曲子的知了们被惊动了。不知何故地盲目地纷纷朝着火堆飞落下来。我们一人提一个纤维袋,手脚麻利地把它们拾起放进袋里。被请进袋子里的知了发觉上了当,在里面左突右冲高声嘶叫,我们早有准备,紧抓袋口使它们只能进不能出。地上的火苗在晚风中不停地跳动着,我们不停地敲打着树干,树上的知了们不停地飞落着。我们拾啊拾啊,一个多小时的工夫,竞收集了半纤维袋。待到火堆完全熄灭,知了飞落的声音由大到小到渐渐消失,树林又恢复了往日的常态,于是背起纤维袋高高兴兴打道回府。
我们把战利品一分两家。因为我是大姐。执意多分给小柱火蛋一些。我把知了倒在放了盐的清水盆里,把翅一一择去,光秃秃的知了在盐水盆里挣扎。看到知了痛苦的样子,我也感到四肢疼痛,我甚至在择完翅后不敢再多看它们一眼。第二天早上,我用清水把知了洗干净,放在锅里用油炒。那些黑黑的大大的肥肥的知了,用油一炒,油黑发亮,香脆可口,美味无穷。此时,我竟有一种成就感。这么多的知了哪里吃得了,于是,我又东一家西一家地为儿时的同学和伙伴们分送,她们吃了都说香。
其实,知了的一生漫长而又短暂。它的一生,要经过卵、幼虫和成虫三个不同的时期。卵产在树上,幼虫生活在地下,成虫又重新回到树上。幼虫的生活期特别长,最短的也要在地下生活2~3年,一般为4~5年,最长的达17年。幼虫们经过4~5次蜕皮后,才钻出地面,爬上树枝进行最后一次蜕皮(叫金蝉脱壳),成为成虫,就是知了。知了在地面上生活的时间只有80多天。在地下。面对的除了黑暗和寒冷,就是死一般的沉默了。所以,它们要在短暂的复苏时鸣出自己的辉煌。它们还是刚刚复苏。还没有真正叫出自己的人生却再次回到原来的世界。
这些知识当然是后来学到的。我懂得了这些知识后突然觉得有一种负罪感。那个火光冲天的夜晚我是无论如何也忘不掉了。一个花季少女为何会这般残忍?她本该是善良的,这大概就是少儿的天性吧!如今,那样的勾当我自然不会再去做,需要的是救赎,最好的办法就是热爱大自然。保护自然界的那些生灵。用真心,用真情。
蝴蝶墙
cc40692424c06ee8d888381a08f3a3d981876cdebfa44b55aa7037ca1ebd30ca
奶奶坐在堂屋的小板凳上择茴香,她从茴香堆里找出一个“茴香妞”递给我,说,它能变蝴蝶。这个信息使我大为惊喜,按照奶奶的说法我养起了茴香妞。茴香妞在我的精心饲养下,在我的殷殷期盼中一天天长大。有一天,我发现它伏在纸盒的边缘不动了,又过了几天,它蜕下了那身带黄色条纹的花衣裳成了一只茧。再过了几天。一只大大的嫩嫩的还没来得及舒展开翅膀的花蝴蝶出现在纸盒里,就像一枚鸡蛋变成一只小鸡一样,茴香妞终于变成了美丽的花蝴蝶。这只花蝴蝶又大又好看。它的翅膀一天天变硬,它能在屋中翩翩飞舞了。
从此,我和伙伴们下地打草。开始留意起生产队的茴香畦和枣树趟子里的野茴香棵来,于是,一只又一只的茴香妞在不断丰富着我家八仙桌下面的小纸盒。一只接一只的蝴蝶。不断地从八仙桌下面飞出,吸引的我那些花蝴蝶般的小伙伴们像倒花红线一样在我家进进出出。一年一年,我在那间狭小的温室里重复着我的蝴蝶梦。为了把蝴蝶、把美丽永远留住。我还别出心裁。把涅槃了的蝴蝶用棘针精心别在屋内的墙壁上,组成菱形、心形等一个个图案,由这些图案打造了一面“蝴蝶墙”。
正是因为蝴蝶的无与伦比的美丽,人们常常把最关丽最鲜艳的东西用蝴蝶来命名,如。小姑娘发辫上的红头绳叫蝴蝶结,少女系在脖子里的彩色丝带常常打成蝴蝶结。人们甚至把漂亮可爱的小女孩和美丽少女也比作花蝴蝶。
最美丽的往往是最短暂的。蝴蝶的种类繁多,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全世界现已记录的蝴蝶达一万七千多种。但蝴蝶的寿命却很短,长的能活几个月,短的只有两三天,其平均寿命也只有两周的时间。蝴蝶的关又给人一种凄美之感。
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常常想起那道蝴蝶墙。
随着社会、科学、环保事业的迅速发展。随着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人们的思想意识、审美意识也在不断完善和提高。我曾不止一次地幻想,把童年老屋的那面蝴蝶墙推倒,让美丽的蝴蝶们飞出去,给它生命,还它自由,让它展开美丽的翅膀尽情地飞翔。
蠕动的青蛙
夏天的午后,我和妹妹还有几个小伙伴常常溜出家门,到村东小桥下面的桥洞里去捉青蛙。
按颜色和大小的不同我们把青蛙分为两种,草绿色的,我们给它取名叫“绿呱呱”,这种青蛙一般个头比较小;另一种个稍大一些,花纹是墨绿色的,我们叫它“大花牛”。桥下的地面是砌了砖的,平整,没有淤泥,流水清澈见底。青蛙也是喜欢凉爽吧,它们常常三五成群或者是单蹦来到小桥下面,浮在水面上伸开四肢慢慢划水,或干脆就浮着不动,自在极了。我们几个脱掉鞋子,轻轻下水去,猫着腰,轻抬赤脚,然后猛扑上去就把青蛙抓在手里。我仔细打量手里的青蛙,只见两眼鼓鼓的汪着一潭清水,从里面透出哀怨和悲伤。攥在手里的青蛙凉凉的,滑滑的,肚皮白白的。看到它们的肚皮就让我想到蛇,瞅着瞅着突然就神经质地把青蛙扔到水里。想想那时的心理真是奇怪,对这些小动物是既怕又喜欢。就像既喜欢又戕害它们一样。
一天,我看见我家当街的猪圈里有一些艰难爬行的青蛙,它们瞪着可怜巴巴的眼睛,头一律向上翘着。仔细一看,都是被拧掉两条大腿的烂青蛙,两条前腿费力地拖着血淋淋的身子和头。在撒着青草和猪粪的湿漉漉脏兮兮的猪圈里挣扎。看到这些我的头发一下子奓了起来,我急急地跑回家告诉奶奶。奶奶小跑似的走到猪圈旁。见到那个惨象气得捂着胸口大骂起来,说,这是生灵,是吃虫子的,祸害它们要遭报应的。奶奶的骂声引来好多孩子,他们都静静地听着,好像说这不是我干的。我低声问奶奶,它们还能活吗?奶奶的气又来了。它一个身子被拧去一半还怎么活啊?真是作孽噢!
天黑哥哥回到家,我跟他说了这事,他吓得赶忙让我止住。我闹不懂,接着还问,哥哥把我拉到门洞里心有余悸地告诉我,那是他的几个伙伴干的,他做帮手,本来他们提议要到我家来让奶奶给煮了吃,胆小的哥哥一百个不同意,他说奶奶看见了定要劈了他。哥哥说着,不停地咂巴嘴,好像在回味那青蛙腿的余香。此时,我看见他的嘴唇嘴角油晃晃的,闪着亮光。
长大以后,我记得还问过哥哥这件事,他说,小时那么残忍。真不知是什么东西在作怪。
在饭桌上,我拒绝“田鸡”,甚至都不忍多看它一眼。看到田鸡就让我想起那一圈蠕动着的血肉模糊的青蛙。
一条棕红色的狗
奶奶常说,狗认八百(路),猫认千里。还说,狗是忠臣,猫是奸臣。家里再穷,狗是不会离开主人的,猫就不行了,谁家喂得好就到谁家去。小时候我家既喂着狗也养着猫,我常常担心,哪一天与我同吃一碗饭同睡一个被窝的猫忽然就变成奸臣跑走了。
养猫是为了捉鼠,养狗却不仅仅是为了护院。
那是一条棕红色的狗,哥哥给它取名叫欢欢。正值秋天,金丝小枣正熟。人走在枣树下,谁都想摘一把红玛瑙似的小枣解馋,狗也喜欢到树下捡拾熟透落下来的小枣,于是它平时扁扁的肚子一天天鼓了起来,毛色亮了起来。这天,父母亲在地里收庄稼一整天没有回家,由生产队送饭;奶奶在场里包棒子也是仅回家喂了猪羊,欢欢一会儿跑到村南去找父母亲,一会儿又回到场里找奶奶和我们,一会儿又跑回家,回到家却进不了门,就再跑回去。这些是我后来推断想象的。当时,我如果知道欢欢这么恋家。定会从奶奶手里要过钥匙,陪它回家的。但是我没有为它考虑这么多。那天夕阳西下时,欢欢离开我们又跑走了,它在穿过大半个村子往家走时。被村西头的一群狗截住了。我只知道人有欺生的,不知道狗也是。我无法想象,欢欢当时斗不过它们时,多想跑回作为避风港的家,但是它不能。它跑啊跑,就是逃不脱同类们的围追堵截。不知是经过了多长时间的鏖战,也不知做了怎样的坚持。可怜的欢欢终于因寡不敌众倒了下去,像一匹精疲力竭的战马。
父亲收工回到家,被告知欢欢倒在了村头。我记得当时父亲听后急急地向村西头跑去,待他把那只还有一丝余温的欢欢背回了家,还不相信这一切是真的。父亲把欢欢放在院子里,围它一遭一遭地转,然后蹲下来摸摸这里又摸摸那里,我知道他是抱一线希望盼欢欢醒来。不知过了多久。父亲给早已僵硬了的欢欢扒了皮,洗净剁粹炖了。当父亲给欢欢开了膛以后他震惊了:欢欢的肺炸得像蜂窝一样。原来那欢欢不是战败而死,而是连气带急气炸了肺。父亲说这些话的时候我不懂。但我知道父亲非常难过。那天是父亲亲自烧的火,红红的火苗映着父亲铁青的脸。父亲是喜欢欢欢的,父亲喜欢所有的小动物,包括小鸟。有一次父亲出差买回一只受伤的信鸽,他精心饲养并为它疗伤一个月,伤痊愈后把它放飞了。欢欢的惨死给父亲的打击一定非常大。
狗肉炖熟了。我们兄弟姐妹负责一家一碗给邻居送肉。我们在吃肉时父亲借故走了出去,他一口也没有吃。这件事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父亲喜欢吃肉,何况在那个年代。姐姐要去喊爸爸,母亲说,喊来你爸他也不吃,他是疼坏了。
欢欢是忠诚的。它喜欢这个家,喜欢家里的每一个人,就像人们都喜欢它。每每襁褓中的弟弟拉了屎,母亲或者是我们一声“欢欢”,它马上跑过去风卷残云般舔个干干净净;天黑后,如果家里的哪个成员下地或者是上学还没有回象,你走在路上一准会碰到去接你的欢欢。它真正做到了狗不嫌家贫;它还像一个善解人意的乖小孩,灵透极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每当看见狗,都会想起欢欢,想起它的点点滴滴。我对每一只狗都投去友好的目光。
那一沟的蛇
奶奶说,蛇是有灵性的动物。家院里的蛇是护家发家的,谁家有谁家就有好日子过;坟茔里的蛇是护阴宅的,家里的地里的都不能伤害它。作为爬行动物,它的外观和行动却实在是疹人。小时候,地里的蛇是很多的,不管是在草丛里还是在庄稼地里,抑或是在水里,我常常被一声童音“这里有长虫”的喊声吸引住。我是即怕蛇又想看到蛇。真是矛盾。
秋天的一个下午,我和几个伙伴在南坟拾豆棍。南坟是我村的老坟地,至于到底有多老没人能告诉我,坟茔地里的那几十棵老松树就足够证明它的古老。忽然,在几十米外的一个沟边上,一个叫超的男孩冲我们几个大喊“快来看啊,这里有长虫”。我们几个互相看了看,携起筐子就往那边跑,生怕那条蛇爬得快钻到哪里看不见了。待跑到跟前。只见沟底堆了一堆从沟崖上扒下来的土坷垃块,并没见到有蛇在那里。小超说,让我们给打死了。他们几个都在撅着腚用小镐不停地扒沟崖。看那沟崖就知道这一带壕沟也是有年头的,宽宽的沟不是很深,沟崖上千沟百壑,有的地方裂了几寸长的缝。那帮男孩像着了魔。顺着缝一个劲地向沟的一头扒。好像这样扒下去一定会有蛇被扒出来。怪事出现了。记不清从谁的镐下嗖地蹿出一条小蛇,然后顺着沟的方向向前蹿去。这条蛇只有筷子那么长,筷子那么细,黑地带着金黄色的点点,爬得极快。我是第一次见到那种蛇。这时,围在沟边上看热闹的男孩女孩有十几个人,个个都伸长了脖子瞪起了眼。其中有人煞有介事地说,这种蛇已经成了精,打不得。说实在的,当时我倒真愿意相信那个孩子说的话,同时愿意让正在卖力扒沟崖的那几个人也听到它从而使他们停止对蛇的伤害。然而,他们好像根本就没有听见,停止了扒沟又追起了蛇。那条小蛇上蹿下跳,麻利得不得了,我倒真的以为它成了精。被那帮孩子追得实在没办法了,蛇急中生智嗖嗖地爬上了沟边一棵挺拔的白杨树,它爬上树梢并把身体紧紧地缠在树枝上。小蛇以为爬到了树梢就能保全那宝贵的性命,然而它错了。当它被那帮执著的孩子用坷垃打在地上。用镐剁成几段又用土埋起时,我的心也跟着沉了下去。
深秋的下午很短,转眼夕阳西下,北风呼呼地叫着,那几个人没有要结束的意思。我动摇着想回家,话刚说出口,只见有一米多长的一段沟崖被扒了下来,断面袒露处,有多条蛇交缠成的大麻花一下子滚落到沟底,黑的白的灰的花的,长的短的粗的细的。见有这么多双眼睛在盯着它们,知道是在劫难逃,有的想做最后挣扎突围,有的想钻进地缝去,有的从那一团里拔出头来,高高的直直的立起,仰起头吐着红红的信子。我是又害怕又兴奋,想回家又拔不动腿。那十几条或者是几十条小生灵生命终结的时候,我看见西面的天空残阳如血!
后来,我特别爱做关于蛇的噩梦一
我背着草筐正在枣树趟子里走着。啪地一下,是什么东西重重打了我的头。抬头一看是一条胳膊粗的大蛇从树上探下身子和头,鼓鼓的眼睛,展开大嘴呼呼地吐着长长的信子,我没处躲藏,吓得毛发直立。我大声喊娘但我嗓子里像被什么东西给堵了……醒来大汗淋漓:
我在河里游泳,正游得累了想停下来歇歇,忽然从水里蹿出几条像莽一样的大蛇。对我紧追不放,看架势非要活吞了我。我想我们前世无怨今世无仇,你们干嘛跟我过不去?想到这里我自己倒先心虚起来,我曾经亲眼看见过那么多蛇死于非命而没有制止,这是它们索命来了。我一害怕,咕咚一声掉进深水坑:
母亲下地干活,我在家里和妹妹睡午觉。一觉醒来,发现妹妹被几条蛇紧紧缠住,胳膊、身子、头、脖子、腿上到处都是蛇的身子,蛇的头。那眼睛鼓鼓的想要瞪出来,嘴里不停地呼呼吐着信子,越缠越紧,信子舔到的地方,一片湿漉漉的黄黄的毒水,一个深深的坑子……
难道这就是老人们所说的报应?
父亲与鸽子
还是在我很小的时候,老家院子里,正房、东西偏房、南房的房顶上,目之所及都是鸽子。洁白的,灰色的,灰白的,黑白的,大的,小的,一律干干净净,精精神神。它们瞪着圆圆的很好看的眼睛,或左顾右盼,交头接耳;或健步行走,边行边觅食;或扑棱棱,飞起又落下,热闹极了。这些鸽子的家,就在我家老屋的屋檐下,是父亲用秫秸插好,又用泥巴糊起来的,以正房的屋门为中心,在其上方大概有十来个连在一起的方方正正的鸽子窝。
这些鸽子有时很安静,有时咕噜咕噜直叫唤,像是人睡觉在打呼噜。最好玩的时候,是小鸽子等待外出的妈妈回来喂食。小小的脑袋探出窝来,看不见眼睛,只露出一张尖尖的小嘴。忙了一天的父亲,晚上回到家,不是先吃饭,而是搬来木梯,拿上手电,一个窝一个窝地看鸽子。他看什么呢?是看看鸽子们是否全部回了家,还是看看小鸽子吃没吃饱,或者是看看有没有小鸽子孵出来?
每当这时奶奶就嘟囔一句,也不知道累,看这些东西是当了吃还是当了喝?母亲常常也跟上一句,一天不吃饭能活。一天不看鹁鸽(我们老家叫鸽子为鹁鸽)可活不成。
父亲在梯子顶端忙碌时,我常常仰着小脸望着父亲的手。我喜欢看那些袖珍鸡蛋似的鸽子蛋。有时,父亲就从窝里掏出一个温乎乎的鸽子蛋递到我手里,说小心啊,别摔了。我赶忙接过来,仔细端详把玩,心想,这么小的鸽子蛋,里面有蛋黄吗?
在我七八岁时家里翻盖房子。房檐下的那一溜鸽子窝跟老房子一起一夜之间不见了。父亲把鸽子们弄到哪里去了呢?当然,这个想法我一直没有问父亲。
新房盖起来后,鸽子窝没有再垒。这时,妹妹、弟弟相继出生。不再养鸽子的父亲似乎更忙了。下地干活,外出挖河,在大队弹簧厂跑业务(经销员),在公社综合厂当副厂长兼业务员,父亲还是生产队的记账员。父亲的算盘打得很好,他在生产队的办公室里打,晚上回到家也打。有时父亲还教哥哥、姐姐打算盘,边教边对我们说,若是你奶奶让我念书,我会念得很好,早就不在家种地了。
父亲在差十天不到两周岁的时候,我的爷爷出夫离家就再也没有回来。20岁的奶奶带着父亲,跟老奶奶3人过着孤儿寡母的生活。父到在距家3里路的百尺竿村读私塾。9a33ac8592fe9a4e4678aefdc6e93d9e老先生对父亲这个聪明好学的学生很是喜欢,留他吃住在家。这样的时光没过多久。奶奶坚决让父亲退了学,奶奶是怕父亲学成后远走高飞。听话的父亲只念了3年书就回到奶奶身边,也就决定了父亲的一生只能和土坎垃打交道。长大之后,我几次想问父亲但始终没有问。他喜欢鸽子是因为鸽子有一双飞翔的翅膀吗?
过早成熟的父亲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他不但勤劳,而且上进。父亲先后三次要求入党,都没有遂愿。第一次,是被告知有历史问题,怀疑离家20多年没有音信的爷爷去了台湾。当时,台湾跟大陆关系正十分紧张。父亲没有多说一句话,那天散了会他没有回家。母亲放心不下,就带领哥哥、姐姐分头去找。我们在村西北角的金迎三爷爷家找到了父亲,他跟三爷爷正在门洞里看鸽子。三爷爷是个党员,母亲说父亲准是找他诉苦去了。后来我想,父亲也是把失落与希望都交付给他的好朋友鸽子了吧?
听母亲说,父亲第二次要求入党被关在组织大门之外,是说他跟富农划不清界限。我们家本来就是中农成分,再经常跟富农搅在一起。那还了得?夜里,父亲睡不着,母亲也睡不着。听着父亲跟母亲感叹,宝鼎哥戴上富农的帽子,几辈子人都抬不起头了。父母亲的那次谈话。还让我知道了一件事。一次父亲在挖河工地上不小心铲破了脚,伤口成了冻疮被感染,宝鼎大爷,彭庄的张洪志大爷,茄刘的常青叔叔,仨人轮替着背父亲去几里路以外的村里换药,这一背就是20多天。为此,父亲与洪志大爷常青叔叔拜了把兄弟。他说。这三位兄弟的恩德啥时候也不能忘啊!
现在想来,没有多少文化的父亲,处在那个特殊年代,遇到这种事他是无论如何也想不通的。那一段时间,父亲下地回来就往邻村杨集跑,一直到半夜才回来。父亲说,去找他从小一起玩大的朋友邵兄了。母亲说,你们说什么呢?父亲说,不说什么,看他养的鹁鸽。
又是鸽子。
父亲第三次要求入党没有被批准的理由更直接,说父亲搞投机倒把,长了资本主义的尾巴。父亲这一段历史我就知道得比较清楚了。那时,我们全家九口人。挣工分的只有父亲和母亲。生产队分粮分物有时按“人八劳二”,有时按“人七劳三”。不管按什么比例,所分的粮食几乎年年不够吃。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家连续3年,只分60.4斤小麦,而缺粮款高达50多元。父亲不能眼看着全家人挨饿。就偷偷买回小猪崽,再和自己家老母猪下的崽放在一起,用自行车栽到天津郊区去卖。父亲还买来竹竿,让母亲编小竹筐来卖。去天津卖猪,父亲常常是夜里一两点钟出发,到次日凌晨两三点钟回家。在冬夜里,骑了五六个小时自行车的父亲,棉衣常常被汗水湿透。
生活上的艰难困苦自不必说。政治上的磨难令父亲难以忍受。要知道,这几顶不大不小的帽子,在当时是能把人压垮压死的。宝鼎大爷就是因为受不了家庭成分的压力,在一个漆黑的夜里跳井自杀的。要强的父亲一句话也不多说,他把他的心事,他的重负都托付给了鸽子。在中午或者傍晚,收工回来的父亲常常坐在门前的台阶上,向远处、高处望着,望着。如果有一两只鸽子从院子上空飞过,父亲就兴奋得大叫,目不转睛地看。父亲是羡慕鸽子吧!
长大以后的我常常想,父亲瘦瘦的身躯,骨头竟是那般坚硬。父亲走路始终是昂首挺胸,直到现在都是如此。日子,一天一天地过,他,一天一天地忙碌着。村里成立了弹簧厂,有经济头脑、见多识广的父亲这会儿派上了用场。常年的奔波,为村里跑来了资金和富裕。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村是周围十里八乡最早通电的村,也是第一个买拖拉机的村。我记得,刚刚安上路灯的日子里,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老太太。都把纺车搬到路灯下,人们说着,笑着,闹着,忙着,每天都熬到路灯熄灭才回家。过年时。人们走亲访友,外村人都夸我们村副业搞得好。人们的日子过得滋润,说到这里,人们准是夸奖父亲是个大能人。父亲的名字在全县和周围村子里响亮了起来。
前些日子,父亲来城里,在街上碰到了当年一起在公社综合厂的杨叔叔,我们兄妹几个请杨叔叔吃饭。几杯酒下肚,父亲和杨叔叔说起了当年。杨叔叔说,你们的父亲有能力,人也耿直,处处给你们几个孩子走道。有那么多人想拉他入伙,把拿来的合同私下做了,他就是不上那个套,他说,挣着集体的工分,不能干那种见不得阳光的事。你们的父亲是干净的,心里是明亮的。那么多的苦和难都由他一人扛着。他只希望你们好好念书,将来奔个好前程。
农村实行责任制,我们家分到了二十多亩责任田。当时,我们兄妹几个都在上学,父亲就起早贪黑地忙。父亲像一头不知疲倦的牛,他亲自赶车,亲自耕地,亲自打场。没想到我家责任田很快成了样板田,引得那些种地把式们纷纷蹲在地头研究。父亲笑了,说地是死的人是活的,它又不犟嘴,你想怎样种就怎样种。
在父亲的精心培养教育下,哥哥和我还有弟弟都考上了大学,妹妹也参加了工作。父亲说。你们赶上了好时代,要积极工作,有多大本事使多大本事。哥哥要入党了。他把表格从学校寄回家,父亲高兴得就像自己入党一样。他顾不得吃饭,骑上自行车就去亲戚家,写政审材料,盖公章。我想,哥哥入党,对备受挫折的父亲该是一种极大的安慰,毕竟儿子是他生命的延续。我和弟弟入党时,父亲同样欢天喜地,欣喜若狂。
早已从乡镇企业退下来的父亲,与乡亲们合伙搞起了电阻器加工和体育器材加工。他还像年轻时一样,整天忙得脚不沾地。父亲从新老客户那里了解到,家乡的传统产品低压电器,如不提高技术含量,就适应不了工业快速发展的需要,就要被淘汰。父亲心里那个急啊!他一闲下来就抱着资料研究,无奈文化水平有限,常常是研究半天也研究不出个所以然来。有一次在沧州弟弟家里,他提出让弟弟教他打字、使用电脑,说也要从网上做生意,弟弟无奈地笑着。兄妹几个心疼父亲,不愿意让他负重大半生的身心再受煎熬。我们几次劝父亲搬到城里来住,父亲总是笑笑,坚定地说,在家还有那么多的事要做。在家里住挺好。
父亲常说,现在的社会好啊,人有多大本事就使多大本事,我要是年轻20岁,定要风风火火干一场。我常想,父亲说这些话,是对我们兄妹的激励呢,还是对岁月不饶人的感叹呢?
有一次,父亲出差带回一只受伤的信鸽,他说是从一养鸽人手里买下的。回家后父亲精心喂养医疗了一个月,鸽子痊愈了。那些天。父亲很愉快,出出进进都哼着小曲。我经常见到父亲一个人与鸽子在说着什么,他们头对着头,眼对着眼。一待就是老半天,他们到底在说些什么呢?在一个晴朗的天气,父亲将体肥毛亮的鸽子载到国道边把它放飞了。母亲说,后来这只鸽子回来过几次,站在房檐上就是不肯走。它是舍不得这个家,还是来表示那分感恩的心呢?
70岁的父亲,鸽子梦又复活了。他在院子的一角拉起铁丝网,在里面垒了鸽子窝。空闲时,父亲就坐在铁丝网前与鸽子对视交流。隔一段时间,他就用摩托车栽上它们,到开阔的田野里,国道旁,或是渤海边去放飞。常常是父亲到家时,那些信鸽早在他之前就回到了家。
前些天,我往家里打电话没人接,又打了父亲的手机,手机里传来父亲愉悦的声音,他说,我在崔口呢。我问父亲去崔口干什么。父亲在电话里笑了,他说放鸽子。父亲的话。把我的思绪一下子拉到了百里以外的渤海湾畔。夏日的海风吹动着蓝天上的白云,湿地里的芦苇、柽柳、红荆透出诱人的绿,东方白鹳、灰鹤、海鸥、红嘴鸥等大大小小的水鸟在湿地里或湿地的上空盘旋。父亲哪,坐在一块石头上,轻轻地打开鸽茏,让一只只精心饲养训练有素的信鸽,浴着海风飞向辽阔的天空。父亲的目光紧紧追随着信鸽投向高空,投向远方。
我独自遐想,父亲为什么偏爱到开阔的地带比如海边去放鸽子呢?是不是鸽子承载了父亲大半生的苦难、挫折、希望和梦想,他要亲眼看着他的鸽子,载着他的一切一切,毫无阻挡地在蓝天下飞翔?是不是鸽子就该在广阔的天地里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