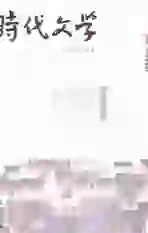时光温存(三题)
2011-12-29李庄
时代文学·上半月 2011年2期
潘叔和潘姨
在首尔大街上,一家店铺门一侧的一块好看的石头引起了我的兴趣——石头上刻着两个汉字:明山,而且是楷书,规规矩矩的颜体。这家店铺经营什么呢?明山在韩文中是什么意思?我回去要查一下《辞海》、《辞源》。明山令我感到亲切。是因为我儿时的一个伙伴就是这个名字:于是。一张熟悉的脸不用签证,就浮现在我的眼前……
那是小学一年级的下半学期,我家刚搬入这个大院不久,我倚着墙根看一群和我一般大的孩子打闹。比我们大几岁的华子他二哥走过来食指一勾,说:你,过来!我知道是叫我,便慢慢走过去。华子他二哥食指一勾:明山,你也过来!孩子堆里走出一个白净的男孩,我知道他就是明山。摔跤,给我摔!华子他二哥命令。
一交手,我就知道赢了,他太轻了,像张纸。我一抡,明山双脚就离了地,一圈、两圈、三圈。抡圆了,放手!明山就平摔在地上,滚两个滚儿。再来。依旧滚两个滚儿。华子他二哥哼了一声说:笨蛋!明山慢慢爬起来,面色苍白,他掸了掸身上的土,看了我一眼,转身回家。那是我与明山的初次见面。我觉得他挺坚强,他没哭,他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明山是家里的老大,老二弟弟民丰,老三妹妹红梅,他爸潘叔在甘肃野外队工作,一年只回来一回,也就两个月,他妈潘姨是家属,在家带三个孩子。潘姨比一般家庭妇女干净,家里也弄得利索,铁炉子每年都刷一次银粉,亮锃锃的,煤球整整齐齐地码在一边,煤灰一下来。就倒,小院子也扫得光洁,就一棵歪脖子梧桐树。叶子一落,就扫。但是,百密必有一疏,那天民丰放学回家,一看当院放着一个黄澄澄的窝头,好像是才出锅,还冒着热气。民丰很惊奇。咦,窝头,一个窝头,嘴里念叨着走过去,身子一弯,双手捧起,呸的一声,又把窝头扔了,碎了一地。原来这“窝头”是他妹妹红梅屙的屎,十分美术,酷似窝头。潘姨批评民丰不知脏臭,实在是错怪了他呀!那时,民丰刚上小学,就是如今读完了博士的个别批评家的眼神,比民丰高级吗?不一定。
潘家的东边是谢家,西边是大宝家,再西边是徐华家。潘家与大宝家之间只隔着一道竹篱笆,透过篱笆,可以看到大宝养的几缸金鱼:大眼睛长尾巴的是龙睛,更大眼睛的是水泡,浑身长疙瘩的是珍珠,顶着厚帽子的叫狮子头。鱼缸是几片红瓦凑在一块,用水泥粘的。到夏天,里面长满绿绿的青苔,你一点也看不出来,它的外面,该水泥还是水泥,瓦还是瓦,金鱼不管这些,只要大宝按时换水,一天喂一次红红的鱼虫,就舒舒服服地活。大宝还养花,花们也活得滋润,红的红,白的白。五彩的就很烂漫。
徐华家也是哥俩一个妹妹。妹妹比红梅还小,因为打小在乡下姥姥家呆了三年,所以被她妈打或被小孩们惹哭之后就用河北东光的口音骂:日你奶、日你奶……没完没了的。有点不像话。不过她家养得那只公鸡真是英俊,特别是尾巴两侧的几根羽毛,墨绿墨绿的,闪着金属般的光泽,让人眼馋。有一天中午,大家都午睡了,我和公鸡围着一排宿舍跑了十几圈,终于把公鸡累趴下了。于是,我小心翼翼地揪下了那几根美丽的羽毛,当作礼物送给了我姐。我姐做了个毽子,一群女孩围着她。一个、两个、三个,毽子上下翻飞,我姐的脚尖上缠满了羡慕,我心里充满骄傲。
噢,徐华家的公鸡,请接受我三十多年后的歉意。
潘姨可不像谢姨厉害,她干什么事都静悄悄的,偶尔摔个碗也估计是被潘叔一声断喝吓得失手。潘叔怎么就这么凶呢?我和明山都上班了,又在一个厂工作,来往比小时候更密切。那时潘叔就病了,在家长期休病假。我去看他的时候,他会扔一棵烟给我,然后像对大人一样和我说话。记得有一回我和潘叔谈到了煤:这煤从矿里挖出来,装车,运到城里来,你说遇到一个坑,车一颠,掉下一块,如果教谁瞅见了,拾回家,烧火做饭也行;如果谁也没瞅见,又过来一辆车,一轧,碾成了煤末子。再来一阵风就没了。你说这块煤窝囊吧,人家那些煤就在炉膛子里痛痛快快地冒火苗呢,蓝蓝的。潘叔叹了一口气,说,这是命呗。他脸焦黄,胡子有几天没刮了,又问,你小子多大了?我说十九。他又扔过一棵烟,说,你小子心里的事还不少呢。于是,香烟缭绕,缭绕……
明山结婚时潘叔已去世好几年了。那时候结婚办酒席没有去饭店的,都在家里摆。小院子搭起大棚,垒上灶,四凉,六热,八大碗,邻居谢家,大宝家桌椅是现成的,摆上,开喝。热闹到半夜,客人散尽了,剩下几个小弟兄在收拾,明山对着我们一拱手,弟兄们辛苦了,也早回去歇着,明天再拾掇吧,我先行一步,做好梦去了!
新媳妇跳上自行车后座,搂着明山的腰,俩新人一齐回头,招手,一脸的喜气,去他们的温暖的小窝啦。众人哄笑,潘姨也笑着,目送俩人远去。我当时看着潘姨脸上的表情,猜她心里一定在说:明山他爸,你也看见了吧?看你儿子多么不像话。
潘叔在病床上躺了有两年,他得了好几种病,身子是越来越弱,脾气却越来越暴,整天骂潘姨,什么饭菜热啦凉啦,手巾干啦湿啦的,纯粹找茬。潘姨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逆来顺受,人是越来越瘦了。那一阵,我听不得济南话,你说这济南话怎么这么难听呢?而潘叔骂声依旧,并且是原版的。邻居们都说,这小潘也真是的。潘姨这时才流下泪来,说他是病人呀,心里烦,他才四十出头呀,骂就骂呗,心里还好受点。
潘叔的脾气升级了,发展到不吃药,动手拽吊瓶,嘴里气喘吁吁地说:让我死!让我死!
我去劝潘叔,说你对潘姨好点。他两眼发直,说你小子不懂。直到他去世时我才明白他的用心。他拉着她的手,说:对不起了,孩子他妈,我这一辈子拖累你啦,下辈子再好好过日子吧,你带好孩子。潘叔变了形的脸上挂着两行长长的泪水。这是我看到他第一次哭,也是最后一次哭。潘姨早已泣不成声,身子抖成秋风中的一片叶子。
秋风凉呀。
潘叔虐待潘姨是想让她恨他,死后不惦着他。可他最后还是软了,说出了心里话。潘叔,潘叔你他妈的怎么就软了呢?你狠到底呀。
潘姨一直没有改嫁,如今民丰,红梅也都结婚生子了,她一个人在大院里住着。前年我在街上遇到她,人比从前胖了,话比从前多了一些,一头白发在风里飘,她伸手去摁。我一阵心酸,想起潘叔最后入殓是我给他理的发。他头发漆黑,一根白发也没有呀。
潘姨嫁给潘叔时,还是个刚刚高中毕业的学生。为拉扯三个孩子,她一直没有工作,孩子们大了,她才去街道居委会帮帮忙。
潘姨会后悔吗?不会。没准夜深人静时潘姨醒来,还以为是昨天。她嘴里念叨:孩子他爸,你倒是骂一句呀,怎么不骂了呢?
老谢家
我妈说,你谢叔、你谢姨、你谢芳姐、你谢平哥、你小眼弟弟。
谢姨姓姜,但我叫她谢姨,是从谢叔那儿叫的。就像谢叔叫我妈李嫂,这是——从我爸那叫的。后来我知道,这如果是放在解放前,谢姨就得叫谢姜氏,我妈就得叫李孙氏。这有多别扭,幸亏解放了。可还是有那么点封建残余,文化嘛。
谢叔家住在我家的前面,老白家的后面,右边是潘叔家,左边——隔着一条小马路——公用水房。做饭前洗菜,饭后洗碗,那地儿就有些热闹,人们七嘴八舌地说话,手里忙活着,地上就湿漉漉的,脚下有些不利索。而脏水顺一条二尺宽的明沟,慢悠悠地流到后院小树林里那一方五米宽窄的污水池中。泛着几片菜叶和几团油花。那池子也没有盖儿和水沟一样。那时候好像什么东西都是公开的,透明的。洗菜、洗碗也不用什么洗涤剂,更没有什么污染的概念,就那么一搓、一抹,完了。
谢叔和谢姨打架,不动手,只是谢姨一句接一句的尖利的咒骂夹杂着谢叔粗重的咆哮和随之而来的茶壶茶杯的清脆的破碎声。谢叔家的茶壶茶杯老换,陶与瓷的少见,普通玻璃的居多——摔着便宜。
记得明山他爸——潘叔。操着一口原汁原味的济南话对谢叔说:老谢,你先摔,猛摔!看嫂子心疼不心疼,心疼了,她也就不摔了。
从实际情况来看,潘叔的办法没起一点作用。也许这个办法谢叔根本没用。潘叔对潘姨那是召之即来,挥之即去,一不顺眼。张口就骂。潘姨不像他家的女主人,倒像是他家的使唤丫头。所以。潘叔有点为谢叔的处境打抱不平了。
如果我爸歇探亲假在家。就会和我妈一起去劝架。我爸说,老谢,你看我们那么多仗都打过来,现在倒打到家里来了……我妈只是拉着谢姨的手,塞给她一块手帕,谢姨擦擦红肿的眼便平静下来。我爸和谢叔喝酒时会吼起解放军军歌:向前,向前,向前……也唱志愿军军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为祖国,就是保家乡,中华好儿女……真是雄壮。男人,这气质现在找不着了。我爸的左腿曾有一粒子弹穿透,留下两个圆圆的疤,是打上海的纪念。而谢叔的一条腿短了一寸,是在朝鲜负的伤。谢姨和谢叔打架就骂:你这个老谢瘸子
我趴在桌上,仰首,看谢叔和谢姨的结婚照,他俩是那么清秀,好看,眉宇间有英气勃勃而出,但又那么干净,柔和。于是,对他俩打架无法接受。再看另一张全家福,谢叔、谢姨、谢芳姐、谢平哥还有一个男孩,幸福地笑着……那男孩不是小眼弟弟,那时他还没有出生,那男孩我不认识,但我知道他是“三儿”。三儿的眼大,漂亮,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时饿死的还是得大脑炎病死的呢?我忘了。谢姨每当和谢叔打架和孩子们生气就念叨三儿。好像这些不愉快都是三儿惹的似的。
小眼和我手持弹弓伏击“破鞋”,小眼不时地从墙洞里向外边马路上探头侦察。突然。他说来、来了,真、真破。小眼是个结巴,越急说的越费劲。我们拉紧了皮条,欲射,这时小眼又说,别、别射,是、是、是我、我、我姐。我定睛一看,果然是谢芳姐,穿一件花上衣袅娜驶过。还摁铃呢,全然不知险些被弟弟当成破鞋伏击。那时我们把一切穿着花哨的女青年当做破鞋,这实在是时代的局限。谢芳姐眉眼清秀。腰肢纤细,和我一起逃学的峰峰曾对之有过评价:这腰好,风吹杨柳哇!找媳妇就找这种腰。那时我们才上五年级,这家伙是早熟。现在每回和峰峰一家人吃饭我都要用目光量一量峰峰媳妇的腰,心中每每感叹: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哇。谢芳姐后来嫁给陈大爷家的万仓,育有一女。
谢叔,孙叔每回捕鱼回来,都会捡两条大个的送来,而我家每回包饺子,炖肉也都会每家送上冒尖的一大碗。谢叔家是小眼独享,孙叔家由两个双胞胎的妹妹,立青、立杰分而食之。那时候有点好东西,都是尽着最小的孩子吃。
我幼时多病,如果发病时父亲还在青海,又赶上是深夜,那准是谢叔深一脚浅一脚地送我上医院,边走还边说,李嫂,我看这孩子没事,打一针烧就退了,放心吧。记得我有一次休克,吓得我妈大哭。有几次病好了,下地,站不住,竟只好扶墙而行,一点点挪到户外,晒晒亲爱的太阳。不久又奔跑、呼啸、顽皮如故。
一九七六年我爸自青海格尔木发回电报,说某日即归,我们高兴地等,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个人影。听新闻里说是一列火车出轨了,死伤惨重。一查车次。如果我爸按时走正好赶上。于是全家惊慌,乱成一团,我妈,夜夜饮泣,我与姐妹也是眼肿如桃,鲜艳得很。最可恨是高家老二,竟对我说:小屁孩,你爸准死了,等个屁呀。我扭头疾走,心里狠狠地骂:我操你妈!走远些,高声骂:你爸才死了呢!往家跑,手摸到家门的刹那泪落如雨。
那个恶毒的高中生,其嘴脸,我一生不忘。
又是谢叔到单位打长途电话。从市里打到山东省。从山东省转到青海省再转到格尔木市,又转回西宁市才问清:我爸,自格尔木去西宁,坐汽车到橡皮山时出了车祸,车掉入山沟,我爸的前额撞破一条一寸长的口子,问题不大,现正在西宁治伤,一星期后出院,回家。谢叔说,这个老李呀,老李,你让人打个电报回来呀,你看把人吓的。我爸后来说,我没看到那轲火车出轨的新闻,伤也不重,就晚回来十多天,你看这事儿闹的。
我妈没有埋怨,默默地把我爸那顶满是血迹的棉帽子洗净,晾干。我爸的额角上多了一条蟋蚓似的疤痕。
我还在睡懒觉,谢平哥推门进来。说狗肉,一只碗递过来。我吃,腮帮子努力。谢平哥问香吧,我说香,他又问,不酸?我说不酸。我吃干净了,他说是猫肉。我说猫肉?他点头。昨夜他在后院树林里下套子,准备套狗。没想到套了一只大猫。也好长时间没吃肉了,猫也凑合,连夜宰了,炖好,一早送来。猫肉的确不是酸的,可没吃过猫肉的人都说是酸的。看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本身就是真理。要想知道猫肉的滋味就亲口尝一尝嘛。
谢平哥比我大十几岁,经历颇丰,进过监狱下过乡。结过婚离过婚复过婚。谢叔,谢姨最操心的就是他。他生有一子,名宁宁,实为鸡犬不宁,一个人就搅得整个大院山呼海啸。掐指一算,宁宁也该是一条二十多岁的汉子了,很久没听到他的消息,看来已风平浪静矣。
一九八一年二月十三日。我爸带我回胶东老家,坐火车,转汽车,耗时两日。到家的第二天早晨落了场小雪,我爸一早出去,在台阶下跌了一跤。起身活动筋骨,无恙,遂上北山老宅,一路指指点点,说昔日故事。在老宅盘桓至十点多钟。我三大爷家的大姐上山来。老远就喊四叔,走近,神色慌张,递给我爸两封电报,说四叔你看,我四婶不好。我爸一看愣住。我接过,一封:李嫂病危速归,老谢。二封:李嫂病故速成归,老谢。日期一是十四日,二是十五日。
归心似箭。车至潍坊,我醒来,见我爸一脸的老泪,纵横,全然没有了回程时嘱咐老家亲人们诸多事宜时的沉稳和镇定。此时,正红日东升,新的一日开始,而我妈已不在世上。大恸。
原来,我妈买菜归来,恰逢谢叔。谢叔打招呼,回来了李嫂。我妈未答,径直走,但身子摇晃,欲坠。谢叔赶紧上前抱住,又呼李嫂,不应。速送医院,大夫诊断脑溢血,一天一夜后。我妈撒手人世,不管我爸、我姐、我和刚满十一岁的妹妹小铭子。而她还不到五十岁,满头青丝,一脸光彩。痛哉!我妈再也不能爱抚或痛殴她的唯一的儿子了。
治丧期间,谢叔忙里忙外,一瘸一拐,那身影铭刻我心。
一九九三年我妹出嫁,彩车刚走,谢姨来了,一手一个红包,说,这是我给小铭的,这是你沈姨给小铭的,你沈姨说,你妈是个好人,小铭结婚时一定随个礼。我已十多年没见沈姨了,她和谢姨一样还惦记着我妈和我妈的小女儿。我又一次大哭。是替我妈和我妹哭的。
我爸在世的时候,常回大院看看,回来说,你谢叔谢姨身体挺好的。咦,小眼当科长了。我说是吗?细一想,一点不奇怪,你看小时候小眼就是孩子头,那一拨孩子教小眼治得多顺溜。但一想小眼正经八百地说:开个,小、小会。不禁笑出声来。
离开大院十多年了,我总想去看两位老人家,可我怕见到他们:我怕我想起已去世的父母。想起过去的美好又辛酸的往事,又会像小时候一样嚎啕大哭。我也是近四十的人了。
去年在东风路看见了谢叔谢姨,我赶紧叫出租司机回头,跟上。谢叔慢悠悠地骑着三轮,谢姨坐在后面。他俩老了——时光小刀把他俩的脸刻出了更多的皱纹。慈祥呀!我的谢叔、我的谢姨,你们不知道那个让你们疼爱。操心的孩子正泪流满面地盯着你们:他正擦着挡住了他目光的泪水。盯着你们:他明白这样的日子也不多了,——金子一样的岁月啊。慢慢骑吧,谢叔,安心地坐吧,谢姨……
那只鸭子
秦叔家住西头,我家住东头——一排宿舍。秦叔家三个女孩,老大叫英英,老二叫二子。老三叫三儿,秦叔和庄姨这么叫,我就这么叫,当然,英英和二子的后面要加一个——姐,而三儿比我小,则直接一三儿啦。
秦叔那时是石油钻探研究队的指导员,庄姨是队里的会计。英英和二子与我姐上初中,我和三儿上小学,她比我矮一级,我妹还没上学。三儿放学后和我妹玩儿。秦叔个子不高,面黑。头发更黑,乌亮而弯曲的头发向后,梳一个派头十足的背头,十分严肃。他也有不严肃的时候,晚饭后和维利,光明,连宝等比我大几岁的孩子们在篮球场上摔跤:半大孩子们一起上,将秦叔团团围住,抱腿,搂腰,拽胳膊,真热闹。秦叔总是赢,偶尔输了,就气喘吁吁地擦额头上的汗,笑眯眯地吐出一两个脏字。秦叔喜欢男孩。秦叔很亲切。而庄姨身体瘦弱,驼背,面黄,是个老病号,她上下班从我家门前走过,像一个歪歪斜斜的影子,飘过去,飘过去,就像今年过年,我妹回家说得那样,庄姨好像一阵风就能将她吹倒,但这些年了。院里多少老人走了,人家庄姨还是那样飘,那样飘。真想庄姨就那样永远地飘下去。嘴里叼着一根烟那样地飘下去。
我有多少年没见到庄姨了?
秦叔和英英、二子、三儿走路目不斜视,走得慢,庄重,这时候你就能看出他家人的气质:有些忧郁。而庄姨走得不在乎,这是她的脾气。我觉得好。
立成家和我家隔着一家,和秦叔家隔着两家,立成家住在我们两家中间。立成家那时日子过得艰难:孙叔一人上班,翟姨农业户口。没工作,在家照看立成和立成的两个双胞胎妹妹——立青、立杰。三个孩子都没有非农业户口,你说四个人,没有供应粮怎么吃饭?从那时起,我就对户口有意见,什么农业非农业。孙叔业余时间就织鱼网,打鱼,就下套子,逮狗,填这几张没粮吃的嘴。有时立成的姥爷会赶着驴车,拉点棒子,地瓜来看他们,还跟着一条黄狗。那只狗据立成说,是他姥爷村里掐架最厉害的一只,有一次我和立成差点把它弄死,这事以后再说。翟姨厉害,叫孙叔:老家伙!一声声的,是喊,是骂,也是爱。
立成他爸手巧,那天用一个鸡蛋做了满满一锅汤。那鸡蛋壳只在头上破了筷子头大的洞,蛋清,蛋黄一点点甩出来,一片片蛋花在锅里盛开,舒展极了,只是蛋花太薄了,好看是好看,就是没嚼头。
我和立成用炉渣灰灌满蛋壳。又找了一摊新鲜的不干不稀的鸡屎,一抿,把小洞封上,然后,小心翼翼地捧着,走到西房山,放进秦叔家的鸡下蛋的窝里。一会儿,也记忘了是二子还是三儿的惊喜声响起:咦,又下了一个蛋,还热乎呢!怎么还有鸡屎?我和立成蹲在西院墙上,不出声,等她去水笼头上洗,她一洗,露了馅,气急,手一挥“鸡蛋”碎了:谁呀,这么缺德!
我和立成纵身跳到院外。说:谁呀,这么缺德……我俩捏着嗓子,女声女气的。
英英小个子,圆脸,一副大大的眼镜,镜片后面是一双清澈的眸子。她喜欢看书,厚厚的,长篇。天气好,她会在她家门口的树下看书,两根小辫有些翘,一会儿推一下眼镜,又滑下来,再推。阳光透过树阴,洒在她的身上,脸上,书上,镜片反射,亮晶晶的。树叶在响,书页在响
二子个子比英英高了许多,眼睛比英英小了许多。她上不了银幕是定了。但当时我推测:二子没准能当上配音演员。有一回。我听见我妈在她家说话,就走过去,一看,是二子在学我妈叫我吃饭,催我写作业。以及训斥我之累累劣迹等等。那一口胶东话真是说得亲切。惟妙惟肖,我目瞪口呆。当然,二子说得最好的地方话还是天津话,我能听出来:海河上的大铁桥和杨柳青的年画。
三儿比英英高,比二子矮,正好的个儿。她脾气还成,整天也不知和我妹玩的什么,这得问我妹小铭。哪天。
英英后来去了济南,在探矿厂工作,干什么不知道,只是过年回来,见面,笑一笑。没两年,英英病了:神经病。我听说她宿舍住好几个女工,女工们的鞋全堆在英英的床下。你说这不是明摆着欺负人吗?英英就是和她们打也打不过呀,这么小的个子。英英回家养病,时好,时坏。
几双臭鞋不会造成致命的伤害,只是英英整天生活在那种灰色的压抑的氛围中。能不崩溃吗?自以为善良的人啊!你是否无意中扮演过生活中的隐形杀手?
英英仍看书,只是书页不翻,总在那一页上,她固执地在上面找什么东西。她有时会急冲冲地走进我家,问吃什么饭,我就把菜谱,主食报一遍,她噢一声,表示知道了,扭头就走。有时她就站在二小家门口的那棵大槐树下,向北向大院门口张望,一身花衣服,两根梳不直的辫子,你走近,看她镜片后的眸子,清澈依旧,只是没有了眼神,她的眼神去了老远老远的地方。
英英死了,是自己喝药死的。我和小铭去看秦叔、庄姨:秦叔坐在桌边不语,像块黑石头,只是背头乱了,不亮,有了几根白发:庄姨躺在一床薄被子下面,连头带脚地蒙住,身体偶尔抽动。怎么一个人说没就没了呢?我觉得不对,好像什么地方一下子空了,一块很大很大的空白,而且这空白空得有分量。说不清。
我记得当时,我写了一篇散文,题目是《英英》,开头一句:英英不是《西厢记》里的莺莺。这扯得太远,有些哗众取宠,太年轻。后来,这篇散文发表在德州当地的一家报纸上,这也许是我第一篇散文作品,文友看了,说你再编编就是一篇小说,我说,我这就是一篇实实在在的散文,编什么小说,生活才他妈的编小说呢!谁也编不过它。
上个月,我突然想起曾替秦叔宰过一只鸭子,那只鸭子让我想起了我在其中度过了童年,少年,青年时期的大院,想起了已逝去的父母,想起了……夜不能寐,泪不能禁,我写下了这首《那只鸭子》:
秦叔家三个女孩
秦叔叫我,宰那只鸭子
我把鸭头整个剁下来
鸭子站立,举着突兀的脖子
在雪地上画了几个鲜红的圆圈
那时,我还不知道
我的童年已经结束
后来,母亲走了
她脸上有着安详的笑容
后来,父亲患了肺癌
咳了十一年后离开
后来,妻子在病床上呻吟
一年半后停止了挣扎
后来,我在这张白纸上
写下这首无声哭泣的诗
那只鸭子正迅速地画下——
句号
这首诗只有一个细节是假的,不是雪地上,而是秦叔家墙根下的花岗石上。那只鸭子画下了触目惊心的,淋漓的几个圆圈。是啊,一个孩子怎么会知道那几个圆圈象征着什么呢?那只鸭子为我的童年、少年、青年的时光,为我生命中曾经历过的事物,为我的诗。为我的这篇散文迅速地画下——
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