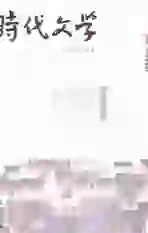那年代的恋爱
2011-12-29王兴海
时代文学·上半月 2011年2期
王兴海,男,1959年11月出生,山东省禹城市人。在《山东文学》、《大众日报》、《联合日报》等多家报刊发表小说、散文、故事、杂文等100余篇。《一壶茶》《阉匠》被《小小说选刊》选用,并收入《中国微型作品精品库》。《一壶茶》还被编入《中国当代小小说排行榜》、《小小说选刊佳作鉴赏》。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
半里宽的河里装满了沸沸扬扬的河工。
这是一条有名的河,河坝很高,淤泥厚厚布了一河底。因为河宽,一个大庄也只能分一两米宽的一溜儿。河沿上装了一溜滑车,都拖着长长的绳子。推车的绷直腿,顶着向上的独轮车。拉车的弯下大腰,整个身子都坠在绳子上向河底缓行。
早晨,东边的日头还没失去它淡红的颜色,一位二十来岁的姑娘站在河岸,双手卷成喇叭筒朝河底叫响:
“亮哥——!”
一河河工的目光都被她拢来。
一个庄叫赵庄。几乎隔年这个时候都有一帮子河工推着行李涌来,分散到有闲房子的人家。
一胖一瘦两个小伙子从大街上走到一个胡同。瘦的手里握着一本书,显得机灵,走在胖的前头。两个小伙子走进一个大门。迎他们的是一个扎着长辫子的姑娘。
“俺住在你这儿啦。”瘦的对姑娘说。
“谁住都一样,只要住得开。”看了两个小伙子好久,姑娘说。
瘦小伙子笑笑,害羞地把手里的书转两圈儿。
两个小伙子红着脸钻到屋里去,默默地收拾起来。
两个小伙子的庄里正翻腾着——
高嗓门儿的队长吆喝几十口子河工。
“跷板都装上!钢丝绳、铺草都装上!”
“谁谁怎么还没来!还没跟老婆子热乎够!”
大街上满满的人,直肠子的爱贫嘴的女人不放过逗引别人的机会,吵得满街飞声。
“掉泪啦老三家?老三可是一去就是一个月啊!老三!老三!”
老三被吆喝得直往人背后躲。
“男人要走了,你倒乐得嘴也合不上了!乐得是没人管你了吧?”说者拍着一个孩子的头说,“看住了你妈,出了事告诉你爸!”
笑声在人们的头顶上响成一层。
队长大喝一声:“驾车子,开路!”
几十辆小车子呼啦啦跷起,在寂静和各种眼光的交织中上路了。
胖瘦两个小伙子一直收拾屋子到中午,队长他们还没到。他俩拿着自己带来的一点干粮,疲惫地倒在屋里一堆干草上。
“让房东给热一下干粮怎么样?”瘦的说。
“要热你去热。”胖的说。
瘦的拿起干粮就进了北屋。
“大嫂,……”
姑娘那么爱笑,把搭在胸前的长辫子甩到背后:“热干粮?放这里就行。嘻嘻。”
一个小男孩背着书包飞跑进来,随口叫了一声“姐姐”。小伙子有点呆了。庄户人家忌讳把姑娘叫成大嫂。姑娘是纯洁的,而大嫂,那就成了贴过男人的身子的女人了。小伙子搓着手出了屋门。
瘦小伙子叫白亮,刚出校门,还是学生的打扮。两个机灵的圆眼嵌在白净的长脸上,有几分标致。把一个姑娘叫成大嫂,他不像老河工那样一笑了之。他觉得这是大失误,没脸再去见人家。
他称“大嫂”的姑娘悄悄走进来,他的脸突然像着了火。
“饭做好了,嘻嘻。”姑娘一边说一边笑。
白亮只顾红脸,话也没答。胖小伙子一直拉着他走到正屋桌子边,他头脑都没反应。姑娘没热他俩的干粮,摆在桌子上的饭是净白的面条儿。
队长他们“大部队”来了。
姑娘的母亲从娘家回来。晚上,刚吃罢饭的时候,队长领着白亮和胖小伙子走进北屋。
姑娘的母亲一片热情,姑娘只顾收拾碗筷。
“来给您道歉哩,大娘。”队长说。
“……”大娘一怔,看了看女儿,女儿也没明白是怎么回事。
队长说:“这两个小伙子刚从学校里出来。社会上的事还不懂。说句笑话了,他们连闺女和媳妇都分不清。他们还叫大妹妹个大嫂呢!”
“这有啥呀,”大娘也笑了,说不出别的话。“俺这闺女叫玉秀,也腼腆着呢!”
玉秀在桌子上拿起香烟,挨个递过去,白亮舒了一口气。
天空没有多少电闪雷鸣,雨却下得不小,地上水流急,满是流动的时起时破的水泡。白亮站在西屋门口,两只手扣着腰,直望着这雨景。北屋里的玉秀纳着鞋底,不时透过窗户,透过雨网望着他。
雨下得急,停得也快。雨刚停下,太阳就等不及似的出来了。雨后的天气凉爽宜人,别的河工都出去呼吸新鲜空气了,白亮在屋里随手拣起一块砖。坐在院子里看起了书。玉秀溜下炕在屋里拿起凳子送到白亮的跟前,而后去了厕所。她叫白亮以为她是去厕所随手给他带上的凳子,并没有特意给他的意思。腼腆的姑娘不善于尽快暴露自己的心灵。
白亮接过凳子,觉得什么话也不好说,干脆什么也没说。
白炽的日头几乎烤焦了河工们的皮肤,他们巴不得连仅在身上的裤头也脱掉。白亮用一块黑了的白毛巾,只盖住两个肩膀。他把腰弯了再弯,头几乎贴着了河坡,拉绳连毛巾一块杀到肉里。钢丝绳通过滑轮紧牵着缓缓上坡的泥车子……突然,车子一下失去了牵引,连滚带蹦落到河底。白亮拽着一块绳子猛地戳到河底的泥里,脚和胳膊被铁锨划出了血。
这天,别人都上工了,西屋里只有白亮一个人。他捧着一本书正聚精会神地看。
“挖河的人看书有什么用!嘻嘻。”玉秀突然走进西屋。
“看惯了,一时放不下。”白亮。
“书里讲些啥道理?”
“书里啥道理也讲啊。呵呵。”
“你是叫白亮吗?”
“是啊,你怎么知道的?”
“我就知道。嘻嘻。”
“……”
“你今年二十岁?”
“是啊。”
“我还叫你哥呢。”玉秀羞涩地笑了。“你的胳膊疼吗?”
“好多了,不怎么疼啦。”
“脚呢,还疼吗?”
“还有点疼。”
玉秀想摸摸白亮的脚,白亮却把脚撤回去,留下她的手在空中悬着。突然大门响了一下,玉秀一溜烟跑出了西屋。
刚才是谁家的狗进了院子。玉秀骂了一句什么把它赶跑,随即从北屋里拿了点什么又进了西屋。
“吃个柿子吧!”玉秀对白亮说。
“不,你自己吃。”
玉秀向白亮递一个媚眼,放下红红的柿子出去了。
天晌午时分。
玉秀说:“妈,做什么饭?”
“有馍,炒点土豆算啦。”
“妈,那鸡蛋放得可有时候啦!”
“愿意吃就炒几个。”
玉秀从罐里拿出几个鸡蛋,只磕开了三个,那三个她默默的放进锅里。做好了饭,玉秀拿出那三个鸡蛋,偷偷送到白亮的跟前。
“吃两个,伤能好得快。”玉秀对白亮说。
“不,你……”
“好好的鸡蛋,没毒的!”
玉秀把鸡蛋硬塞到白亮的手里。
初几的夜,没有月亮,只有满天的星星。别人吃了饭看电影了,屋里又只剩下白亮一个人。白亮正看书,玉秀推门进来。
“你没去看电影?”白亮问玉秀。
“看那个还不跟听你讲书。”
“……”
“你这本书,能多少日子看完?”
“得好长时间呢。”
“能给俺讲讲书里的事吗?”
“这?”
“讲讲吧!”
白亮讲完了书,玉秀沉思起来。半天,她才抬起头对白亮说:“你的背心破了呀。”
“挂破的。”
“我给你缝缝!”
“不啦,我自己会缝的。”
“女的总比男的缝得好些。”
“那,太麻烦你了呀!”
玉秀扑哧一笑,“一家人怎么好说两家话!”
白亮听了这话低下头,没有言语。
许久,白亮说,“那鸡蛋真好吃!”
玉秀接上说,“好吃,我再给你煮。”
玉秀用牙咬断缝衣线,把缝好的背心套在白亮的脖子上就跑出了屋。
又一场雨。
这场雨下得更大,雷闪一个接着一个,像整个宇宙在交火。
“这里漏雨啦,妈!”玉秀说。
妈急忙拿起脸盆放到炕上,雨点砸得盆子“啪啪”响起来。
“妈,这也漏啦!”
妈又急忙拿起一个盆子放到炕的另一个地方。
“又一个地方漏啦!”
“又一个……”
炕上放满了盆子,各自发出不同的声音。
雨下了半天,外边停下来,可屋里还下着。
白亮伤好些了,就试着给房东家压水。见房东家有木头,就让玉秀找家什,他给做木活。玉秀一到没别人在的时候就看着白亮做活。
“你真能,还会做木活。”
“这没啥。”
“昨儿个下雨,俺屋里各处漏,炕上摆满了盆子。嘻嘻。”
“家里有瓦刀吗?”
“有。”
“我修。”
“你还会瓦工?”
“啥不是学的!”
玉秀找出瓦刀,白亮几下窜上房。玉秀担心地说,“小心你的伤!”
白亮在房上看了看,然后下了房,在屋里往房顶上仔细看一番,再就去和泥了。和好泥,几下扔上房,一点也看不出是个有伤的人。
“递给我一把麦草!”房上的白亮对房下的玉秀说。
玉秀没递,抓一把麦草也上了房。
很快房被修好了,玉秀娘回家来,玉秀忙对娘说:“房子修好啦!”
玉秀娘问,“你修啦?”
玉秀说,“不,是白亮。”
“哦。”
“妈,咱是不是得请人家吃顿饭呀?”玉秀机灵地瞟妈一眼。
“可有啥好饭做哩?”
“要请的话,饭我来做就是啦。”
“那你做就是啦!”
灶里的火舌舔着锅底,锅里的挂面和鸡蛋沸起来,涌出半锅的白沫。玉秀一会儿顾锅,一会儿顾火。锅里还沸着,她就舀起挂面往碗里盛。四个碗里只有三个碗里有鸡蛋,有一个碗里面上露着一个鸡蛋底下压着仨鸡蛋。
白亮被玉秀拽到北屋吃饭。吃完饭,玉秀妈说:“你有伤,以后跟俺在一块吃饭就行,跟一家子一样,别见生!”
白亮觉得自己伤好多了。就不时到工地上去,能干点什么就干什么。玉秀家一做好饭,玉秀就到工地去喊白亮。
十五的月亮又圆又亮。
庄东头学校里传过来锣鼓的声音。
“妈,吃饭啦!耍杂戏的都耍上了呀,看不上头还不如不看!”
玉秀凑到饭桌上自顾吃起来。吃罢,她把碗朝水里一涮就跑出去。
杂戏场上满满的人,从里往外人头高出来。汽灯“滋滋”地响,照得跟白天一样,人们能清楚地看到玩杂耍的脸。玩杂耍的打跟斗、竖直立、玩枪弄棒……白亮早早来到这里,抱着胳膊正看得出神。
玉秀来到杂戏场,在不被人发觉的地方扫到了白亮的脸。她悄悄走近他:
“亮哥,有人找你。”
白亮跟玉秀离开了人群。
“谁找我?”白亮问。
“我呗。”玉秀娇媚地说。
“上哪?”
“跟我走。”
白亮跟玉秀来到庄外庄稼地里,一大片庄稼地被月亮照着。
“不知怎的,俺就是愿意跟你待在一块儿。”玉秀说。
玉秀望着月亮问白亮:“为啥这月亮到十五就圆了呢?”
白亮说:“咱踩着的地是圆的,在围太阳转着……”
玉秀瞅着白亮说:“骗人骗人,啥转呀,俺怎么没觉得!”
庄里的锣鼓一阵阵响,除了这,偶尔有狗吠和牲口叫。他俩的身边有蛐蛐呜,微风像鸟儿鼓动的翅膀。玉秀掐一根草放在嘴里靠近白亮,把从背后轻轻拽过来的辫子递到他手里,白亮死死抓住了它。
这时,杂技场外集起了一帮人,烟灰落地的工夫,这帮人像车轮辐条一样向四处散去。
地里的白亮听到有人围拢来的声音,拉起玉秀就跑,一些人吆喝着追来。
“站住!”
“站住!”
白亮最终没有逃脱,他被一伙人拧着胳膊押到了工棚。
“给我吊起来!”玉秀的哥哥指使一些人。
白亮被死死捆住吊起来。
“往死里打!”
野蛮的棍子打在白亮的脊梁上。
玉秀蓬松着头发闯进来:“放开白亮!事不在他,要打打我,打我!”
玉秀的哥哥不说话,两眼瞪着玉秀瞪出了血。他慢慢走过来,一脚把玉秀踢倒。玉秀顾不得自己,她爬到白亮的脚下,双手抱住了白亮的脚。
“亮哥——!”
白亮听到玉秀的叫喊,只微微睁开眼,无力地垂着头。
白亮的队长听到白亮挨打的事,脸色变得黄白。他对河工们说:“兄弟爷们,想想办法呀,咱怎么也不能拉一个死人回去啊!”
有人说:“那就赶紧买酒办个场合。越快越好啊!”
酒席办起来了。六七个人给玉秀的哥哥赔着笑脸,玉秀哥哥的脸耷拉着。
队长斟完一圈酒,催着各位:“来来来,喝酒喝酒!别嫌酒孬,别嫌酒孬啊!”
玉秀的哥端起杯,在半空悬着,其他人也端起酒那么悬着。
玉秀的哥说:“你要好好教训教训那姓白的小子。”
队长一日应承着:“那是那是,他办出这事太对不住您了,我这当队长的也该死!白亮这个小子的事交给我,我要好好收拾他!”
玉秀的哥支使两个人,“把人放了去!”
白亮被放了,队长赶紧叫两个河工,“快,拉车子来!把白亮拉回家!”
车子很快拉来,几个河工把白亮抬上车。队长急慌说,“快走!”
车子刚走,玉秀急急地跑过来。玉秀的哥喝住玉秀,“给我回来!”
玉秀好像一点也没听见,紧紧地跟着车子。她哥使劲拉倒她,她什么也不说,爬起来继续走。她哥拽住她的胳膊,玉秀便死死抓住白亮的车子。
车子被两个河工拉着,车轮转动。玉秀的哥拽不住玉秀,玉秀带着一脸的跌伤紧紧地追赶着车子,追赶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