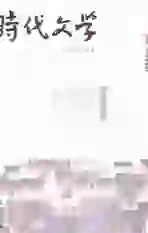小说二题
2011-12-29李宽云
时代文学·上半月 2011年2期
李宽云,生于1962年12月,现供职于山东古贝春有限公司文化中心。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发表文学作品计百余篇,作品曾被《小小说选刊》、《青年博览》等刊物转载。主编过《古贝春诗词选》、《春之声》和《古贝春散文选》。
闯关
经过一番周密的谋划,邓成终于从监狱里逃了出来。他先换了一身装束,又匆匆买了一些零食,连同“五四”式手枪一同装进食品袋里,然后上了一辆公共汽车赶往火车站。他心里十分清楚:警方在发现他越狱后将会迅速设卡堵截并在当地撒网搜捕,因此,他要赶在警方行动前逃离险境。
然而,邓成的行动还是晚了半拍,汽车行驶到半路,一辆警车呼啸着越过它向前方急驶而去。邓成吃了一惊,下意识地扫了一眼窗外光秃秃的荒滩,决定冒险闯关。邓成认为,尽管各个关卡都已掌握了他的体貌特征,但要在流动的人群中一下子认准他也并不容易,关键是不要让警察起疑心,否则就全对上号了,这需要沉着、冷静。邓成稳住心神,向车厢内扫视了一眼,见人们都在探着脖子盯着远去的警车,只有一个二三岁的小女孩趁她身边的妇女不注意,悄悄地从提包里拿出一块奶油蛋糕吃起来。邓成灵机一动,蹲下身子假装系鞋带,凑近小女孩冲她做了个鬼脸。小女孩一点也不怯生,把奶油蛋糕往邓成脸上一递,邓成故意往前一迎,“啪”一下,奶油正抹在邓成的鼻梁上,活脱脱一个舞台上的小丑模样。“嘿嘿、嘿嘿!”小女孩开心地笑起来,小女孩身边的妇女闻声低头一看,忙不迭声地对邓成道歉说:“哎呀同志。实在对不起!快拿手绢擦擦。”邓成接过手绢,故意在脸上涂抹了几下,然后做出一副宽厚的样子说:“不要紧,我就喜欢活泼的小孩儿。”说完,抱起女孩问:“叫什么名字,几岁了?”借机和妇女搭讪起来。估计火车站快到了,邓成对那位妇女说:“你一个人出门,带着孩子又带着东西,太不方便了。待会儿下车我帮你一把。”妇女求之不得,连声道谢。
火车站到了,邓成让妇女拎着提包,他抱起孩子,提着食品袋,一同下了车向出站口走去。邓成想:警察一般不会怀疑孩子的食物。如果有所怀疑,他就把手枪抢到手里或把孩子作为人质。来到出站口,警察果然在对乘客进行盘查。邓成挨到近前,从衣兜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假身份证。警察看过证件,打量了一下邓成,忍住笑问道:“你这脸上是怎么回事?”邓成故意停顿了一下,紧跟在他身后的那位妇女红着脸凑上来答道:“都怪这孩子,太调皮了。”警察盘查的重点对象是单身男性青年,邓成脸上的奶油痕迹和怀里抱着的孩子从很大程度上掩盖了他的体貌特征,警察以为这是一家人出门,无形中放松了警惕,稍做检查便放行了。狡猾的邓成终于闯过了第一关。
邓成利用妇女做掩护,混上了火车。为了防止警察的突击检查,他找了一个靠近厕所的座位。火车开动了,邓成看到一些小站都增添了警察盘查,心想:还得找个人做掩护。主意一定,他就在车厢里搜寻起来。在最后一节车厢,邓成发现有个中年汉子坐在角落里,身子紧护着茶几下面的一个行李卷。邓成从行李卷凸起的棱角上判断出里面裹着个盒状物的东西,再看那人皱巴巴的衣服、茫然四顾的眼神,邓成认定这是一个没经过世面的人。而且携带了常人不常带的东西。邓成假装找座位,在那人对面坐下,眼瞅着窗外的风景,用腿脚触了触行李卷,不露声色地低头闻了闻气味,心里有了数。他用手碰了一下那人的胳膊,起身向那人做了个“跟我来”的手势。那汉子一愣,一脸疑惑地抱起行李卷随邓成来到车门处的过道里。邓成指着行李卷对那人说:“老兄,火车上带这玩意儿可是犯法的!”“哎呀同志,这个俺实在不知道哇,你就饶俺一回吧!”那汉子吓得脸上冒出汗来,咧着嘴向邓成诉说道,“俺爹早年逃荒死在了关外,逢年过节连上坟燎草的都没有。俺是想把老人的‘骨尘’起回来尽个孝道,谁知道这也犯法呀!”邓成微微一笑,继续吓唬道:“人家警察可不听你这些,只要抓住,少说也得关你十天半月的。”“啊!”那人吓得呆立半晌,嘴里只顾念叨,“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邓成见状说道:“老兄,听口音咱也算得上老乡,我看你也是个实在人。这样,我来安排安排,帮你渡过这一关。”“哎呀大哥,你真是活菩萨呀!”中年汉子激动得两目放光,“你怎么安排,俺都听你的。只要过了这一关,俺就是给你当牛做马都行啊!”邓成说:“我先把这东西重新包装一下。”说完,他夹起行李进了厕所。关死门,用水果刀把包裹里的木盒打开,见里面除了散碎的尸骨,还有腐烂的棺木、泥土等。邓成把手枪拿出来,在泥土里涂抹了几下,把它夹在四节腿骨中间用塑料袋绑裹起来。然后,解开裤子,在木盒里撒上一泡尿,再合上盖。出来后,两人回到座位上,邓成问:“你在哪儿下车?”汉子回答“柳树镇”。邓成拿出车票说:“我比你早两站,这样,我在这儿盯着应付乘警检查,你去补票处补两站的票,我把你送出车站再回家。”中年汉子激动得千恩万谢。柳树镇到了,邓成拿着中年汉子的车票,换上他那件皱巴巴的上衣,嘱咐中年汉子远远地跟着他,出了车站在对面的花园门口等候。然后,邓成扛起行李快步走向检票口。检票处站立着好几个警察,其中一个打量了邓成两眼,对他说:“请跟我过来一下。”随后又过来一个人,一前一后把邓成带到一间值班室。一个坐在桌前找开笔记本问道:“叫什么名字?”邓成答道:“魏强。”“有身份证吗?”“有。”邓成说着把身份证递给了桌前的警察。警察看着身份证,又看着邓成,冲同伴使了个眼色,另一名警察飞快地把邓成的全身上下摸索了一遍,冲同伴摇摇头。桌前的警察又指着行李卷问道:“这里边是什么?”邓成说:“是俺爹的‘骨尘’。”警察说:“我们要打开检查。”邓成一屁股坐在行李卷上叫道:“这可不能乱动啊!”“躲开!”警察推开邓成,解开包裹,用螺丝刀撬开了盒盖。“噗!”一股腥气、骚气、臭气混在一起扑面而来。警察用手呼扇了两下,正要仔细察看,邓成喊道:“乡下有规矩:‘骨尘’不能见亮光啊!”抢步上前,倒撩起上衣,俯身遮住木箱的上方,两眼紧盯着警察的手部动作,一旦警察发现破绽,邓成准备先把手枪抢到手,拼个鱼死网破。邓成这一手遮暗了光线,干扰了警察的注意力,还使他们产生了错觉。两人见邓成为了老人的骨尘不避恶臭,急切紧张成这个样子,心中着实不忍,又望见木盒里确是尸骨,便交换了一个眼色,对邓成说道:“同志,打搅了,我们这是例行公事,你可以走了。”
邓成心有余悸地走出了车站,溜进厕所把手枪取出藏好,然后到花园门口来找那位中年汉子。中年汉子刚才看见邓成被警察带进了值班室,心慌得不得了,现在见邓成把行李卷原封不动地扛回来了,激动得不知说什么好,执意要让邓成到他家住几天。邓成正想避避风头歇歇脚,于是就顺水推舟地答应了。
几天后,邓成出现在省城繁华的街道上,虽说眼下风头还没过去,但邓成认为乡下并不是理想的避难地,乡下新鲜事少,一家来个生人全村都知道。城里则不然,同住一个楼道,互不知情的有的是。因此,尽管在省城的车站、码头上贴有通缉令,但邓成却不屑一顾。当然,邓成来省城绝不是有意无事生非的,他想选准几个抢劫目标,然后再找几个旧时的弟兄一块弄几个钱,过一番花天酒地的日子。邓成心里这么想着,便踱进了一家大商场。
商场里人头攒动,唯独进口处一反常态地留出了一片空场,邓成刚走进去,“刷!”耀眼的聚光灯一下子罩住了他。邓成眼前一阵眩晕,他朦胧觉得有两排人步伐整齐地向他逼来,似乎还有几支枪筒对准了他。邓成暗叫不好,右手飞快地伸进怀里去摸枪。正在这时,耳边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灯光也变得柔和起来。邓成定睛一看,一个笑容满面的中年人正手持话筒站在他面前,向他伸出手说:“先生,恭喜您,您是光临我们商场的第10万个顾客,您将获得10万元的奖金!”
“什么?!”邓成听到这话,其惊讶程度甚至不亚于听到警察喊“不许动!”他向四周看了又看,这才明白,刚才排着队向他走来的是4位年轻貌美的礼仪小姐,那枪筒原来是摄像机的镜头。邓成从惊恐中醒过神来,不禁暗暗嘲笑自己神经过敏。他悄悄地把手枪送回口袋里,望着眼前一张张羡慕的笑脸,一时间心驰神往起来,他想,人常说:兔子走时气,城墙挡不住。看来我邓成要时来运转了,这不,我刚想打个挣钱的主意,天上就掉馅饼啦……
“先生!”主持人的话音打断了邓成的思绪,“您马上就会拿到10万元的奖金,现在请接受我们商场对您的祝贺!”话音刚落,4位礼仪小姐手捧鲜花、礼服、礼帽一齐拥上,围着邓成忙活起来。望着眼前鲜花般美丽的笑脸、闻着醉人心魄的脂粉香、感受着美女轻柔的触摸,邓成体内涌起一股冲动,一时间心猿意马起来。这时主持人把一张现金支票递给他说:“先生,现在请告诉我您的尊姓大名。”邓成接过支票脱口答道:“我叫邓成……”
话一出口。邓成就好像万丈高楼一脚踏空,脑袋“嗡”一下涨大起来。朦胧中,他看到不知从哪儿冒出几个警察已经向他包抄过来。邓成下意识地伸手去摸枪,但没摸着,这时他才发现装着枪的外衣已被套上了礼服。此时,警察已经逼近。邓成绝望地哀叹一声,束手就擒。在被带离商场的那一刻,邓成突然发起狂来,他撕碎了支票,踩烂了鲜花,踢倒了摄像机,然后带着一丝苦笑被推上了警车。
走鏊子
清朝末年的一天上午,武城县衙前人山人海,上百名军卒和衙役手持毛瑟枪和水火棍等围成一个大圆圈。圆圈中央用石头和砖架起了十二只铁鏊子。衙门口处端坐着行刑官,身后是三辆囚车。众衙役肃立左右,等候号令。传令官敲着铜锣晓谕众人:今天将有三名犯人被处以“走鏊子”之刑。
“鏊子”就是烙饼用的炊具,把鏊子烧红了让犯人光着脚在上面走,是一种酷刑。走鏊子的个数根据犯人的罪行而定,但一般情况下不超过十二只。
九时许,行刑官宣布:第一名犯人“忤逆不教”,被判走四只鏊子。号令一下,众衙役捧着炭火、干柴、麻油等物一拥齐上,霎时间,四只鏊子下面燃起了熊熊烈火。刽子手把犯人从囚车内架到鏊子前充作台阶的条石上。挽起他的裤管,脱去鞋袜,等待鏊子烧红。犯人是一个二十出头的车轴汉子,胖头粗脖,满脸横肉。他看看烧红的鏊子,把牙一咬,快走踏上去,“嚓嚓”两声,已迈过两只鏊子。然而,就在这一瞬间,脚板已被粘脱了一层皮,当冒着血丝的新鲜皮肉触到第三只鏊子时,一阵钻心的疼痛“倏”地传遍全身,他“嗷”地吼叫一声,像只被毒蛇咬伤的狗熊从鏊子上蹦了下来,抓着两脚咬牙咧嘴。两名刽子手冷笑着走过来,用两块布头把犯人的脚裹起来,架进囚车里。
第二名犯人也是一个小伙子,瘦高个,长得溜肩细腰、尖耳猴腮。他以“欺兄奸嫂”之罪被判走六只鏊子。瘦高个被架到鏊子近前。两只眼珠子转了转,两脚快步站到了第一只鏊子上。“咝咝!”随着响声,一股热浪夹着焦腥气从脚跟直窜头顶,瘦高个晃头拧肩地怪叫着,硬挺着没动地方。但仅过了十几秒钟,他终于忍不住了,拔腿向前跨去,就在这时。他的两只脚板竟粘下一块肉来。瘦高个收脚不住。血淋淋的脚板再度踏在通红的鏊子上,“啊!”瘦高个一声惨叫,滚落尘埃,抱着双脚哭爹喊娘。残留在鏊子上的肉块“咝咝”地响着,上面的血没等淌下来便被烤成了浓沫儿,眨眼之间,那肉块便由红变黑,成了焦炭,风一吹,上面的炭末儿冒着火星点点飘散。
看着第二名犯人惨叫着被拖进囚车,围观的人们都倒吸了一口凉气,这时第三辆囚车被打开了,从里面走出一位白白净净的少妇。行刑官宣布她以“谋害亲夫罪”被判走十二只鏊子!人群中一阵哗然,目睹了刚才的惨景,人们认定:即使少妇不被烤死烫死,也免不了落个遍体鳞伤再被砍头。一时间,许多人的心都揪了起来,一些老太太又是担心又是埋怨:“唉!她怎么没缠脚呢?这又平又大的脚丫子要多挨多少烫哟!”这时,剩余的六只鏊子都已经点着了,刑场上烟雾弥漫,一时间连天空也变得昏暗起来。一名刽子手不知是收了少妇仇家的黑钱,还是出于对女犯人的憎恨,恶狠狠地往鏊子下面加了一些炭火,又抄起一把大铁铲,“哧哧”两下,刮掉前两位犯人在鏊子上的残留物。随着铁铲的滑动,鏊子上溅起一串串火星,一时间鏊子变得更红了。少妇平静地等待着刽子手做完这一切,双脚毫不犹豫地站到了第一只鏊子上。在令人窒息的蒸烤中,少妇微微弯下身子,稳住身形,她的眉头拧成一个疙瘩,一缕鲜血从咬紧的嘴唇中汩汩流出。此时,刑场上变得静寂无声,连空气似乎都凝固了,人们摒住呼吸,目不转睛盯着少妇,经历了漫长的一分钟的煎熬,她慢慢地挺直了身躯,颤巍巍地抬起了已经发黑的脚板,坚定地向前迈去,一步、二步……乖乖,竟如穿着皮靴走沙地,一步比一步稳重,一步比一步快捷。在万人的目瞪口呆中,少妇走到了第十二只鏊子上!人群中爆发出一阵欢呼,少妇用衣袖抹了一把脸上的汗水,转过身形,昂头甩了一下额前的长发,两眼喷射出愤怒的烈火,冲着行刑官大喊一声:“看你姑奶奶再饶上两趟!”说完,不等行刑官回话,甩开大步,刷刷刷,眨眼间,又在十二只鏊子上走了一个来回。“哗——”人群沸腾了,刚才还凶神恶煞般的衙役不等行刑官传令,便毕恭毕敬地把少妇的衣物送了过来。围观的人们冲进圆圈,争相近睹心目中的女神。当少妇被她的亲人接回家时,浩浩荡荡的人群尾随其后,经久不散。
此事成了方圆百里的特大新闻,少妇的家里从此门庭若市。少妇不胜其扰。于是在一个风雪之夜只身躲到百里之外的一个表姨家,靠着姨母一家的帮助和保护,以纺织为生。深居简出,过起了独身生活,绝口不提当年之事。
全国解放时,少妇已是年逾七旬的老妪了,有一天,与她最贴心的表妹问她:“大姐,这些年人们都说你是神仙,俺看不像。不过,俺一直想问问:连皮糙肉厚的大男人都没走下来的鏊子,你怎么就能走下来呢?”老妪淡淡地一笑说:“其实也没什么,关键是要经住起初的那一烫。头一个人不懂,没走下来;第二个人看明白了,但没挺住;我明白那一烫连着我的生死,就咬牙挺过来了。”
一九五一年,老妪去世,享年七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