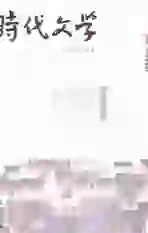某天的开始
2011-12-29徐永
时代文学·上半月 2011年2期
徐永,自由职业者,在《长江文艺》、《热风》、《星星》、《海燕》、《青春诗歌》、《莽原》、《当代小说》等文学刊物发表过中、短篇小说和诗歌。2001年年底辞职经商后停止写作,2009年始重新业余写作。现居德州。
早晨王朗醒来,闹钟像一根绳子把王朗从水底拉到岸上。他摸索着把闹钟拨拉倒。眼皮发胀,他费劲地睁开,阳光有些刺眼,赶紧又闭住用一只手压在眼睛上。阳光是金黄的,透过窗户一缕缕光柱洒在空荡荡的屋里,有些在墙上,有些在床上,大小不一,形状各异。那一缕缕金黄色的光柱里,有很多腾舞的粉尘。王朗突然感到无比的恐惧,每天呼吸到肺里该有多少这样的粉尘啊!映在地板上的窗户一点点变大。屋外的声音,逐渐热闹起来。先是一只鸟叫声,然后是一群鸟的鸣叫,后来是一个老人的咳嗽声,自行车的车铃声,汽车的喇叭声,小商贩的叫卖声……各种声音混杂在一起,搅得他来了精神。他用力伸展四肢,想象着有四条绳索从四个方向用力拉扯着四肢,那床单被他弄得到处是褶皱。伸展到第四次,他猛地坐了起来。身后油黑的枕头被他的后脑勺压了个窝,上面有几根头发,像几根枯草,王朗不由自主地摸了摸自己的后脑勺,还好没有凹下去。
王朗趿着鞋,揉着眼睛进了洗手间,撒了一泡又长又黄的尿。马桶的冲水开关早就坏了。他用昨夜的洗脚水冲完马桶后,开始刷牙。在镜子里他看见一个黑眼圈,眼角沾着眼屎,满嘴牙膏沫的男人。他挤了挤眼睛,皱了皱眉头,他对镜子里这个男人很不满意,甚至他觉得这个男人有些可笑。洗脸的时候,他仔细洗了洗眼角。又和镜子里的那个男人对视了一会儿。最后他很无奈。只好对那个男人挥了挥拳头,那个男人给了他一个恶狠很的表情。
王朗从塌陷的沙发上找到还算干净的衣服穿上,只是衬衣的领子有些发黑了,不过套在里面,别人是看不见的。临出门的时候,他发现门口有一张纸条,不知道是谁从门缝里塞进来的。他拿起来一看,原来是房东给他留的。那个胖女人立即浮现在他眼前,掐着水桶腰,瞪着三角眼,脸上都是赘肉,露出一口齐整的大白牙:
你已经拖欠房租半个月了。这周如果你还交不上,请抓紧收拾行李搬家,现在排队租房子的人很多。
王朗把纸条揉成一团,在皮鞋上擦了擦,然后扔向茶几后的纸篓。纸条抛出的抛物线很漂亮,但是没有丢进纸篓。王朗拣回来,反复抛了三次,才把纸条仍进纸篓。他这才吹着口哨出了门。王朗住在顶楼,每次下到三楼,他总是停顿下,看看东户那家Io8d6xZy61ZCmrJKV6yAv9uQOPSLk9c3DTLElM2Lsgw=的门,他希望有个人从里面走出来,那是个留着长发的漂亮女孩,喜欢穿米蓝色的长裙。王朗和她对视的时候,她总是撇下嘴,露出两个小酒窝,王朗的心里会荡漾起来。一天都会有个好心情。
在小区的大门口,每天早晨有个摊煎饼果子的,味道不错。王朗会要一份,边走边吃,吃完了也到了站牌下。前后不会超过十分钟。公交车就到了。等车的人很多。王朗挤车很有经验,一般从门侧面挤能抢到前面。运气好的话。车上还能有坐位。那就可以再眯一会儿了。否则要站四十多分钟才能到站。
“咣哨”车门关上了,王朗笼罩在车上那股混合的味道里。顿时他的胃开始翻腾,刚咽下去的煎饼果子又涌到嗓子眼,他强压了下去。过了好一会儿,胃才开始平静。车的空间不知道是小,还是人多的缘故。有时候左脚站立着,右脚开始放下,就会踩到别人的脚。王朗经常站着就睡着了。
这个城市的公交车司机驾驶总是急停急驶。如果没有抓牢扶手,就会出现碰撞。火气大的人占大多数,不分性别,吵架甚至打架的事情屡屡发生。王朗就夹在这个狭小、喧闹的空间里,让他的呼吸不顺畅。他经常有把脑袋探出车外的欲望。
那天,站在山顶,他凝望着北方,树枝上怯生生地冒出些新芽,空气里弥漫着清新的味道。一股乡愁涌了上来,家乡就在山的北面。到底离这座山有多远他也不清楚,他只记得师父在他六岁时带他上的山。他在村子边的树林里和小伙伴玩游戏的时候,被师父用一颗棒棒糖诱走的。那时候师父背着他走了好多天,才来到这里。家里是什么样子,已经很模糊了,就像远处的群山。好像门前有条河。河里时常漂浮着发黄的菜叶和鸭子。鸭子把头伸进水里,然后又迅速地露出水面,抖抖脖子上的水珠,骄傲地左顾右盼。河边有些妇人浣洗衣服。衣服平摊在河边的青石上,妇人抡起木棒噼里啪啦地在上面敲打。有时候木棒会敲到水里,顿时水花四溅,水面漾起一层层水纹。家里是个四合小院,院里的一角有棵海棠树。窗台下摆满了一排排金黄的苞米。母亲坐在门前的台阶上,把一粒粒金黄的苞米搓到簸箕里。一会儿,簸箕就满了。母亲的身后就堆满了一堆苞米芯儿,像群光腚的娃子。母亲把簸箕放在左腿上,细心的挑拣着什么。一只芦花老母鸡,踱着四方步,带着几只毛茸茸的小鸡崽,上前叨食。母亲挥挥手。老母鸡扭头就跑,肥大的屁股一扭一扭的,留在地下几只好看的脚印。母亲从簸箕里拣出一粒瘪了的苞米,看了看,叹口气又放了进去。他趴在母亲的背上,被阳光照得有些迷糊了。母亲说,“小,别睡着了,你爹赶集马上回来了,给你带了糖人。”说完母亲端起簸箕就簸,苞米糠子洋洋洒洒地就飘起来,落在地上,薄薄的一层。他的鼻子一痒,忍不住直打喷嚏。
决定下山的那天,他在山泉里洗了个澡。用师父锈迹斑斑的剃刀刮了刮脸。剃刀对他来说不如剑好使,一不小心脸上留下了几处伤痕。他找出师父的一件旧袍子穿上,风从袍子底下钻上来,晃晃荡荡地飘起来。他索性在腰里扎了根麻绳儿,从墙上摘下剑走了。尽管他知道师父不会再回来了,可他还是留了张纸条,用一块石头压好。
“师父:
我下山看我娘去了,很快回来!”
他又回头看了看,山门上斑驳着脱落的红油漆。这时一只鹰在天上叫了一声,他知道鹰在张着翅膀盘旋。
师父五年前就消失了。那天他们对坐着用嘴拆招,他说出第三招时,师父没再说下去,长叹一声,垂下霜雪样的头。沉默了许久,师父的嘴唇动了动:“你没对手了,可你的剑术还没达到最高境界。”他疑惑地盯着师父毫无表情的脸,师父却站起来盯着窗外的山峦:“剑术的最高境界就是不比武。”说罢,师父推门而出。师父的脚步声渐渐远去,最后只剩下风在那条山路上低语。门前松树上,一只小松鼠咀嚼松子,叭叭叭地脆响。师父再也没有回来,他静静地坐在屋里,琢磨师傅那句话。越想越糊涂,像被一个洞吸住了。那是一个幽深且带着许多暗道的洞。他以手做剑温习剑招,却叉开了手掌,像在寻找一根绳子。一根稻草也行啊,他为自己这种想法感到恐惧。四肢舞扎、握,没抓到。再握,还是没能抓到。他仿佛溺水的人,慢慢地向深渊里沉。最后他绝望地闭上了眼睛,放弃了挣扎。不知道过了多久,突然有道光在他脑海闪亮,犹如即将燃尽的蜡烛。他拼进全力,伸出手,居然抓到一根绳子,坠落开始停止。
他醒了,屋外面是蒙蒙的亮。他侧头看了看。那柄剑斜斜地挂在墙上,正在冷冷地凝视着自己。他想站起来,却跌倒了。他不停地捶打两条麻木的腿,直至恢复知觉。当他推开屋门:那棵松树、木栅栏的围墙、没有掩住的院门、迷茫的山峦、灰蒙蒙的天空、时隐时现的太阳——它们依旧。而他觉得有一种重生的感觉。
后来山上的日子,是他一个人度过的,师父不会再回来了。师父在的时候是他的标尺。师父之所以消失,就是为了让他没有这个标尺。只有这样,他才能进入更高的境界。那柄剑,他再没拔出过来。剑和剑鞘的接口处起了一层暗绿色的锈,好像自己的身上蹭了脏东西一样。他时常和这柄剑互相凝视,在脑海里,他无数次拔出剑。在屋里劈、砍、刺、撩、挡。夜里他经常猛然醒来。他听见了剑的叹息声。他坐在黑暗中,看见那柄剑闪着幽光。剑鞘晃起来,咣当咣当地响。剑似乎就要脱鞘向他刺过来,他赶忙用双手挡住,却挡了个空。
过去他每月只下山一次,到镇上买师父喜欢的烟叶和盐,然后回山。他沿着向北的大路走,穿过村庄、城镇、田野、河流。干粮吃完了,他就给人家打短工,换些吃的。累了,他就搂着那把剑在墙根儿眯一会儿。
有次,在下山后的第七天上午,在一个叫天衢镇的地方,他到一户人家讨水喝。土坯垒院墙围着茅屋,屋顶上的枯草在风里发出刷刷的响声。他叩门的时候,隐约听见里面有哭声。开门的是一个双眼红肿的老妇人。他说明来意,老人颤巍巍地端出一碗水,有两个缺口的粗瓷碗里,水晃阳光,有些晃眼。他一口喝了,那水真甜,让他想起了当初师父诱他上山时的棒棒糖。他向老人致谢,正打算离去,却一眼看见屋里的大梁上垂下一根绳子。他忍不住问老人,“大娘,有什么想不开的。”老妇人顿时失声痛哭起来,额头的皱纹挤成一堆,从那浑浊的眼里滚出一颗颗大粒的泪珠,让他有些不知所措。从老人断断续续的讲述中,他才知道,老妇人的老伴早已去世,她和独生女儿相依为命。前些日子,飞来横祸。女儿到集市上卖菜被日月帮帮主古金掳走了。她多次到县衙告状,却因日月帮势力极大,县衙不敢受理。如今女儿不知生死,老人对余生失去了指望。如不是他恰巧来讨水,老人已悬梁自尽了。他叹了口气,这尘世纷争他不想插手,否则自己多年的修行将毁于一旦。他转身想走,却瞥见老人满头的白发,他心抖了下,他想起了自己的娘亲。当年自己被师父掳走,自己的娘亲是否也和这位老人一样肝肠寸断。他猛地回过头一把抓住老人的双手,告诉老人,中午他就会带她女儿回来。老人用疑惑的眼神看着他,他拍了拍老人的手,“大娘,你放心!我和日月帮帮主是朋友,中午一定带你女儿回来。”
日月帮是天衢镇最大的府邸。他向门房说要见古金。门房见他一身打扮活脱脱一个乞丐,正打算撵他走,却发现他在青石板上踩下了两个浅浅的脚印,赶紧一溜烟消失在深院子里。古金听说有人来滋事,气就不打一处来。这种小事找个堂主去打发就行了,何必来麻烦我。他刚想叱喝门房。但听门房说那人在青石板上踩出一双整齐的脚印,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他清楚自己最多能用内力将青石板震碎,根本不能在上面留下脚印。古金有些犹豫到底出去见这个人么?他看了看挂在墙上金光闪闪的日月剑。走过去把剑摘了下来。沉吟了一会儿,他把剑拔了出来。那剑顿时发出夺目的光芒,还有一股冷飕飕的剑气,古金的信心一下起来了。他挥手让门房把那人带到院子里来。想当年古金和楚留香、西门吹雪在华山之颠,大战三百回合,要不是当时刮大风,一粒沙子吹进古金的眼里,他不一定落败。因此日月神剑被天机老人列在江湖兵器谱上第三名。这把剑陪古金无数次恶战,除了那次在华山,古金至今未遇对手。
他进来了,站在院子中间。穿着肥大的灰袍子,袖子挽到胳膊肘,左手拎着那把长锈的剑。他看见一个圆脸的胖子,右眼角长着一颗黑痣,那痣上有两根长长的黄毛。从眼神里,他知道这人就是古金。他简短地向古金说明了来意,最后补充,“请帮主高抬贵手,放过这一对母女。”古金顿时大笑起来,那笑声跳到空中,像鞭炮一样在空中炸响。古金突然止住了笑声,脸色变的冷酷漠然。他扬起手中的日月剑,“只要你赢了这把剑,谁你都可以带走。”他本想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古金放人。但这时候他明白。一切的说词都是徒劳的。他不情愿地拔出了那柄剑,剑与剑鞘之间的锈,顿时化成粉末,纷纷落到地上,剑发出一声快乐的呻吟。
古金笑了,日月剑在出鞘的一刹那,发出的是夺目的光芒,天地之间都黯淡了。
这时,他的剑刺了出去。
是一柄乌黑的剑,闪着幽幽的光。剑的速度并不快,隐约听见剑c8TvEODFYtlc1DQukho5uTF4hFIcwRPFm588M2cs30M=与空气摩擦发出的声音。他知道那是剑在和自己说话。他明白,这剑刺出以后,十几年来,在古树旁,飞瀑下,云峰上的修行,全付之东流。他曾以为自己不会理会这尘世中之事,这柄剑只会是自己自言自语的对象。但是今天这剑刺了出去,刺向尘世中人。
他那柄剑刺出去的时候,古金就知道自己输了。那柄黑黝黝的剑速度并不快,但是古金却感到无处闪躲。古金被剑气罩住了,他成了被网住的猎物。古金握着日月剑的手湿漉漉的,他觉得无论往那个方向抵挡,都会被那柄剑突破刺向自己的身体。古金万念俱灰,绝望地闭上了眼睛。过了好一会儿,古金睁开眼睛,发现那柄黑黝黝的剑已经归鞘。
“请帮主放人吧。”
古金勉强挥挥手。
门房吓呆了,跌跌撞撞地跑了下去。一会儿,一个穿米蓝色衣服的长发女子走过来。女子眼睛红肿,神情委顿。
“你是不是璇璇?”她咬着嘴唇点点头。
“我带你回家。”她笑了,脸上露出两个小酒窝,过来把手放在他手里。他们并肩走向门口。她的手很软,他的心也柔软起来。
这时候古金嚷了一声:“少侠,请留步。”璇璇的脸上顿时露出慌张的神色,他冲她笑笑,示意她不用害怕,然后转身面向古金。
“请恕金某眼拙,少侠能否留下名姓?”古金的日月剑不知何时掉在了地上。
“我叫王朗,无名之辈。”王朗说完,领着璇璇走了。他听见古金在身后喃喃自语,“王朗,王朗,王朗……”
公交车一个急刹车,发出吱、吱……的刺耳声音。司机把头探出窗户,叱喝前面一个慢吞吞骑着三轮车的老人,公交车内乱哄哄的声音戛然而止。王朗的头撞到了前面的座位上,他不停地揉着,同时看了看窗外。
闪光灯不间歇地闪烁,快门声咔嚓咔嚓地响着。他面带微笑,踩着红地毯快步走向主席台,坐到正中间的位置。一边是美女主持,一边是集团新闻发言人——一个面色严肃的中年人。他坐下后,感觉椅子有些不舒服,欠欠身,然后环视下会场。会场基本上坐满,大约有百十人。主席台的灯光有些耀眼,看来会场的安排人员经验不足,他想。领带扎得有些紧,他轻微地晃了晃了脖子。身后的背景是一幅写真的喷画:一幢幢高楼,天空湛蓝,远景湖光山色。还印有两排醒目的红字:乾坤集团为民房地产项目实施新闻发布会。
先是集团新闻发言人对项目进行介绍。他正襟危坐在那儿,脑海里却盘旋着一个西亚油田开发的项目。直到女主持人的膝盖轻轻地有节奏地碰撞他的腿,他才从思绪中走出来。他低头瞄了一下,她穿着一件黑色的短裙,雪白的大腿暴露在外面。脚上穿一双白色的凉鞋拖,十个脚趾甲染着血红的指甲油,很耀目。幸好桌子上的台布垂到了地上,这一切只有他和她知道。他端起茶杯,吹了吹漂浮的茶叶,顺眼看了下她。她面若桃花,眼睛看着新闻发言人。她看起来很面熟,好像是一个经济栏目的女主持,看来今夜又有故事发生了。集团新闻发言人的讲话持续了十几分钟才结束。之后会场沉寂了一小会儿,女主持才嗲声嗲气宣布:“下面热烈欢迎乾坤集团董事长王朗先生为大家讲话。”他点点头,算是打了个招呼。没有看发言稿他就开始讲起来:各位媒体的朋友,各位来宾:
“大家好!”他顿了下,等热烈的掌声响起后,他继续讲下去。
“首先感谢大家长期以来对我们乾坤集团的支持和帮助!”掌声又响起来,只是没有刚才热烈。他用眼镜后面的眼睛扫视下会场,发现后排有两个人窃窃私语,好像搞什么阴谋似的。他感觉耳朵里有一只小虫子,不由自主地用手掏了下耳朵。他咳嗽了一声,这咳嗽声顺着麦克风,传遍整个会场。那两个私语的人停下来,茫然地看着主席台。他呷了口茶继续讲下去。
“二十年来,乾坤集团走过了风风雨雨。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全体员工的努力下,把当初只有几个员工。经营项目只有房地产中介的小公司发展成今天上万员工,涉及房地产开发、能源、金融、信息产业、汽车制造、酒店餐饮等多元化经营的世界五百强企业。”
这时候一个中年女服务员上来给他续水。他用眼光瞄了下,这个女服务员四十岁上下,胖胖的,一对小眼睛,脸上都是赘肉。他感觉胖女人的胸在自己的后背上蹭了几下,有些发痒,他不由得耸了耸肩。发现他观察自己,那胖女人赶忙笑笑,露出满口齐整的大白牙。脸上的赘肉堆在一块如同一块肉坨。他心想,五星级酒店里怎么会配置这种档次的服务人员,看来这个酒店的总经理要换了。
“乾坤集团之所以有今天是因为我们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是这个社会赋予我们今天的辉煌,因此回报社会,回报百姓,是我们乾坤集团义不容辞的责任。为解决低收入人群的住房问题,我们将奉献绵薄之力。经董事会研究决定,自今天开始,全国80多个我们集团新开发的房地产项目全部实行成本价销售。对没有首付能力的低收入家庭我们将实行零首付,同时三十岁以下的购房者可以贷款四十年偿还购房款。我们这绝对不是商业炒作。我们所有的建筑成本和销售成本都将对外公开。欢迎社会各届对我们监督!”
美女主持带头鼓掌,掌声雷动。他下意识地摸了下口袋,又把手放回到了桌子上,这个场合是不能抽烟的,要注意公众形象。下面开始记者提问。在新闻发言人的指点下,一个矮胖子站起来,他五短身材,肩膀上扛着一个大头颅:“我是《经济日报》记者王祖祥。请问王董事长,贵集团的这次降价行为,是否会导致整个房地产市场的巨大震荡,影响地方经济的增长?”
他挥手示意他坐下:“我对这位《经济日报》记者的提问,有一点要纠正。乾坤集团的这个项目的实施,不是降价行为。我们原来开发的房地产项目,还是继续按着市场来操作。这个项目中的80多个新楼盘是今天才开始陆续开盘的。我们这次利民房地产项目,针对的对象是无购房能力的低收入群体。这些群体本来就不是其他房地产企业的销售对象,因此我们的行为不会影响到房地产市场,更谈不上影响地方经济的增长了。”
他的回答顿挫有声,整个会场出奇地安静,只有他的回音。
“您好!王总。我是中央电视台记者代福军。”这是个戴眼镜的瘦高个,“贵集团的这次房地产成本销售,具体的价格是多少?这次行为是否对贵集团的经营造成影响?”
“由于80多个楼盘,分布全国各地,土地、建材等成本存在着差异,因此价格不可能一致。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讲,我们让出了80亿人民币的利益。另外这位记者对我们集团需要有一个深入的了解,房地产项目在我们企业的经营当中只占10%的份额。作为世界前十强的企业,光能源一个经营项目,每年带给我们的纯利润就远不止80亿。我再一次强调这个项目是一次公益行为,要的不是利润的回报。今后,每年我们都要加大对这个项目的投入,让更多的低收入人群有房住。尽管这也是杯水车薪。我们会联合更多的企业和单位加入到这个项目里来,并积极获求政府的支持!”
“王总,您好!我是新浪网记者璇璇。”这是个长发披肩的美女记者,由于名字和他昔日暗恋的女孩重名,他不由得多打量了下。“请问王总,实施成本销售,对炒房团有极大的诱惑力。低价房所带来的巨大升值空间,会驱使炒房团想方设法购房,容易鱼目混珠。贵集团如何保证低收入群体的购买率?谢谢!”
“这个问题提得很好。”他颌首称赞,“针对炒房者的觊觎,让我们这个项目真正做到名副其实。我们制定了周密的措施,并且这些措施将随着项目的实施不断完善。第一,我们会对购房者的收入进行两次调查。购房者的收入必须低于当地人均收入。第二次调查人员如果发现第一次调查人员的调查有出入,我们将对第二次调查人员进行奖励。同时对第一次调查人员进行处罚。如果第二次调查和第一次调查基本相同,我们将奖励第一次的调查人员。同时我们欢迎大家举报,一经落实,对举报者重奖。第二,我们将与购房者签订一个合同,购房者要保证提供的收入证明真实可靠,如有虚假,我们将收回房权,并对房子进行评估,收取房屋的折旧损失款。同时购房者在十年内不得将房子的产权转让。第三,进入我们这个项目的所有楼盘,三分之二销售。另外三分之一出租,租金是市场价格的二分之一。”
“咣当”一声,同时伴随着一股气流声,车门开了。王朗摇晃着脖子下了车。他的目光尾随公交车后屁股冒出的一股黑烟渐渐远去。站牌离公司还有段距离,步行大约十分钟。王朗习惯在路上数人行道上的方块砖。这段距离他数了快两年了,但是每次方块砖的数目都不相同。他低头数砖,经常撞到行人。如果是女人,他会龇牙一笑,继续前行。如果是男人,他低头哈腰,嘴里直道歉。经常受到叱骂和白眼,他已习以为常。今天他数得有些心不在焉。狗日的老板,一定要让他给涨工资,要不这日子怎么过啊?他脑子里老是这个念头,因此方块砖被他数得七零八落。
踏上十二级大理石台阶,就来到了一座气派的大厦门前。进进出出的人很多,都行色匆匆。王朗的公司在十二楼,每天都要乘电梯上下。王朗在电梯里的感觉非常不好,他觉得自己的命运被这个严严实实的铁笼子掌握。一群陌生人表情严肃地挤在狭小的笼子里,一起抬头看那个红色的数字,等待数字变黯淡。然后脆脆地“当”的一声,电梯门开了。有人侧着身子,拼命挤出去。还有人挤进来。电梯里不像公交车上,大多是沉寂的,偶尔有人在接电话“喂,喂……”信号时断时续,接电话的人的声音逐渐变大。开始有人给他白眼。
电梯在十二楼下的每次停、开,王朗的心就会沉一次,有时候会让他焦虑不安。他多么希望电梯一下驶到十二楼或者从十二楼一下降到一楼。可是从来没有过,即使有几次他加班到很晚,电梯下降的中途也会有人上来。
“当”的一声,十二楼到了,王朗迫不及待地挤了出去。公司的员工在一间开放的大房间里办公。每个人的办公桌又被隔成一个个隔断。只要站起身来,可以看到每个角落。王朗打完签到卡,回到自己的隔断里沏上一杯浓茶,然后开始每天的画圆。这个习惯从他参加工作时开始有的。每当他开始画圆的时候,无论如何烦躁,都会慢慢平静下来,渐渐心无杂念。让他感到有意思的是,圆要一笔画下来,起笔和末笔必须完美地重合。如果中间停顿了,就很难画圆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圆画的越来越好,几乎能和圆规画的圆媲美了。他每天一上班要画满十张纸,才会开始工作。他现在已经不满足画的圆不圆了,他开始追求画圆的速度。
可是今天他画了快十张纸了,依然心神不安。他喝了口茶,左手托着腮帮子。办公室乱糟糟的声音,仿佛与他一点也不相干。过了好大一会儿,办公室突然安静下来。他抬起头看见老板夹着包,匆匆从隔断中间的过道走过,径直走向大办公室尽头的总经理办公室。王朗看见老板后脑勺上有一绺子头发翘起来,像鸡尾巴。王朗站起来,又坐下,用铅笔吧嗒吧嗒地敲桌面。他前面的隔断响起手指的敲击声,他知道前面那个自以为妖艳的女子在抗议。他突然感到尿急,但是到了洗手间站了很久,就是尿不出来。他打开水龙头,仔细地洗手。直至有人上洗手间他才惊醒,赶紧回到办公的那个囚笼,把几张画圆的纸撕得粉碎,然后把纸片放在手心里攥成一团。
王朗终于下了决心,来到总经理办公室门前。犹豫了几分钟,开始敲门。门发出沉闷的“咚、咚”声,如同王朗的心跳。随着公鸭嗓的一声“进来”,王朗推门而入。映入眼帘的首先是一张宽大的老板台。老板正靠在老板椅上来回晃动,他的腿不时会碰到身边的一棵芭蕉树,弄得叶子发出细碎的响声。看见王朗,老板的眉毛只是扬了扬。双人沙发真大啊,王朗坐下去,感到身子陷下去半截,这让他有些不知所措。茶几上的一盆兰花,兰花有两片叶子枯黄了。老板点了根烟,ZP打火机清脆地响了一声,恍恍惚惚的火苗子攒动着。
“王朗,我正打算找你呢。你们最近跟的那个项目有什么进展了。”王朗绞着双手,看见老板的鼻孔冒出两股轻烟,这让他想起来公交车后屁股的排气管。
“正做项目可行性分析报告。”王朗的声音小得怯怯的。
“效率太差,到现在报告还没出来?客户不会等我们的!”老板的声音让王朗感到刺耳,“金融危机对整个市场影响非常大,公司受到了很大冲击。即使这么困难,公司也是按时给你们发放工资,你们怎么能一点危机感都没有呢?”老板的脸在淡淡地烟雾中有些朦胧了,见王朗依然沉默,他气咻咻地把烟摁在烟灰缸里,“你们不要拿着公司的薪水,在这混日子!”
“古总,我想辞职。”说出这句话,王朗自己都感到吃惊,但是也有一种释然。老板面无表情地盯着王朗看了一会儿。
“来,抽支烟。”老板把烟扔向王朗。王朗有些走神,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烟掉在了茶几下面,王朗俯下身摸了好长时间才摸出来。他不会吸烟,身上没有火,只好把烟放到了茶几上。
“王朗,你要是有好的去处,我就不拦你了。”王朗感觉整个身子都木了,“你大学一毕业,就到公司了。我是把你当做人才来培养的。让你一直在最重要的岗位工作。你扪心自问,我古金有那点对不起你的?逢年过节,我看你家不在本地。即使不叫你出来吃顿饭,也会给你一个红包吧!公司目前正是需要人的时候,你拍拍屁股就走,是不是有些辜负我对你的培养,有些不负责任啊!”老板很激动,喘气声变得有些粗。王朗的视线飘落到落地窗上。窗外有些灰暗,远处那些楼群,仿佛水墨画,若隐若现。
一阵橐橐脚步声,让王朗的目光从窗户那儿飘回来。老板已经站到了他身边。老板一手拿着烟盒,一手擎着打火机。他把烟盒递向了王朗。王朗本想说茶几上还有呢,但他还是起身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老板打着了打火机,蓝色的火焰跳了出来,王朗凑过去把烟点着了。淡淡的烟雾散开,王朗和老板的脸庞开始朦胧起来。
“王朗啊,现在很多公司都是外强中干,表面风光。实际举步维艰。要是你去意已定,我不拦着你。可我要提醒你,到一个新公司,你还要从头做起。适应新的环境,新的岗位,新的人际关系。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我敢打包票,没有一个公司像咱们公司这样单纯,都很复杂。你的性格不适合勾心斗角啊。年轻人要脚踏实地,做事情不要一时冲动,选错自己的位置啊!”老板边往座位上走边说。
王朗低下头,大口地抽烟,不时被呛得直咳嗽。烟头时明时暗,他的心在挣扎,他觉得自己如同在水里沉浮。这时候,他突然发现自己的皮鞋很脏。上面不光有灰尘还有不知从那沾上的泥巴,这让他很沮丧。脚不由自主地伸到了茶几下面。
老板眯着那双小眼睛盯着王朗,王朗把烟抽完了,两只脚在茶几下使劲地绞着。沉默了好大一会儿,时间似乎凝固了。挂钟突然打破了宁静,响了十下。王朗终于鼓足勇气站起来。他刚打算开口,老板的嘴唇动了,“王朗啊,你再好好考虑一下。年轻人嘛,一时发热,我是理解的。放心,我不会放在心上的。”
“那,那我先出去了,古总。”王朗盯着脚上的皮鞋,有些窘迫。老板挥了挥手,王朗赶忙走了出去。
一出门,王朗感觉自己的身子有些发飘,他没有回自己的办公桌,而是到了楼道里的电梯前。他刚摁了下楼键,电梯门就开了。里面有两个面无表情,西装革履的中年人。他们手里都拎着同样的黑色公文包。中途又上来几个人,都是一进来用目光在众人脸上扫一下,然后垂下眼睑,面冲电梯口。到一楼的时间很漫长,一到王朗就第一个窜了出去。电梯里的空气有些稀薄,他觉得自己快窒息了。穿过一楼大堂,王朗站在了楼前的台阶上,长长的吁了口气。天色不知何时开始阴沉。大街上依然热闹,车水马龙,人来人往。那些混杂的声音如同利剑一般刺进王朗的耳朵,王朗突然失聪了。他捂住耳朵揉揉,使劲眨了几下眼睛。才恢复了听力。他感到额头几丝冰凉,雨落下来了。手机随后响起来,是同事的电话。问他在哪儿呢?王朗回答在洗手间。电话那头的人让他赶紧回办公室,公司有重要的会议要召开。王朗答应着把电话挂了。
“这狗日的天气。”王朗走进写字楼时,心说。
到了电梯口,王朗又踅身回去,来到一楼大堂。在免费擦鞋机前把皮鞋擦得锃亮。当他再来到电梯口,一楼的显示灯亮了,王朗吹着口哨,闪身进了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