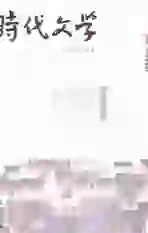用史笔写成的小说
2011-12-29山东黔首
时代文学·上半月 2011年2期
笔法
我一直认为,司马迁和陈寿是中国最早最好的小说家。《史记》、《三国志》,篇篇都是生花妙笔。把读者诱进你创造的文字里,让他们为你的抑扬顿挫而心潮澎湃,为你的人物命运而揪心,这样大家就成了你的创造的参与者。只有这样的文字,才可信赖,才值得一再咀嚼。
虚构即真实,真实亦虚构——你写的真实对于读者来讲是陌生的,关键是你能不能让读者哑口无言——这就是写作的秘密所在。
近读邢庆杰的小说《透明的琴声》和《像风一样消失》,我总将他笔下的人物和他的写作方法跟古典对比。这不是褒奖,这只是我对他写作的一种理解。对于他的文字,我的这些言说只能是增加一个阅读的视角而已。
邢庆杰是以写小小说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但他的小小说一点都不小,比如《玉米的馨香》、《屠夫胡一刀》等,都是掬起一捧生活之水,酿造的醇酒,透明甘冽又劲道十足。他曾说“我把小小说当成短篇小说来写”。这句话比许多人的长篇大论还值钱,这是“两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后的心得,没真正玩味过小小说的人,说不出这样甘苦之言。因此到邢庆杰开始写短篇小说了,他又将短篇当成中篇或者长篇来写,就好像八大山人在一张上好的宣纸上,只画三两笔,几枝梅花或一只鱼鹰,留下大片空白,将你挂在空灵里。
《透明的琴声》、《像风一样消失》这两个短篇,逼真到生活态的叙写,构筑起老温、邹先生、傻小宝荒诞不经的一生,看后让人唏嘘不已。这就是中国普通小老百姓原汁原味的生活态,也是一个个小人物的心灵史。想把文字写好,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爱:爱生活过程爱那些人物。有时也恨,恨不能一拳就把他废了,可攥攥拳头,又松开了,心里说这也是爹娘生养的血肉之躯啊。这种纠葛让笔尖复杂了,饱满了。其实爱和恨是一种心理活动,不同的仅仅是脸部表情。
写小说,是附着了作者爱恨的人物牵着笔在纸上行走。《透明的琴声》里的老温、《像风一样消失》里的邹先生、傻小宝就是牵着作者在纸上行走的人:
“老温缓缓地从他那张旧办公桌后站起来,木然地看了我片刻,终于认出了我。桃核一样的脸上便绽出了几分笑……他那两只枯干的大手同时摸了摸旧中山装上面的两只口袋,然后急急地拿开,又摸了摸下面的两只口袋,整个人就定格了,少顷,他冲我尴尬地一笑,还不到发工资的时候哩。……算完账,我一摸口袋,竟然也没带钱,就习惯地从柜台上拽过一张包肉的草纸’拿起圆珠笔打了张欠条。……老牛又仔细地看了看我。忽然大惊失色道,你……你不是死了吗?死前还欠我三十块钱的酒钱呢?我脑子里忽然灵光一闪,分辩道,不对!我没死,死了的是老温!”
这是《透明的琴声》的开头,作者运用导入性语言将读者导入到他想写的故事里。作者倾注了爱意,入木三分地雕刻他的人物。核桃一样的脸、探了探身子、枯干的大手以及摸口袋的动作和顺序,这些不厌其烦的描摹是构成一个活生生的人物的基础。怎样导入就会有怎样的小说。从一开头能不能让读者为你的塑造的人物揪心。为你的故事废寝忘食,是一篇小说能否成功的关键。《透明的琴声》很好地做到了,就是那句“我没死。死了的是老温”,使得读者欲罢不能,只能乖乖地随着他的笔尖一直走,跟作者一起回味老温充满传奇的一生。
《像风一样消失》,作者想写的是傻小宝的故事,上来却冲着邹先生的医道和药鏊子下手,并且下起手来不厌其烦,津津乐道。就像吃正餐前,先来几碟小凉菜吊吊胃口。这几碟小凉菜就是闲笔,闲笔不闲,并且让闲笔在正笔衬托下变得摇曳生姿,荡出一片空灵的天地,这样的文字就有了绕梁三匝的劲道儿。好手笔是调和这闲与309a2117463d379944776414f5838753不闲的厨师。他从不怪食客的口味,他知道自己的手艺就是艺术。写作跟侍弄一桌宴席是一个道理,不下狠心去整,众食客就不会吃得盆干碗净。宴席上的菜肴就好比写小说需要的故事,而这侍弄就是功夫,就是小说笔法。缺一不可。
我将这两篇小说开头的一部分放在一起,是想说作者的笔法在同中也存在着差异。《透明的琴声》上来写一个梦境,看似虚写实则实写。因为这个梦就是作者观察老温的最佳角度。而《像风一样消失》的开头和《透明的琴声》正好相反,他用了传统文学中的传奇笔法。本来是实实在在的事情,却让一个药鏊子和一只受伤的狐狸弄得神乎其神,看似子虚乌有的事情,想想又在情理之中。
故事
小说是发现和创造之旅,不能只满足于把读者的眼泪从眼眶里掏出来。作品的深度就是作家的深度,走马观花的人不是作家,他甚至连阅读杰作的资格都没有。
《透明的琴声》是蘸着悲悯的血泪写成的,看似写了老温的一生。实则只写了他一生中具有代表性的过程,几种能够让老温跃然纸上的道具:劣酒、“毛找”烟、用信封装着的各屋里蹭来的茶。只是这些道具,如果没有二胡,文化站长老温只能是一个让人讨厌又让人可怜的人。有了二胡,他就不再是那个大院里可有可无的人,二胡的声音是大院里的一种风景,是老温命运的陪衬:
“星期天再赶上下雨时,乡政府大院里冷冷清清的,老温便乘了酒兴,一个人在屋里拉起来……有轻薄的人这时想讽刺老温几句,但刚一张口,便会引来一屋子人的怒目而视,老温也是一脸的庄重,完全没了平日的谦卑。他很投入地拉着,瘦瘦的身子随着曲子的旋律前后左右地摇晃着,很陶醉,连他脸上的皱纹都有些烁烁放光。”
二胡把老温的一生串起来。手术后的老温,乡政府不再安排他什么工作,他就整日拉二胡。我想老温可能不再拉《春江花月夜》了,只能一遍遍地拉《二泉映月》。闭着眼,什么也不想,仿佛听见了瞎子阿炳的琴声在一个个胡同口徘徊。这时老温的二胡和阿炳的二胡已经融为一体。作者虽然没有点明这些,而从他的文字里,却能够体会到老温最后的心境:
在一个月光如水的静夜,老温的琴声飘出了屋子,飘出了乡大院。……看门人老张的那条杂毛笨狗在月光下扑来扑去,笨重的身影和着那琴声竟有了几分韵致。忽然,琴声戛然而止,狗疯了般在院子内奔跑着、狂吠着,一直折腾到天亮。才虚脱在乡政府门前。
有人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如果作者仅仅写了我上面分析的老温,那么老温只能是一个让人怜悯的人。不够全面。这个小说的高潮,实际上是老温代理乡党委办公室秘书以后,不再喝“二道子茶”,不再抽“毛找”,喝酒,档次也有了质的提高:
……老温平生第一遭尝到了被重视被尊重的滋味,更加深刻地感受到文化站和党委办公室的天壤之别。……在那一段难忘的时光里,老温整天像生活在梦里,感觉到不真实时,他就咬一下自己的胳膊。让疼痛来证实幸福时光的真实存在。
当更大的喜讯——给他们这一批文化站长“转正”——降临时。老温却将自己提早“转正了”——他在“工作单位”一栏里填了“××乡党委办公室”。这个让老温魂牵梦绕的“乡党委办公室秘书”的位子,却成了压倒他的最后的一根稻草。
这就是老温的故事。读者在掩卷唏嘘之余,陷入对人生无常的思考,这种思考使得这个小说的外延越来越丰富。也具备了让读者再创的可能。这就是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里说的把小说讲成“悦耳的旋律,或是对真理的领悟”的又一例证。
《像风一样消失》是邢庆杰又一篇佳作,张元珂在评价这篇小说时说过一段透彻的话,在此引用。我就不赘言了:
“精神失常”的傻女人和傻小宝,鬼使神差地产下一男婴,一时打破了原有的乡村秩序,“傻”与“不傻”的界限因男婴的诞生被打破。邹先生以其高超的医术救活了傻小宝,唤醒了傻女人,结果却是,前者自愿绝食饿死,后者无影无踪。邹先生医术高超能救活人的肉体,却无法拯救病痛中的灵魂——这受血脉亲情支配的痛苦灵魂,这是谁的悲哀?
这又是一个充满着隐喻意象的空间。药鏊子、撒在患者门前大街上的药渣、医治创伤的野狐狸的传说、村前的墓穴、傻女人及其孩子,一切似乎都没有确定的指归,模糊而又神秘,充满着无限阐释的可能,小说的意义空间无限敞开着。
性情
活到什么份儿上,作家就说什么话。没活到,硬说。也是白说。
在谈到这两篇小说的创作时,作者曾对我说《透明的琴声》是真人真事,开头那个梦也是真的。《像风一样消失》这篇带着鬼魅气息又有着匪夷所思情节的小说,他说:“也不是虚构,是从乡亲们讲给我的,我只是将这些道听途说的事情进行了精心的剪裁。”这话说得谦虚,即使是真人真事,小说哪能没有虚构?也许他故意忽略了自己的煞费苦心和随故事之形所倾注的悲悯吧。借小说的酒水浇自己胸中块垒,又将这块全消化成一腔血,喷洒出一唱三叹的文字。我想,这就是邢庆杰最大的性情吧。
好文字的性情必是孩童般得天真烂漫,文字fSwX3746w/KY1zY3yHzU7n0bYuy92l9ehYqU5DrhNPg=的天真烂漫就是人的天真烂漫。已届不惑之年的他,在我们去公园锻炼时,却常常能来几个前手翻,来一通旋风脚。虽然有些喘,可还是令我们这些臃肿的身子望而却步,毕竟我们都是些“奔五”的人了。他的功夫确实不错,玩到高兴了,就给大家演示演示擒拿手、扫堂腿什么的。在你还没缓过神儿来,他一趟短拳已毕,收式的庆杰紧攥双拳放在两肋,头向左甩,目光生寒,和大伙对上眼神儿了,又欻拉一下子升起一片桃红般的羞涩,两腮竟然还有浅浅的俩酒窝儿。他说练武跟写小说一样,熟能生巧,能生意味儿。他勤奋,又耐得住寂寞,写不出好东西来,反倒是怪事了。
邢庆杰更善饮,白的、红的、啤的,来者不拒,即使鸡尾酒也照单全收。饱满的杯子里盛着武侠、爱情、小人物的悲欢离合,一仰脖子咕咚咚灌下去,然后拍拍肚子,说全是故事和细节。必须有一个好胃,消化这些将要变成小说的故事和细节,像一盘磨,能磨棒子麦子,来了大盐,照样能磨成雪白的粉末。一个好胃口是性情的关键,能成大小仅是一面,又能成万物,才是一个好胃。这就是常说的文章既有广度又有深度。
有个诗人私下跟我说,庆杰有点儿像侠客,从文字里就能看出他的爱憎。我读他的文字。老是觉得他读了不少的武侠,比如《刺客列传》什么的。否则,他的文字不会流淌着侠肝义胆。他的主人公,怎么看怎么有他自己的影子,即使没有,也是他用爱憎的泪水浇灌出的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