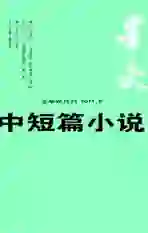子宫内膜上的息肉
2011-12-29王颖
星火·中短篇小说 2011年6期
芝云第一次见到孟超的时候,几乎连他是个男大夫都没有注意到。因为她吓坏了。
她手里拿着的心脏彩超单子上,赫然写着:
主动瓣膜反流(轻度)
三尖瓣反流(轻度)
左心室充盈异常
芝云闲着无聊的时候喜欢乱猜自己哪里有病,但从没想过心脏。她这么没心没肺、无牵无挂的人,心脏不用说是一流的。它每天都兢兢业业地跳动着,即使李桥说要和她分手的时候,也不过沉吟了那么一两秒钟,让她有了点不过是生理方面的头晕而已。要不是准备住院把突然造访子宫的一小块息肉割掉,她永远想不起来去给心脏做个彩超。当然子宫和心脏算不上啥直系亲戚,不过大医院么,总是很谨慎,她的主治大夫,一位五十多岁,依然精致漂亮的女教授,瞄了她一眼,就给她开了一连串的住院检查,血、尿、胸透、心脏彩超。
心脏彩超室在门诊三楼。走廊里堆着一群昏黄模糊的动物,是患者。每个人都噤若寒蝉,恨不得捧着自己的心。芝云事不关己地看着,冷酷地想:来不及了。
做彩超的是个五十多岁的男大夫,冰冷,岩石一样。他手里拿着仪器,看都不看她一眼,仿佛仪器就是他的眼睛,有它在看就足够了:“姑娘,侧过身去躺下。”
她乖乖地躺下了。
这个房间高大得不合常理,四周用薄透的帘子遮挡着。
她躺好了,医生仍旧不看她,仪器在她的身体上滑动了一下,马上停止:“把衣服褪到胸上。”
不知道是他在说,还是那个冰冷的仪器在说。
她迟疑地把衣服褪到乳罩下,那仪器紧接着又贴上来,冰凉粘腻。
“把内衣松开。”
芝云迟疑了一下,才确定医生说的“内衣”就是“乳罩”。她不情愿地反过手去解开乳罩的扣子,眼睛却不放心地盯着那薄如蝉翼的帘子。
忽然一阵风吹来,帘子徐徐地滑开了。芝云不由得惊叫一声。医生没说话,手中的仪器却用力一按,芝云不吭声了。此后那仪器就所向披靡。
芝云拿到单子,看不懂,只知道心脏有了问题。她听老人们说,心脏不好是很难长寿的。芝云是个立志要活到一百岁的人,所以一瞬间深受打击。她拿着那单子,几乎是哭唧唧地朝着病房楼走。上楼的时候她一阵心慌,腿一软,竟然扑倒在楼梯上,手里的单子呲啦啦弄皱了。二楼楼梯口是产科病房,一堆大男人都在那里等着,大概都是要当爹的人罢。有几个关切地走过来,问她是否要紧。芝云觉得大腿疼痛难忍,但慌乱中仍知道不过是肌肉受伤而已,忍痛站起来,道了谢,去找她的主治大夫,好像是要他还她一个公道。
芝云我本来是个要活一百岁的人,做了这个检查,梦想破碎了!都怪你!
但是医生办公室里只有孟超在。
她什么也不说,呆着脸把单子递给他。孟超拿过单子,第一个动作是把单子展平,扑打一下,把灰尘弄掉,然后细细地看。
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动作让芝云一下子安下心来。孟超看着单子,迟疑了一下说:“问题不大……你平常有什么感觉吗?”芝云带着哭腔说:“以前没有,做了检查之后就有了,胸闷,心慌!”
没说错吧?心脏有问题的话,是应该胸闷,心慌。
孟超好像笑了一下,说:这是小毛病。做宫腔镜不妨碍的,没问题。
芝云心里想:那么活一百岁有没有问题呢?
孟超又说:你不放心就去找心内科的大夫问一下。我觉得问题不大。你最近很疲劳么?
语气里有一丝安慰的意思。
芝云点点头,想:失恋……如果失恋算是一件疲劳的事情的话。
孟超打开电脑:来,让我们看看你其他的检查结果。
她放下心来,才开始打量孟超,发现他是个雄性。大概三十多岁?比自己大一点的样子,不过男人的年龄,也真是说不准。头发有点卷,皮肤很黑,但是很干净,嘴巴很……很充盈。该死的充盈,难道这不是一个优美的词?可是左心室“充盈”,听起来着实不那么美妙……看他的样子,应该是个住院医生吧?
更重要的是,芝云准确地嗅到了他身上未婚的味道。
至于这味道到底是什么,芝云是说不出的,但她知道自己的鼻子永远值得信任。夹杂着找不到发泄口的荷尔蒙味道?忧伤的,刺鼻的,酸涩的?对,就是这样。
检查结果找到了,芝云凑在一边看,血常规也不标准,白细胞低了。
孟超又一次扭过头看着她:怎么回事?
仿佛忘记了自己才是医生。
芝云摇摇头,自嘲地说:年纪大的缘故?
过了三十岁芝云便喜欢做倚老卖老状。其实何须如此着急。
孟超仍旧很平静地说:现在的人压力大,很容易出各种问题,亚健康。不过做手术是没有问题的。明天做可不可以?
芝云说:当然可以。
孟超说:那么我们需要签一些字。你家属来了吗?
芝云说:我没有家属。我自己签字。
孟超为难地拿着几张纸站在那里:这样是不符合规定的。
芝云正在犹豫,女教授一阵风地走进来,交代孟超:2床是子宫内膜癌,下医嘱吧,子宫全切,明天做。
女教授后面跟着一个男人,四十多岁的样子,头发油乎乎地,脸上居然还挂着笑。但一看就知道,那笑容不过是惯性,此时夹杂着震惊和晕眩,看起来格外凄惶。
孟超转身坐到电脑前操作,芝云听见他轻轻叹了一口气,但也许只是吁了一口气而已,谁知道。
女教授转身看见芝云,问道:检查结果都出来了?
芝云点头,孟超腾出一只手把病历递给女教授,女教授粗粗一翻:行,没大问题,明天手术。
芝云指着心脏彩超的单子给她看。女教授轻描淡写地说:没事。
噗通,芝云的百岁之旅重新起航。
芝云走到走廊里,拿起手机翻看联系人,在李桥和母亲之间犹豫了一会儿,打了一个电话:妈,麻烦您到医院帮我签个字好吧……
等妈来的时间里,芝云把表格其他部分都签了。孟超和她并排坐在一起,给她细细解释手术有可能造成的后果,宫颈受损、静脉栓塞……芝云根本没有听。孟超的声音软弱而犹疑,断断续续。婚姻状况那一栏她在未婚那里打上勾,孟超的手指伸过来,在那一栏里犹豫地停留下来。他的手指像大部分的大夫那样,干净,修长,秃秃的指甲。芝云听见自己说:喔,这个,没关系的。于是那有着秃秃指甲的手指就沉默地缩了回去。
“没关系”的意思当然就是“不是处女”。甚至在李桥前面她就已经不是。大学时候和第一个男友夜晚出去约会,就在学校浓密的树林里,男友激动地在她身上上下摸索,不得其法地挤压来挤压去。恋爱过的人都知道这是平淡无奇的,有点奇怪的是回到宿舍她发现内裤上有血痕,还以为是例假提前来了,赶紧去买卫生巾,但卫生巾只用掉了一张。当时也辗转反侧来着,此后的十万八千年都想到,怎么给这个人交代,怎么给那个人交代。但很多年过后,芝云知道这不干地球上任何其他人的事儿。李桥倒是问起过,她不耐烦地说早忘记了。
妈打电话说路上堵车,芝云告诉了她病房地址,要她来了签字就好,她自回自己的小家收拾住院用品去。收拾好简单的用品,她准备洗个澡。脱衣服的时候吓了一跳,大腿最显眼处好大一块青紫,楼梯那一跤的辉煌战果。看来,当时她全身的毛细血管都沉浸在心脏出了问题的震惊之中,毫无防备,所以一摔跤,毛细血管们猝不及防地砰砰砰,全部碎裂了,就像一个烟花,还没准备好,就开放了。
洗澡的时候她仔细地看着自己的肌肤,肘弯和脚踝都该去角质了,看起来皱巴巴有些发黑,但时间似乎来不及了。她悻悻地擦着身体,万般不甘心,最后还是拿起去角质膏,细细地磨起来。忽然她觉得,她对自己的身体要求这么高,不像是要去手术,倒像是去偷情。她几乎有点不好意思继续磨下去。
当初第一次带李桥到自己的小房间,本意不过是要把关系往前推动一小步,但李桥显然是准备跨大大的一步。他抱着她一步步蹭到床边,腾出一只手,把她小床上几乎多半个人高的熊熊扑哧扔在地上。他的嘴巴紧紧地压住她的,没有缝隙,芝云几乎要窒息,要命的是,此时脑子里想的,却是早晨穿袜子的时候发现的,脚指甲缝里的一块泥巴。上班要迟到了,来不及处理,这会儿那泥巴就开始阴魂不散。芝云勉强应酬了一会儿,到底在泥巴前败下阵来,拼命推开李桥,跑进了洗手间,关上门发了一会儿呆。待脱下袜子,那块泥巴却根本无影无踪。芝云坐在马桶上,莫名其妙地大哭了一通。
芝云提着大包小包回到病房楼,先到护士办公室报到。有几个老太太在那里,捂得结结实实,头上带着明显很假的假发,各自由自己的老头陪着。老头们扛着水壶盆子被子们,很齐备。一个护士从外面进来,亲热又嗔怪地和她们打着招呼:“怎么回事,又来啦!”扭头看见另外一个:“怎么你也又来啦?”“又来了”的这些老太,有一个笑嘻嘻地,另外几个都木着脸,但看起来也都不怎么哀伤。
报完到,芝云径直去自己的病房,六个人的大间没有住满,但每张床上都坐着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说说笑笑的,看起来热气腾腾,倒像是家庭大聚会。芝云的床上躺着一个彪形大汉,见状赶紧站起来。芝云笑笑,拿出自己的床单和枕巾铺好。旁边床上的胖老太太说:一个人来的?这是俺儿,有事就指使他。
彪形大汉温顺地笑,一瞬间从老虎变成hello kitty。芝云连连点头。老太太又说:咱这就是有缘分。不生病还没这缘分!芝云觉得缘分这个词虽然恶俗,但有时候确实值得琢磨,于是笑纳了胖老太的说法。
她几下收拾好了东西,拿起水壶去热水间打水,孟超正站在走廊里,和一个女患者说话。
走廊空荡荡地,只有他们两个人,刚刚拖过地,湿漉漉的消毒水味道。芝云这才发现孟超是个瘦高个,背微微驼着,简直伶仃,如果不穿着白大褂,看起来倒更像个病人一些。
芝云从他们身边走过,女患者仍在絮絮地问个不停,大致是手术后多久才会干净,孟超仍旧用那软弱的声调断断续续地说着:血出完了会有血水,血水完了会有黄水,干净怎么也得半个月。
芝云偷偷地笑了。
听起来好像他亲自经历过一样!自然,写犯罪小说的不一定要真去犯罪,治癌症的大夫不需要真正得癌症。但孟超煞有其事的样子还是让芝云觉得十分好笑。
病房里有一个农村来的姑娘,20多岁,得的是盆腔肿瘤,良性的,长的有一个海碗那么大了。早就做完了手术,马上就要出院了,父母都是农村的老实人样子,一直陪着她。仿佛是故意做给芝云看的:这一家三口真是和睦。三个脑袋凑在一起有说不完的话儿,时不时嘎嘎地笑起来。半夜里爹娘轮流起来给女儿盖被子,女儿起夜,当爹当娘的都巴巴地跟着。
昨天夜里芝云睡不着,看着他们一家三口出去又很快回来,窸窸窣窣地都睡了。芝云对着自己眼前那浓密的黑暗默默地伤感了一会儿。她想起孟超有点微卷的黑发,干净修长的手指。当然芝云知道,想谁也是没有用的,自己的问题只能自己面对,任何其他人都只不过是人生的工具。彻底绝望之后才是平静。好在那些彻底的绝望都已经超额完成,现在的芝云非常平静。
但是,他会参加手术吗?一定会吗?但愿他感冒,或者忽然睡过头了。芝云知道自己的肉体远远不够完美。
第二天一早,母亲来了,居然还带着自己20多岁、娇艳如花的继女,芝云名义上的妹妹。母亲和芝云关系淡漠,倒是和继任丈夫的女儿关系处得不错,常常一起逛街吃饭。芝云从不嫉妒。和母亲生活十几余年,她早就视与母亲相处为畏途,有人肯陪伴母亲,那是求之不得。芝云成年父亲才去世,她还算有一个健全的青少年期,该得到的爱勉强也都有,现在是自己寻爱的时候了。母亲再组的家庭完满自足,所以芝云格外自觉地和母亲远一些再远一些。
当然芝云有时候会觉得四周的虚空比别人更大一些,以她自己的力量填不满,尤其是黑夜。她有一张小床,床上躺着她所能买到的最大的毛绒玩具,一只熊。她就喊他熊熊。黑夜她躺在他的臂弯里睡觉,温暖,无害。自从李桥常常造访她的小房间,熊熊常常被他粗暴地扔在地下。事后芝云会爱惜地捡起他放回原来的位置。李桥不比熊熊更必要,更充分,从开始她就明白。
母亲掏出两张购物卡,问是不是需要给大夫红包,一千够不够。继父是个有实权的官,想必这些购物卡之类是不缺的。然而芝云很感动,赶紧拒绝,连说不用。
不过是一个子宫。她很爱自己,但对这个世界的感情也就如此而已。她没想过要孩子,所以,子宫只要不妨碍她的存在就够了。要不是大夫说息肉有百分之零点几的癌变率,她才不想要做这个手术。
但做了也不错。不错只是芝云的预感,以后也许会有答案,也许没有,都可以。
担架床在外面等候,病房里的男人一并避开,芝云手忙脚乱地脱下自己的衣服,换上病号服。邻床的小姑娘提醒她,病号服里连乳罩内裤都不能穿的。芝云愣了一下,只是一个宫腔镜,至于吗?芝云很不情愿地脱下乳罩和内裤,用干净袋子装好。她是一个小小的A罩杯。
李桥对她的A罩杯很漠然,从不评论。芝云有一次看他的电脑,发现他存了大量的艳女照片,胸前的肉块一个比一个庞大。她嘲笑他的恶趣味,他却一时丧失警惕,推心置腹地说,乳房太大了也不好,重要是质感。其实对男人来说,B罩杯足够了。
这句推心置腹的话让两个人冷战了一周。后来李桥发表了长篇大论的对A罩杯的赞美,才重新占领了熊熊的位置。
现在大概他手里有一对B罩杯了。芝云想。求仁得仁,芝云甚至替他满足了那么一下。
躺在担架床上,看这个世界的角度骤然改变。妹妹垂下头亲热地握住她的手,问她害怕不害怕,柔软的长发垂在她的脸上,香水味儿一阵一阵地飘过来,她忽然后悔忘记洒一点香水在身上。当然,对一个要做手术的人,这种感觉着实有点过头。芝云不好意思地舔了一下嘴唇。很干。从昨晚十二点开始,她就被禁止进水进食了。
担架床走过长长的病房走廊,进了电梯,又吱吱呀呀地走进通向手术室的走廊。走廊两侧站满了等候的男人女人,一张又一张倒置的脸从眼前飘过,十分怪异,像是某部故弄玄虚的滥电影。苍黄的脸,白皙的脸,明亮的脸,暗淡的脸。湿漉漉的黑树干上花瓣朵朵……谁的诗?庞德。这个老头子死了很久了,然而她还活着。
这些脸都看着她,仿佛看着一具尸首。她忽然觉得有点怕了。
都说人死之后会通过一个长长的通道,终点光明,而四周黑暗。那么现在大概就是彩排。走上它几次,就可以开始那永恒的末日旅途了。
咣当一声手术室的门被撞开,有人吆喝着:“家属不要进来了!”母亲和妹妹的脸像潮水一样退下去,不见了。
现在,头顶上是电视里常见的那种硕大的无影灯,周围一群杂乱的人,统统用帽子和口罩武装着,他们口齿不清地、乱糟糟地聊着天,仿佛她是隐身人。各种工具和陶瓷托盘碰撞着,那声音真是寒冷。某个人嚷嚷着:俄罗斯机场被炸了!死了35个人。芝云想,死的这些人里面,不知道有没有人子宫内埋伏着息肉,那么,就和子宫,和心脏,和四肢,和头颅,一起从这个世界上消失吧。世界就是一个屠宰场。
忽然芝云的魔法消失了,有人看见了她,大声命令她脱掉衣服,从担架床上移到手术床上去。芝云愣了一两秒钟,哗啦脱下裤子,爬上手术床上,把两只脚高高搭在架子上,这个姿势像是被仰面翻过来的青蛙。又有人命令她脱掉上衣,她本能地护住,迷茫地看着四周。有人伸过手来,一把扯掉她的上衣,给她静脉注射。她绝望地想着,A罩杯,A罩杯。那么,孟超在吗?
仿佛孟超就住在她的脑子里。她听见孟超那断断续续的声音从一片忙乱中响起:大腿上的淤青怎么回事?
奇怪地,芝云放松下来。她微微一笑说:家暴。
孟超的脸忽地出现在她的上方,一双眼睛在口罩上面惊疑不定地看着她。
“完了,这人真是一点儿幽默感都没有……”
麻醉面罩扣下来,芝云不再抱怨了。
后来翻着那惊人的账单的时候,芝云看到:全身麻醉,900块。
哈,不错,九百块买来一段生命的空缺。但她似乎又明明记得一个梦,一个最深的梦。
仿佛是在世界尽头,化外之境。景深处是巨大的火山,赤红色的岩壁。一个个巨大的丑陋的、仰面朝天的女人体,土黄色的乳房,浅黑色的乳房,乳头也是各式各样,绛紫色的,粉红色的。阴部有着各种各样丑陋的皱褶。一个很小很小的男人站在下面,缩成一团,看不清相貌,没有任何行动。但不用说,那人是,孟超。
芝云清醒后已经在病房。担架床刚好走到自己的病房旁边,母亲和妹妹扎撒着两只手,不知道怎么办,她挣扎着自己往病床上挪。倒是邻床小姑娘的妈妈跑过来,力气很大地把她连抱带拖地弄到病床上,这才躺妥当了。麻醉的劲儿还没过去,芝云只觉得自己仿佛在云山雾海中,但总算还记得连连道谢。
这一天芝云昏昏沉沉,睡了又睡,但她知道孟超一直未来病房。
第二天一早,女教授带着孟超来查房,在芝云这里只有简单的停留,问出血量多不多。孟超几乎没有看芝云,只顾在本子上记录。芝云知道那躺在手术台上的姿势有多么丑陋。
一行人随后走到要出院的姑娘那里,女教授让孟超看看女孩儿的伤口愈合怎么样,是否可以拆线。孟超在女孩儿的肚子上细细地又摸又看,说下午拆线应该没问题。女孩儿高兴极了,连声说:谢谢王大夫!谢谢孟大夫!
那声音真是清脆。到底是二十几岁的女孩子,即使生了病,还是脸色红润晶莹。芝云知道自己的脸色本来就惨淡,更禁不住手术一次。自己二十多岁的时候在做什么?和堂吉诃德勇斗大风车一样,和绝望做斗争……一直到脸上的红晕和色泽被榨干。
孟超从她的床前经过,总算停住,对她客气地微笑一下。
可是这个微笑让芝云几乎一下子偃旗息鼓。她灰心地把头埋在被子里,想如果睡过去会好一点。可是麻醉劲儿过去了,芝云今天格外地清醒。
也就格外悲哀。
昨晚芝云就让母亲和妹妹都回去了。她已经能吃能动,自理没有问题。给她来打点滴的是一个和她年纪差不多的护士,说不上多么漂亮,可是声音柔媚:“这个药刺激血管,速度要慢点。”说完对着芝云微微一笑。
芝云自己拿着液体上厕所,远远看到孟超和女教授站在医生治疗室门口。孟超说着什么,女教授拍拍他的脑袋,亦师亦母的样子,不,不仅仅是亦师亦母。还有撒娇。有一次芝云偶尔看到过母亲向继父撒娇,赶紧走开了,觉得惨不忍睹。但当事人是开心的,那就好。看客算是什么?
走廊里游逛着各式各样的病人,年轻的,年老的,胖的,瘦的。这一具具的肉体都会用那个丑陋的姿势被摆放在手术床上,褶皱的皮肤,有鱼鳞网纹的干燥皮肤,脱屑的皮肤,各式各样的阴部。看过这些之后,还能爱娇一下的话,那真是令人佩服……或者说正是看过这些,才格外要撒娇一下,对不对?
回到病床再躺下的时候,芝云就已经很平静了,甚至有点开心。她用一只手打开床头柜的抽屉,拿出阿加莎的书,心无旁骛地读起来,看,世界充满了阴谋和谋杀,但阿加莎笔下的谋杀总是那么的直率单纯,令人向往……直到另一床的女人提醒她,液体滴完了。
是的,液体滴完了。
三天后芝云出院。孟超给她交代出院后的注意事项,照旧是用那种犹疑不定的语气:“如果出血严重,要来医院复查。一个月后要来医院做彩超”……停顿一下,他说:“近期不要有性生活。”
孟超说到“性”的口气非常奇怪。是,他们一定是习以为常了,性就是生理,和左心室充盈异常、子宫长了息肉一样,都无非是生理。但他说的时候好像非常厌恶,说完了要弹一弹身上的灰一样。
芝云微笑不语。孟超也就继续说下去:息肉的病理结果要五天左右出来,到时候你可以来医院查看。
芝云平静地问:你们没有电话吗?
孟超犹豫了一下:办公室电话一般不给患者留。我,到时候我给你电话吧。
芝云说:谢谢。
两天后芝云接到孟超的电话,告诉她息肉果然只是一个息肉,排除了癌细胞。虽然是意料之中,芝云还是很开心,道谢之后忽然异想天开地说:要不要一起去看个电影?
电话那边忽然无声无息,骤然黑屏。声音再响起来的时候,又是断断续续地,孟超说:你刚手术完,要好好休息一下,以后有机会再看电影吧。
挂了电话,芝云甚至笑了一下。那么好吧,好好休息。芝云统共请了一周的假期,还有两天可以用,48个小时,自己和自己在一起。
朋友送了一只乌鸡来,芝云就用这只鸡煲汤,加了红枣和枸杞。芝云在厨房里甚至快乐地哼起歌来。
两个月之后,春天来临。空气一点一点热起来,感觉更为逼人。一个周末的夜晚,芝云忽然很想出去走走,要去人最多,最拥挤的地方。
她去了最繁华的步行街。还好,人够多,川流不息。芝云买了一只冰淇淋,坐在路边的藤椅上慢慢地吃。路灯太亮,月亮完全看不见,没有一颗星星。高楼粗鲁地伸到天空的深处,像是某种远古时代的凶猛生物,生硬,突兀,蠢蠢欲动,富有侵略感。当孟超在这样的天空下,慢慢走过来的时候,芝云还以为是幻想,是梦。人流和噪音疏忽变得模糊,而只有这个人像梦游一样走过来。他没有穿白大褂,普通的夹克衫牛仔裤,歪歪的背着一个背包,眼神是了无生气,夸张点说,几乎是奄奄一息。
芝云本来可以把他放过去,让他像任何一个陌生人那样从她身边滑过。事实上,他就是一个陌生人,一个离得越远,越安全的陌生人。然而在最后一刻,她的身体还是忍不住准备跳起来。可是,毫无征兆地,在最后一秒钟,孟超转过脸来停在她的面前,准确地喊出她的名字:李芝云。
芝云完全是应急反应:对,是我。
孟超笑了一下,两个人一时无话可说,还是孟超提起话题:你喜欢吃冰淇淋。
芝云笑了。
孟超迟疑地说:我请你喝杯东西吧。
从此芝云又算是有了男友,或者说,男性朋友。芝云不是很拿得准。
有一次两个人走路,大概是去看场电影,或者吃饭,芝云忘记了,她只记得孟超忽然转过脸来对着她微微一笑,好像有什么秘密要和她分享。
芝云最喜欢这个角度看过去的孟超,有一点孩子气的英俊。
孟超说:喂,你这个患者。
芝云答道:听着呢,孟大夫。
孟超说:今天天气真好,我们谈个恋爱吧。
芝云笑着说:听大夫的,我没意见。
孟超就来拉她的手。芝云发现他带着皮手套。她停下来,把他的手套摘下来,把自己的手放进他的手。
孟超有点抗拒:天气冷。
芝云说:都春天了。我也没有带手套呀。要不,我们一人带一只。
芝云戴上他的手套,里面很温暖,但奇怪的是很干燥。她把另一只手放进他的手心,那里开始微微的出汗。
芝云悄悄地笑了。
孟超家也在本地,父母健在,不过他不喜欢回家。夜晚、周末或者值夜班的白天他往往赖在芝云这里,但从不过夜。芝云有时候加班,出来的时候常常看见他站在某根电线杆或者路灯下面。他和它们看起来一样单调,一样无辜,影子笔直,沉默。他不太爱说话,似乎没什么朋友,但是很喜欢做饭。他值夜班的时候,芝云下班回家,厨房里总是做好了两菜一汤,像是田螺姑娘来过。芝云打电话过去,喊他“田螺先生”,孟超总是好脾气地笑着说:乖啊,在上班。
芝云再也没去过那个病房楼,那个湿漉漉的带着消毒水气息的走廊。想起做手术的那几天,恍若隔世。她甚至再也没去过医院。有一次她浑身不舒服,请假在家,孟超下班后来看她,开门的时候她就哭了。真是矫情。这样的日子过了许久了,何必今日才哭。但她忍不住。
孟超看嗓子,量体温,安慰她不过是感冒,然后下楼为她买药。芝云躺在床上等着孟超回来,把被子蒙在头上,一片温暖浑浊的黑暗。还是小姑娘的时候她就喜欢这样,黑暗里有无数的秘密和故事。她觉得幸福极了,心满意足,想要在那一瞬间就彻底结束,死掉。
但孟超似乎不喜欢肢体接触。有一次他在芝云房间聊天累了,随便往床上一躺。芝云走过去,把熊熊抱下来,放在沙发上,然后在孟超的臂弯里拾掇出一片地方,让自己舒服地躺上去。孟超不说话,但是身体变得很硬。
芝云闲闲地说:喂,亲爱的,你是同性恋吗?
孟超不满地说:喂,你这个患者!
芝云嘿嘿地笑。
孟超语焉不详地说:不喜欢这个,不能证明我就喜欢那个。
芝云扳过他的脸,问:那么你确定不喜欢女人?
孟超不吭声。
芝云说:就因为她们会长息肉,会流血,会有各种各样的炎症?
孟超拒绝回答。
芝云说:吻我。
孟超像个父亲那样吻她,宠爱,但只是宠爱。
这日已经很晚了,孟超在外面敲门,进来的时候很反常地没有先去洗手间洗手。脸色通红,浓重的酒气。芝云很吃惊,因为从未见他喝过酒。
孟超把自己四仰八叉地放在床上,看样子不准备解释。
芝云端来蜂蜜水,孟超却不肯喝。把她拉过来,吻她。他的舌头因为酒精而僵硬,或者,仅仅是因为很久未接吻的缘故。他解掉芝云的衣扣,几乎是恶狠狠地蹂躏着她的乳房。芝云以为自己早就放弃了这种渴望,但原来不是。她躺在他的下面,被热火炙烤着。晕眩中她听到孟超切齿说:这不过是一大团乳腺组织。
芝云几乎笑起来,又觉得难过。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孟超开始大声地喘息,筋疲力尽地轰塌在她的身上。芝云发现没必要说了,因为孟超几乎是立刻打起了酣。
芝云把他仔细地放好,坐起来,等着心里的火山慢慢地安静下来,熄灭。
后来芝云才知道那晚是女教授请客,她评上了博士导师,孟超可以直接考她的博士了。
也许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也许不是。但显然孟超不准备和她分享。
孟超和芝云的婚礼上,母亲竟然送了两万块的红包,芝云很吃惊。女教授看见她,好像有点想要认出来的意思,红唇夸张地张成一个O型。她主动地殷勤地低声附耳说:内膜息肉。女教授恍然大悟,哈哈大笑。
是的,真是够可笑对不对?
不久之前他们刚刚有了一次成功的性生活。孟超终于愿意把他放到她的里面,芝云非常满足。孟超几乎刚刚进去,她就迎来了高潮。她被疯狂的气流顶到高空,母亲,熊熊,李桥,都在那里等待着她。她和他们轻飘飘地说着hi,说自己很好,一切都很好。人生这么短,难道这已经不够好?世界忽然爆炸,一切都化为粉尘,寂静一片,亘古横荒。
一个很深的梦。几乎可以和那次花费九百块的麻醉相比。
芝云微笑着说:九百块。
孟超说:什么?
芝云说:没啥,咱们去洗个澡吧。
(责编:杨剑敏电子邮箱:yjm196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