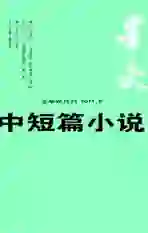赌徒的老婆
2011-12-29杨云香
星火·中短篇小说 2011年6期
1
我不知道怎么说好,蹲在窗台根儿下发呆,草泥墙发出苦味,直冲鼻子。木头窗框裂歪了,风一吹,飒飒沙沙,露出玻璃边,积了黑乎乎的烟灰。我偷觑娘,她仍在哭泣,几绺头发散落在枕边,一抖一抖的,泪水湿了半边枕头,白色的褶皱,已经暗了,灰吞吞的。被垛板下啷当一截棉裤腿子,磨破了边,毛刺刺的,像伸出来一只胳膊,袖起手,就要摸着娘的头了。
爹在西头石大骡子家看牌,昨儿一宿没回家,这是常事。雨水一过,眼看要种地,没种子没化肥没钱雇牛具,爹才不管这些呢,钻头不顾腚地耍,娘说他要烂肠子了。偏赶这时,北屯的侏儒表舅来要钱,一年也不怎么来往,娘诧异得手都哆嗦,颤着音儿问:“大哥,他爹啥时拿的钱?”表舅阴了脸:“去年腊月,大丫头得急病那回啊,这才几天,你咋还不记着呢?”娘茫然地瞅我一眼,我一激灵,忙低了头,狠劲揪小辫梢子。表舅冷眼瞧了娘一会,尖着声音:“我刚卖完苞米,一万块钱还没捂热乎呢,你家大研究急火火地奔我去了!说好五天还,都快五个月了,这可咋好?”他噗噔出溜下炕沿,转磨磨,搓得手指节咔咔响。娘脸色煞白,嘴唇发青,神经质地抖个不停。从过年到现在,莫名其妙来家要账的多起来,加起来五万、十万,有二十来万吧。这个家一年到头,靠地里粮食出钱,娘养猪养鸡卖菜仔,出点零星用,全算上不超过两万。这么大窟窿张着,就像棉袄里的虱子虮子,挤成堆,起篓子了,肆意咬人,就不觉得疼了。
表舅愤愤地走,身子一挫一挫的,小地缸一样,歪头吐唾沫,啪啪响。娘面无表情,眼袋膀肿着,天热没脱下去的棉裤腿褶皱成罗圈,蹒跚地往院里移动。小园子积雪化尽,垄沟垄台土质细腻,被风抽得酥软,鸡爪子鸭巴掌猪蹄子痕横七竖八,天书般陈列。我小心地跟在她身后,还没开门,她回头厉声说:“去叫你爹,快点死回来!”我扭身往外跑,木栅栏门边支棱出碎屑子,刮着了,手背上蹭出一条口子,鲜血直流,使劲捂着,朝屯西头奔来。秸秆棍儿在路上摊着,老黄牛慢悠悠地嚼苞米叶子,车辙印里汪着稀泥,被人和牲畜们搅和得肮脏凌乱,人得溜着园子边走,还干爽点。后趟房的人家有出丧事的,老远看去,人头攒动,偶尔,传来哀号声,像风一样,呜呜叫着,飘远了。韩家大狗冷不丁窜出来,冲着我吼叫,汪汪汪,汪汪汪……我堆碎在墙边,一动不动,它也不敢冲上前,我要跑,它准扑上来,狗就这样。直到房子里走出人,大鹅嘎嘎叫开了,它才悻悻地缩身子,跑回院里。我挪着不好使的腿,瞅不清前边的道了,泪眼模糊。我家在屯子东头,东头的赌博场子里时兴推牌九,开拖拉机,拔大点,输赢快,码子大,大手云集,寒夜里赌场周围有望风的,鬼魅般阴森。西头看纸牌、打麻将,输赢慢,浑浑噩噩捱时辰,钱章子少,聚集着小手、穷鬼、损贼和浪荡之徒。爹是长年累月,两头都占。钱多时,呜嗷喊叫、耀武扬威;钱少了,埋头扎进西边,匍匐几日再说。屯子中间一条大道,南边斜插进泥河,分头发缝一样,分开村子里五趟房,东头西头,泾渭分明。最后一趟房连着大地,大地坡似的向下蔓延着。老远看,村子像一个破草帽,扣着脑袋,却裸着前奔儿头后勺子。
石大骡子家在村西头,最后一趟房,放眼撒眸,两间土屋,歪歪斜斜地趴着,房顶草暗灰色,一片片被风掀起来,起窝漏洞,像脱毛的狗皮。爹就坐在他家西屋炕上,左手握牌,一把接着一把,没完没了,腿弯处,有个掉漆的白茶缸,里面装着苞米粒,哗哗叫唤,那是赌码子。石大骡子,豹眼,卷毛头发,沙哑着嗓子,一股刺人的膻味,有房顶那么高,走道喇叭着腿,人们都说他是杂种的,就像马和驴子交配,生出骡子一样。他家东屋有两伙麻将,他老婆围着黑绿的头巾,小眼睛滴溜乱转,专门伺候局儿,我挤进去,她厌恶地挡住西屋门,怪声怪气地说:“找谁?”“找我爸,我妈让他快点回家!”我怯怯地说。“快了,你爸一会儿就回家了!你走吧!”说着,她就伸出粗壮的胳膊,眯着眼,往门外推我。出了门,我气喘吁吁跑回家,告诉正在喂猪的娘,她手里抓着一团猪食,猛然用力,葫芦瓢里传出唧唧声。接着,一趟、两趟、三趟,第七趟时,斜阳在天边滑动,村里的烟囱们纷纷鼓出炊烟,我徘徊在石大骡子家窗台下,一个十六岁的大姑娘,欲哭无泪,门挂了,讪讪地,无奈地,招摇地。
娘躺在炕上流泪,悲伤盘旋在屋里,灰尘静止了,苇席花子沉默了,黄昏凝固了,风儿变得柔和了。
2
淡淡的暗,薄纱一样弥漫过来,满屋子都是朦胧。灶台和大炕间竖着一面火龙,上边安木框子,镶一截玻璃,火龙通炕洞,日日走烟火,全家人倚着它熬过严寒。去年上冬,舅舅来家忙活一阵子,重新砌砖,清灰渣,选烟道,布置插板,里里外外抹草泥,糊上焦黄耐磨的牛皮纸,啪啪拍几下,直泛亮光,脸颊贴上去,暖流涌动,像一面厚实的脊背,踏实可靠。此刻,灶坑里火苗眨眼睛,馋嘴巴舌地东摇西晃,探出灶门瞅瞅,我没理它,塞一把苞米秸秆,没了声音,撅身子瞧,灶坑里火光聚成一团,一拱一拱的,锅底通红。水蒸汽就像一棵大杨树,腾腾地婆娑起来。我使劲掀开铁锅盖,小米和大米在沸水里翻滚,漩涡层层,吱吱响边儿了,拿勺子搅几回,看饭粒八分熟,操起笊篱捞饭。娘不知啥时站在身后,梳利索了头发,眼睛肿着,苍白着面色,麻利地撸袖子,抓一棵酸菜,在案板上咔哧咔哧切,细细的菜UXHBbV53U6NdczJwTaFzhm2Z39rxBeN7LbjEzac1Bxc=丝泄了气一样,一摞摞散下来。突然,她愤恨地说:“你爹就回来了,疼死他!”“咋?”我疑惑地看她,端一舀子米汤去后屋,准备熬猪食。门被咣当一声撞开了,爹勾着身子,脸更长了,胡子拉茬,咧着嘴,哼呀着,手捂肚子,跌跌撞撞进屋了。
爹在炕上滚来滚去,喊肚子疼,眼看着豆大的汗珠子冒出来,我急得翻抽屉捣盒子,找止疼片。娘拉长了声:“闺女,架火了!”我折回身,几步跑到柴堆前,往灶里送把柴,火舌忽地窜出来,我吓得一仰,扑通坐在地上,娘嘴角上翘,像是笑了。她一只手往锅里抖落酸菜丝,一只手握搅勺子,哗哗炒着,一股白烟携了油脂的香气顷刻间溢满屋子,继而,又淋上一瓢水,锅里的汤汁停了叫声。她随手够着了墙上的锅叉,担在铁锅壁上,把二米饭盆放上去,盖锅,烧火,开透了,焐一会儿,饭菜一锅出。闲下手来,娘习惯地扑打着衣襟,闪转腰身,拧着脖颈,左手背过去能摸着右肩头,我羡慕不已。她踱进里屋,站在炕沿边,冷眼看爹。爹吃了药,咝哈着,脸儿仍是青黑色,那是熬夜吸烟熏的、腹疼折腾的。他把肚皮贴紧炕席子,两条大长腿折过来,快够着屁股蛋了。炕上热乎劲儿来了,他的疼痛缓解了,石大骡子家的西屋炕几天不烧一回,冰的,爹从他家回来经常这样。
我搬来小炕桌,端上饭菜,特意给爹盛一碗酸菜汤,爹爬起来,抖着手,自知理亏,眉眼不抬,只顾往嘴里扒饭。娘也不出声,吃几口饭,啪地摔了筷子,往炕角一退,瞪圆眼睛看着爹吃饭。爹被眼神剜得疼,更了一下脖子,故意挺直腰,搁下筷子,嚷嚷:“老娘们家,你作个啥?”娘一听,发狠似的从炕上站起来,满嘴喷唾沫星子,指着爹:“你个狗屁研究,还是人不?到处坑蒙拐骗,我看你怎么还那些帐?”爹的长脸涨红了,仍是坐着,仰脖子咧嘴,猥琐地说:“你把那个金佛给我,我研究了,能卖五十万元!”“哦……”娘的手开始发抖,浑身颤着。爹以为她同意了,手拄着炕往娘脚下蹭蹭,讨好地说:“给我,我就不玩了!”谁知,娘猛然从被垛上扯过一床大被,呼地轮过来,劈头盖脸蒙住了爹,把身子重重搡在被子包上,挥拳就揍。爹在被子里挣扎着,鬼哭狼嚎。我去拽娘,娘疯了一样,回头就给我一巴掌。我转身倒腾饭盆和桌子,空出场子来,他俩又开始支黄瓜架子了。一会儿,娘打累了,长拖拖跪在炕上,万念俱灰般地痛哭,爹坐在炕沿上,双腿耷拉着,低头不语。
窗外有风掠过,刮得房檐草嗦嗦摇摆,月亮皎洁,却缺了一块,像谁咬一口的发面饼,还有影影绰绰烙糊的痕迹。我知道娘的苦,当闺女时人长得好,十里八村地挑,挑来挑去,挑到爹。爹却不务正业,游手好闲,嗜赌成性,但脾气好,娘怎么闹,他都不还手不还嘴,娘没办法,又好面子,只有自己作践自己。像这次,娘彻底明白爹的心思了。去年秋天时,姥姥去世了,姥姥供了八十年的镀金佛,早让爹瞄上了。据说这尊佛是纯金的,很值钱,传给娘了,娘不说,爹急得抓耳挠腮。娘就一个弟弟,对娘又极好,人家姐弟的事,爹插不进去,爹就破罐子破摔,赌得更甚了。
爹有两天没赌成,害肠炎,起不来炕了。娘忙里忙外照顾他,打针吃药,喝面汤。娘一边种园子,一边张罗着卖掉圈里的猪,拿钱种地。第三天,刚吃完早饭,爹就没了影,娘恨得牙根痒痒。做了好吃的,喂那只大黑猪。还叨咕着:“多吃点,一会儿过秤时,压点分量!”大黑猪像听明白话了似的,扑棱着耳朵,哐哐吃食,小细尾巴悠闲地拧着,娘看着,脸上露出笑容。太阳暖呼呼的,我推开玻璃窗,一股温润的气息涌进屋子,园子里小毛葱都拱出绿芽了,脆生生、壮壮的,像串起来的眼神,充满欣喜。小生灵子们还阳了,母鸡东寻西找,咕咕叫着,丢给它一个筐子,它就穷汉得了狗头金,趴着不起来。黄麻鸭子的扁嘴啄来啄去,三五成群,刚化冻的小河水清亮亮,虾子、蟹壳、七星仔鱼和蝎虫子都是美食,蛋包在浅灰色羽毛下蠢蠢欲动,快够着地了,娘就喊:“闺女呀,快吃开张鸭蛋喽!”我美得揪起浓密的刘海,让额头也晒晒。
这天晌午,地里干活的人们下工了,南院的许家哥三个,开着拖拉机,突突突地过,唱歌似的喊我名字,还在车上蹦跳着招手,我急忙瞅娘一眼,羞得满脸通红。我们是同学,没考上高中,都回家务农了。我和娘种了豆子、栽茄子秧和辣椒苗,拉走了院子角落的碎砖头,小园子小院子小清爽一下。娘站在干净地方,上上下下啪嗒身上的灰土,末了还拢拢乌黑的头发。一辆蓝色大卡车停在房后,横着膀子走过来三个小子,为首的金黄头发,八字眉,刀条脸,嘴角歪着叼一支香烟,看见我和娘,就往跟前一杵,左手一扬,无名指上一个明晃晃的大金戒指,夹走嘴上的烟蒂。赖唧唧地盯着娘:“你家有一头大黑猪要出手,我要了,顶大研究的赌债!来呀,给我抓猪!”娘气得直哆嗦,她使出全身力气喊道:“不行!你们休想!”那两个跑腿小子哪管娘的抗议,扒拉一下娘就奔猪圈,娘趔趄着后退几步,坐在地上。我冲过去,站在娘前面,瞪着黄头发小子,突然大声喊:“快来人啊,来强盗了!快来人啊!救我们……”黄头发小子慌了,骂咧咧地喊:“废物,还不快点!”大黑猪吃多了,不想起来,一碰就哼哼,谁都拉不动。东院王大叔拎了镐头跳墙过来,许家哥三个正跑过来,卡车已经被村民们围住了,那三个小子见势不妙,跳上卡车逃走了。
这次,娘没哭,我睡一觉了,从被窝探出头来,娘还一个人枯坐着,不点灯,没声响。我歪着头,看不清娘的面庞,就凑过来,枕在她腿上,她摸索我的背,像小时候,舒服极了。“闺女,找丈夫,可得睁开眼呢!我这辈子算完了。”那声音苍老、晦暗。我抬头,努力地看:“娘,我找丈夫,你说了算,呵呵,呵呵……”清白的星光晃过来,牛皮纸的火龙墙贼幽幽的,娘就倚在上面,眯起了眼睛。
五月刚过,谷子苗该间了,娘说不喷除草剂,十几垄地,玩一样就侍弄好了。我和娘匍匐在大地上,谷子苗圆茎,绿色,少绒毛。稗草呢,扁根茎,紫色,光滑无绒毛,见到就拔掉。灰灰菜,扁猪牙,接骨草,都好辨认,我跟着娘的影子,把自己种在土地上了。几天下来,我像沾满泥的土豆,硬邦邦,黑溜溜,整个一个土丫头。娘就拍着我的肩,看我和她一边高了,伸胳膊挎住我,娘俩来来回回,相依相伴。邻地的三花婶愿意跟娘唠嗑,那天晚上,往家走,正好碰上她,她就神秘地凑过来:“咋回事?你家大研究陷进去了,在东头盛二家,连赌六天,听说还跟人家签字画押了!”娘木呆呆地听完,没说话,一直往前走。三花婶看她没表情,觉得没意思,就快步走开了。娘等她走远,突然停住脚步,把手里的小锄子递给我,叮嘱道:“闺女,你先回家,娘一会就来!”我哭腔道:“你上哪儿,我也去!”娘正色,瞪我一眼,我赶忙往前走,回头瞧时,娘的身影窈窕,已经走远了。
我干完家里活,点上灯,娘就回来了,脱下衣服洗,刷鞋上的灰土,把自己收拾干净,才坐下吃饭,显得轻松愉快。半夜时分,村里传来瘆人的警车叫声。抓赌的来了!我惊慌地爬起来:“娘,快救爹吧,他在赌呢!”娘坐在黑暗里,一只手伸过来搂住我,镇定地说:“他可能被抓了,教训教训吧!”我有点忍不住,泪水无声地流下来了。感觉娘的手冰冰凉,我惊奇地抬头看,她早已泪水满面。
3
爹被派出所拘留十五天,因为娘报的案,派出所暗地里免了爹的罚款。我和娘坐早车,来拘留所大门前等爹,阳光红彤彤地晃着娘的脸,有点兴奋。那两扇刷了黑漆的大铁门,冷冰冰。娘瞅了一会儿,低头寻思着,一只脚蹭着泥地,绿茵茵的小草冒出头来,忽而连成片,像在嘻嘻笑。我凑近娘,不自觉地勾住了娘的胳膊。九点钟时,大门咯吱咯吱地开了,爹和其余七八个人排着队走出来,有的认识,有的不认识,都是赌徒。爹被剃了光头,故意佝偻着走向娘,胡子纠缠着,像烂苞米须子,大眼珠子骨碌着,讪讪的,乞求的,娘顺势搀了他,谁都没话,我突然没了扑上去的热情,也没了言语,看着就感觉行了。中巴车卷着风尘,一路沉默,到家了。搭上炕沿,爹开始呼呼运气,破口大骂报案的人,还说准是村里人,逮着非得揍死他。接着,絮絮叨叨诉说,那天晚上,他正是兴点上,把把都赢大点,裤兜里的钱都装不下了,眼看要翻本,欠的债都能还上……娘偎在锅台甲上,半个身子颓在那儿,泪水穿线,无声地流。锅里咕嘟咕嘟叫唤,下的面条要糊了,我拔出柴棍,手忙脚乱,盛进碗里,端给爹,堵住爹的嘴,屋里没了动静。
娘倚着那面火墙,头发嘶嘶地磨着牛皮纸,坐了一宿。爹的呼噜声不断,兴许多少天没休息好了吧。我爬起来熬猪食时,娘抻着衣襟下地做饭,饭刚做好,炕上被窝鼓着洞洞,爹没了影,娘愣怔一下,猛然把舀子甩进泔水桶里,哩哩啦啦溅了一地,我跟在她脚后扫着擦着,她突然说:“闺女,放桌子,吃饭!”大田地里人少,庄稼齐裤腿子了,苞米叶子抖出绿色弧线,整齐划一,一片地都是脆生生的浪,滚过来,荡过去,淘气般地旋着,抹一把汗水,直起腰,娘落出我老远,躬身子扯着大稗草,连根拔。它们疯了一样,异常茂盛,抢土抢肥抢收成,硬是长得比苞米秧都高。大多数人家的地里都掸了除草剂,春天播了种,就甭管了,秋上收粮食。闲下来的人呢,一窝蜂地赌,大姑娘小媳妇都上阵了,打扑克、蹦麻将,吵得脖子粗脸红,像我家地里长的大稗草,没缘由地长,长得心都疼,几天时间,地就荒芜了。我就在村里转悠,半天看不着一个人,一间间土房子挤在一起,蔫头耷拉脑袋,没有声响。几只黄色芦花鸡聚在灰堆上,爪子不停地抓挠着,细咝咝哼叫,饿得要昏了的样子。三五只黑猪和花猪蹭着墙头,身上的稀泥斑驳淋漓,它们刚从村子中央水坑里爬出来,晃荡悠悠,无聊极了。
大约母推栅栏门,进我家院时,看见娘正蹲在小园里,给柿子秧掐蔓子。她立刻响亮地啧啧嘴,眼睛眯出一条线,像额头的褶皱,五十多岁了,硬是翘翘尖下颏:“哎呦,大研究媳妇可真能干!难怪大研究那么有劲地吆五喝六!哈哈哈……”拿腔作势地嗲着,扭着屁股往娘跟前凑,娘皱着眉头,盯着她脚下,生怕踩伤小秧苗。她搂住娘,娘恶心地挣着,回头狠狠斜了我一眼,我心里噔噔地跳起来,果然,大约母嘀嘀咕咕,说媒来了。后乡黄五村,有个小伙儿,忒带劲了,只有大研究的姑娘能配上人家。娘犹疑着,经不住她烂舌碎嘴地磨叨,就答应看看。村里的姑娘十六七岁、十七八岁都找婆家了,有的结婚了,有的抱上小孩了。娘口上不说,心里着急,姑娘留在家里,岁数大了搬人呢,自己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有好的,趁年纪轻先处着,可不能耽误了。第一次见着那小伙,一个肥婆娘领着他来我家的,他旁若无人地坐在炕沿上,东张西望,烫了头发,奓散着,女人连帽樱子一样,长得触领子了。那肥婆娘花布衫勒肚皮,稍一喘气,那枚粉色纽扣岌岌可危,就要崩飞了似的。娘面无表情,一唠嗑,小伙二十八了,整整大我一旬呢,娘就冷了脸,冲着大约母说:“今儿到这吧,俺们下地干活了!”谁知,话音刚落,肥婆娘脸一横:“咋着?我们娘俩是来领人的!大研究输给我当家的十五万块钱,拿姑娘做的抵押!有文印子,你们还想耍赖不成?”娘青着脸,气得说不出来话。大约母应和着肥婆娘,嘿嘿哈哈说笑开了,小伙有多好,人家有钱有势,姑娘过去就享福了……我忍着怒火,冲大约母说道:“大婶,你说的话我信,我同意谁也挡不了,这么大的事,您不得给我点时间和娘商量商量?”说着,故意向那个小伙一眨眼,微笑一下。肥婆娘缓和了语气,挤出笑来搭讪娘,娘的脸憋得通红,始终不言语。大约母叽里呱啦畅想了一堆婚后的笑话,什么小媳妇、胖小子、美被窝之类的,肥婆娘乐得身上肉直颤,领着儿子,恋恋地走了。
我把客人送到房后,懊丧地看他们背影,脚还没踏进屋,娘呶地一声哭出来了,她跪在炕上,脑门咣咣砸着炕席,嚎啕大哭。我的眼泪也憋不住了,跪在炕沿上抱起娘:“娘不哭,她们不会咋样,咱们报警吧?”娘模糊着眼,抬头茫然,谁能救得了啊,连公安局也没啥好招子,咱还不是挺着?我觉得委屈啊,让爹给输了,人家来逼婚,这都啥年月了,还有这样的事情?我抱着娘呜呜哭,一副不想活了的架势。娘立刻停止了哭声,拍着我的背,安抚着:“闺女,别哭,娘还有办法,你爹是个祸害,咱治他!”
我的村庄叫小王岗,王姓居多,许多年前,有几个王姓老百姓,占岗子为王,官府又鞭长莫及,自古以来,民风剽悍。如今是两个城市的边界点,邻着泥河,小船一摇,遛几步就到人家管辖区了,偏远寂寥,现代文明蔓延这里时,软弱无力。村里时兴娶嫂子送妹子——换亲,彩礼钱都省了;两姨攀亲的,姨哥姨妹儿;有输了老婆的,真就让人领走的;还有勇敢的姑娘跟着陌生人跑了的,让家里人叫苦不迭,损失了巨额彩礼钱。肥婆娘也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再来,可咋办?我趴在窗台上发呆,小园子绿得呼嗵呼嗵的。娘抱一捆子灰灰菜、苦麻子进屋,按在菜板上剁碎,白色浆汁四溅,累了,抹一把肿胀的眼皮,睁开都费劲,娘就咬紧牙关,不停地干活,来消解心中的苦痛。昨晚,爹半夜才回家,晃荡着,不洗脚就爬上炕,娘捂着鼻子,给他一个冷漠的背。爹还不识相,唧唧咕咕招惹娘了呗,娘翻身骑在他身上,一顿拳头,自己恼得一塌糊涂,爹顶多杀猪般地哼呀嚎叫几声,不说道理,不讨饶,说正经事没嗑儿,跟一个闷杵子似的。娘喘着粗气时,爹的鼾声起来了,娘又是一夜不睡。我夺过娘手中的菜刀,接着剁菜叶,大铁锅里冒尖了,菜叶、糠皮子、碎苞米粒,还有豆饼渣子和土豆块,压得实,添足水,熬猪食。我转过身,搂住娘,一头触在发丝上,在她耳边小声说:“娘,你可以放弃爹,不生气,不跟他有关系,咱不就安生了!这样做病呀!”我有自己的小心眼,怕她真“治”爹,爹有点像残疾人,身心里少了啥,可恨可怜。娘一把推开我,嗔怒地瞪我一眼:“死丫头,少管闲事,烧火!”
苞米杆子一根根塞进灶坑里,熊熊火焰聚成一束,贪婪地舔着铁锅底。娘也蹲在灶前,直勾勾盯了一会儿,转过脸去,快步跑到外面了。我听娘的话,一心一意烧火,这是我的强项。大铁锅里咕咕咕叫开了,白色蒸汽袅袅升腾着,火映得我直发呆,想起前院许家的二小子,他从不沾赌,开四轮子车拉货,拉脚,揽牛具,地里活样样通,能过日子,还总看我笑,真好。门外一阵骚乱,吵吵嚷嚷地近了,我站起来,房门被撞开,五六个人抬拽着爹,吆喝着,把爹放在炕上,娘傻呵呵奓开了手,跑来跑去,人们七嘴八舌地说着,刚才还好好地推牌九呢!不一会工夫,就这样了。爹仰面摊在炕上,我爬上炕,拿了被子和枕头,搬着他的腿,让他舒服点。爹不吭声,微睁着眼睛,嘴唇煞白,有白沫子汪在嘴角。两只大手胡乱地颤,要捂肚子,指关节都磨得黑亮。我下地穿了鞋,飞快地往后趟房小卖店跑,那有电话,可以叫到出租车,拉爹去镇里卫生院吧。我回来说着时,娘一个劲点头,感觉她浑身都哆嗦,我忙去搂着娘,娘又哭了:“天啊,咋成这样了呢,这可咋好啊!……”
镇卫生院没诊断出爹的毛病,只说有可能是肠炎,我和娘又把爹送到县城医院,得出来诊断——肠癌。医生说,和患者长期饮食不规律、着凉有关系,可以手术治疗,但再犯病一次,人就没救了。娘找来舅舅商量,凑足了手术费,给爹动了大手术。娘把我赶回家,自己日日夜夜守着爹,吃得少,睡得少,常躲在角落里哭泣,拿脑袋撞墙,被人发现了,还以为她头疼呢。一个月后,头发白了一半。爹握住娘的手,含着泪,一遍遍叨咕:娘合他的心,连汗毛都中意!就不说赌博的事,死也不说。娘哭得背过气了,医生和护士过来抢救,劝娘要想得开,再说,这病能挺个十年二十年的,没事。
爹回家了,没两天,又去赌了。娘坐在炕上掉眼泪,这人要是活着,天天赌也成啊。她明显地迟钝了,头发稀了,黄了,干草一样。仍爱干净,衣服裤子洗得一尘不染,憎恶那些好赌成性的邻居,来来往往,不是好眼睛瞪他们。我笑着说:“娘,他们不知道,您别作践自己了,生了一身病,谁给治?”娘拿食指头点我脑门:“你呀,你给治!”嘻嘻嘻……我跟在她身后顶她的背,她也笑了。那天,我正在园子摘豆角,娘搀着爹回来了,爹有气无力地坐在院子墙上,嗔怪着娘:“你咋那傻,说那些话有啥用,人家以为你有精神病,谁听啊?”娘的泪在眼圈转:“连你都听不进去,这世道还能好了么?”原来,娘跑到赌场去了,硬是劝说那些赌意正酣的人们,没人理她,爹疼她,只好跟她回来了。一次好使,再次,连爹都烦她了,娘心里明白。
娘的话越来越少,倚着火墙,沉默着,丢了往日的鲜润,变得憔悴、虚弱。夏天倏忽间过去了,庄稼收了,粮食裸露出来。轮到我家拉苞米棒子,娘非要跟我上地,念叨着,给我闺女看看堆儿也好啊。田野里的秧稞都放倒了,像剃了头发,光秃秃的。我家地头上有棵歪脖子榆树,粗壮、苍劲,树干黑黢黢,飘下一地的叶子,厚厚的。我铺了小毛垫子,让娘坐下。就去往四轮子车里装苞米棒子了,许家二小子开车,他开一段,停下来帮我,装得快,捡得干净,连散落在垄沟里的也不落下。我回头看娘,她正绕着榆树转悠,便放心地笑了。
那天,我去地里收苞米秸秆,回来时都黄昏了。一开门,就听屋里咚咚地响,我心里一颤,急忙冲进屋子,看见娘正操着搞头刨火墙,光滑的牛皮纸炸裂开了,土块、水泥疙瘩和砖头纷纷掉下来。我着急地喊:“娘,这是干啥?”娘绷着脸,不理我,仍是刨,时不时地用手掏出碎土渣子,忽然,一个四方的金色纸面佛龛显现了,娘小心翼翼地抱出来,放在炕上,拉着我坐在跟前。掀开厚纸帘子,从里面捧出一座金佛。啊,我惊讶地张开嘴:“这就是姥姥供的金佛,爹做梦都想得到的金佛!”娘像明白了我的心思,轻轻地说:“闺女,这尊佛是铜质的镀金的,有灵性的!”娘说着,把佛像倒过来,从佛像肚子里捏出两根钢针,就是普通的做活计的针。娘把两根针凑到眼前仔细瞧,喃喃自语:再也没了心思了,再也没了心思了,再也没了心思了……
天短了,昏暗的光漫进来,那两根钢针细微微的亮。姥姥去世前,一直心疼女儿,找了一个不省心的男人,日子没了旺兴。就派舅舅去庙里请了一场法事,许了两根钢针的尘事,惩治爹的邪性。为了不让爹发现,把佛龛隐在火墙里,走烟火时,只要娘动了心思,爹就腹痛,但只能有两次。没成想,等于要了爹的命。
我装做轻松地收拾垃圾,大声说:“娘,咱得相信科学,别瞎想,那些都是蒙人的事!您瞅瞅爹那样,不得毛病算怪呢!”娘慢慢地说:“闺女,我害了你爹。我不放心你呀!”感觉娘哪里不对劲,我趴在娘腿上撒娇,心里想着,娘放下心思,和爹不相干,就能舒服地过日子了,我也开心。
娘一天天地衰老了,弓了腰,走道迟缓了。第一场雪花飘得缠绵肃静,田野铺了洁白的被,正是娘喜欢的样子。爹又一宿没回来,娘睡得沉,不去惊动她,我开始喂猪、喂鸡、打扫鸭子粪便,抱回两捆子干柴,哗啦啦,哗啦啦……
“娘,娘!娘!……”娘没在屋,我呼呼地往外跑,天旋地转,娘憎恨赌博的人家,娘能去哪啊?
娘在那棵歪脖子老榆树上,她走了。
(责编:朱传辉电子邮箱:zch76110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