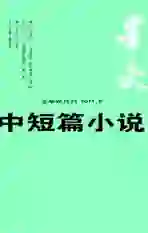上门儿
2011-12-29阮家国
星火·中短篇小说 2011年6期
二伏里头,田水沟儿的苞谷开始黄了,一进三伏,苞谷地里头星星点点儿的青颜色就叫太阳撵跑了,细细儿看一下儿,个个儿苞谷坨儿都黄壳儿了。三伏第五天,田大正开始扳苞谷,二女儿田本珍跟幺女儿田本玉两个人扳,比起挑苞谷,扳苞谷就是轻省活儿。田大正一个人挑,两担花箩筐轮换着装苞谷坨儿挑。他把一挑儿苞谷坨儿挑回家,再回到地里,另一担花箩筐就又装满了苞谷坨儿。天热得透不过气儿来,昨儿晚上都没回一点儿凉。他穿着汗衫儿,肩上搭着一条擦汗手巾,可连擦汗都舍不得耽搁时间,只能捡拿打杵支起挑子歇气换肩的时候儿擦把汗,一换肩,打杵跟着也斢个手。打杵每跟他走一步,打杵脚尖儿杵在地上,捏打杵的手总要刷刷刷来回甩几下儿,每甩几下儿,像是能给肩膀加点儿劲儿。
田大正家在田水沟儿的半山腰儿,房前屋后熟地多,山上的人家原来有不少,家家户户都朝山下撵,现在就只剩下他一家儿还没搬走。山上的人一搬走,再种山上的地就难得跑,懒得跑路,干脆撂荒。看着一块块儿熟地撂荒,他心疼不过,就把人家撂下的地捡一些种,今年春上他就种了一二十亩苞谷。苞谷尽管是粗粮,可人畜都离不得,更是猪的细粮。猪不多吃细粮,膘儿就不得起来。说起来,屋里种了不少地,还多亏两个女儿,她们个个儿都是好做将儿。
活路是撵出来的,苞谷一扳,再把苞谷种挑出来,把黄灿灿的剥了壳儿的苞谷坨儿挂到墙上,再把苞谷子儿掰出来,晒干,天就变了。这天收苞谷子儿时,田大正觉着腰酸背疼,他一腰酸背疼,天就要下雨,比天气预报还准。
雨是半夜悄悄儿下起来的,田大正起夜,发觉天在下毛毛儿雨,在屋外场子上吃了根烟。天热,老伴儿林翠平也摸了起来,还给他拿了个小板凳儿,两个人轻脚轻手摸到屋东头儿的屋山头儿坐。屋东头儿外是一个大山坡,顺风,不像屋西头儿那边,有个沟,是个卧凼儿,背风。房前屋后树扒里,知了跟各种鸟雀儿虫虫儿叫得好像比白天还有劲儿。林翠平说,下雨了,难怪屋外还凉快。田大正又点根烟说,今儿出伏。林翠平说,雨好像下不下来。田大正咂口烟说,瞎说,明儿得下一天,还有几天雨。林翠平说,大女儿快回来了。田大正连咂几口烟说,苞谷一扳就得打谷子,明儿得请工,看找不找得到人打谷子。林翠平说,你请得到工,我就做席面儿。田大正好像不相信地说,真的做席面儿?林翠平说,原来栽秧打谷子,哪回没做席面儿?就怕你请不到工,莫光找些七老八十的老汉头儿。田大正说,这回我非得请几个像样儿的工。林翠平说,量你请不到。田大正说,请不到工,我就不打谷子。隔一下儿,林翠平说,正月间大女儿说,给二女儿找个家儿,只看定下来没,过一向她肯定回来。先头,林翠平就想说这个话,可田大正没接腔儿。现在再不接腔儿好像绕不过去,他说,急个卵,急婆娘嫁不了好汉。
天差不多亮了,雨下得好像也大了一点儿,是麻麻儿细雨,比毛毛儿雨大一点点儿。
田大正起个大早出门儿,本来从屋东头儿走才顺路,可他却从屋西头儿走,要就便儿看看田里的谷子。他本身有一点儿水田跟旱田,又捡了一点儿旱田。旱田在半山腰儿,水田在旱田下头。旱田的谷子在黄了,谷穗儿上头的颗颗儿谷子儿都透出一点儿金黄来。水田的谷子比旱田黄得好像还快一点点儿,有的谷子儿都看不出来青颜色了。看来,等天一晴,再晒两个太阳,谷子就能打了。说起打谷子,人多打谷子才有劲儿,去年打谷子就没劲儿死了,他又没请工,又没换工,自个儿打,谷子打了五六天才打完。今年他不想自个儿打谷子,得请几个工,可请工又哪儿请得到像样儿的工。像样儿的工都外出打工去了,可他就不信,这门跟前就请不到几个像样儿的工。
请工该在门跟前请,对他来说,门跟前的人就是山脚下的人。山下人户集中,可却看不到几个能下力做活路的人,更看不到在家的儿娃子。
他心里盘算着,只找陈宗贵、张有庆、刘粮仓,看他们请不请得动,能不能跟他换个工。要说做活路,他就还看得中他们,他们跟他们的儿孙,都能做活路,做活路个个儿都是好做将儿,犁地栽秧耙田打谷子,做么子像么子。
陈宗贵在掰苞谷子儿,见田大正来,起身给他装烟(鄂西北由来已久的俗语,意为敬烟),烟是两块钱一包的红金龙。红金龙烟有好几种。陈宗贵不大吃纸烟,卷旱烟吃。陈宗贵屋里人给他泡了茶,他给陈宗贵装一根五块钱一包的红金龙,要旱烟吃。陈宗贵一手接他的烟,一手把烟卷儿已插进烟袋锅儿的烟袋递给他,说,你还吃得惯旱烟?田大正先给陈宗贵点烟,说,旱烟又香又有劲儿,我今年就种了亩把地。陈宗贵咂几口烟说,这山上山下,今年还数你收成大。田大正点旱烟,长长咂一口,叫烟子从一个鼻孔出来,说,还是你收成大,呃,你打谷子换工不?陈宗贵说,现如今打谷子的声气儿稀稀拉拉,有一下儿没一下儿,听着没劲儿死了,大不了多打几天,各打各的也打惯了。田大正说,你儿子他们呢?陈宗贵说,不朝外跑的人怕是还没生出来,还不是在外边儿打工?我这老胳膊老腿儿,还得给他们打谷子。田大正说,老胳膊老腿儿打谷子就是没劲儿啊。陈宗贵说,不是个球,工是又换不到又请不到。
田大正去张有庆家,见张有庆正从茅厕出来。张有庆跟田大正打招呼说,早哇,走人家?田大正见张有庆要从身上摸烟,抢先装烟,说,瞎晃一下儿,走个么子人家,你换工打谷子不?张有庆说,正月十五贴对联儿,你咋不早说?先头还有人找我换工,我倒是想跟你换个工,可哪儿换得成?我屋里要打谷子不说,儿子女婿要我打谷子,老丈母娘跟舅母子还要我打谷子。田大正说,你倒成了小姐的屁股沟子——俏货儿。张有庆说,真像你说的,又值钱了,吃根把两根烟就能捡张红票票儿。
跟张有庆换不成工,田大正又去找刘粮仓。刘粮仓屋里人死五六年了,他一个人过日子,却不在家,门上挂着锁。田大正又去刘粮仓儿子屋里找刘粮仓,刘粮仓儿子出门儿打工,儿媳妇儿柴米秀倒在屋里。田大正问刘粮仓去哪儿了,捡一把空椅子坐下。柴米秀憋了憋才说,他呀。柴米秀好像不愿提说老公公,又说,瞎跑惯了,不晓得又摸到哪儿去了。田大正问,他这两天回来不?柴米秀说,你要是请他打谷子,就莫打这个米,谷子都打完了,看他能滚回来不。柴米秀说老公公滚?田大正心里头猛地一掣,觉着自己是不是听岔了。柴米秀说,老骚货,就好给人家寡妇屁股沟子卖气力。田大正听不下去了,起身就走,说还得过河去。柴米秀说,表伯茶都没喝一口,我正要给你泡茶呢。田大正说不渴,心里头却说,我走起来,你倒要泡茶。
柴米秀出门,摸到屋山头儿,好像是送客,眼睛有一下儿没一下儿地把田大正看着。田大正从柴米秀门前走到前头的大路上,站了一下儿,好像是拿不定主意,该朝哪儿走。从大路朝下走是过河到乡上去,朝上走是上山,对他来说就是回家。他本想朝上走,可他一下子想起来,他当柴米秀说过过河的话,再说柴米秀还站在屋山头儿,明明儿是在看他到底朝哪儿走。看来,他还得朝下走,免得叫人说他哄人。见雨好像下得小了,他把弯把把儿长雨伞收起来,刷刷水,夹到胳肢窝儿里。实际上,他还真得朝下走。打谷子的工没请到,他还得请工。东边儿不亮西边儿亮,黑了南边儿有北边儿,他就不信,打个谷子还请不到工。还有,他觉着,谷子黄了,这时候儿刘粮仓应该在屋里,柴米秀说刘粮仓瞎跑,那是她见不得老公公。他估摸着,刘粮仓是过河去了,到乡上买东西,说不定自己还能遇上。打谷子请工请不到,那就只有换工,可换工也要半斤对八两,只能跟年纪差不多的人换。
从这儿到乡上有二十里路,快到乡上了要过一条河,过桥,桥是能过车的水泥桥。半路儿上,前头又是一个岔路口儿。走到岔路口儿,田大正磨蹭了一下儿,还吃了根烟,好像是要等刘粮仓从乡上转来,可一根烟咂完,他也没看到刘粮仓的人影儿。对面儿山上,有一坨坨儿的白雾,林翠平的娘屋就在对面儿山上。岔路是下山的路,从这儿下山过河,能到对面儿山上,比从乡上绕过去要省路。这条过河的路,他都不晓得走过好多回了。最早走这条路,他是跟老子一路儿去修林翠平家屋门前那条车路。车路一头儿接从县城进山的车路,一头儿通乡政府。他们生产队的民工负责修林翠平家屋门前一截路,那时候儿,他还是个小娃子,才开始拿工分儿。他在那边儿修了一个冬的路,心里头就想说林翠平做媳妇儿,倒还真说成了。
门上换不到工,他就想去找两个舅官儿换换工。
河是大河,河水青耿耿的,过河的点儿水面儿宽展,水不深,把裤子卷到胯丫子上就能过河。
过了河,田大正才想起来自己是淋着雨过的河,雨伞还没过河,还搁在那边儿河岸上。他骂自己老糊涂了,又过河拿伞,叫伞过河。
河边儿有个水田田坝,田坝里头的谷子好像黄透了。这个田坝他来过好多回,里头有大舅官儿跟小舅官儿的水田,他们的水田,田大正都来帮过工,栽过秧,打过谷子。他绕到他们的田边,细细儿看了看他们田里的谷子,看见几根长到谷子头上的稗子,还顺手扯了起来,甩到田坎儿上。
树大分杈,人大分家,老丈人跟老丈母早已去世,大舅官儿跟小舅官儿都有了孙子孙女儿,又都跟儿子分家儿了,他们的儿子也都打工去了。说起打谷子请工,大舅官儿说如今人心都钻到钱眼儿里去了,哪儿还找得到年轻娃儿。田大正想跟大舅官儿他们换工,还想再请两个工。亲戚跟亲戚换工当然好,又能换工,又能走亲戚。大舅官儿说,请工莫指望,现在连换工都换不来。
隔大舅官儿家不远,有一家儿在盖楼房,看着有点儿惹眼儿。大舅官儿说是李福山在盖楼房,李福山有两个好娃子,会挣钱不说,人还争气,今年都在屋里头没走,要把楼房盖起来,说媳妇儿。说起来,李福山跟大舅官儿他们还有一点儿亲戚关系,李福山把大舅官儿的奶奶喊表奶,大舅官儿的奶奶是李福山姨奶的表妹娃儿。田大正问,那兄弟俩儿多大了,说到媳妇儿了?大舅官儿说,老大李为民二十五,老二李为田二十三,媳妇儿好像都还没说成。春上有个外乡的女娃子还来看过家儿,没看上,嫌李为民没在县城买房子。大舅官儿说,现在的女娃子心野,都想朝外跑,可他们又想在本地说媳妇儿。田大正觉着,李为民兄弟俩,他应该看到过,他们的大名儿也都起得好,一个叫为民,一个叫为田,叫着顺嘴儿,听着顺耳儿。
河那边的谷子比河这边儿黄得快,天一晴,田大正就过河帮大舅官儿跟小舅官儿打谷子。李为民兄弟俩儿也来帮工,看他们头一下儿,田大正就看出来了,他们小时候儿常跑到大舅官儿家玩儿,他好像还记得他们小时候儿的模样儿。再看他们现在的模样儿,打谷子的劲头儿,他就觉着,他们这些解放初出生的人是真的老了。不用说,一看就晓得,做活路,李为民他们兄弟俩个个儿都是好做将儿。他还发觉,他们俩儿都不吃烟。不吃烟好,现在不吃烟的娃子还真少见。话说回来,他能跟林家开亲,林家就是看中他做活路是个好做将儿,又不吃烟。不吃烟好,省钱不说,身上不沾烟气儿,还不讨人嫌。直到幺女儿田本玉出生,他才开始吃烟。
栽秧打谷子是大活路,做大活路人手儿多才有劲儿。
打谷子要有打谷子的样儿。
打谷子的日期定在七月二十六,二十五这天,田大正家就忙了起来。实际上,还就是忙下两个日期吃的喝的。吃的喝的要有鼻子有眼儿,跟过喜事儿做席面儿差不多。一大早,田本珍她们姊妹俩儿就把围腰儿系了起来,系得紧了点儿,就把细腰身儿勒了出来。田本玉先发屋里的煤炭地炉子,地炉子风口儿外边儿有个地坑儿,她下地坑儿擞炉膛里头上回烧火留下的煤渣,给炉膛里烧底火儿,等底火儿烧旺,再倒木炭渣子,给底火儿加把劲儿,末了再倒煤炭砣子进去。山上烧煤不容易,煤炭贵不说,还是他们爷儿伙的肩挑背驮从山下盘上来的,烧煤就轻易舍不得烧,不是要做席面儿不得烧煤。
说起做席面儿,林翠平也是半个厨子,只是不给人造厨。做席面儿,少不了要在头一天提前炸菜。炸菜得炸豆腐丸子跟瘦肉丸子,就得先打豆腐,等豆腐出来。田本玉把黄豆搓洗两遍,再淘洗两遍,搁到捅里泡。黄豆得泡涨,不泡涨出不了好豆浆。黄豆一泡,跟着就得挑拣炸菜的猪肉。去年杀了两条猪,灶屋墙上还挂着不少用柴火熏过的腊肉。田本玉搭梯子拿肉,一上梯子,林翠平就走过去,拿一只脚抵住梯子脚,仰头看墙上的肉,心里划算着,叫拿哪一块,田本玉就拿哪一块,下几步梯子,把肉递给站在梯子边儿上接肉的田本珍。林翠平见肉拿得差不多了,叫田本玉下来,田本玉却不动脚,说,再拿一块炸红肉。林翠平没吭声儿,看田本珍一眼。田本珍头一扭说,哼,只晓得吃。田本玉哪儿是省油的灯,还嘴说,哪个不晓得吃?有人有客不吃,客一走就吼起来吃。田本珍脖子一梗说,你。田本玉说,不就是好出风头儿?到人家屋里去出。田本玉这个话就说重了,田本珍一声儿不吭,眼窝儿就红了。林翠平说,瞎说,再拿一块就是。田本玉就又拿了一块炸红肉的肉,也不递给哪个,自个儿下了梯子。实际上,田本珍已不见了,像是摸到房屋去了。本来,今年春上,已嫁到山外边儿的田本玉大姐说过,要给田本珍找个家儿,可这事儿却叫田本玉一下子捅破了,由不得田本珍心里头不辣辣儿疼。
灶屋有个耳门出进,田本珍磨蹭着从房屋出来,不走耳门,板着脸从堂屋出大门,在门口儿站着,像是要朝哪儿去。门外场子边儿上磨刀声哧哧响,背对着大门磨镰刀的田大正眼睛只看磨刀石,可他晓得田本珍在门口儿。田大正像是要清嗓子,咳一下儿说,嗯,倒缸茶。他习惯大清早喝酽茶,一起来就要喝两大缸子酽茶,不喝茶,烟都吃不香。喝茶的大搪瓷缸搁在磨刀石边儿的一个石板上,田本珍倒茶过来,田大正说,你磨磨刀,我喝口茶。田本珍好像不情愿磨刀,说,伯(父亲),你歇一下儿就是,灶上灶下的活路都码成堆了。田大正就抿了抿嘴,像是笑了一下儿。喝两口酽茶,他点根烟叼着,又坐到小板凳娃儿上,叉开两腿,磨刀。磨刀石还是他爷爷从旱田那边的田水沟儿里头盘回来的一个大磨刀石,是个老磨刀石,有半截埋在土里,黄泥巴颜色的口面儿又长又宽。屋里有五六把割谷子的镰刀,一年也难得磨一回,他把它们都拿了出来,要都磨一磨。他正磨的是头一把刀,刀锋两面儿已磨了一个来回,在磨第二个来回。磨刀要一面儿老一面儿嫩,要磨得老的一面儿,刀要拿陡一点儿。一根烟咂完,第二个来回也磨完了。他看一下儿刀刃儿,拿左手大拇指来回荡荡,就晓得刀磨没磨好。他搁下这把刀,拿起另一把刀,拿刀面儿在放磨刀水的木盆里荡一荡,沾点儿水,搁到磨刀石口面儿上,开始磨第二把镰刀。
田本珍进屋,坐在煤火炉子边儿上的田本玉拿眼睛钩她一下儿,她却连眼皮儿都没抬一下儿,走到要和面的桌子边儿,背对着田本玉,开始和面。坐在灶门儿前烧火的林翠平说,先擀一顿面吃,吃了早饭再炸点儿麻叶儿麻花儿待客。
煤火起来了,有绿火苗儿在朝起蹿。煤火里头插着一把火钳,一根烙铁,一根炉扦子。田本玉左手拿钳子夹住一块肉,右手拿起烧得红亮亮儿的烙铁,贴着肉皮一顺溜儿地烙,烙得刺溜儿刺溜儿响,等烙铁不红了,又把它插进火中,拿起火钳烙肉皮。烙肉皮,要烙掉肉皮上看不见的绒毛儿。肉瓤子也得烧一下儿,在煤火面上燎一燎,撵撵肉腥气儿。跟着就要洗肉片肉,片炸大酥、小酥、酥骨、红肉等蒸菜的肉。片肉也显手艺儿,片红肉得片得不厚不薄,只能带一点点儿肉瓤子,肉瓤子多了吃起来就腻嘴儿。
田本玉洗肉,田本珍把面和好揉好,开始擀面。案板那边开始片肉,田本珍就把面擀好,把面条儿切了出来,在炸芫荽辣子了。田本珍又打了一大钵钵儿酸菜瘦肉汤,朝门口儿走几步,喊伯吃饭,回身就在另一口已烧好开水的锅里下面条儿。
吃头一碗儿面条,个个儿都不吭声儿。田本玉吃得快,先换碗儿,一下子又舀一大勺子芫荽辣子,说,这芫荽辣子炸得就是好,想不吃都不行。隔一下儿,田本珍说,你本来就是个大吃将儿,比哪个都吃得快。田本玉说,要怪就怪你不该炸芫荽辣子。田本珍说,招呼结火儿。田本玉说,敢吃还怕结火儿?田本珍起身给伯捞面条儿,林翠平说,瞎说过来瞎说过去,一点儿吃相都没得。田本玉说,不说不笑就有吃相?林翠平说,药铺的甘草,做冷做热。田本珍又起身给妈捞面条儿,悄悄儿笑了一下儿。田本玉不吭声儿了,隔一下儿又说,哪儿板桶在响,还怪好听。林翠平说,就你耳朵尖。田本玉说,妈,你细细儿听一下儿,是有。林翠平细细儿听一下儿,问田大正,你听得见不?田大正说,你听得见?林翠平说,有一下儿没一下儿,轻飘飘儿的,嗵嗵,嗵嗵。田大正说,怪,这才怪了。林翠平从去年开始,有点儿耳背,可田大正没说她耳背。
吃了早饭,又各撵各的活路,田本玉接着片肉,田本珍又来和面。麻叶儿麻花儿是打零吃啖嘴儿的面食,和面时得搀鸡蛋跟碱面儿,把面擀出来,再切成差不多跟麻将牌大小的块块儿,搁到油锅里炸出来,吃起来又香又酥又脆。和面时,林翠平叫多打两个鸡蛋,鸡蛋多打两个,炸出来的麻叶儿麻花儿就更香更酥更脆。
这几年,也就是过年炸个菜,从去年起,一炸菜,林翠平就动嘴儿不动手了,她是门第师,把二女儿幺女儿这两个徒弟都带了出来。豆腐一打出来,田本珍她们姊妹俩儿就开始捏豆腐丸子跟瘦肉丸子。林翠平坐在灶洞前给油锅烧火,拿柈子柴烧火,免得喷灰。炸菜得用菜油,菜油炸菜香,田本珍给锅里倒上大半锅菜油,又把红薯粉浆水儿调出来,把大酥、小酥、酥骨等蒸菜肉在红薯粉浆水儿里拌好,一样儿一样儿地搁到油锅里炸,隔一下拿漏勺儿在欢欢笑的菜油里翻一翻,等炸得不老不嫩,捞起来搁到大筲箕里。
田本玉好吃,等到麻叶儿一炸出来,她就啖起嘴儿来了,还说,我有好多年都没吃过麻叶儿了。田本珍说,去年过年吃到狗肚子去了。这回,田本玉倒没还嘴儿,说,这简直都跟过年一样儿了。林翠平在灶洞前笑一下儿说,大人望种田,小娃子望过年。田本玉说,我就不信大人不望过年。田本珍说,就是就是,我心里也这么想,就是没说出来,也怪我嘴笨,没得人家嘴快。田本玉眼一翻说,说给窗子给门儿听,又在敲打人,说我好吃吧。田本珍抿抿嘴儿说,敲不敲打人,我敢赌咒,赌么子都行。田本玉噗嗤一笑说,我这人,你也晓得,刀子嘴,豆腐心。田本珍腾手递给田本玉一块麻叶儿说,反正,反正也没人记气儿。田本玉瞪她一眼说,这块麻叶儿可比哪块儿都好吃。
这天天还没亮,田大正就起床了,见田本珍她们姊妹俩儿早都起来了,正在灶屋忙。他上茅厕转来,他的洗脸水都倒好了,茶也泡了。喝了酽茶,他到场子上吃烟,一根烟要吃完了,又转到屋东头儿,拿烟头儿接一根烟。这根烟吃完,天才有一点儿麻麻儿亮。他看见,有四个人影儿,在朝山上来,前头一个人像是大舅官儿。
他没想到,李为民他们兄弟俩儿也来给他帮工。大前天,他给小舅官儿打谷子,只是随便儿当李为民说了一下,请他们帮工打谷子,他们倒真来了。
田大正本身有一亩水田,一亩半旱田,又捡了一点儿旱田,谷子倒有四五亩。今儿早上先在水田里开镰打谷子。早饭一吃,李为民兄弟俩儿就去抬板桶。板桶是打谷子用的大方桶,形状像量粮食的斗,桶帮子厚墩墩儿的,四角儿有牛耳朵大小的把把儿。他们把板桶翻个面儿,倒扣着,一人抓个对角儿的把把儿,搁到肩膀上,把板桶朝水田里抬。
田本珍她们姊妹俩儿先下水田割谷子,要给板桶腾地方儿。板桶一到,水田里的谷子都割出一大块儿了。板桶一进田,田大正给板桶一方插上遮挡谷子朝桶外飞的竹篾席子。大舅官儿跟小舅官儿先打谷子,各自双手握着一把谷子,一左一右站在席子对面两边儿,高高扬起谷把子,把谷穗儿刷地甩打在各自这边儿的桶帮子上,把谷穗儿又在桶帮子上刷刷刷轻磕几下儿,磕的时候,谷穗儿在手里刷刷刷就斢了几个面儿,等谷穗儿不得随便儿掉谷子了,再扬起来打下去,一把谷子差不多要甩打好几下儿。眨个眼儿,一把谷把子刷刷几下儿就打利索了,稻草就手靠在板桶外边儿,大舅官儿他们走开去拿谷把子,李为民他们兄弟俩儿又靠上去打。谷穗儿拍打板桶,接二连三地发出嗵嗵嗵嗵的声气儿,这个声气儿听起来又瓷实又妥帖,好像是天底下最好的声气儿。等到板桶边儿上靠着的稻草够绑谷把子了,打谷子的人会拿几根稻草就手把稻草从杪子上一扎,再一甩,把草蔸儿甩开,叫草把子稳稳当当地站在田里。
打谷子的人个个儿是好打将儿,割谷子的人也个个儿是好割将儿,可谷子好像还不够打。田大正也拿把镰刀去割谷子,过一下儿,割谷子的人好像这才喘得过气儿来。田大正伸伸腰说,你们也不吃根烟,歇一下儿?我们这边儿都割不赢。大舅官儿说,我们一歇,不就打不赢了?还是等一下儿再歇气儿。田大正看一下儿板桶说,谷子都够挑一挑儿了,你们可莫笑话我这老胳膊老腿儿。大舅官儿说,还要你挑谷子?又打几下儿,大舅官儿说,行了,我们兄弟三个来吃根烟。李为民眼尖手快,从身上拿烟出来,给三个长辈儿装烟。请工打谷子,一个工见天儿要给四十块钱跟一包烟,另外还要给一条擦汗手巾。今儿早上吃了早饭,田大正给帮工的人一人一条擦汗手巾跟一包烟,可李为民兄弟俩儿只要手巾,却不要烟。烟是五块钱一包的烟,田大正蛮叫拿上,他们才揣到身上。
李为民拿木撮瓢朝篓子里铲谷子,李为田等着挑。李为田把一挑儿谷子一挑上,坐在田坎儿上吃烟的人就坐不住了,叼着烟来打谷子。
活路是撵出来的,吃晌午饭前,打谷子的人撵着撵着把水田的谷子打利索了。
田本玉提前回屋帮妈弄饭。请工做活路管吃管喝,饭菜油水儿不薄,晌午饭却不上扣碗子蒸菜,只上炒菜,炒了八大盘儿荤菜。扣碗子蒸菜得等到晚上才上。
旱田的谷子又撵着撵着打了一天半,才打利索。
今儿的晚饭好像跟哪一顿饭都不一样,林翠平还想弄个蒸盆儿出来。席面儿除上蒸菜炒菜外,再上个蒸盆儿,口味儿就重一点儿。蒸盆儿是把猪蹄子跟炖汤的母鸡搀到一起,拿卤子卤好后装到搪瓷盆儿里,搁到锅里蒸,蒸的时间要长,得好几个钟头儿,是装门面的一道大菜。蒸蒸盆儿要用的肉,也都收拾妥帖了。
灶上有三口锅,里头一口锅蒸蒸盆儿,中间一口锅架蒸笼蒸蒸菜,外头一口锅炒菜。晌午饭一吃,把猪一喂,林翠平就开始蒸蒸盆儿,等蒸盆儿的肉蒸得差不多有五六成儿熟了,她把蒸笼架到中间锅里,跟着又装扣碗子蒸菜,把蒸菜朝碗里装,在碗里拼好,把洋芋、红薯、豆豉等碗底子压到蒸菜面上,压严实,搁到蒸笼里蒸。怕红肉不够吃,她多装了一个红肉。
等蒸菜也蒸得八九不离十了,田本珍她们姊妹俩儿先回来了,跟着,李为民他们两个儿娃子就把打谷子的板桶抬了回来。
大舅官儿他们三兄弟闹着要玩儿一下儿,就是要斗斗小地主,两个人斗一个人,输一把牌给一块钱,要是连输带炸,那就再加一块钱。李为民给大舅官儿煨火儿抱膀子,李为田给小舅官儿煨火儿抱膀子,见李为民给的烟才吃完,李为田就给三个长辈儿装烟,李为民又赶快跟着挨个儿递火儿。
地主正斗得热火儿,屋里喊叫吃饭。大舅官儿这回可是个大地主,正在扣底儿,叫唤牌上得鼻子不斗嘴儿。实际上,他是打马虎眼儿哄人,加上底牌,他手上有一对王四个二三个尖儿,稳当要炸输家两炮。可小舅官儿把牌亮了出来,说吃饭了再斗,害得大舅官儿喝酒都在念亏欠。
李为民他们兄弟俩儿烟酒不沾,喝酒也就是大舅官儿他们三兄弟喝,今儿有活路,昨儿晚上不敢多喝,今儿晚上好像要较较酒量儿,三个人喝了满满两酒壶苞谷酒。酒壶是装一斤酒的铜酒壶。炒菜都热了两回,蒸盆儿的汤菜还热了一回。
早上,天还没见亮儿,大舅官儿他们就起来了。李为民他们兄弟俩儿倒不见了,溜了,早就悄悄儿溜了,可他们却还没拿工钱。田大正叫大舅官儿给他们带工钱,可大舅官儿却说不妥当。
大舅官儿他们走后,田大正愣了好半天,他摸到李为民他们兄弟俩儿睡觉的屋里,左看一下儿,右看一下儿,到边儿到角儿地看,又到各个屋里细细儿看了又看,好像是看他们掉没掉么子东西,又好像是看屋里头掉没掉么子东西。怪,看来看去,屋里却没掉么子东西。他就是想不透,哪儿还有做活路又不要工钱的人,他们咋就悄悄儿溜了。他打算等把黄豆芝麻一些杂粮收到屋后,抽空儿再过一回河,亲手把工钱给他们送去。
隔天,大舅官儿却又来了,是来说媒。李福山请大舅官儿来说媒,想把田本珍说给他大儿子李为民做媳妇儿。田本珍她们姊妹俩儿上山打猪草去了,田大正他们两口子好大一气儿都没吭声儿,末了,田大正才说,娃子倒是要得,要得,两个都是好娃子。大舅官儿说,你是看上李为田了?田大正不吭声儿,憋一憋才说,你也晓得,我这屋里头就缺人手儿,也没得个儿娃子。大舅官儿说,你是说上门儿,叫李为田来上门儿?田大正又不吭声儿了,不吭声儿好像就算答应了。大舅官儿说,也该他们李家屋里有福,双喜临门。田大正跟大舅官儿说正事儿的时候儿,总是要拿娃子的口气说话,他说,大舅,这可不是说着玩儿,还请你过个话,看人家情愿不情愿上门儿。
实际上,大舅官儿他们走的那天晚上,等田本珍她们姊妹俩儿睡了,田大正跟林翠平也说起过李为民他们兄弟俩,说他们为么子不拿打谷子的工钱,悄悄儿溜了,是不是看上田本珍她们了,要是他们兄弟俩当中有一个肯上门儿才妥当。他们也说过大女儿要为田本珍找婆家儿放婆子的事儿,可都觉着二女儿跟幺女儿的婆子放远了不妥当,还是该放在门儿跟前。
说起来,他们一直都想屋里能添个放牛娃儿,可林翠平生来生去,都生不出个放牛娃儿。实际上,二女儿应该是三女儿,大女儿脚下又是个女娃子,生下来的当天晚上,林翠平就把她甩进尿桶,盖上盖子,闭死了。等幺女儿田本玉生下来后,林翠平就再也生不了了,要不,她非得生个儿子出来。
一晃,二女儿跟幺女儿都大人了,该找婆家儿放婆子了。说起来,田大正心里头还就一直想能跟哪家儿开个斢换亲,给二女儿放婆子,他就想谋个二女儿有个小叔子的家儿,好叫她的小叔子来上个门儿。田水沟儿的田地,到他下不了力的时候儿,总得有男将儿种啊。不用说,李为民弟弟李为田天生就是个做活路的好做将儿。看来,李为田的大名儿还真起得好,好像就是为了来种田家的田地。要不,李为田为么子不叫李为周李为龙?对他来说,来上门儿的李为田就是他家请的一个长工,也是他的儿子,他家大门儿的顶梁柱儿,还要给他们老两口儿养老送终。反过来说,要是李为田不肯上门儿,李福山请人来说媒,要给大儿子李为民说媳妇儿,就说球不成。
田大正喜欢在门口儿转悠,这个时候儿,在屋东头儿,他背着双手,眼睛有一下儿没一下儿地在看上山的路。有一下子,他眼睛好像花了一下儿,好像真看见李为田上门儿来了。
(责编:朱传辉电子邮箱:zch76110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