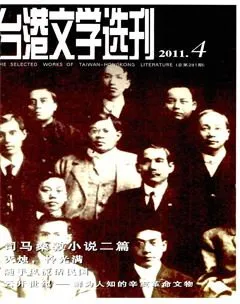沉香.寻香
2011-12-29董启章
台港文学选刊 2011年4期
李维怡拒绝自称为作家,更别说小说家,虽然她写得一手好小说,得过小说大奖,已经出版了一本中短篇小说集。她形容自己是一个“文字耕作者”。这绝对不是出于不必要的谦虚,更加不是自信不足;这和她的另一个身份有密切关系。李维怡是一个社会行动者,她通过录像艺术和纪录片制作,参与香港近十几年的种种社会抗争运动。像李维怡这样的行动者的特殊自我定位,在她的小说中可以清晰看到。她小心避免采取启迪者、救助者由上而下的姿态,与弱势人士站在同一位置同一高度,像劳动者一样默默耕作。
不过,我还是坚持称李维怡为一位作家,一位小说家。这并不是说作家或小说家有何超然之处,而李维怡符合这个超然的标准。李维怡和我应该也同样是汉娜·阿伦特(鄂兰)的追随者(我不敢说是“信徒”),那我就尝试用阿伦特的一套来说服她。阿伦特把人类的行动生活分为三个层次:劳动(labor)、制造(work)和行动(action)。大部分的弱势者、被欺压和被剥削者,也属于劳动阶级,而针对种种不公义作出社会(广义来说其实都是“政治”)抗争的,是较为少数的行动者(当然不排除劳动者自身变成行动者的可能性)。在其间,还有一批制造者,当中包括艺术品的创作者,那当然也包括作家了。制造者所创造之物,为人类提供一个实在的、持久安住的世界,并赋予这样的世界以意义。作家所做的,说穿了就是这样的一回事。根据阿伦特的分析,写作和劳动不可能是同质的,所以,“文字耕作”只可能是一种姿态,而不可能是实情。相反,写作和行动的关系更为密切。除了记录行动,反思行动,赋予行动意义外,写作也可以成为行动的促发和根据。由是观之,李维怡的两个身份不但没有冲突,反而可以互相增益。
在香港,在文学创作和社会运动两个范畴里,双重身份的例子很少。社运人士间中也会以诗文言志,而文学人也多少会触及社会性的题材,但两个身份同样鲜明,而且在两个范畴都同样走在前线的,却并不多见。李维怡可以说是非常独特的一位。她2000年以《那些夏天里我们的蛹》夺得台湾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中篇首奖,之后持续写作中短篇小说,在2009年结集为《行路难》(香港:Kubrick)一书。表面看来,李维怡的小说在形式和语言方面好像并没有特别过人之处,但这样的观感只是我们习惯了现代和后现代文学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法所致。令我最为惊讶的是,李维怡竟然承传了陈映真的现实批判和黄春明的乡土情怀。这种隔代和隔岸的渊源和影响,为何在此时此地开花结果,我暂时不敢贸然分析。在香港文学中,写实主义小说当然不是新鲜事物,早于五六十年代,一批南来作家便把中国新文学的写实传统带来香港,同时期的香港本土作家则有写实、现代和抒情等不同取向。自七十年代一批战后成长的香港作家冒起,形式创新似乎占了文学创作的主流,传统的写实主义的确逐渐式微。
2000年后才着力创作的李维怡,却“回到”写实主义的“老路”上去,骤看似是令人费解,但回顾香港最近十年的社会状况,又觉有其内在必然性。香港回归祖国几年后,因为旧区重建和历史建筑物的清拆,掀起了一波关注本土身份和社区生活的“新社会运动”。这场运动的主力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他们既非重建区居民,也非历史地标的怀旧者。他们所反对的是过度发展的港式资本主义,保卫的是家园价值和符合人性的生存条件。从喜帖街(利东街)重建(2003至2006),到天星码头(2006)和皇后码头(2007)抗争,再到反高铁和保卫菜园村运动(2009至2010),行动的规模逐渐扩大,参与的年轻人有增无减,甚至出现了所谓“八零后抗争青年”的标签。李维怡的大部分小说,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写成的。这种针对资本主义社会金权结构的批判,以及对社区关系和在地生活的维护,正好是陈映真和黄春明的隔代和隔岸延伸。李维怡师法两位台湾前辈作家,写出来的小说不但没有过时之感,反而给予写实主义新的活力和意义。而她最得益于两位的精髓的,是对笔下人物的大同情。
这次台湾出版的《沉香》一书,精选了李维怡三个中篇。最早的一篇是2000年联合文学小说新人奖的中篇首奖作品《那些夏天里我们的蛹》,中间的一篇是发表于2009年的《笑丧》,最近一篇则是发表于2010年的《沉香》。当中《那些夏天里我们的蛹》较为“文艺”,以写人物的成长经验和情感的幽微难解为主,虽也已触及社会议题,但着眼点为主流价值观对生活的渗透,而非个别的事件。《笑丧》摆明车马写社会运动的参与者,主角林曦由旁观和被动变为积极,女主角林采希更加是全情投入全心奉献的行动者。《沉香》采取的角度稍微后退,以大学物理系男生阿斌的角度,写普通人对社会不公由无知到觉醒的历程。很有意思的是,三篇小说也是以年轻主角的成长为出发点,结合了个人情感经验和社会意识的建立。他们或由于个性的独特不群,或由于某些事件和人物的触发,而拒绝成为合模的成年人,努力而艰难地寻找不同于主流的生存方式。这样的成长不是表面的反叛,而是对既有社会价值的怀疑,继而对受压迫者产生疚歉,并意识到自己对他人的责任。这些主角年少时出身低下层,学业成绩不错,都能接受高等教育,在社会阶梯向上流动到中产阶层(虽然现在中产也变成了一种劳动阶级)。可以说,他们都是享受到较优厚社会条件的年轻人,但却因此而自觉 到可能成为建制的共谋。当然也不是说他们可以完全自外于建制,于是质疑与谅解、批判与同情,便成为了必须同时并存的意识。
问题是个人觉醒虽然可能,但认知的深度和阔度毕竟有限,社会问题也不是一朝一夕,而必有其长远的历史渊源。为此,李维怡的人物也必须展开一场“寻根”的过程,也即是往先辈身上,找到理解目下问题的参照。在最早的《那些夏天里我们的蛹》当中,这种追本溯源的意识还未明显,只略一提及何宇漫的父亲年轻时曾经是工会分子。是以这篇小说的三位年轻主角何宇漫、何宇明和小碧,总好像处于精神孤儿的状态(事实上他们的确先后经历了丧母丧父的伤痛)。《笑丧》中开始出现前代的楷模人物。刚去世的三叔公年轻时曾是共产党人,1957年离开大陆南来香港,但心中的理想主义还未完全熄灭——三叔公给主角取名林曦,临终遗愿是在丧礼上播放《国际歌》。虽然没有详细描写这个人物(他没有正式出场,却是丧礼的主角),但三叔公对主人公林曦产生了深远微妙的影响。这种曲折的承传关系,也即是隔代和非直系的继承,也出现在《沉香》中。主角阿斌通过刚去世的太姑婆的遗物,了解到当年“自梳女”(女性自梳发髻,誓言终身不嫁的习俗)的艰苦命运和独立自决的勇气,以及二十年代大罢工被英军血腥镇压的来龙去脉。这一番寻根令他更明白当前的社会问题和自己可以扮演的角色。李维怡又通过太姑婆制造沉香,而上溯到香港历史的源头——香港名称的来由的其中一种说法,就是本地曾经盛产沉香,并外输至南中国和东南亚各地。
李维怡结合成长和承传两个主题,把年轻一代和前代先人重新联系起来,带出意味深长的信息——当下的觉醒和未来的走向,必须建基于对过去的认识和继承上。然而,当中的隔代和非直系传承,却有点耐人寻味。这是否意味着,香港的历史意识存在断裂,致使前人和后人无法直接地代代相传?而这个断裂,按小说中人物的年纪来说,为何大概发生在八十年代,也即是他们的一段蒙昧的成长期?这样的成长期就如一个蛹,封闭、内向、自绝于外部世界,但却可以孕育出新的更灿烂的生命。可是,这新生的蝴蝶却难以忆记自己的前身。人毕竟不是蝴蝶,人的成长不只取决于本能,而更取决于集体的回忆和族群的认同。这说明了承传的必要,和可能。
李维怡上一本书名叫《行路难》,标点出一个“难”字——行动之难,写作之难,以及兼顾写作和行动之难。这次新书名为《沉香》,我以为重点在“沉”字。这肯定不是低沉的意思,而是沉着、沉勾、沉潜。只要以沉着的态度,往历史和记忆的深处沉勾,一直沉潜的种种关联和可能性,就会回到日光下,明明可见,有迹可循,有路可依。这就是写作的意义之一。在广东话里,“沉”和“寻”同音;“沉香”即是“寻香”。香是根,沉着安稳;也是气,飘逸自在。再者,就是一种祈祷,一种愿望。
(选自台湾联合文学出版社《沉香》)
·本辑特约选稿 尤洋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