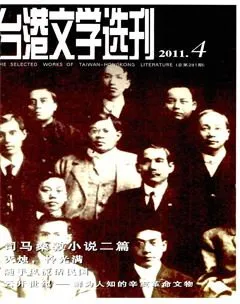拍痰
2011-12-29刘峻豪
台港文学选刊 2011年4期
来咳!用力咳!
接着是一连串急促的拍背声。碰碰碰碰,碰碰碰碰。只开床头小灯的病房内传出规律而响亮的鼓点,在左肺拍完之后节奏稍歇,中间插入一小段翻身时布料摩擦床单的即兴演奏,然后鼓声赶上两步,重新抢回主旋律。
碰碰碰碰,咳咳,碰碰碰碰,咳——咳咳。拍痰声与偶尔虚弱的咳嗽此起彼落,这是病房内常见的音乐会,像是部落祈神时的舞蹈,在火堆旁击打胸膛,最原始的肢体碰撞,希望透过灵魂与肉体的撞击,能够逼出体内带来厄运与灾祸的鬼神。
那些隐晦黏稠、散发着恶臭的,痰。
拍痰是对卧床病人长期照护的重点之一。死水般的分泌物窝居在幽暗的细支气管内,日日夜夜漫结蛛网,在病人的胸腔中形成聚落,张牙舞爪地伸出触手往外扩展。堆积的痰液又常是细菌的温床,日久如滋生蚊虫的池水,在X光片星空qSIo0X2gAnPepas4GODxHQ==般的底色下爆出片片斑斓的肺炎之花。
拍痰原多是照看的家属轮班完成的,而许多人与其被打乱整个家族的生活步调,宁可找医师开张证明请个外佣代劳。也因此在医院日日查房,可以看到除了病情进程之外的人情进展:从一开始挤满张扬的水果花篮与嘘寒问暖(但根本只有婚丧喜庆才会见面)的远房亲戚,几个星期后只剩媳妇女儿相陪,到最后连家属都很少出现了,留了一个外籍看护。
每一个病弱的老人,几乎身旁都有一位黝黑的外籍看护。大眼、微胖,略鬈的黑发。我总是无法区分她们到底来自菲律宾、印尼,还是其他东南亚国家,只知道她们大多羞怯而细心,且总是把身形藏在阴影里,仿佛她们只是病房中一抹淡淡的异国香水,没有实质地位。而早起查房时会遇到的人却总是她们。主治医师拉开帘子,让一声爽朗的早安与晨间淡淡的阳光一股脑倒进病榻上,会问正睡眼惺忪从一旁陪客椅上挣扎着爬起来的她们说:阿公昨天吃得怎么样啊?有没有带他出去走走?
除此之外她们很少说话,一部分是因为中文还不太灵光,另外也是她们总被定位为家属与医师之间,像答录机或接线生之类、常被人忽视的存在。医师要解释病情的时候,她们会慌乱地打开她们在附近夜市买的仿名牌小提包,拿出贴了水钻贴纸的廉价手机,小小声地用不流畅的中文打给她的老板,然后将手机交给医师。
在某些晴朗的黄昏,医院外的湖边常常聚集着还能坐轮椅出来的老人。在这治疗都已结束,却还不必急着回病房的时刻,常常可以看到湖畔轮椅排排坐晒太阳,上面瘫着面无表情的病人,像是晴天时从橱柜深处拖出来晾的冬天厚棉被,散发着霉味与湿气;他们身后母亲般的外籍看护则把握一天中难得的悠闲时光,与同乡用流畅的母语谈笑,完全不似在病房时的那种紧张羞怯。
偶尔下班时经过湖边,黄昏金黄色的静谧时光,老人们吊着点滴,或插鼻胃管,或做气切,在湖畔的微风里仿佛一排阳台上安静地晒太阳的盆栽。他们的外佣就站在身后聊天,阳光斜斜打在她们脸上,深邃五官映出坚毅的影子;而她们脸上线条和缓。这是一天之中,难得不用拍痰、灌食或更换尿布的悠闲时光。
她们喉中也卡着痰。她们远渡异乡,含着那块浓痰,口音混浊地学习陌生的语言,手忙脚乱做医师与家属之间的桥梁;每天在医院里替另一个痰声隆隆的老人拍背,过着缺少新鲜空气的生活。
却没有人想要帮她们化痰。
在这间医学知识建构出来的无比繁复的医院里,病床旁边的医师与家属来去匆匆,留下床上的病人与他们的外籍看护,默默地在剩余的缓慢时光中拍痰。比起医护人员,只会拍痰的她们懂得最少,却也懂得最多。
(选自台湾九歌出版社2010年散文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