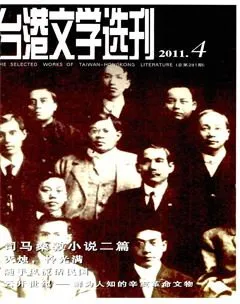离别志
2011-12-29吴妮民
台港文学选刊 2011年4期
我丢失了一本小书。蓝色塑胶皮包覆,口袋大小,封面英文标示着“麻州内科学手册”。这本小册子陪伴了我五年,并不属于阅读性质,而是有需要时掏来救急翻用。几年来,它的内页已经被翻得温润膨胀,纸缘起了细细绒边,纸面含有手泽,如厚厚的一叠旧钞,有令人安心的微暖湿度。
收假回来,它就不见了。原来应该放在急诊区的一个架子上,取走它的人没有归还。我看着那个书垛的缺口,弯身寻找,架子前后目光逡巡了一回,蹲下来歪着头,在满是尘埃的地面查看它的踪迹,里里外外皆翻遍,还是找不着。最后,我在墙壁上贴了协寻启事。
那日上班,因为这本失踪的小书,心神总是不宁,而且有一种怅怅的失落感。我想念它,并非在意重新买一本最新版的额外花费,而是因为那上面有许多不同时刻草草写就的笔记:一些正式的原文书里不一定会提到的小技巧,前辈们积累的经验,和一些无关紧要的注意事项;还因为我熟悉它的页码,不致迷路,可以马上找到我要找的内容。
于是就这样和它分别,向一段从医学生到住院医师生涯的微小见证说再见。不只书,想起那些一路上丢失的物事,有些甚且更微渺:一支笔,一个水壶,一把雨伞。它们会在失落的当下被惋惜,也许几分钟后就被忘记。因而母亲常说:“要回头望一下啊!”于是在起身,或是下车时,就会转过头去看看遗落了什么东西。童年好友性格迷糊,随身物品沿路失踪,她母亲骂她出国一趟回来只差人没丢掉。我被念怕了,真的就养成了那样的习惯,看着一路长大的自己,仿佛眼前看见一个小女孩起身离座,一次又一次地回头,再回头。
有时它则如此庞然。
离开台北的屋子前,话语中,母亲开启衣柜,出示那些她预先为阿嬷准备着的衣物:一顶紫色的绒毛圆帽,被收折好的一件粉红色条纹衬衫,和一条棉裤。我想象阿嬷最终穿上这几件衣服的模样,她即将戴着那顶紫色的帽子,孤身一人,闭目躺在床上。
我们行驶在秋天的街市中,晨起苍白的天光,透穿进计程车窗。母亲送我搭车离城,沉默中,递来一张纸。我从头读完,一份还未签署、栏线空白的同意书。
母亲终于放弃了。或者,她终于准备好,愿意不再尝试任何阻拦地、让阿嬷静静离去。曾经,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日里,母亲用尽她所有的气力,与父亲两人数十次合力来回移动阿嬷于医院和家中,化疗、静养、回诊、急救。彼时,父母将生活切割成两部分,吊桶似的轮流上班,下班后在病床前守望、喂食、清理。在四个孩子中,母亲作为惟一的女儿,尽了最大的责任,她将阿嬷照顾得如同婴孩般干净细致,便溺后拭净阿嬷的臀部,扑上粉;平日用乳液按摩阿嬷肌肉萎缩的细瘦四肢,细声细气哄骗阿嬷如什么事都未曾发生。
事情要翻转回前一年的夏天。长居乡间的阿嬷突然没有因由地消瘪下去,暑气正炽,她却渐渐地什么也吃不下,右脚且如充水的橡皮管般逐日肿起。与阿嬷同住的小舅夫妻先将她带至小镇上的诊所检查,未果。接着他们将阿嬷扛抬至火车上,由火车载运阿嬷到台北来。
阿嬷先被送进急诊室。母亲苍老疲惫的声音在清晨敲醒了我的梦境:他们在阿嬷的腹内发现了数个大小不一的肿大淋巴结。之后,住院月余,厘清切片结果为恶性淋巴癌后,开始化疗。
隐隐然有一条线绑缚所有的人。我们无法飞行,不能移动。父母的作息在接下来的年余里,仿如被螺丝拴牢固定,不得松开挪移。他们环绕、围守在阿嬷的身边,再没有喘息。阿嬷的病况时好时坏,她的身体机能却不住衰败。不知是疾病或治疗造成的结果,她的记忆是一片沉默的海洋,任何探问都向下沉没,偶然浮出水面的只有阿嬷似是而非的回答。
她的双眼亦逐日晦暗。原先就有的白内障,病中急遽恶化,最后连光源也无法辨明。她不能起身,听觉是她的最后窗口,所以我们买来MP3,大量存入阿嬷年代的歌谣,希望铺卷在枕上的两条细长耳机线还能输入一些快乐的感知。
我们叫唤她,她颤巍巍将脸部转往声音的来处。
够了—— 那阵子我与母亲常争吵 —— 你明知阿嬷腹内的淋巴结与那些恶意的转移都是不会消除的,就不要再做JyxgnuhiOSslC1/qaX0e51oUu2MlWC6LazYGqS4tTjs=无谓的治疗了。何况,阿嬷的住院医师——我的朋友,曾经私下向我说明:“你阿嬷身体太虚弱,现在的化疗剂量已经不足以杀灭癌细胞,却只能带来副作用。” 我看着孱弱的阿嬷,为了这些注定无法根治她的癌源的多次化疗受呕吐之苦、无食欲之苦、感染之苦。翻过身去,一条经皮肉穿刺的导尿管从她的胁侧伸出,连接床侧悬垂的尿袋。而母亲说,她怎么可以还未试过就放弃!这些治疗不是为了要根治阿嬷的病,是为了让阿嬷再多活些时日。我说,阿嬷在床上拖磨,有什么生活品质?母亲斥我无情,她说阿嬷怎会要求所谓的生活品质,她要的是阿嬷再陪伴她一段时光。我说,化疗是在治疗你,不是在治疗阿嬷。
彼时,我变成一只天际低飞挣扎的风筝,双脚化成棉线,紧紧抓在母亲的手里。我在往返台东的铁道上,在京都的旅馆里,总接到母亲无好声气的电话:你在哪里?你阿嬷都生病了你还有心情出去?这时候有要紧事问你为何老找不到你人?她边说着,边与父亲七手八脚地以棉被包裹阿嬷准备上救护车送急诊。阿嬷病重,不远游。这是母亲的指责和要求。我知道母亲照顾病人的辛苦,并愧疚于在外地上班的我没有尽到照护的责任,然而同时我也无奈与充满自私地愤愤着:难道家中有人患病,所有人便得放弃自我与自由,像行星般不断地围绕着同一颗恒星回转吗?母亲的限制让我不平衡。那时节,我担心这场看似没有尽头的疾病战争,就要像行星运转的轨道一样,将无止息地往前延展、再延展。
所以,母亲终于撤退了。在阿嬷的身体迅速地败下阵来以后。我指示母亲应在哪里勾选她不要的急救项目,在哪里签名。
丢失了书的那日,我由急诊室下工,隔天傍晚在轮值夜班的周期中醒来。照例打电话给母亲探询阿嬷的病况,母亲却意外地在话线的另一头泣不成声:“你阿嬷叫不醒了。”阿嬷的意识沉没了。她的呼吸缥缈到难以察觉,氧气需由面罩一波波压挤入鼻,气流吹得她薄薄的嘴唇一掀一翕。父母迅即决定将阿嬷送回嘉南平原上,位于旧廍里的老家。于是我搭上火车,由台南向北。彼时救护车载着阿嬷,正在往南的夜间公路上疾驰。我在心里默数这些时日,迢迢赶赴与阿嬷最后的共同交点。那夜,深重的露水已经降临平原,风从平原的角落刮卷而来,一蓬蓬地打着我的头发。我坐在许久未见的舅妈机车后座,抵逆着风在产业道路上前进。
后来,我们陆续地梦见了阿嬷。她到她大陆媳妇的梦里,指示要向某人讨她生前未结的款项;我则在天亮醒来之际,替阿嬷跑腿买她不见得爱喝的咖啡,也梦见早不能行走的她青肿着脸,走来向我们说她又从床上跌落,我与父亲遂紧张地替她缠紧肚腹,怕她腹内的肿瘤破裂出血。连我这个常忘记阿嬷的外孙都梦见了,惟独母亲没有梦。阿嬷去后,母亲变得擅长走路。她打来电话,说她又镇日不停地走,从一个街区走到另一个街区办事,却浑然不觉疲累。话筒里,母亲重复讲述着她一天的经历,忘记她昨天说过同样的话语;她亦变得善感,说几句话便开始嘤嘤哭泣。阿嬷用过的便盆、面纸、针筒和睡过的床 ,母亲未有搬移,让房间陈设维持阿嬷前往医院前的最后模样。
还是会不舍啊。母亲道。
离别的伤感因而巨大。那是一个日期,一个名字,一段时光。离开的当下,彼此生命都将断裂。我们承受那扭曲与断裂。事后当我们开始回想,那断代史的切口与起迄,附近所有的物事或象征都因剧烈的扭转而变得清晰异常。所以我们一再一再回想,仿佛世界就可以回到原初设定,相遇的起点,交会的刹那。
记起冯内果的小说,那里世事被摊成了平面的卷轴,纹理可以被透视,因果层次分明。因为看清了事件纷呈的转变,人物的到来或离去,似乎就能理解某些看似乖违的荒谬,或许,可以拯救我们措手不及的伤悲吧。
所以凡事注定要终结。那些生长中的,等待盛放之后,终究离死亡愈来愈迫近;人们遇合如相切的圆轨,我们朝向彼此而相互吸引、加速,接着擦撞、交会。偕行一段,然后不可避免地预视分离的到来。如同一个男孩说他非常爱我,那时我们已轮回般经历了暧昧、兴奋、热烈、忧愁与哀伤,但我看得出,下一刻,他就要走了。
每一样时间中的物事都在变化。它们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细微的、难以觉察的变动。
宇宙亦然。
守过一夜,阿嬷的事结束后,我们就从旧廍的老家向岛屿各处四散,每个人收拾混沌,暂时回到了自己的生活轨道。再回急诊上工,是送走阿嬷的当日傍晚。隔了一段疲惫的睡眠,醒来觉得和白日的事仿佛相距久远。阿嬷没有惊扰了谁,她在我两次值班夜的间隙悄悄离去,以至于当我回返工作岗位时,无人知晓我刚刚历经了一次重大的离别。
身上还有一些情绪的残余,我安静穿行喧闹如常的急诊室,纷杂的人声和机器运转声充腾饱满了明亮如白昼的空间,似乎什么也不曾改变。绕行至前两日我张贴了协寻启事的墙面,无意间,一抹蓝影闪进我的视线,我惊喜地发现那本小书竟回来了。不知那时是谁取走它,或是谁发现了它,在外流徙两天的手册,如今安好地插在过去失落它的缺口里。
曾经离开的又回返来。我看着它,嘴角扬起,感到一阵心安。那样的踏实没有过分张狂的兴奋,却像是一个难忘的故人,微微笑着,无恙地向你走来。
(选自台湾九歌出版社《迷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