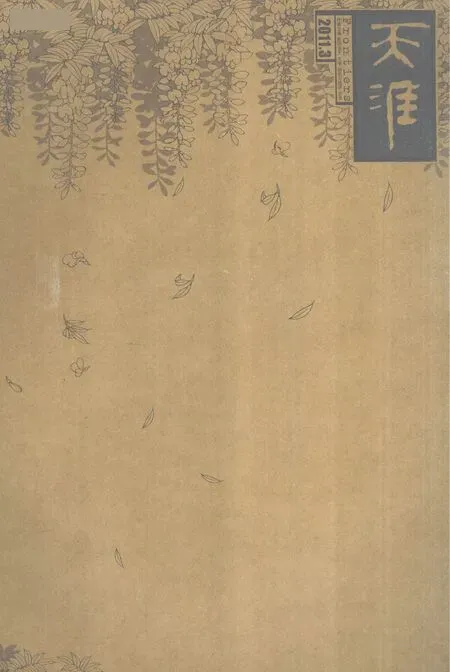哥哥
2011-12-26袁凌
袁凌
烈日下面,平运司的院子很静,滚烫的地上小团的油洼,黏稠得放光。
那些敞开或拆散了的卡车零部件要融化了。光线刺眼,修理车间下却很黑暗。我望了一会,没有看见一个人,心里起疑,似乎我来到的并不是平运司修理厂。就在这时,一个人的头顶从我脚下的地面露出,渐渐地上升,稀少的头发盖不住油亮的顶门心。他往上升着,现了鼻子,发红地淌着汗,顶尖一点油污。我发怔地看着,忽然明白这就是我的哥哥。他正从一条地沟里出来。
哥哥也看见了我,他望着我,身体仍然一步步升起来,蓝色的工装或者近似于蓝色的劳动布工作服,肩肘下摆粘着油污,手上提着一个扳手和一个工具盒。“袁凌啦!”他在地沟口站住了,神情是我熟悉的若无其事。我往近走几步:“在修车啊。”
“我下班了啊。”哥哥说,“走。”
昨夜我来到陈家坝附近的街口。据说,哥哥就在这里,但我并没有看到讲述中的院子。我顺着一条上坡的巷子走,走了一截灯光暗了,远处有隔着围墙的院落。我继续往里走,走到尽头有一盏灯,一个堆着木器的小院。有两个人在堂屋聊天或是做什么,都坐着小板凳,让我莫名想到剁猪草的场景。告诉他们我找袁剑,他们说不认识。又问我是谁,我说起父亲的名字,他们说哦袁登凯呀,点点头。心里燃起了一丝希望。“那你认识我父亲?”“不认识。听说过的。”他们似乎是从乡下来做活路的,对附近并不熟悉。我走出院子,走到有一棵高树的地方,停下来喊了两声“袁剑”。像有什么人答应了一声,再喊却一点回音都没有了。周围不知道是什么单位,灯光稀少。高树的影子落在我身上。
“是跑到哪去了呢?总是土产公司院子啵。”
我问哥哥有没有听见喊,他说没听见。
过马路走一截上坡,两座拱形屋顶的平房,似乎是苏联来的式样。“我就住在这的。”
两座平房是单独的,水泥和沥青的拱形屋顶暴露在阳光下,像一个仓库。我想屋里一定非常热。屋对面不远是一个废品站,成山的啤酒瓶闪着深绿的光,就像不是真的。
屋子的门窗向里,是窑洞式的。意外地看见表弟秦金鱼在门前一个水龙头下淘米,水龙头附近的草地被污水泡黄了一块。污水还顺着我们上坡的小路细细流下去。
“秦金鱼还不是住在这的。”哥哥凑到水龙头下洗胳膊,一边说。
秦金鱼看见了我,显然也很惊奇。“那我还要多淘点米。”
“你不是在西安唦?”
“回来有一个月了,在县上有点事情。你分到法院了啵?”
“嗯。”
屋子里果真不一般地闷热,虽然门窗都开着的。“白天这屋里直接呆不得呀。”老表说。“到傍晚就好了,这屋子晚上凉快。”哥哥说。“凉快个啰。要是睡在草坝上,怕还凉快,我都想睡在草坝上。”“你喂蚊子啵。”哥哥说,“今天我们做点啥菜呢?”“你就是这些品种。盐好像都没得了。”“盐么,买一包就是,未必买不起?”
屋里放着一张床,对面是案板,放着一个炒瓢。床上很乱,有一件毛衣搁在床尾做枕头。我在床头发现了一本原属于我的书,米兰·昆德拉的《好笑的爱》,书翻到亚罗米尔和他的红头发姑娘做爱的段落。这正是我回家想找没找着的书。床上还落着几颗围棋子。
几个月之前,我知道哥哥从技校毕业,联系到了自来水厂。我也即将从所在的大学毕业,面临着发回地区人事局统一分配或者自己联系单位的局面。我联系了家乡这个县的法院。
回家时知道哥哥离开了自来水厂,那里工资太低。父亲有一个朋友在平运司当经理,联系好让哥哥进公司学修车。“好不容易让你进去了,可是要好好学,学好了,修车是挣钱的职业呀。”
“看师父肯不肯教。”哥哥说。
“只要你尖心,虚心,看到看到也学会了嘛。”父亲有些不满地说。“人家陈平娃子,在平运司对面修车,主要就是换个胎补个胎,两三年挣了几十万了。”
哥哥低头吃饭。
哥哥很快把饭菜做好了,居然还有三个菜,酱油醋都有,油是一块肉熬出来的。表弟做他下手,用一个铁刮刮刮洋芋,“你还是刮干净点唦,还是花眼睛啦?”“你这个刮刮像个么啰,你怕是在那个废品站拣的白铁折了两下。”“你不会刮啵,我这个铁刮刮还是在姐姐那儿拿的。”炉子在门外靠墙放着,炒洋芋片的时候夕阳照着哥哥的眼镜腿,起了一层油光。
“好热呀,吃了饭下河洗个澡啊。”吃饭的时候他说。“修车累不累人?”“哪有不累人的?不过活路不多,师父不肯教,做些小活路。今天给他擦了半天车。他个人两句话一甩,手往尻子上一背就走了。”“你经常呆在地沟里?”“修车主要是两项,一项车头,一项车肚子。车肚子出毛病了,就指靠呆在地沟里整。今天我在车肚子底下呆了半天,给底盘上油。”“地沟里是不是赶地面上凉快些,好躲荫。”表弟说。“哼,你去试下嘛,一纹丝风没得,跟人家烤羊肉串的槽槽样的。”
三个人朝河坝走,穿过修理厂的院子,遇到一个中年人。“你把车擦好了哇?”“嗯,我都擦好了才出的沟。”中年人不出声地走了。“这是你师傅。”秦金鱼说。哥哥嗯了一声。修理厂后面的围墙有一个豁口,三人穿过豁口来到了河滩,这里砂土很多,一些砂窝里爬着瓜秧,另一些地方长着发白的草,晒得半枯。
河出现在我们面前,宽广的、漆黑的一幅,闪着幽黑的光,黑暗表面有一些白沫。我和表弟有点发呆。
“这能洗澡?”过了一会儿表弟说。
“这是碱,正好消毒呢。”哥哥说,一边脱下了他的工装。他的背心扯在厚实的肩背上,有个地方破了一个小口。
我费力地回想着,似乎昨天经过大桥时河流并不是这个样子。在县城上游有一个造纸厂,我一直以为它倒闭了,看来它又在排放碱水。
我看着哥哥往河里走,他的下身浸入了乌黑的水中,然后是膀子,一直到只剩下头。他游了两下,在水里站住了。“你们下不下来洗?”
我看看表弟。“我不洗。”表弟说。我又看看哥哥,他的手正在乌黑的水下搓身体。“这又不脏。我经常洗啦。”他说。石滩上实在太酷热,我迟疑地脱下衣裤,进入水中,水一步步淹到了胸口,和平时的感觉没什么两样,只是它是黑色的。刚才在岸边已经闻到隐约刺鼻的气味,眼下这种气味变得明显了。我像哥哥一样撩黑水洗自己的肩背。
“你真的不下来呀?”我望着表弟说。
“我回去用水龙头冲。”他说。
我看着表弟坐在滚烫的石头上,人显得瘦,阳光将依附在他脚下的影子削去了一些。上一次看见他是在家乡的老房子里,我和他睡一个床。“我们上一级有些同学当了导游,一个月挣一万多。”他说,自己也想考导游证。有些同学家里有钱,自己拿几万块钱去留学,回来工作就好找了。表弟说,他现在一心只想的这些事。在学校的时候,班上也有两个女生喜欢他,他都没理会。“我要是有个五六万块钱,去日本留学就好了。”说完了这句话他就沉默了,睁着两眼望着屋顶,双手枕在头下,听着窗外老梨子树的沙沙声。
当时表弟刚从西安一个涉外宾馆回来,在帮家里挖洋芋。对于他离开那个宾馆,亲戚议论纷纷。“我原来是在接待部,每天接待老外,还有机会和老外聊,练些日语。后来来了一个有关系的,他们就把我调到餐饮部,整天擦桌子。你说,我为啥子还要在那干?”
后来表弟一直没找到什么好的工作,在西安呆着没事做。
“你在县上有啥子事情?”我一边打肥皂一边问表弟。
“大哥说是县上饭店里有个工作,叫我去联系一下。我也没得啥兴趣。”
表弟似乎不愿多说。我回头看看哥哥,他竟然在用黑水洗头。我没有他那样的勇气,只是多擦了几遍身子。白光光的太阳底下,县城似乎在发昏,大桥和菜地里都没有一个人影。我和哥哥光着站在一条黝黑放光的河流里。
第二天回到哥哥那去,他的一个高中同学在。
“这是我弟弟。”
“就是你说过的啵?”
“嗯。我们家老幺呢。”
“那你这个哥哥当得好,等到兄弟一年毕业。人家是大学毕业,你技校毕业啦。”
“那说得成,我妈她要把我生笨些,有么办法。”
同学坐在院子里,不愿进屋:“我这里还凉快些。干脆吃饭也在这。”
太阳落到棚屋后边去,微风吹动了同学的白衬衫。
“路口有一家店,凉菜还好吃,去买两份来,还能凑个盘子。”哥哥说,“再整几瓶酒,本人再亲自做两个菜,滋味么子要不得。”
“晓得你的手艺么样。”
“那我的手艺可还不咋的。”
哥哥掏出十块钱,让秦金鱼去跑腿。一会他提着两个塑料袋回来,一个袋子里是冻肉,另一袋是猪肝。
桌子在草地上摆好了,白沫从啤酒打开的瓶口流出来。同学提议一人一瓶,我和表弟连忙推辞,后来找出了两个杯子,一个玻璃杯一个瓷杯,哥哥和同学拿着瓶子对吹。同学很老练地为我们倒酒。
“你的酒量在技校还算是高手?”他随便地问哥哥。
“不行啦。那里喝酒的歪角色多。我们算是不行的。”
“说你在那里是老大唦?”
“你才是老大,我们这样的老好人当得了老大?”
“我还不是老好人。”同学喝了一口酒。
“你是老好人,我信,我的毬都不信。”
“我们学没上好,分到这样的孬孬单位,一个月工资遮不住手,莫说惹那个,酒都要在你这讨到喝,不当老好人当啥子?像你弟弟他们不一样,是国家的栋梁。你修车也有经嘛!”
“有卵经啦!”
“说是说,将来你修车挣大钱,苟富贵,莫相忘啊。”
“嗯,我发了大财,你娃子上门来,我直接装认不到啊。”哥哥大声说,夹了一大块冻肉。他的手没有完全洗干净,拇指和食指间留着机油的痕迹。
草地上真的凉快,有些飞虫擦过腿杆。
吃完了,桌子搬了,空的啤酒瓶子还留在草地上。同学拿起一个,哥哥连忙说莫扔了,他屋里还攒了两个,待会提到对面收破烂的地方:“还不是能换瓶酒,喝起来未必没得买的好?”
“他怕是一年要挣些钱啦。”同学望着那边说。那边场面似乎比我头次来更大,除了垛得整整齐齐的酒瓶,纸壳子也堆了半间房高。
“哼,人家收了十几年,银行存了几十万了,喊的是平利县的破烂王。他又姓王。看到是个不起眼的老头子。”
同学出神的样子。
几个人走到大桥上。
这座进城的大桥非常长,两旁曾经装满了路灯,却被平中和二中的一班弟兄们尽职尽责地一盏一盏瞄准砸碎了,使用的武器有石子和弹弓,一时间“到大桥上练靶子”成为流行口号。最后路灯无一幸存。傍晚的大桥显得更长,有微微的凉风,人们走过来又走过去。都穿得很薄,女生们带来若有若无的气息。同学忽然说:“我们拦住两个女生,验一验脸盘子咋样?”
这提议使我心跳。那天我们并没如此做,只是靠在栏杆上,看着三三两两的女生走过去。
大桥上竟然有几盏灯亮了起来,这一定是在那几年之后新安装的。那些女生仍旧那样走过去,现在是朝回走的多。
“我们在中学的时候,经常是这样的,哪个女生还敢说生气啰?”哥哥说。
“生气?你试下,遇到和尚他们那样的,把你往大桥底下拉!”同学说。
和尚是当年平利县第一好汉,因为犯强奸、杀人罪判了无期徒刑。和尚的人马叫斧头帮,每人一把斧头,都是十三四岁的小娃子,下手就是往死里砍。一次火拼中死了人,和尚被定为主犯。和尚之下的第二条好汉是辣子瓣,平中学生,辣子瓣的人品却比和尚好上十倍。
哥哥目睹了辣子瓣单挑“高氏三雄”。“高氏三雄多厉害的角色,随便哪一个都能打四五个。那天他们把辣子瓣惹毛了,辣子瓣叫他们一齐上,一张课桌促翻,他们一人拿一根桌子腿,辣子瓣拿第四条桌子腿一对三,三个人都打趴下了。”
辣子瓣在学生中特别有威信,连老师都说他是个好青年,有正义感。他脸上有一条很深的刀痕,是在安康火车站“英雄救美”负的伤。那天他在火车站等车,看到三个痞子调戏一个妹子,他上前制止,开始还是言语相劝,人家认得到他是哪个,指缝里藏的刮胡刀片,顺手朝他脸上一下,顿时满脸是血。这下他火了,一顿扫堂腿,三把两下,那几个痞子打倒在地,要拜他为师,他袖子捂着脸转身就走,救的美是哪个也不知道。
从高二的时候,老师就劝辣子瓣当兵,辣子瓣却坚持上到了高三毕业。虽然脸上有那条刀痕,他还是入伍了。他走之后,哥哥他们那一层人也接着毕业,那个时候也就过去了。
哥哥是辣子瓣看得上的人,陪他喝过酒。“啵,喝酒的还有他,你莫看他小,他还不是厉害的很。”哥哥嘴角呶着同学说。
“我是不行,哪个都打不赢。”同学说。
“你轻易不打啵,那回你跟胡汉三打,我在边上看到的啦。”
哥哥说,同学人看到小,反应很快,会冷不防下死手。和胡汉三那次决斗,胡人高马大,还在扎势,同学一边说你这么歪我不跟你打,一边却一酒瓶砸在胡脑袋上,胡立马昏倒了。
哥哥那些年的事情,我一点也没有涉及。只知道母亲去世的那年哥哥跟同学用搪瓷缸子喝酒,一口气喝完一缸子,吐血了。那时他的女朋友也分手了。
这是我上次回家在哥哥的日记中看到的。哥哥毕业之后,带回来一些书和本子,和我的混装在一口箱子里搁在家里阁楼上。我没找到昆德拉的小说,却看到了日记。日记是断续的,在记载他“生死关头”的那几章后,写他终于又能走在街道上,看到树梢上面的一只鸟,感到这只鸟非常的新鲜,自己的生命却似乎陈旧了。“我究竟还有没有新的开始呢?”哥哥用他那粗大的显得忠厚的字体发问。
几个人走到了操场坝,操场坝上一簇一簇的人,都是衣裳轻薄,像一些草地上微白的花。我们也坐下来,聊了一些不知啥子。
有一个女生走过来,微笑地叫了哥哥一声,哥哥就站起。她说某某托她向哥哥问好,哥哥哦了一声。她就仍旧带着若有若无的微笑走开了。哥哥坐下,说是技校的同学,现在分到一个什么单位的。向哥哥问好的是另一个外出打工的女同学。“是你的马子啵?”同学说。“莫乱说,是认交的妹妹。”
“你妹妹怎么不跟你多讲话呢?”
“人家现在是单位上的人,打交道的时候少么。”
又这样坐下去,说一些话,话越来越少了。似乎这样是不够的,我总觉得应该有一些什么事发生。什么人会认出哥哥和他的同学来,带我们去一些地方。我也担心有人会叫走哥哥,把我们留在这里。但是两种情况都没发生。
回去的时候,同学忽然说:“你干脆跟我们一路下去,就在你哥那儿歇。”
我有点犹豫。我暂时住在法院办公楼上,同住的人这几天下乡了,整幢大楼里只有我一个人。走廊里挂着一溜“会议室”、“经济庭”、“刑事一庭”的牌子,夜风吹过呼溜溜地响。前两天刚听说,去年隔壁房间里有个书记员跳楼了。
“下不下去?下去我们三个人挤一个铺就是的,铺宽。”哥哥说。
我跟着往下走。
同学在陈平的换胎铺子前面分手了。“轮胎码了这么高,人家的钱可是挣够了啊!”他说,“你带弟弟哪天下来玩。”
他脚步轻捷,扎住两个襟脚的衬衣飘着。
站在阶沿上对着水龙头洗脸,附近的院落灯光黑暗。想到那天我走错的小巷子,也许只是隔着两层围墙。我的喊声这里为何没有听到,我依稀听到的那声回答又是谁。
睡觉前想上厕所,哥哥说要不要陪你?我说自己去不就行了。表弟说那个地方我是不敢一个人去。三个人一起去厕所,打着手电,我和哥哥蹲着,表弟对着什么地方撒尿。我无意中向后一看,黑漆漆的一方棺材的大头,三口棺材黑暗中整整齐齐叠成一个“品”字。
“这棺材放了多少年了哦?”
“我头一回来,硬是听到棺材里有动静,吓得我皮带一提就跑。”表弟说。
过两天再下去,表弟已经走了,去西安找工作。我又在哥哥那过夜。
哥哥的铺上有一封信,淡蓝色的封皮印的有花纹,我趁哥哥洗脸打开了这封信。是在外打工的一个女同学写的,说自从毕业后到了东莞打工,在一个塑料厂里。那边天气很热。因为不知道地址,到现在才写信,请你原谅小妹。“想起在学校的日子,忘不了你兄长一样的关怀,你总是像大哥一样照顾着我们这些小妹妹。忘不了你带着我们偷胡豆的经历,又紧张,又兴奋,跟做贼似的,现在这种事情像离得很远了,好多同学也不联系了。”
信里提到毕业前夕学校不发技工证引发的风暴,“那次我们女生都吓坏了,还是你们男生勇敢些,领着大家争取权益,自己却吃了亏。”
哥哥洗完了脸,我问他这件事,知道是学校食言,那一届的三个班没有技工证,结果教室的桌子腿都卸下来了,还买了十几把菜刀,公安局来抓了七个人走。最后学校答应补发技工证,但为首闹事的不在其内,哥哥没有被抓,却也拿不到技工证了。所以当时他没有即刻出门打工。
哥哥点好了灭蚊片,关紧门窗,我们坐在收破烂场地旁边草地上。陈家坝一片黑暗,对岸猫儿沟有几点灯火。
“爸爸说要在这里买房子,叫我留心一下。”哥哥指着坡下不远的黑处说,房子就在那里,门面比较小,但有三重进深,带一个院子。
哥哥说,爸爸的意思是我分到了县上,哥哥也在平运司,姐姐姐夫早在城里买了房子,他也在这里买个房子,以后搬下来都在一块。
哥哥看了之后告诉了爸爸,爸爸嫌门面小了,想在猫儿沟口买房,安静些。
对面的猫儿沟我和爸爸去过一次。从城东酒厂出发,路贴在山崖下,一边是河,坎下闪着微光,似乎有鱼起跳。走到沟口忽然开阔,两岸排列着几所宽敞的白粉瓦房,每一座都灯光明亮,其中一座发出细微的嗡嗡,是风车在扬谷子。
那些屋子的灯光似乎一直明亮,到了现在。我想,它们一定也给爸爸留下了深的印象。
“你还下不下围棋了?”躺在床上了我问哥哥。
“哪有人下啰?”
我想和哥哥下一盘,但知道他不肯下。
哥哥和我各躺一头。比起上次三个人躺一铺,似乎又不是很热。虽然烧了灭蚊片,为了要凉快些门窗都开着,蚊子还是要进来。
我说那灭蚊片不是白烧了。
“它留的气能管用。”哥哥说。
一关灯蚊子就扑来了。时候晚了来不及买蚊香,索性开着灯。躺在铺上,哥哥响起了鼾声。
大篷车在街上兜圈子,宣传南方某著名马戏团来我县演出。马戏团就扎在操场坝,搭起了山一样高的帐篷。帐篷四周围起了栏杆,门口有高音喇叭的节目介绍和穿着彩衣,操着四川口音卖票的。
三个人靠在大桥栏杆上歇凉。河流恢复了平常面貌,不动声色地流着。哥哥说到前两天来了一个麻衣相法的瞎子,从湖北过来的。“他一摸我的骨头,说我三十二岁上要发横财,想躲都躲不掉。”哥哥现在二十九岁,还要等三年,“还说我要发远方的财,家乡没有财运。”
“现在这个社会,发财就要发横财,不然我们这些人,不像你弟弟他们学上出来了,有知识,老子又没得权,哪里去发财。”同学说,“我们班上有些娃子在那边贩毒哇,说是一趟搞成了能挣十万。”
“一趟十万,叫你贩毒,你搞不搞?”同学问哥哥。
“我不搞。抓到就是枪毙。我又没得两个脑壳。”
“我搞。十万块钱,我在这个单位一辈子也挣不了那么多,出一趟车才二十块钱,饭还要自己买到吃。脑壳掉了碗大个疤,只要我享受了,用了,这辈子也值了。”
第二天我和哥哥站在修理厂门前,看到马戏团的两辆卡车驰过,掀起劈脸的尘土。车斗里站着昨天那些表演的小女孩们,她们脸上仍然化着妆,被一无遮盖的烈日射着,汗道道流下,妆完全混乱,成了一张张鬼脸了,没有妆的地方晒得黑红黑红。她们的衣服也堆满尘土,失去了本来的绿色。哥哥说这些小孩都是四川来的,一天只有几块钱零花钱。今天她们是去安康表演,下一步又不知道去哪里。
哥哥穿着工装,提着一个扳手,但是没什么事情做。他的师父在修车头里的电路,并不要他打下手。
林英华和我们在哥哥租屋门前的草地上吃饭。她穿着一身暗绿色格纹的衣服,使我想起上学时抢枇杷的事。那天,她带了两衣兜枇杷到教室,不知被谁知道了,于是忽然地,十几个男生扑到她身上,把她压倒在地,十几双手伸进了衣袋裤袋或别的地方。她在底下叫骂着却动弹不得,我也跟着大家,居然能攒入兜底掏出两枚枇杷,自己也奇怪。林英华起来后声泪俱下,痛骂了半天“流氓”,却不知道找谁算账。
她刚从天津回来,不打算在那里干了。她打算在李家坝街上开一个缝纫店。她代表二妹来看望哥哥,和我们一起吃饭。二妹是哥哥以前的女友,师范毕业分配到一所学校教书。“二妹本来要和我一起来,但是学校明天就开学了,她赶回去了。”
二妹在师范念书时,我去她宿舍玩过一次。二妹桌上有一张照片,头发垂到腰际,笑容可掬地端着一杯水。我觉得她真是美丽。这张照片后来我在哥哥的影集里发现了,再后来又不知去了哪里。
哥哥和林英华都喝了些酒。
那天正好过月半。晚上我和哥哥到姐姐家去。哥哥说想过几天把被子拿上来,请姐姐拆洗一下。姐姐说被子已经盖得没得搞了啵,哥哥说还是好好的啦。
哥哥走了以后姐姐说他懒,“被子是从我这拿的,拿下去后就再没洗过。热天的毛巾被也是盖得脏透了拿上来的。虽说我这有洗衣机,我还不是要搓啥,有些地方污的机油,搓都搓不干净。”
“爸爸前天打电话说,袁剑在平运司表现不好,不踏实,师傅不愿意带他。刘叔亲口对爸爸说的。爸爸费那么大力气给他找这么个机会,人家想都想不到,他不好好搞。”
我和哥哥到同学的宿舍去玩。
同学的单位里有很多隔开的院落,一道道的月亮门,他住的那间小院没有别的人,院地上没有植被。同学的宿舍很小,有一个灯泡,没有拉绳和开关。
同学说辣子瓣回来了。他在部队上当了三年兵回来了。在平利上秋坪的车上,他低着头,不想人认出他。同坐的一个人嫌他衣服破旧,嘴里一直在咕噜咕噜,辣子瓣一直没理他。他以为可欺,屁股往辣子瓣这边挤,要把辣子瓣挤掉了。辣子瓣忽然抬头,一手提起那人啪啪打了两耳光,又把他掼回座位上,依旧一言不发低着头。那人也低头再不动弹。
说是辣子瓣回了趟家,很快出门了。
天黑了,同学拿起连着灯泡的半截电线,电线裸露着铜丝接头,墙上的入户线也裸着铜丝,同学把两截电线触到一起,电火花一闪,灯泡登时亮了。
夏天结束的时候,我调到安康市的一所学校工作。以后接到哥哥的一个电话,说他准备出门打工。我叫他到我这里来一趟。
那天傍晚,哥哥和同学来到我的宿舍,每人背着一个鼓胀的牛仔包。他们俩结伴到广州打工,搭晚上十二点的火车。我请他们吃饭,哥哥说吃过了。他说,爸爸已经不打算在县城买房子了。
哥哥在平运司五个月,算账下来落了四百块钱。爸爸又给了六百块钱。我给了哥哥两百块钱,说我也刚工作,只给得了这么多。哥哥说行了。同学说当兄弟的,已经很够意思了。我送他们到校门口,他们上了一辆三轮摩的,呜呜的消失在黑暗里。
姐姐说,哥哥走的时候欠了三百块钱房租费,是她去结的。“两床铺盖都盖得没用了,我没拿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