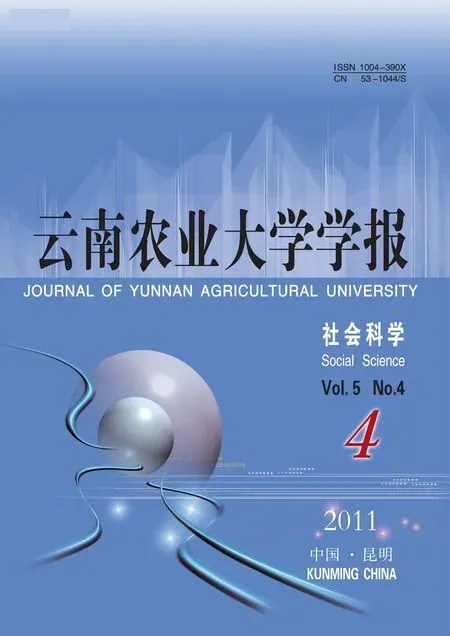叶芝诗歌中的生态性
2011-12-08周海峰
周海峰
(文山学院 外语系,云南 文山663300)
作为英语文学的分支,爱尔兰文学在英语文学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而在丰富多彩的爱尔兰文学世界中,叶芝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作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对其后的爱尔兰文学创作产生了的极大的影响。作为爱尔兰著名的诗人、剧作家和散文家,他一生著述颇丰。作为爱尔兰文艺复兴的中坚,他用文学积极地投入到爱尔兰解放运动的大潮中,为爱尔兰文学的独立和爱尔兰的民族独立作出了贡献。T.S艾略特称赞叶芝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
如今,生态思潮的兴起对文学研究和批评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以及对人与自然和谐的诉求正在成为人们的共同和必须的追求。文学作品,尤其是数量巨大的文学经典,以其巨大的影响力,持续地对人类的生态意识产生着调适甚至改变。对经典作品的重新解读,评估其对人类生态意识的积极或消极的作用,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则是生态批评的重要手段之一。叶芝的诗歌,尤其是前期的浪漫主义诗歌,和其他的浪漫主义诗歌一样,以其对自然的亲近和关注,为“诗意地安居”和存在论美学和参与美学的阐释的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一、 叶芝诗歌综述
叶芝是英格兰裔的爱尔兰人,开始创作于英国浪漫主义时期,并经历了世界文学由浪漫主义向现代主义的转变。因此,叶芝诗歌中的象征主义可以说是在爱尔兰传统文化、神秘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基础之上形成的。这也使其象征主义具备了鲜明的特征,也成就了他非凡的文学成就。
叶芝早期诗歌题材取自爱尔兰凯尔特神话、民间传说及谣曲。同时,英国浪漫主义的影响也使叶芝非常注重诗歌的格律和音乐性。1899年,阿瑟·西蒙斯的《文学中的象征主义运动》一书把起源于法国的象征主义介绍给了英国。叶芝也在神秘主义知与行的过程中完成了自己诗歌创作向象征主义的转向。而玫瑰、天鹅则是叶芝诗歌象征体系的核心。
二、 生态批评的思想与审美
生态批评的思想基础是生态整体主义(ecological holism)。它源自生态学的整体观、联系观、和谐观,并以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此在与世界作为其哲学和审美基础。美国生态批评家格伦·A·洛夫(Glen A. Love)在《实用生态批评:文学、生物学及环境》一书中明确指出了文学研究与生态学及进化生物学的紧密关系。而达尔文、奥尔德斯·赫胥黎在他们的著作中所体现出的生命的联系性,以及进化发展的相互交错和密不可分性,他提醒人类应该更多地把对人本身的关注转移到对自然的关注之上。“生态思维——就它要求从更广泛的视角来考量如何回答诸如有关自然界及人在其中的地位等问题来看……需要采用一种更宽广的生态学视野以认识文学行为发生的社会背景与生物学背景。”[1]作者还进一步指出了文学与自然及生态整体之间的不可分割性。
王诺教授认为,生态批评的美学原则主要有三:自然性、整体性和交融性。自然性原则即是对自然的审美,它突出自然审美对象,与审美者建立交互主体性的关系,并强调自然本身的美。整体性原则来源于生态整体主义,主要考虑审美对象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和影响。交融性原则源于生态主义联系观,主张融入自然的审美。
生态散文家利奥波德(Aldo Leopold)则在其著作《沙乡年鉴》(又译沙郡年记)中提出的“ISB原则”(integrity,stability,beauty),即完整(又译为和谐)、稳定、美丽,做为生态整体主义的价值判断标准(即土地伦理)。并认为人们应当“像山一样思考”。
此外,曾繁仁教授也在其多篇论文中指出由“自然的祛魅”向“自然的复魅”的重要性。即承认自然对象特有的神圣性、部分的神秘性和潜在的审美价值——从人与自然的共生关系上来探索自然美的价值。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自然或者自然取向的审美在文学批评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自然在文学作品中一度被置于附属性的地位:或者认为自然不过是人类行为的衬托;或者干脆把自然置之不理,如傅雷翻译《飘》时,就有大段自然描写的删节。在生态批评中,则要从整体出发——即人与自然是密不可分的观念出发——恢复自然在文学中的合理地位,并以此为依据,把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理清,使人类不再高高在上——即恢复人类与整个自然生态的完整统一性。最终揭示生态危机的根源,为人类的未来创造真正的福祉。
三、 叶芝诗歌中的生态性
叶芝的诗歌,尤其是其前期的浪漫主义诗歌,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首先以《当你年老时》(When You Are Old,1896)为例:
当你年老,鬓斑,睡意昏沉,
在炉旁打盹时,取下这本书,
慢慢诵读,梦忆从前你双眸
神色柔和,眼波中倒影深深;
多少人爱你风韵妩媚的时光,
爱你的美丽出自假意或真情,
但唯有一人爱你灵魂的至诚,
爱你渐衰的脸上愁苦的风霜;
弯下身子,在炽红的壁炉边,
忧伤地低诉,爱神如何逃走,
在头顶上的群山巅漫步闲游,
把他的面孔隐没在繁星中间。
(傅浩译)
此诗叶芝使用了非常简单的词汇和句式所写。诗歌本身是一首脍炙人口的爱情诗,在爱情的主题统领下,诗歌所选取的场所(Place,又译地方)[注]该术语所使用的译法不一。笔者对此词采用“场所”之译,而所引文献中,有的采用“地方”之译。故文中对该术语的叙述有混乱之嫌。特此说明。却值得关注。笔者认为,正是在爱情主题下这对场所的选择和表现,才使得本诗的生态性凸显,并唤醒读者内心向自然纯真回归的共鸣。
场所,或者地方,是“‘被赋予意义的空间’。地方是‘可感价值的中心’…‘一个地方能够被见到、被闻到、被想象、被爱、被恨、被惧怕、被敬畏’”[2]。可以说,场所与人的具体的生存环境和由此引起的感受息息相关。我们当前存在的空间,各种物品的位置和状况,彼此之间的“因缘”都是场所的整体。
在本诗中,作者描述了这样的一个存在——“老去的爱人”(后文简称为爱人)、壁炉和书籍。爱人老去了——头发灰白、睡眼朦胧——坐在炉边取暖时,取下书来,而书籍又进一步引起了爱人对下一个“因缘”、感受的描述:对爱的沉思和略带悲伤的感慨。然而这个场所并未因此而结束。在取暖、诵读、梦忆、“忧伤地低诉”这一系列相互关系,即“因缘”之后,诗人结尾处却把空间扩大到“群山巅”和“繁星中间”,也使得全诗的场所,或“因缘”得以升华——自然,才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根本所在,我们就生活在这个世界中——即所谓“此在的在世”(海德格尔)。老去、炉边打盹、取书、沉思,在这部分中的场所通过爱神的“逃走”最终完成与群山、繁星的融合——隔离人与自然的墙消失了。这种房屋与自然的简略描述,读来则使得人类的居所与自然并无隔阂,“……人与场所是相互渗透和连续的”[3]。从老去到逃走,似乎都指向这样一种隐喻:最终的归宿,悲伤也好,闲游也罢,都是向大地、向自然、向我们唯一的存在之所的回归——既是爱情向纯朴的回归,也是人类情感向生养人类之所的回归。
如果说《当你年老时》一诗中的自然和人性的融和都是若隐若现地如同火炉中的火光,那么,与该诗在时间上较早一些的《茵尼斯弗利湖心岛》(The Lake Isle of Innisfree,1892)则明确地描述了作者心目中的“世外桃源”:
我要起身走了,去茵尼斯弗利湖心岛,
用泥土和枝条,建造起一座小屋;
我要有九排云豆架,一个蜜蜂巢,
在林间听群峰高唱,独居于幽处。
于是我会有安宁,安宁慢慢来到,
从晨曦的面纱到蟋蟀歌唱的地方;
午夜一片闪光,中午有紫霞燃烧,
暮色里,到处飞舞着红雀的翅膀。
我要起身走了,因为我总是听到,
听到湖水日夜轻轻拍打着湖滨;
我站在公路,或在灰色的人行道,
我心灵深处总听见那波涛声声。
(裘小龙译)
叶芝在阅读了《瓦尔登湖》后,受梭罗生态观念的影响而写下此诗。“那时我住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城,城里瓦尔登湖边有片树林,我在那儿亲手搭了个小屋,方圆一英里内没有任何邻居。我用自己的双手劳作,自食其力。”[4]叶芝诗中的场景与此何其相似。想象中的宁静来自于自己亲手建造的简单的一切:小屋、芸豆架、蜜蜂巢;来自于大自然赐予人类的美丽礼物:林间、晨曦、紫霞、湖水,蟋蟀、红雀,一切均融为一体。这样一个令人所向往的地方,让尚身处工业城市的诗人的心也早已飞向了彼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意境呼之欲出。
长久以来,文学作品中的自然并不缺乏。然而,文学研究或者说文学批评中却一直忽略自然的存在。“纵览中国文学史的百年书写,我发现,自然的位置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乃至放弃了。”[5]不仅中国,全世界在对待文学的问题上,在各种以人类中心主义为原则的思潮和运动中,自然、田园却日益饱受批评。但是,“田园牧歌(笔者此处引用田园牧歌一词取其描写自然之意,并非专指某种诗歌、文学类型)一直就是一种对生活的严肃批评”[1],田园或者说田园倾向的描写并非一个培植感伤情绪的场所。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认为,尽管意识形态的内容时有变化,但田园牧歌的形式却始终恒定如一。“田园风情持续不断的吸引力与威尔逊的生物之爱极为相关,就是敬畏生命,就是对我们自身作为源于自然的生物的本能感受。”[1]
本诗中,自然与文明的对立是非常明显的。自然丰富多彩,众多的物种之间和谐相处,到处是歌声和光明。而城市的、工业的修饰词只有一个——灰色,灰烬的颜色:从一座座巨大的工厂那矗立的巨型的烟囱里看似缓缓吐出的烟霾,在原本清明的天空下聚集、扩散,偶尔飘来的风把它带到世界各地,然后慢慢地沉落,覆盖了这个地球,尤其是工业的城市,只剩下灰色。此外,描写自然时,作者沿着内心的追寻,随手即可写出的美丽如此之多。而自己身处的文明社会,却只能找到寥寥的公路和人行道,诗人以第一人称独立其上,似乎也暗示着工业文明在极大地促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其秉承的“技术理性”也瞒下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危险——人类只能孤独存在于大地之上。
诗中有两类场所存在:一是湖边小屋;二则是公路和人行道。同样是由人所建造,然而区别是巨大的。前者是开放的、包容的。小屋不过是“我”生活的必需,在这方寸之地的周围,有许多的伙伴,“我”并不寂寞,在一个充满声音的场所里,“于是我会有安宁,安宁慢慢来到”。这无疑是一个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场所——“我”只“占有”必需的生存之地,没有奢侈的享受和消费,小屋在自然中并不是一种突兀的存在,也不是这一“桃源”的中心,它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与万物之间不相干扰,却也享受着彼此给予的安宁,并由此构成一个整体;这是与梭罗一脉相承的简单生活观。与此相对,后者则是孤独地、隔离的。需要指出的是,后者似二实一,公路也好,人行道也好,在承载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是人类不断地侵犯、挤压其他物种的生存空间,并扩大自己脱离了必需甚至是适度享受这个范畴的享受空间。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是割裂的,原本浑然一体的大地,被一条条公路分割开来,公路霸道地躺在大地之上,切断了大地万物原本的联系。这个场所没有多余的声音、没有多余的色彩,时尚和消费赞美它、引领它,如同公路一般不断地延伸,没有尽头,似乎在暗喻着对大地的侵占和分割永不停止。但是,“我”在这里是寂寞的,“我站在公路,或在灰色的人行道,/我心灵深处总听见那波涛声声。”“诗意的安居”还是“技术的安居”,也成为了一个“to be or not to be”式的两难困境。
与叶芝前期的浪漫主义与自然的天然联系不同,叶芝之后诗作开始向象征主义转变,象征主义在工业社会与自然的隔离逐步加大的背景下,其创作基础和理论显示出对浪漫主义自然传统的背离。柯尔庄园在叶芝的象征主义作品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柯尔庄园的女主人奥古斯塔·格雷戈里夫人也一直支持叶芝的创作。尽管象征主义在逐渐的背离自然和田园,但是,叶芝的诗歌在形式上并没有实验主义的倾向。相反,叶芝的诗作在形式上一直坚持传统,对诗歌韵律的追求终身都没有停止。这种形式上对传统的坚持,笔者认为,恰恰是作者对浪漫主义的自然原则的潜意识守护,或者说田园牧歌所具有的持久魅力给予人性(具体到本文,则是对叶芝本人)的影响。安德鲁·艾廷(Andrew Ettin)指出,“田园这个术语涵盖了多种体验和观念,而这些体验和观念永远是我们思考和写作的组成部分。”[1]:
柯尔庄园的天鹅(The Wild Swans at Coole,1912)
树木披上了美丽的秋装,
林中的小径一片干燥,
在十月的暮色中,流水
把静谧的天空映照,
一块块石头中漾着水波,
游着五十九只天鹅。
自从我第一次数了它们,
十九度秋天已经消逝,
我还来不及细数一遍,就看到
它们一下子全部飞起.
大声拍打着它们的翅膀,
形成大而破碎的圆圈翱翔。
我凝视这些光彩夺目的天鹅,
此刻心中涌起一阵悲痛。
一切都变了,自从第一次在河边,
也正是暮色朦胧,
我听到天鹅在我头上鼓翼,
于是脚步就更为轻捷。
还没有疲倦,一对对情侣,
在冷冷的友好的河水中
前行或展翅飞入半空,
它们的心依然年轻,
不管它们上哪儿漂泊,它们
总是有着激情,还要赢得爱情。
现在它们在静谧的水面上浮游,
神秘莫测,美丽动人,
可有一天我醒来,它们已飞去。
哦它们会筑居于哪片芦苇丛、
哪一个池边、哪一块湖滨,
使人们悦目赏心?
(裘小龙译)
自然或者田园与人类社会在本诗中逐渐地产生了疏离。诗人在柯尔庄园这个有着人为色彩的场所第一次见到天鹅时情景是“我听到天鹅在我头上鼓翼,于是脚步就更为轻捷。”,我很轻松地就数出了天鹅的数目,田园与人类之间的互相呼应是浑然天成的。此后,田园的风光依旧:林中小径、秋色下的小河。然而,“我”还来不及数出有多少天鹅,它们就飞走了,“十九度秋天已经消逝”“我凝视这些光彩夺目的天鹅,此刻心中涌起一阵悲痛。”。到了诗歌的结尾,“可有一天我醒来,它们已飞去。哦它们会筑居于哪片芦苇丛、哪一个池边、哪一块湖滨”,天鹅从人类的注视中离开,虽然其他的风光依旧。可是,下一步离开的还会有什么?是树林、还是河水?在贵族的庄园里,自然与人类社会曾有的和谐,随着庄园一步步在工业社会的压迫下被拍卖,这些和谐也在一步步地走向疏离,甚至是隔绝。
天鹅作为诗人诗中美的象征,在本诗中最后一部分则以梦境中的“神秘莫测,美丽动人”变成了醒来后的现实——“哦它们会筑居于哪片芦苇丛,/哪一个池边、哪一块湖滨”。诗人对自然之美的留恋由此可见一斑。
如果说,此诗中的天鹅是诗人自然审美的重要元素和集中体现。它在这里体现了自然与人类关系的亲密与疏离。那么在《丽达与天鹅》(Leda and the Swan)一诗中,则表现了自然对人类的粗暴:
突然袭击:在踉跄的少女身上,
一双巨翅还在乱扑,一双黑蹼
抚弄她的大腿,鹅喙衔着她的颈项,
他的胸脯紧压她无计脱身的胸脯。
手指啊,被惊呆了,哪还有能力
从松开的腿间推开那白羽的荣耀?
身体呀,翻倒在雪白的灯芯草里,
感到的唯有其中那奇异的心跳!
腰股内一阵颤栗.竟从中生出
断垣残壁、城楼上的浓烟烈焰
和阿伽门农之死。
当她被占有之时
当地如此被天空的野蛮热血制服
直到那冷漠的喙把她放开之前,
她是否获取了他的威力,他的知识?
(飞白译)
应该说,粗暴也好,和谐也好,疏离也好,都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持久组成。显而易见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无论是纯粹的服从还是控制都不能真正解决或者缓解已有的生态危机。最终,两者之间只能走向和谐之路。天鹅在叶芝本人的象征体系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叶芝认为,正是宙斯化身的天鹅与人间女子丽达的结合创造了希腊文明。在古埃及的神话和建筑中,狮身人面像无疑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隐喻,它本身是人与动物的合体。或许叶芝认为,人类与动物的结合,才导致了人类文明的产生。人与自然不应该是对立的,征服与控制并不能创造文明的人类文明,相互的和谐关系才能创造符合人性或者说自然性的人类文明。
在这两首与天鹅有关的诗歌里,天鹅的神秘,或者是作为神的化身,并由此与人所产生的种种“因缘”:“诞生和死亡,灾祸和福祉,胜利和耻辱,忍耐和堕落——从人类存有那里获得了人类命运的形态。这些敞开的关联所作用的范围,正是这个历史性民族的世界。出自这个世界并在这个世界中,这个民族才回归它自身,从而实现它的使命。”[3]在生态存在论美学中,美是关系,是过程,是在自然与人关系的世界结构中逐步得以展开的。“冷漠”和“制服”不过是大自然维持其平衡的手段。 “她是否获取了他的威力,他的知识?”更像是一种追问:灾祸之后,更多的是新生和希望,是酒神的狂欢和重生。
四、 结语
叶芝无愧于一个伟大诗人的称号,即使在生态批评的背景下,其作品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生命力不仅来自于叶芝本人对诗艺孜孜不倦的追求,也来自于其诗作中持续的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探讨。生态思想的注入,必将使叶芝诗作的魅力更为恒久。
[参考文献]
[1][美]格伦·A·洛夫. 实用生态批评:文学、生物学及环境[M].胡志红,王敬民,徐常勇,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57,65,76,79,129.
[2][美]劳伦斯·布伊尔. 环境批评的未来:环境危机与文学想象[M].刘蓓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70-80,70-71.
[3]曾繁仁.生态美学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25-341,337,287.
[4]亨利·大卫·梭罗.林志豪译.瓦尔登湖[M].海口:海南出版社,2007:1,72.
[5]鲁抒元.百年疏漏——中国文学史书写的生态视阈[J].文艺评论,2007(1):181-186.
[6]王诺.欧美生态批评:生态文学研究概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23-67.
[7]王诺.生态与心态:当代欧美文学研究[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7.
[8]李美华.英国生态文学[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8:200-206.
[9]杨晨音.从摹仿到构建——叶芝诗歌中的象征转向[J].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9(5):61-64.
[10]甘文婷.从生态批评的角度解读叶芝的悲哀的牧羊人[J].安徽文学,2009(10):207-208.
[11]傅浩.叶芝的象征主义[J].国外文学,1999(3):41-49.
[12]黄海容.叶芝的象征主义及其发展[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107-115.
[13]曾繁仁.当代生态美学观的基本范畴[J].文艺研究,2007(4):15-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