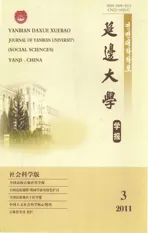论朝鲜朝后期家庭小说中父权家长形象的塑造
2011-12-08李娟
李 娟
(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吉林延吉133002)
在朝鲜朝后期的家庭小说中,人物形象的塑造主要由两大系列构成:一类是作为家庭支柱的男性形象系列,一类是作为家庭附庸的女性形象系列。在这两类人物形象的塑造中,作者表现出了在家庭生活中一个自然人因个体性别、家庭地位的不同,而使其个体在家庭生活中的不同处境以及因社会文化对性别个体的要求而产生的性别文化差异。这些形象包括了父子(女)、夫妻、妻妾、妾与妾、继母与子女以及同父异母子女等相互间复杂的家庭内部的人际关系。而在这些形象中,父权家长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父权家长形象根植的宗法父权体制
父权家长形象的重要地位是和父权(夫权)在朝鲜朝时期的封建家庭中至高无上的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朝鲜朝时期的社会也是和中国一样,是一种封建宗法父权体制,这种体制集合了道德、法律、权力、欲望于一体。男性成员通过家庭婚姻、社会、政治、文化、教育和经济等组织,在家中行使统治权力,对女性进行压制。在宗法父权秩序中,男尊女卑,男外女内,男性以主体身份进入宗法体制,女性则被放置在边缘地位之中,不是完全被排除在体制之外,而是收编在体制之内的边缘位置上,置于婚姻家庭秩序之内。女性丧失主体自我的现象,在文化传承上有其传统性别规范的背景。由于朝鲜朝是家国同构、三位一体的宗法社会,因此,“父权家长”这个原型符号可以被扩展为家长、族长,甚至君主。作为一家之长的父亲,实际上是扩大了性别与辈份的“父亲”,族长实际上是指增加了族权,或许还有神权的“父亲”;君主是指增加了君权的“父亲”。所以,在有关家庭主题的叙事文学作品中,代表一家之长的“父权家长”形象,实际上既包含了父亲,也包括了掌管家庭的丈夫。
朝鲜朝社会一直以儒家思想为正统,可以毫不夸张的说,朝鲜朝时期的儒家文化是一种父权家长制文化,它强调了一种对父权家长的绝对敬畏。因此,无论在父子(女)关系中,还是夫妻关系中,父权家长是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的,子女没有独立性和自主权,必须为父亲而活。家庭的其他成员也必须遵从于父权的统治,服从于父权的权威。正如孔子反复强调的:“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父之道”。[1]也就是说,“孝”的核心是服从父母及长辈的意志,民间广泛地在“孝”字后面加一个“顺”字就形象地说明了这一点。血缘伦理和社会伦理的双重屏障,使得子女在感情和责任上均臣服于父亲。“父亲”作为专制家长,凭借旧家族制度和传统观念所赋予的权力,像君主一样统治着属于自己的“家庭王国”。专制家长们,不仅把握着整个家庭的经济大权,而且还掌握着所有家庭成员的前途与命运。
作为中国儒家文化的传承者,朝鲜朝后期家庭小说的作家们对“父权家长”的态度是复杂的。一方面,由于社会的变迁,人们对于家庭观念的改变,使家庭关系面临着变异和重构。另一方面,深受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影响的两班士子们,又存在着深深的“恋父情结”,传统士大夫的观念、责任感等,两者的冲撞结果,使父亲处在了中心的位置。原本“父权家长”在这些人的内心深处永远是“家”的核心和代表,父权秩序是不可侵犯的,这就形成了:一方面是对父权家长形象的仰视,另一方面则是展现父权家长面对社会制度和文化冲击之下的软弱与无力。一家之长的地位被动摇,以父(或夫)为核心的传统家庭模式被解构,与之相连的崇尚孝道的家庭伦理道德也被颠覆,而父权家长的存在,则成为关于“家”喻言的表述核心。
二、父权家长形象构建的家庭伦理观念
在朝鲜朝时期人们的生命意识中,不仅认为家是生命的最高准则,一切必须服从家,一切必须为了家,而且认为在自然血缘的“家”中从父母,在社会血缘的“家”中臣于君王。在人们的意识中,血缘是不可选择的、万古不移的权威,家也就是不可舍弃与离异的生存依托。家是人的家,人是家中的人,被内化、被规定了,生命行为的终极目的就是为了“家”。“家”是一个等级制的实体,这种等级观念是由具体的亲属制度来实现的,与亲属称谓系统相匹配的“五服制”推演到亲属之外,涵盖整个社会的人际关系,形成了“五服社会”。人们特别看重人际间的血缘关系,人由血缘构成的等级是合理的、公平的,这样就完成了对社会等级制度的接受。家庭中的“父”或“夫”是决定家庭成员命运的“圣旨”,每个人都在一个等级森严的家庭关系之中遵从忠孝观念和礼法规定。“大家庭小社会”,大的家庭、家族俨然就是封建宗法社会的一个缩影。在宗法父权制的朝鲜朝伦理社会中,父权家长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因此,在作为以家庭生活为创作母题的家庭小说中,有关父权家长形象的塑造是极为丰富多彩的。在这类形象中,不少形象是作为观念符号出现的,但角色的相同不等于性格的相同,大多数父权家长形象的塑造还是极具个体特性和文化意蕴的。
三、朝鲜朝后期家庭小说文本中的父权家长形象
产生于朝鲜朝后期的家庭小说,主要以《谢氏南征记》为发端,通过对家庭所负载的伦理道德、爱情、亲情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揭示,形象地塑造了四类父权家长的形象。
(一)在矛盾中彷徨的家长
对内打理好家庭,对外效忠于国家的典型的家长形象,是朝鲜朝社会制度和儒家文化规范的理想家长。家长作为家庭权力的核心,应该处在家庭结构的中心点上以及深处矛盾与纠葛的原则立场中。但是在《谢氏南征记》中,却描写了一位儒家符号化人格与现实生活人情、人性相矛盾的家长形象。男主人公刘翰林是一位文采超群、有谦让之德,同时重孝悌,做事慎重而且为人宽厚的儒家理想君子。他的文采和谦让之德是通过他15岁在考取翰林编修后,上书皇上,请求再读10年书后,再效忠皇上而交待的。对父亲、姑妈等长辈的孝敬、孝顺,体现了他儒家理想君子人格所遵从的伦理道德规范。但是,随着故事的展开,在妻谢氏和妾乔氏之间发生家庭矛盾纠葛时,他却是一个不辨是非、无能无奈的弱者形象。听信妾乔氏的谗言,放纵乔氏使奸计陷害妻谢氏,并最终将妻子逐出家门,也招致自己被流放,差点遭暗算而死,弄得家破人亡。前后的对比较鲜明,明明是一个才德兼备、尽忠尽孝集于一身的理想君子形象,却无力处理好家庭内部妻妾的矛盾纷争,这里显示出了“父权”在妾乔氏的积极“觉醒”与“反抗”中,渐渐失去其权威的一面,也变得无奈与无能了。
谢氏为了继后嗣规劝丈夫刘翰林纳妾时,刘翰林“疑其言或不诚,只是笑而不答”。后来谢氏将媒婆之言告诉翰林时,刘翰林却说:“吾之置妾本不急,而夫人好意亦不可违,乔氏诚如此,宜娶来”。[2]结果刘翰林虽然很喜欢原配夫人谢氏,但是谢氏劝告其纳妾继后嗣的时候,装作不得不接受的样子。纳妾的第一个目的是为了继后嗣,但是刘翰林渐渐失去了聪明和重心,陷入到美妾——乔氏谋害谢氏的奸计之中。
乔氏的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刚刚嫁入到刘家的时候,曾受到刘家人的称赞,并且受到刘翰林的宠爱,但是当谢氏也生下儿子之后,乔氏十分烦恼:“吾与彼容貌之美,无以加焉,而嫡妾之分显殊矣。徒以我则生男彼则无子之故,能被丈夫厚待。彼今生子,而将为此家之主,我儿自然无用耳”。[2]由此可见,乔氏感到了危机,原本自己是出于继后嗣的需要,被娶入刘家的,现在连继后嗣的目的也被否定了,那今后自己的生存、自己所生儿子的处境……在当时嫡长子继承制的朝鲜朝社会中,作为一个母亲,一个没有身份和多少家庭地位的妾,这些都是乔氏不得不去想、不得不去谋划的。于是,为了自己,为了今后儿子在家中长子的地位,乔氏开始了自己罪恶计划的实施。刚开始,乔氏在丈夫面前离间谢氏、陷害谢氏时,刘翰林还能清醒地认识到谢氏的贤淑,并且规劝乔氏:“……然性本柔顺,必不害尔。尔无忧……”。结果在乔氏一次次奸计的“事实”面前,刘翰林的聪明也渐渐被蒙蔽,开始怀疑并远离谢氏,最终逐出了贤德的妻子,并使自己也陷入苦难的境地。当所有的事实都摆在面前的时候,作为丈夫才开始反省自己,并慨叹:怎么有脸去见自己的祖宗呢?内心儒家君子的理想人格形象又重新回到了现实,并占据了刘翰林的心。在刘翰林逐出谢氏之时,就是身边的邻居都慨叹:“夫妇之际,岂不难哉!”文中虽然是邻居们的感叹,也是作者想要表达的观点。这里面既有对妻子的要求,也有对丈夫的要求,谢氏是儒家理想妻子的典范,她不但为继后嗣积极为丈夫求妾,不顾婆婆杜夫人的劝诫:“因一时的无子而纳妾?妻妾是扰乱家中的根本,夫人怎么能自取祸害呢?这是万万不可的”。后来门客董清的出现,又使谢氏执意规劝丈夫:“要亲君子而远小人”。因此被皇陵庙娘娘称之为:“与曹大家、孟德耀比肩”。刘翰林则不然,不仅惑于美色,还误交匪人,导致几乎家破人亡,作品中对此解释为:“翰林亦君子之人,不幸早达,未及周知天下事理,天将降一时灾祸以大警之”。最后,刘翰林从所有误会中解脱,在重新获取功名和名誉后,处罚了乔氏,找回了谢氏,一家团圆。可惜的是,在作品的结尾,刘翰林又纳了许氏为妾,虽然又将许氏描写为一位贤淑之女子,但刘翰林是否会吸取教训,是否能真正处理好“一夫两妻”的家庭生活秩序呢?
(二)害死子女的无能家长
这类父亲的形象大多出现在朝鲜朝后期的继母型家庭小说中。大多数都是由于前妻的过世,后娶进来的继母和前妻子女之间的矛盾纠葛。
《蔷花红莲传》中描写了一位恪守儒家伦理规范,缺乏对事实做出正确判断的父亲形象——裴武龙。平时对幼年丧母的前妻所生的两个女儿偏爱有加,以致引起了继母许氏的嫉妒。为了获得丈夫对自己的爱、对自己所生儿子的爱,就开始谋划着怎么除掉前妻所生的两个女儿。当许氏的妒忌之心被裴武龙察觉到了之后,对于许氏的处理显然是表现出一副封建家长的姿态,面色上很是不满,并严声告诫许氏说:“我们家本来很穷,是前妻张夫人从娘家带来了很多财产,才使我们家变得富裕了,你现在丰裕的生活是得益与张夫人的恩惠,……而现在,你还要虐待她的两个女儿,于情于理都难辞其咎。以后不许再这样,应该倍加疼爱她们才是……”。[3]这些话没有起到告诫和规劝的作用,反而使许氏心里觉得更加反感,背地里对两个女儿的虐待也更变本加厉。
当许氏设计将剥去皮的老鼠放在女儿床上,诬陷女儿蔷花怀孕堕胎之后,不知情的父亲裴武龙在女儿出现了意外之后,态度陡然间大变。告诉许氏:“你看问题和处理问题的能力我清楚,无论怎么处置我就不管了,你就看着办吧!”从裴武龙的这番话和他的行动,我们看到了:一个两班儒家教条的“君子”形象跃然纸上,一个重视体面和名誉的样子顷刻间被刻画了出来,不想调查,也不去了解情况,就拿出儒家礼法的规范去处罚自己的爱女。这时候,家门的颜面要比爱女的生命更加值得裴武龙去考虑,所以主动地让后妻去处理这件事情。许氏也正中下怀,并在旁边添油加醋地煽动:“我们裴氏家族虽然不是很富裕,但是作为这村里的两班,有这样丢人的事,是家门的一大羞耻。如果这话泄露出去,不仅有辱家门,而且整个裴氏家族都抬不起头来,他们三兄弟也会以独身老死,怎么能让这样的事儿发生呢?”[3]裴武龙在听完许氏的计划之后,明明知道是要弄死蔷花,但还是欺骗并命令蔷花回姥姥家。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裴武龙的双重人格:一方面作为父亲一贯很爱两个女儿,表现出慈父的一面;另一方面,在女儿出现了他意想不到的事故时,却变成了一个全然不能够明辨是非的父亲,顷刻间露出了儒家“正人君子”的面目。也正因为如此,才被许氏窥见并利用。在这里慈爱的父亲全然不见了,也不问问蔷花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把自己的女儿强硬地推向了死亡的境地。在蔷花争辩的时候,他还说:“你怎么能不听父亲的话,争辩这么多呢,是要惹怒父亲吗?”
裴武龙比起“父亲”要更加重视家门的体面和声誉,他在这里表现出了回归到封建父权家长的典型形象。为了家族家门连自己深爱的女儿也不会放过,并且连是非曲直都不问一句,就赶紧想草草了事,以免外传有损家门声誉。这一点证明了当时两班社会的男性们,只重视体统而疏于把握事实真相的无能。是裴武龙的心肠软弱,缺乏主体判断能力,最终自己害死了疼爱有加的女儿。前妻的女儿之所以欣然接受死亡,是因为她把遵从父命视为孝,认为这是人伦之道。“百善孝为先”的孝悌观一直主宰着朝鲜朝时期人们的思想意识,作子女的要注重长幼尊卑,晚辈对长辈必须绝对服从。但作为父权统治者的家长们,并没有意识到子女们的孝心,只想着维护社会的传统道德理念,并将其作为人生的全部,而招致自己及其家庭悲剧的发生。虽说小说世界充满了夸张和虚构,但从中还是能窥视出朝鲜朝时期文弱书生只重视体面和名份的观念。
这种家长形象在《孔菊潘菊》、《金仁香传》等作品中也大同小异地出现过,他们全都被塑造成了懦弱和没有自我意识的男性家长形象。正是这种懦弱无能家长的存在,才促成了继母对前妻子女发生施恶行为。
(三)囿于家庭伦理秩序的无奈家长
《月英娘子传》中的家长崔熙圣,比起其他作品中的家长更值得关注。《月英娘子传》中表现出的家庭矛盾与其他作品有所不同。崔熙圣娶妾不是为了后嗣生产,而是因御命不可违。在《月英娘子传》中,第一夫人闵夫人,第二夫人胡夫人,她们俩和第三夫人郑夫人的矛盾对立是作品的主要矛盾。
男主人公崔熙圣在尽孝与爱情方面存在着矛盾心理,遵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儒家理念,就必须遵从父母的意愿再纳妾,但纳妾又有悖于对闵夫人爱情的忠贞。更主要的是崔熙圣觉得再娶个夫人进来不是件妥当的事情,一定会闹得家庭不和。但是又难于皇命不可违,必须迎娶御命之郑夫人时,崔熙圣叫来两位夫人,交待道:“我现在是不得不跟郑小妾结婚,这应该说是我们家门的不幸。但是你们自己不要失去做人的本份,最大的原则是始终不要失去做人最起码的礼数”。在这里作为家长的崔熙圣对即将发生的事情还是有一定的预见性的,这和作品开头就交代的人物具有超凡的能力是相吻合的。所以崔熙圣预感到了以后可能出现的状况,心里总是惴惴不安。
第三夫人郑雪莹仗着自己的权势,不顾及在家中的尊卑位置,任意放肆地胡作非为。如果说《谢氏南征记》和《蔷花红莲传》中出现的矛盾,是对家长的爱情和作为父权家长权利的抗争的矛盾,那么《月英娘子传》中的矛盾却是作为皇亲的郑雪莹依仗着自己的家门背景,希望得到合理的待遇而产生的对家长对抗的矛盾。成婚后的郑雪莹叹息自己在家庭中的处境,她认为崔熙圣轻视和责骂自己,是因为自己处在第三夫人的位置。“妾是皇后的亲妹妹,怎么能违反朝廷风俗呢?妾的心跟柳花、梨花等同,郎君也敢蔑视!不是因为别的,而是让我位居身份比自己低的女人之下,我不能忍受!这是我伤心地缘由”。[4]自己的身份比两位夫人都高,但她却没有享受到作为真正妻子的合理待遇,心中感到不平。郑雪莹娇蛮跋扈的行为,在生完儿子之后愈加嚣张。在封建家庭中,妻子对丈夫的反抗,在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中是绝对不可容忍的。而这里的郑夫人全然不顾及男尊女卑,直白地暴露了当时朝鲜朝社会的等级身份制和皇权御命。
在娶郑氏之前就预见到将来会产生矛盾,在事情出现后,又能够将事情摆在当面解决,行使作为家长的权力,严管轻举妄动的郑氏,显示出了崔熙圣作为一家之主齐家的能力。但这里作为丈夫,俨如一家之长的“父亲”般责骂自己的妻子,不是以丈夫爱的角度,去解决家庭中夫妻之间的问题,完全是一种靠父权家长权力来威慑自己的妻子,显然处理的方式很难让人接受,这是日后郑氏将愤怒转嫁给先前两位夫人的原因所在。就在崔熙圣奔赴战场的时候,家中发生了三位夫人的矛盾纠葛,妻妾矛盾激化,这是家祸产生的根源。这种战争的介入,使恶妾们驱逐和迫害正妻有了可乘之机,同时丈夫处理家庭问题的弱化,因为自己的离开也变得名正言顺。当掌握着父家长权力的男性不在家时,家庭问题发生的同时也爆发了国家的战争。国家的危机和家庭的危机同时发生。当战争结束和男性回到家中时,家庭又恢复了往日的和平。这意味着如果家庭秩序和谐有序,那么国家秩序也会相应的和平,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家庭小说又把家庭问题向外扩大,延伸为社会、国家的问题。男性在此时,首先要把处理国家问题放在首位,体现了“忠君”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
丈夫在婚姻家庭中本应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朝鲜朝后期的国文家庭小说中,对丈夫们的描写却显得弱化了。他们在家庭出现矛盾的时候往往没了主见,对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或存在的重要性也没有积极的觉悟。因此,丈夫们存在的价值在于取得富贵功名,而不是为了家庭、生活。丈夫们虽然在自己生活的圈子里表现得很强势,但对于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妻妾或子女问题却爱莫能助。
(四)期望获得婚姻自主的家长
《淑英娘子传》中塑造了一位爱情至上的家长——白善军的形象,真实地将作为男性的情感与欲望暴露无余。
父母老年得子,生了白善军,所以对他宠爱有加。因为有一天在梦中遇见了一位佳人淑英,并由此得了相思病。在作品中,女性(淑英)通过超现实的力量(以仙女的身份),积极寻找自己预定的姻缘,主动向男性(白善军)坦白,约定三年后的姻缘。在当时的现实生活中,这种做法应该是淑英(女)在诱惑善军(男),并超越等级身份制度的束缚,对于淑英来说是具有女性自觉意识的。在朝鲜朝时期的小说中,女主人公的身份一般是很明确的,但淑英的身份并没有明确的说明。善军只是在梦里看见淑英以后,在不知道任何有关淑英的情况下,就爱上了淑英,并因相思而到了危及生命的地步。父母想尽了所有的办法,也未能治好儿子的病。看到善军的样子,淑英心里很不安,就又出现在梦里,背着天庭的规定,约善军见面。善军准备启程时,父母再三劝阻,还是未能拦住善军。善军去与淑英约会,实际上已经超越了人间和天界的界限。白善军有意与娘子结百年之好,不是父母之命或媒妁之言,只是一个托梦而已,在现实看来,是很荒唐的。作品将白善军设计成了一个纯粹的爱情至上主义者。在朝鲜朝的封建社会中,对于将来要承担家长职责的男性继承人来说,善军形象的塑造是完全缺乏维护家庭秩序和儒家伦理道德准则的。这里的所作所为,只是欲望没有实现之前,心理驱使下的迫切需要。而且为了解决欲望的煎熬,侵犯了婢女月梅,以缓解对淑英的思念。白善军对于月梅的态度,与其他古小说截然不同,白善军只是为了满足个人的心理和生理欲望,她只是白善军泄欲的工具而已。在其他的家庭小说中,娶妻或纳妾是以继后嗣为目的,起码在家庭中给予一定的身份、地位,但月梅却连作“妾”的名份都没有。淑英的做法,也使自己变成了一个不贞的女人,违背了天规,被处罚回到人间,善军将淑英领回了家。父亲白公了解了这期间发生的所有事情,并没有太多地责怪儿子,并默认了这桩婚事。在作品中,作为家长的父亲——白公,对儿子这桩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姻的默认,可以看出:父性的权威和“特权”在这里被打破了,作为父亲对儿子的选择和需要能够理解,并给予尊重和关爱。宗法父权体制下的“父亲”形象渐渐消失,而作为家庭成员之一的“父亲”渐渐出现在读者的视线里。但是作品中白公作为一家之长迎娶儿媳的过程却被忽略了,毕竟父权家长的意识还深深地扎根在父亲们的心中。善军跟淑英结婚以后,只是沉迷于与娘子的爱情中,根本无心于学业,看到如此的样子,白公很是痛心,无奈于对儿子的溺爱,也只能听之任之。
白家也是属于当时封建官僚的两班家庭,父亲白公对儿子的要求,也完全是按照儒家规范去要求的,只有科举及第和考取功名,才能实现自身价值,延续家门的繁盛。而儿子善军的想法只是追求自己的爱情,认为只要有娘子陪伴,过着舒心的日子就是最大的满足。父子之间因价值观的不同而产生了直接的对立。父亲下令将白善军送到京城参加科考,但善军因想念娘子而中途转回。白善军的这一形象在当时的儒教社会里,绝对是一个不思进取、不能齐家治国的叛逆形象。作为男子大丈夫为求取功名,去参加科考,却因为思念家中的妻子,而欲放弃考试的男人,从情感上来说应该是值得肯定的有情有义的好丈夫。但是在当时作为家门的继承人,只有科考及第、立身扬名,才能胜任齐家立业,白善军却做出了让父母伤心的举动,在当时的宗法父权社会中,这是儿子对父母最大的“不孝”。
当他知道月梅使用计谋害死淑英后,逼迫月梅写下供书,用刀砍断了月梅的脖子。但是这件事情的发端是始于善军的。善军并不反省自己的行为,认定这只是月梅在作恶。而对于月梅心中的积怨、妒忌,月梅在八年中积蓄的恨,白善军是意识不到的。在他的思想深处,一个婢女是不会有自己的主张的,她的一切行为都应该是以服从主人的意愿为终极目标。在这里白善军根本没把月梅看做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女人,而完全是自己家庭中的一件物品而已,可以随意任自己使用。白善军的形象有别于封建家长式的父权形象,虽然在婚姻爱情的选择上走出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束缚,但是在其思想的深处还是深深地根植着父权家长对于家族成员的统治与支配的思想。
四、结语
父权是伴随着父亲的发现而兴起的。父亲身份的确立必然要求父权的出现来维护这种父亲身份。而离开了父亲身份,父权则无处容身。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父权和君权在儒家思想的演绎下,巧妙地联结在一起,在封建社会及家庭生活中,一直占据着强势的地位。但父权还是无法逃避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它在朝鲜朝后期也无法选择地走向了下坡路。
在本文中,大家也许只能从行文中感觉到父权的渐行渐远,其实父权的衰微就是这样的一种趋势。可能启蒙运动和新思想并不能表现父权的衰微,只能看到整体有瓦解的趋势。但是从女性主义理论中,从小说作品文本中,女性渐渐独立的姿态上和女性觉醒的意识上,我们已经能够清晰地看到父权、男权的渐渐远去。
[1] 论语·学而篇[M].北京:中华书局,2007.
[2] [台]林明德.韩国汉文小说全集:第7卷[M].汉城:韩国国学资料院,1999.9,14.
[3] 作者不详.蔷花红莲传[A].古小说全集(13)[Z].汉城:仁川大学民族文化研究所东西文化研究院,1983.134,134.
[4] 作者不详.月英娘子传[A].古小说全集(4)[Z].汉城:亚细亚出版社,1976.2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