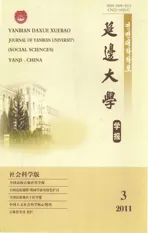论《左传》代词别称词的使用及其贵族文化特点
2011-12-08董淑华
董 淑 华
(延边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中文系语言教研室,吉林延吉133002)
上古时期汉语的人称代词同现代汉语的人称代词比较起来既丰富又复杂,除了数量多和用法丰富之外,有的还可以用别称词替代。这些别称词在行文中长期地稳固地替代这些人称代词,使其成为古代汉语人称代词用法的一个特点。
人称代词和别称词是指古代汉语中除了“我、余、吾、予、而、尔、若”等人称代词之外,还有一些相当于这些人称代词的词,如“寡人、不谷、孤、臣、君、吾子、子、小人”等。这些词在行文中用以自称或对称,有时替代相应的人称代词独自使用,有时同人称代词一起并行使用。它们的使用不仅丰富了古代代词的用法,同时又使表达的感情色彩多样化。这些别称词产生于特定的时期,应用于特定的时代,因此,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它所使用的时代的文化特点。往往一个词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作品中所表露的不仅仅是本身的含义,还牵连着那个时代的丰富文化内涵。在它使用的过程中,可以透视出来自社会习惯、民族心理、社会心理,乃至伦理道德规范的诸因素的影响。
《左传》是先秦时期的典范文学,它从政治、军事和外交各个方面反映了春秋时期的社会生活。《左传》在行文称对上广泛地使用人称代词和别称词,这些别称词和其他人称代词并行使用,形成了《左传》人称代词的使用特色。这种使用特色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春秋那个时期的语言特点,同时也折射出那个时代的文化特点。
一、《左传》人称代词和别称词的使用反映了谦恭礼让的贵族文化风范
《左传》人称代词和别称词的使用特色,反映的是春秋时期“以礼为质”的贵族文化特点,正是这种“礼”文化导致了在行文称对上大量别称词的使用,体现出极尽谦恭礼让的贵族文化风范。
春秋时期正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的时期,虽然此时奴隶制度已经解体,但是奴隶制时期的文化作为一种精神积淀,仍然在社会中制约和规范着人们的言行。因为文化是一种社会意识现象,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附着于经济基础之上的观念形态。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着文化的特点,取决于一定经济基础的文化一经确立,便广泛地深植于民众的内心,成为社会的共识,对社会思想起着调控和导向的作用。它又是靠民间的约定俗成,或统治阶级的长期教化而沉积下来的,因此,文化是一种历史的长期积淀,它不会因为社会制度的迅速解体而烟消云散,它有相对的独立性,还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影响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相对于社会制度而言,文化具有一定的持久性和深重性。《左传》别称词的使用正体现了文化的这种持久性和深重性,虽然《左传》反映的社会生活是春秋时期奴隶制度社会的解体时期,但是奴隶制时期的贵族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的积淀,还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起着规范作用。
奴隶制时期的文化是以“礼”为核心的贵族文化,我国的奴隶制社会经历了夏、商、周三个时期。夏商是以王权为质的神权礼文化时期。这一时期的神权畸形发展,几乎无物无处无时不问神,也正是这种对神的崇尚文化才产生了礼。“礼”,“所以祀神致福也”。[1]“礼”本指的就是祭神的仪式。因为对神的盲目祟尚和神的无处不在,这些敬神的仪式就散布在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演化成约束人们言行的准则和行为规范,即“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明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2]这种礼文化在西周时达到鼎盛时期。“礼”表现在贵族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词、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3]“礼”是贵族文化教育的核心,因为当时的“礼不下庶人”的标准,庶人是没有接受这种礼文化教育的权利和机会的,可以说“礼”只是贵族阶层的专利,也是贵族文化的核心,以这些“礼”文化教育出来的贵族为主导构成的社会系统不是靠法律来调节的,而是靠“礼”来维系的。在这些“礼”的教育和熏陶下,贵族以有“礼”为上,以遵“礼”为德。春秋以降,文化下移,民间私学兴盛,但以孔子为代表的民间私学也是以“克己复礼”,践行周礼为教育目标的,因此“礼”仍然成为春秋时期人们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礼、乐,德之则也”,[4]“礼所以观忠、信、仁、义也”;[5]“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姐妹、甥舅、婚媾、姻亚、以象天明”。[2]整个社会的文化显示着“礼”的风范。在“礼”的约束和规范下,人们自觉自愿地进行道德的自我修养,以“温、良、恭、俭、让”为自身修养的尺度,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践行自卑而尊人,谦让而有礼。
《左传》是一部记载和议论国家大事的史书,而在当时,可以对国家大事发表议论和见解的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有识之士,因此,整部《左传》的应对言辞都体现着受过良好教育而表现出的恭让有礼和谦逊雅驯的贵族文化风范。我们只截取《左传》中言辞应对里人称代词和别称词的使用情况来考察这一时期贵族文化讲“礼”的特点。这在《左传》中有两个方面的表现:
(一)君臣之间的言谈称对上,极尽恭谦礼让的文化风范
1.祭仲曰“:……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
公曰“:多行不义必自毙,子姑待之。”[4]
2.对曰“: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矣,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
公曰“:尔有母遗,繄我独无 ?”[4]
君对臣在谈话当中的称对,在对称上用的是相当于“您”的敬词“子”,在自称上用的是相当于“你”的“尔”和“我”,这说明春秋时期的诸侯王在对待他的臣下的态度上是尊重和礼遇的。一方面,当时的诸侯王处于周天子的统治之下,不具有高高在上、唯我独尊的自大心理,这同封建社会时期的君王心理状态是不同的。另一方面,春秋时期是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时期,社会处于急剧的变革之中,诸侯纷争风起云涌,在争斗中,各个诸侯王都跃跃欲试,有雄霸天下的野心。谁能任用贤人,谁就会多一分争霸的机会,因此当时开明的诸侯王纷纷礼贤下士,广纳能人,对有才能的士庶人极尽谦恭之礼,在言辞称对上表现出尊重礼遇的态度。同时,诸侯王本身受的是礼的贵族教育,因而在言谈中也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谦敬有礼的儒雅风度。
臣对君的言谈中,在对称时,他们用敬称词“君”相当于“您”,在自称上用谦词 ,如“臣”、“小人”等 ,尽量降低自己的身份,以提高对方的身份,达到“谦卑有礼,恭让有序”,显示出良好的文化修养,这说明春秋时期在言谈称对上君臣之间讲究文雅得体、谦恭礼让的文化风格。
(二)外交辞令的称对上,显示着恭让有礼、温文尔雅的贵族风度
1.郑伯对许大夫曰“:天祸许国,鬼神实不逞于许君,而假手于寡人,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亿,……吾子其奉许叔以抚柔此地民也。”[4]
2.齐侯曰“:岂不谷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谷同好 ,如何 ?”[4]
3.郑伯肉袒牵羊以逆,曰“:孤不天,不能事君,使君怀怒以及敝邑,孤之罪也,敢不惟命是听”。[4]
4.下臣不幸,属当戎行,无所逃隐。且惧奔辟而忝两君。[4]
这些句子都是两国外交上使用的辞令,这些外交辞令自称总是“自卑而尊人”,用降低自己身份的谦词,如“不谷”、“寡人”、“孤”、“下臣”、“敝邑”等,而在称呼对方时彬彬有礼,总是用“子”、“吾子”、“君”等这些相当于“您”的敬词,即使在大兵压境的前提下,也不失“寡人”、“吾子”等谦敬的儒雅风度,在极尽谦恭文雅之中,不卑不亢,内藏锋芒,显示着决心和力量。任何时候都不失安详典雅的风度,这无疑说明了谈话人即贵族官员的良好文化修养,同时也代表着春秋时期贵族的辞令风格。
二、《左传》的人称代词和别称词的使用反映了贵族文化等级差异的特点
《左传》人称代词和别称词尊人卑己的使用特色也反映了春秋时期贵族文化具有明显的等级差异的特点。
春秋时期是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时期,奴隶制时期的社会等级秩序在这一时期仍制约着当时的社会秩序,特别是春秋社会的早期和中期。而奴隶制时期的社会阶级秩序除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两大集团层次外,单单是统治阶级内部也存在着层次差异。奴隶制时期的统治阶级贵族上层分五个等级,即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其中士是贵族阶级最低的一个层次,属于上层社会的被领导阶层。在春秋社会的初期,这种阶级结构的社会秩序制约着整个社会的结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动乱的加剧,又由于各诸侯国内部的争权夺利和各国间的频繁战争,原有的社会等级秩序受到了激烈的冲击,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亡国丢爵的贵族下降到士庶阶层,而一些有才干和能力的庶人,凭借着战功或某一方面的才干上升为贵族的官员阶层,形成了春秋末期的贵族下降和庶民上升的双向流动。但这种双向流动并没有破坏奴隶制社会原有的阶级秩序的尊卑差异,只不过是阶级身份的交换罢了,降为士庶阶层的贵族不再拥有尊贵的身份和地位,而上升的庶民则具有了上升为贵族阶层的身份和尊贵的地位。这种交换不能也不可能改变社会整个阶级的秩序,因为随之而来确立的封建社会仍是一个阶级社会,仍需要这种等级差异的秩序来维系社会的结构。因此,春秋时期虽然处在急剧的社会变革时期,但是奴隶制时期的等级秩序仍在社会上起着一定的制约作用,人们安于这种等级秩序对自身身份的等级差异,并在言谈中自愿地表露自身有差异性的身份,如“君、臣、小人”等。同封建社会比较起来,奴隶社会的这种等级和身份的差异性,更易于被人接受并遵从。这是由它所产生的特定的社会基础决定的。中国的奴隶制社会是以原始社会血缘亲族为基础的宗法宗族制度,原始的宗法宗族制是以血缘为纽带连结起来的人际关系,在这种制度下,人不是作为社会的个体来认识个人在社会中的存在价值,而是作为整体家庭的一员,以他在家庭中所处的地位和身份来界定作为家庭成员的个人的感情辐射和投入。例如,为人子与其父的服从关系,为人兄与其弟的友爱关系等,这就形成了为人子与其父兄的服从和敬爱关系,然后再把家庭中的这种人际关系推而广之,把社会作为一个更大的家庭来活动,这样在家庭中祖父子的辈份等级,服从关系就随之而进入社会。这种缘于亲情的等级关系,适合人情,充满了人情味,因此易于被民众接受。奴隶社会的统洽阶级正是看重了这一特点,把它加工整理而形成了奴隶社会系列的人际关系,把社会上的人际关系家庭化,用父子关系看待君臣关系和长幼关系,给这些用以维护君臣、父子、夫妇等级和名份制度的人际关系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虽然是维护奴隶制的等级关系,但让人感到合乎义理,因此,人们自觉地甘于自身身份的规定性。在言谈举止中安于特定的身份和地位,当身份低于谈话者,作为下级与上级谈话时,使用敬称词,而自称时则用谦称词或平称代词。例如:
1.天方授楚,楚之赢,其诱我也。君何急焉?臣闻小之能敌大也,小道大淫。[4]
2.谓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4]
3.对曰“:可哉!吾侪小人所谓取诸其怀而与之也。”乃复封陈。[4]
4.小人有母皆尝小人之食,未尝君之羹,请以遗之。[4]
上文例句中使用的“君、臣、小人、我、吾”这些代词和别称词的使用特点,都说明了说话人的特定身份和地位的尊卑。在整部《左传》中,每个人在言辞称对上都不忘自身身份的规定性,及时地表露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身份的尊卑,这说明那个时期的文化,即以“礼”为质的贵族文化规范着人们的这种言辞习惯,反映了人们的身份上存在着这种差异性,这也正说明奴隶制时期的贵族文化具有规定身份差异性的特点。
[1] 许慎.说文解字[Z].北京:中华书局,1979.67.
[2] 十三经注疏[M].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影印本.1611,2107.
[3] 李志敏.礼记·四库精华(卷一)[M].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02.4.
[4] 左丘明.舒胜利,陈村霞,译注.左传[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97,1,2,12,53,169,200,24,122,167,2.
[5] 韩铁铮,石延博.国语[M].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2005.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