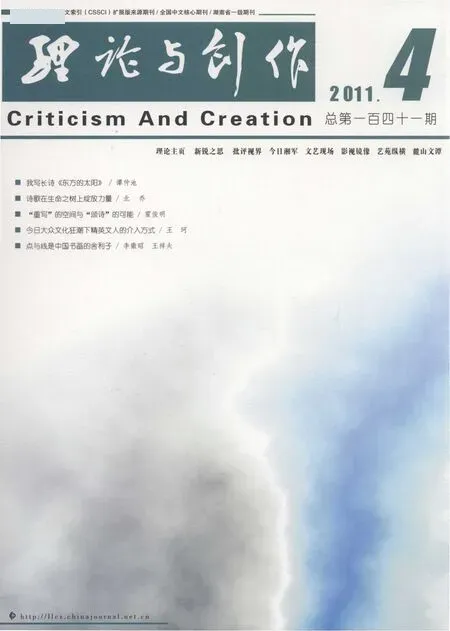《村庄秘史》的湖南地域文化色彩
2011-11-24颜浩
■颜浩
一
长篇小说《村庄秘史》的精彩独到之处,首先自然在于它是一部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的批判书。作品通过叙述老湾村五个具有“秘史”性质的故事,对现代中国你死我活地斗争的社会形态及由此形成的身份文化,进行了视野独到的审美剖析与历史批判。但这部小说另一个更为重要的精彩独到之处,还在于作者的这种审美批判,是通过一种民间文化色彩极为浓郁的乡村叙事表达出来的,这种民间文化色彩不仅存在于对区域风俗民情丰富而鲜活的展示,而且渗透到了文本的审美视角、思维方式和价值倾向之中。正是历史文化反思的理性主旨与民间文化底蕴深厚的审美境界二者有机融合,才使得这部洋溢着湖南地域文化色彩的长篇小说,显得既视野开阔、立意高远,而又深邃混沌、耐人寻味。
大体看来,湖南的地域文化底蕴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屈骚”楚文学所体现的浪漫神韵和巫楚文化意味,二是近世湖湘文化所提倡的经世致用立场、以及由此衍生出的社会政治情怀。在当代的湖南文学创作中,这两方面的地域文化特性都有鲜明的体现。以1980年代获得广泛赞誉的两类作品为例。古华的《芙蓉镇》、叶蔚林的《在没有航标的河流上》、孙健忠的《醉乡》等“乡土文学”类作品,以乡土风景、风情画卷侧面展示时代的社会政治现实,谱写出一曲曲境界清新而主题严峻的“乡村牧歌”,其中既有先秦楚文学内含痛楚而依然明丽神奇的浪漫风韵,又有近世湖湘文化经世致用聚焦于政治功利的特征;韩少功的《爸爸爸》、孙健忠的《死街》、彭见明的《大泽》等“寻根文学”作品,则致力于“打捞”具有神秘、诡异、原始的巫楚文化特性的民间生态碎片,以之为基础,拼接、拟构出一个个极富荒诞意味和寓言色彩的艺术境界,从而使自我基于文革梦魇和民族忧思的、孤愤而迷茫的文化生存体验,得到了深邃、独特的审美表现。可以说,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构成了这些作品享誉文坛最为重要的审美优势。
王青伟的长篇小说《村庄秘史》,则融贯了湖南“乡土文学”和“寻根文学”的审美传统,更为广泛、深入地开掘出20世纪湖南“村庄秘史”中所蕴藏的地域文化资源,并以极富先锋精神和魔幻意识的艺术笔调,将其有力地表现了出来。
二
承接湖南乡土文学谱写“严峻的乡村牧歌”的审美传统,《村庄秘史》也是通过描述处于社会主流文化边缘位置的“村庄秘史”,来实现社会历史批判的创作意图。
作品的整体艺术构思,就承接了湖南“乡土文学”寓时代风云于乡土生态的审美传统。一方面,从章大、章小革命历程所包含的人生隐曲,到章顺和章义故事有关阶级成分、社会身份的纠结与困苦,从老湾和红湾之间集体杀人事件显示的文革乱象,到再娃“大炮”泄愤事件体现的市场经济困局,作者社会历史批判的意图表现得相当明显。另一方面,这些故事又都是以老湾村“秘史”这种民间生态显示出来的。木匠章顺的性爱故事和再娃的“大炮”泄愤故事,本就是老湾村内部一种民间自在生活性质的矛盾纠葛,即使是与外界时代风云联系相当密切的章大革命故事和章义身份故事,作者也不是以既处于社会价值主流位置、又极具类比意义的章小为审美视角和价值本位,而是选择了革命伦理的罪错者、坠落民间的失意者章大和章义作为叙事的重心,着力表现他们在革命者身份失落的卑贱状态中无法获得生命存在意义的困局,以及由此带来的身心折磨与精神屈辱。由此,一种聚焦乡土民间生态、侧面透露时代动向的审美路径,就明显地表现出来。
作品价值基点的选择,也体现出一种民间文化本位的倾向。作者反思老湾村的人生故事和村落历史,总是特意地选择一种具有民俗性质的地方风物来作为价值参照物。章大慨叹其坎坷人生的意义,虽然也存在以衣锦荣归的革命成功者章小为价值参照物的倾向,但作者着重描述的,却是章大对于章小幸运的嫉恨和关于人性常态的感慨,这其实是在以别一种方式,对未曾亲尝被捕滋味和“筷刑”恐惧的章小的人生姿态,表达着某种不以为然。而作品对“神童”、“才子”章大进行人生可能性体察更为重要的价值参照物,其实是湘南著名的文物古迹“浯溪石壁”,以及那乡野石壁上所呈现的、历代文人天性自由发挥的潇洒人生。无独有偶,在木匠章顺的性爱故事中,对老湾人矛盾纠葛、恩怨情仇进行价值判断的参照物,也是一种非主流的民间文化形态,就是麻姑所携带的另一种文化民俗“女书”,以及千家峒“女书”文化那“从来不与人争斗”、“我们爱朋友,也爱敌人”的价值立场。实际上,章春从逃逸空间的角度,将自己存在抢劫杀人嫌疑的冤屈和父亲章义因“历史问题”而无法证明身份的境遇相比较;再娃以同归于尽的复仇方式,来表达老湾人在资本经济压迫面前的耻辱与愤怒,这些也都是一种民间式的世道理解和情绪表达。利用民间文化资源开启价值视角、展开对世道人生体察,《村庄秘史》民间价值本位的审美倾向,在此已表现得相当充分。《村庄秘史》的人物关系构架,同样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其中最为突出的例证,就是女性人物形象的设计。在作品的五个故事中,不管每个故事的具体社会历史内涵如何,作者一律设计了一个理想化的女性人物形象。章大、章小的革命事业,是以皮肤嫩白、眼神忧郁的县城美女斯美的情感偏向,作为成败与得失的分野;章顺的性爱故事中,只有千家峒来的麻姑显得善良无辜而楚楚可怜;在战俘章义的凄苦人生中,是贤妻良母田香的似水柔情,给了他生命的滋润;老湾和红湾的集体屠戮事件中,也是女生亦素,才使长期卑贱屈辱的红湾人“在静默中彼此心照不宣地达成共同的意志”;即使在章得杀死了蒲月丈夫的情形中,前来缠住章得做婆娘的蒲月,也还是由沉默地劳作,而逐渐心疼起因恐惧日渐消瘦的章得,然后甚至反过来,协助章得“让娃崽彻底变成老湾人”、“从根子上断绝他复仇的欲望”。作者对这些女性的美好品性及其不幸遭遇的描写,对她们人格形象理想化、诗意化倾向相当一致的刻画,实质上是创作主体本身对人性、人道应然状态的精神感应及其审美对象化。而这种“香草美人”式的审美阐述路径,恰是从“屈骚”楚文学典型的意蕴表达方式,地域文化精神的审美传承,在此表现得何其鲜明!
三
《村庄秘史》还以覆盖面相当广泛的意象性叙事和象征寓言性描述,从而使文本在对社会历史层面理性内涵的表达上,显示出浓厚的巫鬼文化色彩和巫性思维特征。作品审美境界浓厚的神秘、荒诞乃至诡异的气息,也由此而来。这又从审美思维方式的层面,体现出湖南地域文化的深刻渗透和影响。
先秦时期的楚人,就有“信巫鬼、好淫祀”的民俗习性。《楚辞》中众多作品那万物有灵而人神、神鬼不分的世界景观,那充满神奇幻想和浪漫情思的审美境界,正是巫楚文化的审美体现,一种以直觉和启示去感悟的、原始人类对世界的诗意认知方式,也就隐含于其中。千百年来,巫楚文化这样一种具有原始宗教意味的区域文化,似乎成为了湘楚大地根深蒂固的一种传统。湖南新时期的“寻根文学”作品之所以充满神秘色彩和浪漫意味,也正是因为创作主体在追溯和发掘“绚丽的楚文化”的基础上,将散落于三湘四水之间的神话传说、宗教巫术、节庆礼俗之类的民俗民风都纳入创作视野,进行了文化感悟诗性化的审美诉求与湘楚民间遗存的巫鬼文化传统二者的审美融合。《村庄秘史》就是同样的审美道路和叙事策略。
《村庄秘史》描述了大量的湖南乡土风物。从老湾标志性的大枫树、老湾和红湾的隔河相望而以石拱桥相联等乡村景观,到木匠章顺的葫芦把、老湾村民的鞭炮制作等民间事像,再到目连戏、女书、浯溪、树皮书等实有和带有神话色彩的文化民俗,等等,作品中所在皆是。作者将有关这些乡土风物的内容有机地融入故事情节,进行了引人入胜的描述。在这类描述中,作者超越以优美笔调写明丽地域风情的审美层次,采用诗意和哲理相融合、极富象征寓言色彩的笔法,在亦实亦虚、亦真亦幻的描述中,显示出一种民间生态神秘化、精神感悟具象化的审美特征,神秘、诡异的巫鬼文化气息也就自然地弥漫于其中。实际上,全书以章一回被“索命”之际的讲述为叙事框架,包括章一回那张“与他村里的一块岩石一模一样”、与女人在一起时却又“会变得灿烂无比”的脸,包括章一回在讲故事的过程中逐渐变年青、变小,最后“变成了一个蜷缩的婴儿”、“像一团透明的血球落进了那棵樟树的黑洞之中”,“仿佛回到了子宫”的生命形态,都使全书从整体上显示出一种巫鬼文化的神秘、诡异的色彩。
作者对于具有老湾村整体意象性质的“大枫树”的描写,在这方面具有相当典型的意义,我们不妨以此为例,来进行一番更深入、具体的分析和阐述。
首先,在老湾村作为对乡土风物的写真,大樟树具有老湾村沧桑历史见证者的意义。从前,老湾村前是一片浓荫蔽天的樟树林,创造了传奇性伟业的老湾村祖先章巴掌和章可贴,就都埋在河岸边那棵最大的樟树下,由此,樟树林不仅是老湾村的标志性自然风景,而且成为了“老湾祖先曾经兴旺和发达过的象征”。历史进入“现代”之初,章铁才创办新学堂,教生物的女先生领着学生“到樟树里去捕捉知了和金鹏、蝴蝶、蚂蚱,把那些东西全部制成标本”,从而给老湾村带来现代科学的气息。在现代中国风云变幻、血雨腥风的年代里,大樟树林又成了伤痕累累的老湾人情感与心灵的栖息之地、寄托之所。革命的背叛者章抱槐见到了故乡的樟树林,才觉得“一股沁人的乡情渐渐地融化温暖着他那颗受伤的心灵”。回乡以后,他甚至常常在梦游中走进樟树林、爬到樟树上看书,最后干脆住到了樟树上,在樟树上练嗓子,无师自通地蜕变成一个唱戏的名角。在战乱年代的白云苍狗中又被国民党所抛弃之后,他“像一个被丢在荒原中的野狼那样找不到归途”,仍然是“想到那片樟树林中去寻找自己的灵魂”,“只有在樟树林中他才能找到心灵的憩息”。解放后,衣锦荣归的江河水回到故乡,自惭形秽的章抱槐在众人的欢笑声中惴惴不安,所选择的还是“躲进村前的那片樟树林”。最后,在一个雷电交加的夜晚,章大终于“死在那棵比他还要苍老得多的古樟树边”。后来,“有一年大伙发了疯,到大山上见树就砍,砍了就烧”,最后终于“把一片樟树林砍光了,剩下那棵葬有章巴掌和章可贴的樟树”,“于是那棵老樟树就变成了老湾人记忆中遥远的回响”。显然,大樟树在这种客观写实型的描述中所显示的,仍然是它的自然形态和地域风情的意味。
但作者的描述,同时又延伸到了老湾村民俗文化形态的层面,使大樟树显示出一种老湾村文化图腾的性质。作者细致地描述了老湾人“敬畏樟树”的现象。“什么东西老了都会成精”,樟树林也是如此,在老湾村的夏夜,小矮人在“樟树下跳舞表演奇异节目”的“相似的情景”总是反复出现,“热闹”而“神奇”。于是,老湾人渐渐地“把那颗樟树当作不死的祖先”,积淀成一种集体性的敬畏心理。以至在那“见树就砍,砍了就烧”的年月,本来不信“鬼神”和“树精”的章天、章水,在砍伐樟树时也表现出对“砍树的罪孽”的恐惧与避讳;而他们后来“被响雷劈死”和“饿死”的横死结局,在村民的联想性追述中,也逐渐演绎成了砍伐樟树林的“报应”。大樟树的神奇甚至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就是再娃在红湾和老湾之间“勾接血脉”、变成老湾人,也需要“在樟树的地底下捕获一百只雄雌各半的蚕蛹”,捣碎并用精血浸泡后吃下去。很显然,在老湾村民的民俗文化心理中,“对那棵大樟树有着近乎图腾般的崇拜”,而且其中散发着浓厚的巫鬼文化气息。
以这种老湾的村落历史、个体情感和集体精神的积聚为基础,作者对大樟树形象的刻画,就顺理成章地进入到了意象叙事的层面。具体说来,就是将大樟树作为老湾村及其全部历史文化内涵的象征,并以之为基点,拟构出意象化地表现主题的超现实情节。集体杀戮事件无疑是全书情节和主题演绎的高潮。在对这一事件的描述中,最初挥刀砍向老湾的“红湾的陈生死在樟树上”、“整个树周围的地面全都染红了”这样的写实性场景,实际上是略写的,而作者详加描述的、对展示文本意蕴更为重要的情节,则带有明显的魔幻性质。首先在老湾村方面,集体杀戮的指挥者章一回,“发现自己的那张脸像极了那棵樟树上的皮,而且他觉得自己就是那棵树的幻影”。在他被一种神秘力量“吸进樟树里时”,发现了那卷“用树皮订成的书”,“一部关于老湾人秘不可传的史籍档案”,已经成为“上面派来的人”的章一回,由此知道“破译了这页文字的人,他才是真正的王”。其次,红湾方面则密谋着将那棵樟树当作“封建的最大象征和见证,他们将以反封建的名义将老湾那棵树砍掉”,因为有一个“红湾和老湾人共同知晓的传说,只要砍掉那棵樟树,老湾整个村子就将沉没”,他们毁掉大樟树,竟然就真能“把老湾的命根子给拔掉”。于是,他们齐心协力,把桐油浸泡过的“奇长无比”、“水桶般粗”的绳索捆在樟树上,用火烧;制作锋利无比的火箭,万箭齐发,“用火箭刺中它的心脏”。最后在那个深夜,“从对岸的红湾射过来无数支带火的箭,齐朝老樟树飞去”,而“老湾人在惊恐中感到那些箭不是射到了树上,而是击穿了他们每个人的胸膛和灵魂”。第二天,“樟树身上流满了红色的樟液”、“红湾连接老湾的那座石拱桥突然断裂坍塌了”,“老湾和红湾人全部处于了一种失忆状态”。万物毁灭、天地洪荒,只有几个老人“在寻找记忆的时候,他们忘掉了仇恨,也忘掉了河对岸那个叫红湾的村庄”。在有关大樟树的这极具魔幻色彩的描述中,巫鬼文化的审美思维特征就相当明显地表现出来。
综上所述,作者实际上是将大樟树作为老湾村生存状态和文化特征的艺术象征,采用写实性与魔幻化相结合的笔法,对其自然形态、民俗形态和意象形态等多层次的审美意蕴,进行了深入的审美发掘和精神批判。正是这众多的由意象叙事和鲜明的巫性思维特征,使《村庄秘史》显示出一种将价值观念普适性与内涵呈现地域性方式相结合的审美追求,地域文化底蕴的渗透和影响,也由此清晰地显现出来。
四
《村庄秘史》湖南地域文化特色的形成,与创作主体的审美意识存在密不可分的联系。从这方面看,作品显示出以下方面的主要特色。
首先,《村庄秘史》中重要的乡土风物和民间事像都是湘南地区民间的真实存在,文本审美境界的地域文化意蕴,则是从这种客观实在出发所展开的审美阐释。“正因写实,转成深刻”(鲁迅语),遵循着这样一条思想路线,创作主体的价值原则和精神立场,就获得了深厚的文化资源来作为支撑和依托。章抱槐对“才子”类文人生命意义的慨叹、麻姑对乡土社会人际关系的判断,都是因为有浯溪石壁和千家峒女书这样确存于湘南地区的著名文化遗产作为价值基础,才具备了底蕴的深厚、坚实性。而且,这种审美选择,还使那种纯粹的民间风情想象和民间文化“碎片”拼接所可能导致的“伪民俗”色彩和底蕴空疏、含混的局限,得到了有效的避免。
其次,作者在对于乡土风物的描述中,显示出强烈的思辨色彩和暗喻、象征等意象化叙事的特征。比如驼背、断腿,本来都是平淡无奇的特殊民间事像,但作者以章义的驼背来暗喻他处境的卑贱与屈辱,以断腿及假腿的钢棍来表达再娃困兽般的焦躁与宣泄,并把他们的人生境遇和生理特性融汇到一起,来拟构极具寓言色彩的故事情节,于是,一种将精神问题具象化、又将民间事像描述引向精神境界的思辨色彩,就相应地形成了。这又使作品超越了对于奇风异俗进行猎奇性描述的、“为民俗而民俗”的审美境界,显示出一种精神的深度和更多的艺术回味的余地。
再次,《村庄秘史》的地域文化发掘,表现出一种对于乡土病态事像的关注和鲜明的批判意识。在这部作品中,对于各种丑陋、病态乃至污秽的民间事像的描述确实相当密集,甚至让人阅读起来心生某种生理上的不快之感。这其实是对“寻根文学”以来中国文学审丑意识的一种借鉴与承接。虽然其中描述的详略和渲染的程度,确实存在尚有可斟酌之处,但总体上看,作者选择这类乡土事像来建构艺术意象,目的显然在“以毒攻毒”,从审美感受的层面与文本的社会历史批判倾向达成一致性;而作者灌输于其中的严峻、深邃的历史批判内涵,也能够有效地构成对丑陋民间事像的审美超越。比如,在女人“那流淌着奶与蜜”的隐秘地方加上一把锁、以男人的精血浸泡蝉蛹喝下去以改换血脉,这两个意象化的细节初看起来确实相当污浊。但是,前者正因为细节的令人触目惊心,才使作品对老湾村乡土伦理的暴力、非人道特性,体现得格外地残忍、阴损和刻毒;后者则以一个颇具诡异色彩的细节,情理并茂地将当时所谓“改造”、“脱胎换骨”的时代要求及其荒谬、滑稽的特性,高度浓缩地揭示了出来。
所以,对湖南地域文化进行视野独到的发掘与表现,并以之为基础谋求社会历史批判的理性主题的深化,这其实是创作主体相当自觉的审美选择。正是这种充分的主体自觉,使《村庄秘史》的审美境界显示出一种文化视野的宽广度和精神探索的独特性,并以深厚的地域文化后援,夯实了文本审美意蕴的价值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