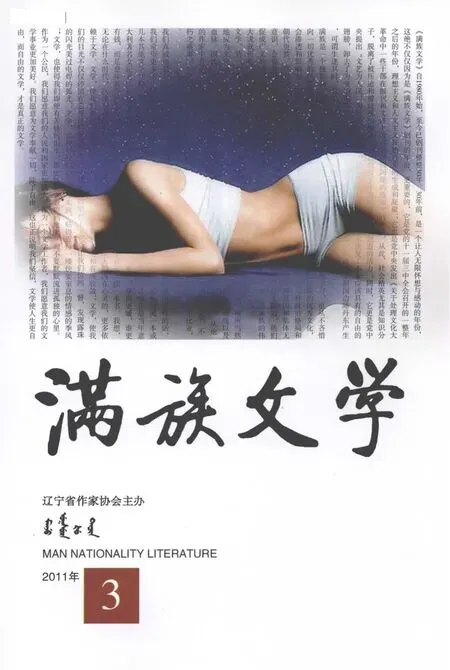子夜雨潺潺
2011-11-20聂鑫森
聂鑫森
子夜雨潺潺
聂鑫森
一个个焦雷拽着紫蓝的火花,在空旷寂寥的郊外滚动,好像是一个个疯狂旋转的车轮,互相撞击着,发出宏重的声响。大拇指一般粗的雨鞭,嘶叫着抽打远近稀稀落落的几栋漆黑的建筑物和这条坑坑洼洼的土石路面,溅起一大团大团湿漉漉的水雾。
墨黑的天幕上,不时地划过一道灿白的闪电,如一把利剪“嚓”地剪开厚重的绒布。满耳是风声、雨声、雷声,却没有人声。在此一刻,尽管时令已是初夏,我却蓦然感到了逼人的寒意。
刚才听音乐会的兴奋,采访歌星们的愉悦,全在蹬车的途中被这场突如其来的雷雨洗涮得干干净净,衬衣湿透了,冰凉地粘在脊背上,让人觉得难受。但难受总比被雷火击成一段焦黄的“鱼”来得潇洒,当然在采访归途死去应该荣获“烈士”称号,可那时我什么都不会知道。
离家还太远,无法一口气蹬完这长长的路程,终至被逼到这空空洞洞的公园的门楼下。因为寒冷,因为孤独,于是一种深重的寂寞便铺天盖地而来,幸而这门楼非常粗重非常结实,否则真有可能被压塌。
这场雨什么时候会停下?不知道。至于我还得在这门楼下呆多久,同样不可预测。
渐渐地,我的心情开始平静下来。看看表,快十二点了,长长的夜对我来说,在哪里都一样。回家?哪里是家?那只能叫“屋子”,所谓“家’,即表示在厚重的屋顶下活跃着几个生命,妻子、孩子什么的,可我没有!至今为止,还是光棍一条。
大学毕业,招聘到报社当记者,一晃就是几年,自个儿去找过对象,多事的熟人也介绍过,就没让我碰到过只要见一次面、谈一次话就为之神往的异性。并不是我条件有多高,我不问门第不问学历不问职业,甚至连相貌也不怎么注重,只希望彼此间一个眼神一句淡淡的话,能达到一种默契一种心的共振,可是没有。于是我开始耐心地等待。就像此刻等待雷雨停歇,我好蹬上车回我那空落落的屋子里去。
身后的这座公园漆黑一片,真静,它离市区太远,加上夜深人寂,加上这一场雷雨,再有雅兴的人也不会在里面呆。只有我傻呆在这门楼下,孤零零地等待。
雷还在响,雨还在下。
我靠着门楼的石壁,希望想点儿什么,可又什么都不愿意想,脑子里空空的。
有一团黑影,急速地朝门楼扑来,一直扑到门楼下,才猛地刹住车。
又是一个躲雨的人。
我莫名其妙地高兴起来。这该有多好,我不再孤独不再寂寞,在这雨夜,总算有个可以搭腔的人了。但一刹那间,我又失望了,来人是一个女的!这门楼下将划分出两个世界,一个陌生的男人和一个陌生的女人,彼此将互相警惕互相提防。在这寂静的深夜,谁知道会发生些什么事呢。
尽管如此,借着微弱的灯光,我还是把她打量了一阵。她大约二十五六岁的样子,一蓬短发湿湿地重重地覆在头上,发梢不停地滴着水;但那张脸很白净,眉目间充满一种孩子似的天真;白色的连衣裙紧紧地绷在她身上,勾勒出各个部位很流畅的线条。
我的心不知道为什么“砰”地一响,脸颊竟有些发热。
也许是她刚才仓皇之中驰入这门楼下,竟然疏忽了我的存在。她利索地支好车,然后抹了抹脸上的水珠子。但突然之间她感觉到了一点什么动静,她的目光扫向了我。她万万没有想到,还有一个陌生的男人在避雨,抹水珠的那只手停住了,然后又飞快地抹了几把,那动作分明透出她心底的慌乱。她低低地说了一声:“这雨……这雨……”然后,迅速地用双手抓住车把,把车头调过来,准备离开这地方。
雨哗哗地下得挺有耐性。
她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一个流浪汉?一个在逃犯?一个无家可归的小赖子?而且随时会对一个手无寸铁的弱女子进行袭击!
一种受辱的痛苦和愤怒煎熬着我,心如一块生铁被一团烈火焚烧,扭曲成一个难看的形状。这么大的雨,她一路淋回去,准会感冒的。既然这门楼下只能允许一个人的存在,作为一个男子汉,就应该毫不犹豫地离开这儿,闯到雨中去。
她已经把车头调过来了。
我大声说道:“喂,你别走,你留在这儿,雨太大,会感冒的。我就走!不过,我想对你说,我不是歹徒!”
我边说,边推上单车,朝门楼外走去,很有一点视死如归的气概。
她惊愕地停住了推车,转过脸来,轻声对我说:“先生,对不起。我……不走,你也别走,这雨实在太大了。”
“你不怕……”我揶揄地问。
她好看地笑了一下,摇摇头,显出一种调皮的样子,说:“不怕。”
我松了一口气,心头一热,升起一股感激之情,是的,我得感激她对于一个陌生人的信任。
我们重新支好车,各自靠着门楼的一边,单车成了一道庄严的“三八线”,彼此默默地对望着。
我发现在她的发梢上,粘着一缕白色的棉絮,衬着湿漉漉的秀发,很是显眼。她一定是一个纺织女工,对,这郊外有一爿国棉八厂,她准是下夜班回家,和姐妹们没走在一道,在途中遇到了这场雷雨,急匆匆只好避到这门楼下来。
我注意到她不停地眨巴着眼睛,借着昏暗的灯光仔细地打量我。她准在猜测我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会在这儿避雨。我真想告诉她,我是记者,因为采访一场音乐会,耽搁了时间才遇到了这场大雨,没法子赶回去,只好躲到这门楼下来。可我没有说,打着“记者”招牌行骗的人多着哩,谁信这个!那么向她出示记者证?荒唐。人与人之间,不是凭一个证件可以达到互相理解的。于是,我什么也没有说,也没有做,只是默默地靠着门楼。我真想抽一支烟,一摸口袋,烟早湿透了,只好悻悻地掏出来,丢到地上。男人有时可以靠一支烟摆脱尴尬,可我没有烟,真他妈的晦气!
她忽然“咯咯咯”地笑起来,笑声如晶亮的珠子,滚落在石块地上,滴溜溜地颤到我的脚边,真好听。
我问:“你笑什么?”
她不笑了,顿了一阵,才说:“我想起小时候,和哥哥到外婆家去,傍晚时候,遇上了雨,我们躲在一个屋檐下。天渐渐地黑了,雨真大,我好怕。哥哥只比我大两岁,就哄着我,给我讲故事,什么‘灰姑娘’啦,‘小人鱼’啦,一直讲到雨停了,星星出来了,我们手拉着手到外婆家去。”
这回轮到我笑了,我觉得挺有意思,于是说:“你想让我哄你?”
她摇摇头,说:“不过,你总可以讲点别的什么吧,不讲话,真让人难受。”
“你喜欢听什么?”
“我想,你讲什么我都会爱听的。”她有些调皮地说。
我说不清为什么竟有些激动,我说,我给你讲《聊斋》的故事吧。
她捂上耳朵,说:“不听,不听,尽是鬼呀狐狸呀,怪骇人的。”
“那么,我给你讲琼瑶的《庭院深深》。”
伴着雷声、雨声,我绘声绘色地讲起来。
她听得很认真,听着听着,眸子里盈满了泪水,显然她被这个故事感染了。
故事快结束的时候,一辆车“呼”地窜到门楼下。因为我们都沉浸在这让人又辛酸又高兴的氛围里,所以当车猛地刹住,车闸与钢圈发出难听的骤然一响,我们都吃了一惊。
从车上跳下一个很粗壮的汉子,脸黑黑的,眉毛很浓,一个脑袋又圆又大。他支好车,走到她靠着的那面墙边,蹲了下来。
我再没有心绪讲《庭院深深》了,她也再没有心绪听了,这个故事就这么被扼杀了,扼杀得悄无人声。她把身子往旁边移了移,尽量离那汉子远一些。
我死死地盯着这汉子,努力地观察着他。
他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这么晚还在外面游荡?他这相貌,又无端地带着几分凶气。
第二、驻村干部(“访汇聚”工作组)帮扶。自治区督促各级驻村力量落实帮扶职责,自筹和协调引进帮扶资金、项目。
他勾着头,理也不理我们,突然伸出手去,在腰部用力地掏着。那儿放着什么?一把匕首?还是一截铁棍?我全身的每根神经都紧张起来,我得有所准备,别让他打我一个冷不防!
掏了好一阵,他从腰间掏出了一个小烟锅和一个小小的黑布烟袋,然后在烟锅里装上烟丝,又到腰间去摸了一阵,摸出一个打火机,“叭”地打出一束金黄的火苗,凑到烟锅前。他鼓起腮帮使劲地吸起来,呛人的生烟味立刻弥漫开来。
她咳嗽起来。
我依旧盯着他,心里说:你别跟我来这一套,我在看着你,真要动起手来,你也得使把劲儿,在大学我好歹是个田径队员,掷铁饼的,手脖子粗着哩。
大约是风太大,雨斜着往门楼里飘,黑脸汉子又往里面移了移身子,嘟哝了一句:“这狗日的天!”
她脸上出现了莫名的惶恐,下意识地又把身子往里移了移,两只手抱在胸前,很可怜的样子。这样子让人想起是到了世纪末,仿佛灾难不可避免地就要到来。
应该把她叫到我呆的这一边来,可是该怎么称呼她?直到目前为止,我还不知道她姓什么叫什么,但我似乎觉得有权力保护她,好像她真成了我的什么人了。
就叫她马兰吧。
“马兰,到这边来吧。”好亲切的口吻,我这是怎么啦?莫名其妙!
她自自然然地“哟”了一声,迅速地绕过三辆单车,站到我身边来,而且站得很近。她一定早就在等待着这一声呼唤,要不绝不会反应这么快。
她侧起脸,望了我好一阵,忽然说:“星期天,你来我家吧,我妈说给我们包饺子吃,你来嘛。”
“好。我来。”我爽快地答应着。
同时,我又对自己的回答觉得惊异,我这是犯傻还是怎么的?到她家去,她家在哪儿?她妈是什么模样?一切都是谜,一切皆不可知。她是曲曲折折地告诉这个黑脸汉子我们是什么关系,警告他不要打什么鬼主意。那么说,我们是在演一个小品,而且彼此就这么顺顺当当地进入了角色。是可笑?还是可悲?一时真还说不明白。
“我妈好喜欢你。”
“嗯。”
“她还说,爸爸快转业了,特地从广州给我们带回一台录放机。”
“嗯。是日本的还是美国的?”
“是美国的。”她认真地说。
我有些陶醉,这么说我们是恋人了,而且已经“恋”了不少日子,一刹那间我相信这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真实得连自己都没有丝毫的怀疑。
黑脸汉子忽然站起来,努力对着我笑了一下,说:“你抽不抽烟?这烟味儿正哩。”
我冷冷地说:“不。谢谢。”
她惊慌地把身子靠住了我,说:“这雨,真讨厌,妈准会急死的。”
我大声说:“别怕,有我哩!”
黑脸汉子尴尬地收回拿着烟锅、烟袋的手,然后望了望天,再望了望我们,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我该走了,这雨一时还停不了。”
他推起他的单车,缓缓地走出门楼,然后骑上车,飞快地蹬起来,很快就在大雨中消逝了。
我觉得很内疚。这黑脸汉子应该是个农民工,那烟锅、烟袋昭示了他的身份。他刚才一定很痛苦,因为他被我们所误解,正如我开始时被她所误解一样!这门楼下,本可以容纳许多人的,因为隔膜和猜忌,使他无法呆下去,只好冒雨而去。
她利索地把靠近我的身子移开了,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绕过单车,重新回到门楼的那一边去。一点也没有牵挂,一点也没有依恋。门楼下依旧是两个互不关联的世界。
沉默。
雨终于停住了。
到处弥漫着湿润润的气息,一切都显得很美好。
云缝间漏下了几点星光。
假如她真是我的恋人,我会邀她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浴着稀疏的星光,去公园里走走,听听虫鸣,看看幽蓝幽蓝的萤火,让那些小径写下我们缠绵的情愫。可惜她并不是“马兰”,“马兰”只是她一个短暂的符号,这符号顷刻间就与我毫无关系了。
她望了我一眼,淡淡地说:“雨停了,我也该走了。”
她一边说,一边迅速地推出单车,慌慌张张地骑上去,连头也没有回一下,就使劲地蹬起来,仿佛为了躲避一场瘟疫。
她走了,如一缕烟,如一个梦。
我依旧靠着门楼,一动也不动,今晚发生的一切,我得细细地咀嚼,而且有一种想痛痛快快哭一场的欲望。
夜更深了。
聂鑫森,男,1948年6月生于湖南湘潭,汉族。中国作协会员、湖南作协副主席。著有长篇小说《夫人党》、《浪漫人生》、《霜天梅影》、《诗鬼画神》;中短篇小说集《太平洋乐队的最后一次演奏》、《爱的和弦与变奏》、《镖头杨三》(英文版)、《诱惑》、《都市江湖》、《生死一局》、《塑料人》、《铁支子》、《吃官仓考》、《轿杠》、《老号手》;诗歌集《地面与地底的开拓》、《他们脖子上挂着钥匙》;散文随笔集《旅游最佳选择》、《收藏世界的诱惑》、《优雅的存在》、《阑干拍遍》、《一个作家的读画笔记》、《触摸古建筑》等文化专著共30余部。曾获过“庄重文文学奖”、“湖南文学奖”、北京文学奖、萌芽文学奖等奖项。
〔责任编辑 宋长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