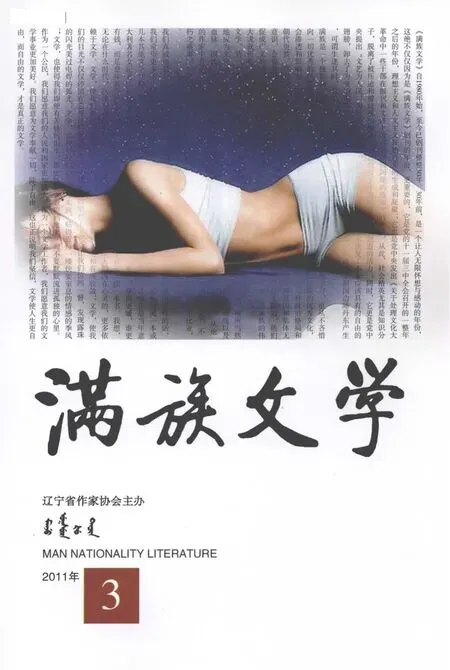让世俗的鸟飞得高一些
——宋长江小说浅论
2011-11-20满族李保平
[满族] 李保平
让世俗的鸟飞得高一些
——宋长江小说浅论
[满族] 李保平
小说是小道,小说、小说,说的就是它的市井的意味。从话本小说开始,我们所记得的《卖油郎独占花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说的都是癞蛤蟆吃到了天鹅肉、多情女子无情郎诸如此类的小人物的幸福生活片断和翘着脚就能够得着的美好愿景。这是第一层意义上的小说,能在这个层面上做得饱满,就已经逼近了小说的属性。
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整个大的小说环境发生了变化,宏大叙事正如其政治上的遭遇一样,被人们敬而远之地悬置在墙壁上,日常叙事温暖地回到人的世界。小说家们正在重新捡拾遗失的常识。从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历上看,日常叙事似乎是由刘震云、池莉等几个领衔人物带动的结果,其实那只是便于文学史的叙述而采取的书写策略,作为浩浩荡荡的人心所向,远不是几个标志性的人所能阐释清楚的。日常叙事在当下找到了双重的聚会点,它既是写作的潮流,同时也是写作的常识。
从宋长江的小说品相上看,他的小说不是潮流的驱使物,而是常识的自然表达。他的生活积淀比较殷实,小说充满了人物与环境之间亲密往来的细节,这亲密是生活常态的文本再现,是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底层社会自然史的一部分。它清晰地显明了小说发生区域的地理特征,那是一个北方中等城市城乡杂糅的属性,它一边消化着城市的欲望,一边守候着乡村的旧梦,当它们彼此纠缠在一起的时候,一个立体而地理的文本坐标就在我们的印象中逐渐矗立起来了,这可能是宋长江的日常叙事小说在社会学意义上的贡献。
我认为,谈一个人的作品与探讨小说的质地合并在一处,会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特别是当我们面对宋长江这样一个基础不走偏的样本时,更能夯实我们说话的起点。在谈之前,我想先引出一个概念——小说的弹性。
什么是小说的弹性?任何事物的最佳状态,我们都称之为充满了弹性,也就是说它不是粘附在某一点上,而是若即若离,似粘而非粘,它意味着坠落与飞翔,它是天空与地面之间游走的一股张力。
我们一开始就谈到了第一层意义上的小说,这种小说是世俗的周折加上一点美好的愿景,也就是说人物和他所要达成的目标之间的那一点子事。世俗的饱满性,是这类小说最大的优长,它包括了生活化的语言、世俗的心态,以及俯拾即是的饱和的信息量。我们说,宋长江的小说具备了上述的素质。但我们应当意识到,这仍是一般状态下的写作,尽管它因为生活的大量占有,而显示出一种强悍的实力。
宋长江的小说对这种一般写作的突围,是因为他终于学会了捕捉一个“点”,这个“点”就是小说的玄机。现代小说与传统小说的区别,根本就在于看作家是否在小说内部布置了一个玄机,而所谓的玄机就是超越生活的力量。
可以说,宋长江在玄机方面捕捉到了一点点,它通常是通过短篇结尾处人物的一句或者带有感官印象、或者不经意间触动人物的心理、或者直击问题的核心的“玄机话语”而表达出来的。
《拉线开关》(《鸭绿江》2009年第八期)结尾,一对父子重新生活在一起,没有女人的日子充满了寂寞,一个邻居女人潜进了两个男人的意识深处。在帮助女人修好了断电的线路之后,找回自信的儿子回到家对父亲说出了一个感受:“爸,隔间的女人家挺干净。”两个男人落魄的生活从此变得积极了,这种积极的改变源于“隔间的女人”给予他们的深刻的感官印象,它使两个男人一潭死水的日子起死回生。这句话是整篇小说的诗意之核,它像光一样瞬间照亮了全篇。因为这句话,宋长江变成了一个卡佛式的诗人,卡佛在他的极简主义的小说里,就是以人物莫名其妙的“冰山”般的对白,显示他对生活的驾驭。
《牌局》(《北方文学》2010年第一期)结尾,丈夫与妻子的牌友经历了一夜情,到家后妻子向他讲述,遭到性敲诈的牌友邢姐的丈夫已被警方解救,妻子说她顺便问邢姐最近在忙什么?邢姐的回答:“混账的男人。”这句感慨所包含的心理内容,尽可以任我们展开联想,它具有一箭双雕的功效,既隐含着邢姐可能对丈夫的不依不饶情节,又击中主人公的羞愧之心——“郭广达脸一热”,这种一箭双雕的况味,使这篇小说具有了开拓意识空间的弹性。
《鱼饵飞翔》(《长江文艺》2010年第六期)在题目设置上显现出它的空灵,在一定意义上化解了小说内容的凝滞。小说的结尾与小说的开头恰成一组对比,开始妻子担心丈夫仕途不利心生恶疾,故而劝他爱上了钓鱼,谁知丈夫在仕途上屡屡挫败,是何原因?当丈夫沮丧地讨好妻子时,妻子把他新买回的鱼饵抛出窗外,说道:“玩物丧志!”妻子的这句话,叼住了问题的实质,它直指官场的潜规则,丈夫从佯装旷达的此一极,一不小心跳到了无所事事的彼一极,在意也罢,不在意也罢,左右、右左,从何把握,竟不由人。
第二层意义上的小说是包含玄机的小说,它因为玄机而有了文学的意味。而文学最终的定义就是有意味的形式。这注定了现代小说与《故事会》的分野。
宋长江开始了他的起跳,他离开了地面,由于他的起跳,他空中的旋转,多少具有了快镜头式的观感,因为,他跳出的只是一小步。
我们在多大的程度上把握小说的弹性,这全看我们对于玄机的理解在多大的范围内。一种是形而下的玄机,一种是形而上的玄机。形而下的玄机是从世俗而出,又归回到世俗之处,从实到实;形而上的玄机是从世俗而出,然后飞升而去,从实到虚——如此形而上的玄机就有了精神性和彻底的超越性,它可以谓之为写作力的解放。
玄机的设置使小说具有了超越的属性,它比生活的结论更超迈了一点,更缥缈了一点,也更艺术了一步。我曾经设想过,假如宋长江的小说剃掉结尾处的“玄机话语”,那么他的小说会显得填的很实。这在开始可能是他的优势,会显示他现实的底盘很大,但越逼近最后,越会使他翻不过身来,而最后有可能变成他的负担。
他为什么不一开始就考虑这个潜伏的危机呢?像卡夫卡那样,在《变形记》的开头就开始了起跳:小职员格里高利一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除了这一假设的前提外,卡夫卡通篇全都是现实主义的叙述,但是因为开头的一句,他成了标准的现代主义的大师。
因为他选择了一个自由的起点,这个起点就是他充分发掘小说的可能性潜质,看这一锹挖下去能够有多深。有多深呢?我们看到了一家之主的焦虑,他不能按时上班,全家人的生计都背负在他一人的身上;久病床前无孝子,他的妹妹首先厌弃了,他在影响家人生活的质量,他们在怜悯的同时也在盘算怎样抖掉这个累人的麻烦。这就是我们人生的残酷性真相,当它没有置于这种绝对的处境时,它还是可以被我们容忍的,甚至会得到我们惬意的赞美。
在我看来,小说的可能性是小说存在的第一步,接下来才是它的世俗性和超越性,它必须走完这三步,才能完善现代小说的定义。
我很高兴,在宋长江的小说《素装》(《芒种》2009年第五期)中,我看到了小说的可能性的佐证。一名中学男教师趁妻子陪领导外出之机,到一个单亲家庭的学生家去做客,他受到年轻的学生母亲的款待。在整个准备过程中,他的心理活动充满了若干指向,知识分子总要为自己的心安理得找到一个逻辑化的托词:“他不想对妻子实话实说,又不想说谎,唯一的办法就是避开与妻子对话,那样,自己要办的事情就算是临时所为”;他在购买礼物时那种拿捏的心态;他把自己的做客解释为做一日临时的父亲化身。我们看到一个男人心理出轨时的丰富想象,它的很多内容最后都没有得到现实的实施,但是我们在小说的可能性中看到了这种实施的结果。
所谓小说艺术,说起来其实很简单,就是把我们心中所想,变成笔下之物。
而我对当下小说家们的忠告,不是请他们在日常叙事中现实、再现实,而是希望他们在作品中注入超越的力量,让世俗的鸟飞得更高一些。
〔责任编辑 丛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