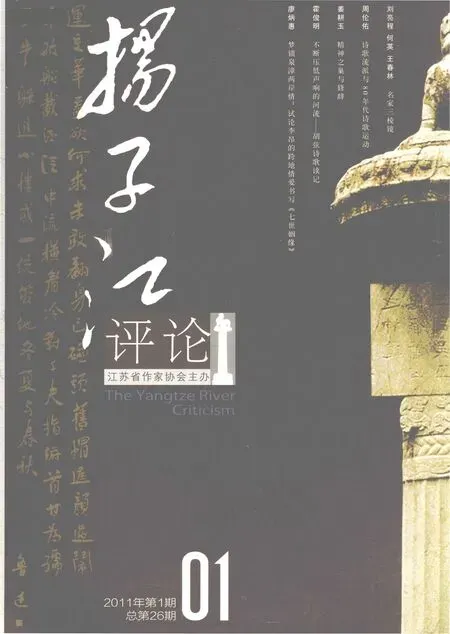蛰伏于掌纹的刀锋
——非非的隐喻诗学
2011-11-20蒋蓝
蒋蓝
蛰伏于掌纹的刀锋
——非非的隐喻诗学
蒋蓝
隐喻是非非写作的动词
十几年前的好莱坞恐怖大片《异形》让我们发现,外太空的生物往往都是恶形、恶力的代表,在它突然贴住人类的太空服面罩、贴住人民的面孔,进而成为人体的一部分后,它最终取代了人的思想,由喻像而成为本体。然后挣破人体的牢笼,成为自己。开始阶段,“异形”不过是人的面具化,就是说,“异形”作为人类“性本恶”的隐喻,逐渐发展到《续集》中“异形”成为主体,而正常的人类心智反而成为了它的隐喻了。记得在1970年代初期,一夜之间,我突然发现一直没有腰身的阿姨们穿着制式统一的“江青裙”,色泽上的微小差异被蛇腰放大,衬映着几丝春色的参差。这本是对“蓝蚂蚁”制服的“异形”,但表达的还是制服的修辞方式,比起现在马屁精设计出来的“中华和谐服”,“江青裙”反而要高明一点,毕竟是那个单色时代的美学隐喻,但前者却是后极权时代急功近利的比喻。
勇士奋力击缶。自先秦以来,击缶之歌就是丧礼之乐,主要用于悲伤的葬礼,而不能出现于喜庆场合,除非设计者有更深远的用意——蓄意把它变成一种政治诅咒。朱大可对权威主义之缶的叩问用力过猛,打破了瓦器之缶,但2008个勇士击打出来的瓦釜雷鸣,隐喻了“东风吹,战鼓擂”的壮怀激烈和昂扬斗志。这2008个勇士的服装,是中山服的长袍化,既在道袍里鼓吹起了猎猎汉风,也暗含了男权对裙裾摇曳的美学期许,又在制服的坚硬领口得到了纪律的约束,不至于自由主义的泛滥,并构成对革命身体的颠覆。
以上现象,不过是我顺手拈来的现实隐喻。毫无疑问,隐喻既是人类固有的思维方式,也是共时性和历时性、中断性与连续性、单向性和重复性的双重结构以及多重递进模式。隐喻是在三个层面获得生衍的——作为修辞的隐喻(修辞手法)、汉语固有的“隐—喻”范畴(比兴、意境等古典诗学概念)和隐喻性(包括了诗学、语言学、修辞学、意识形态学等等),考察部分非非诗人近年的隐喻写作与写作隐喻,我将更多地使用第一义和第三义,但有时会混同使用。在这个意义上,个别诗人“拒绝隐喻”的美学自况,如果可以立论的话,即便是在狭义修辞方面也是难以立足的,更何况他不可能拒绝隐喻性,否则就没有诗性写作这码事。中国当代最为重要的女性思想家、诗人萌萌说得好:“字、词,从它们一诞生起就携带着隐喻。即在字、词的具体性和单一性的后面隐藏着它们与生俱来的、甚至是促成了它们诞生的象征性和隐喻性。诗,或许就是对原始语言的追问、追逐。”①就连“拒绝隐喻”本身,也是隐喻——因为你要拒绝的,不过是虚构的、附加在本质事物之上的象征、隐喻、比兴等等造成的舌头管辖失控的厚实舌苔,但用刀片对诗歌施行的刮痧术,却已经伤及了美学的肌理。
学术界几乎一致认定,隐喻大于、高于比喻。隐喻是将一个概念或意象“映射”到另一个概念或者意象上,使人们可以用一个概念领域的词语去“接近”另一个概念领域。隐喻不是“是”什么的问题,但近似非非与鸟群的关系——我也必须进一步“隐喻”一下:我们看见的一棵胡杨,只是一棵胡杨而已。但胡杨的根须吸纳、牵扯、纠结着我们知道或不知道的地域和潜流。字面上的胡杨是一个所指,字面之下、作为维系胡杨生命的根须则是一群所指,它们之间的关系,使得比喻有了很多类型。按照赵毅衡先生的说法,这些都是隐喻的变体。而“胡杨眼”“胡杨泪”和“胡杨泪尽”的提喻性叠加,则让我们得到了一次为生命欣喜之后的重击。每一个事物均可通过隐喻来呈现,每一个词语都可能拥有隐喻。当这些带有比喻色彩的词语为人们广泛接受,并成为日常词语的一部分后,这一词语的增义过程可被看成一个连续体:下端是富有无限生命力的形体,上端是形式的凝固和定格。开掘、培养前者的生衍空间,刮除、省俭后者的平庸语义,一直是语言炼金术的初衷。
我曾经提出过“非非话语链”一说。简要地说,是在非非诗人的诗歌、评论、批评、随笔、小说等文字形态中,已经逐渐形成了彼此互相生产、互相发明的一条相对锁闭而又趋于完整的诗学—历史的话语链。这包括政治话语、批评话语、修辞话语等等,“非非话语链”成为了非非诗人向现实与理想敞开和进入的路径。因此,一旦离开了非非历史话语的锁钥,忽视了非非历时性的话语演变,人们自然不容易得出关于非非话语历史的完整性结论。而在我看来,历经20年的非非主义,已经逐步由反价值写作——红色写作——体制外写作的嬗变,形成了独特的整体性理论。而非非成员的写作风格的巨大差异性,又在逻辑学上形成了“加总的谬误”,意指“个体的特性也存在于整体”。
为了避免把问题细化而可能犯下的偏差,实际上,周伦佑等人在研究法上,强调以非非整体作为观照的对象,是基于“整体大于个体的集合”,坚持的是完型理论模式研究。近年来,一些高校的研究者和非非同人,开始对非非的写作个体进行跟踪,对诗人迥然各异的想象、神性、智性以及经验话语,展开了一系列研究,话语转型、诗性的跨文体写作、意识形态话语、价值向度、文学与政治等等,是很有建设性的,而着眼于梳理写作空间内部的肌理与细节呈现,也应该成为一种俯身于诗学本身的劳作姿势。这也就意味着,非非诗学中的一系列隐喻,构成了非非价值学的基石和架构。
非非的修辞话语体系当中,隐喻已经远远不止是狭义修辞了。隐喻是非非诗歌的动词,隐喻对文本的“深度撞击”,完全动摇了以往建立在隐喻基础之上的四平八稳的、静态孤立的修辞论、方法论、本体论,在隐喻的策反之下,隐喻的修辞论、隐喻的本体论、隐喻的方法论转换生成,互为依托,逐渐构成了非非写作一种良性的、日益深化的文学生态。在这一体系之下,是否存在迥异于一般汉语写作的“非非修辞”?我提出这个问题,希望引起同仁们的关注。
隐喻与不死的神话
对诗写者而言,拥有不死的隐喻的确是一个神话。就像周伦佑与我交谈中所言,实际上一个成熟的诗人一生就是依靠几个不死的隐喻,来集聚、来呼唤他们散落在这些隐喻四周的言辞断片,这些阶段性的隐喻就像他们的脊椎,最终擦亮了那诗意的额头。隐喻既是诗人的面具,也是他们的脸。既是自己的异形,最终异形也成为了自己的主脑,自己反而消匿在隐喻的浓荫之中。
戴望舒的“雨巷”,冯至的“蛇与旗”,穆旦的“玫瑰之歌”,曾卓的“悬崖边的树”,韩瀚的“带血的头颅”,牛汉的“华南虎”,北岛的“通行证与墓志铭”,芒克的“向日葵”,舒婷的“流水线”,杨炼的“诺日郎”,海子的“麦地”,王家新的“帕斯捷尔纳克”、“游动悬崖”,欧阳江河的“玻璃工厂”、“手枪”,翟永明的“黑夜”、“静安庄”,周伦佑的“大鸟”、“石头”、“象形虎”和“打锣坪”,钟鸣的“硬椅子”,柏桦的“江南”、“左边”,李亚伟的“豪猪”,梁晓明的“篱笆”,阿吾的“相声专场”……在西方诗人中,这类隐喻标志更为显著:雪莱的“云雀”,威廉·布莱克的“老虎”,卡夫卡的“穴鸟”、“甲虫”,爱伦·坡的“乌鸦”,里尔克的“独角兽”、“豹与黑豹”,叶芝的“塔楼”,诺瓦利斯的“蓝花”、“小兽”,博尔赫斯的“迷宫”、“黑暗”、“沙和镜子”,米沃什的“菲奥里广场”等等,有些隐喻是阶段性的,有些则贯穿了诗人的一生。在我的阅读经验中,这些隐喻逐渐从写作者的所有能指当中具形而出,似乎其庞大的隐喻阵营已经成为了主体隐喻的背景一样,用山麓的连绵阴影,托举起了一轮突然的明月。
英国学者C.路易斯说,隐喻是诗歌的生命原则,是诗人的主要文本和荣耀②。我赞同法国哲学家保罗·利科在《活的隐喻》中的结论:隐喻不仅提供信息,而且传达真理。隐喻在诗中不但动人情感,而且引人想象,甚至给人以出自本源的真实。他甚至指出,隐喻的诗歌性与诗歌的隐喻性乃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③。其实,非非主义本来就是中国当代写作中的最大一个隐喻(周伦佑统计的有关非非的解释就有二十多种),但隐喻不是导向含混和虚无,而是“凿壁偷光”。那些走向澄明的言辞,往往都是隐喻,在一件缁色的大氅下完成了偷天换日的大挪移。
阅读非非诗人的诗作,让我想起卡夫卡的话:“通往同仁的道路对我来说非常之长。”
袁勇的豹子
袁勇的豹子展示的是豹子置身围剿而激发的绝杀之力。
诗人袁勇蓄着不变的八字胡,在阆中的古迹与酒肆之间高亢而蟹行。出于某种地脉的神秘作用,其诗作云蒸霞蔚,隐喻满纸。这个时代已经比较枯竭的激情,在袁勇那里却是汹涌而酣畅。他有时会从纸背悄悄偷走一些字词,让读者难以洞悉他的近景魔术。他的近作《一只豹子闯进广场》④向我们展开了一幅后现代的广场诗学图景:
一只豹子闯进广场
空气凝固
人群四散
一辆警车火速地开过来
停在豹子跟前
豹子
毫不理会那些全副武装的警察
径自钻进车身
把警车的发动机
一口一口啃吃干净
正如美国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误读图示》中所指出的那样,一位诗人对另一位诗人所作的批评、误读或者误解,构成了一种阅读与写作之间的关系。“因而阅读是一种误写,就像写作是一种误读一样。”⑤既然没有文本的早出与晚生,我们就不妨考察一下,袁勇对早出的“豹子文本”的误读与修改,这实际上也是他对既有“豹子文本”的影响施加。
此处的“豹子文本”与里尔克较远,但显然与卡夫卡有牵连。卡夫卡写道:“豹闯入寺院中,把祭献的坛子一饮而空;这事一再发生;人们终于能够预先打算了,于是这成了宗教仪式的一个部分。”⑥大体一样的记载,还出现在卡夫卡不同的日记里,可见这头突然的豹子一直跟踪着他的理智和神智。无论袁勇是否知道这个文本,他用自己的血气和现实发现,使用虚拟的场景,反而达到了一种深度写实,着意改变了“豹子文本”的格局。
卡夫卡语境中的豹,显然是上帝的幻形,这样的豹还出现在但丁的体系当中。袁勇把蛰伏在自己体内的那头藐视规则、惩罚制度的豹子驱赶出来,他如同一个放蛊的巫师。豹子落地,让周遭的坛子与牢笼都形同虚设,豹与广场的巨大反差所构成的张力,暗示了我注意到的一个修辞法:当广场与豹子这两个能量巨大的隐喻相遇之际,它们在对峙之中互为彰显,彼此进入对方的身体,企图将对方隐喻的根须吸纳为自己的组成部分。能量越是巨大的隐喻,这种对峙的过程就越发漫长,此消彼长,恰恰拓展出了作品的想象空间,并形成张力。而广场卫士的助手角色,却使得这种修辞的角力,演变为了一次“广场法律”的训诫。
但袁勇没有让这样的对峙持续,他用豹子“自投罗网”的方式,彻底消解了围剿主义的天网布局。而通达监狱的警车,恰恰是两个对峙隐喻的锁钥,豹子使用了古汉语中“吃铁兽”(即熊猫)的口齿技术,使得“惩罚与规训”得到了深刻的中断。
显然,汉语中的广场一词,具有藏策先生所独创的“超隐喻”一词的特征。“超隐喻,就是‘超级’隐喻,或‘过分’隐喻的意思,而绝不是‘超出’隐喻或‘超越’隐喻的意思。”⑦希腊语中的广场,本是民主集会的场所,它不需要辽阔威严。汉语里的广场,没有这种民主成分,它往往只与公判大会、十万人的批斗会以及振臂如林、歇斯底里的高音喇叭、口号有关。进入新时期以后,汉语的广场上回荡着双卡录音机的靡靡之音,穿中山服和喇叭裤的男女摩肩擦背,搂作一团。某些地方,广场成为了渴望先富起来的部分人的黑市、旧货交易场所……这些努力,消解了广场的挺阔和语法,呈现出了民间的“人迹”。但在高打和谐牌的后极权时代,它又成为和谐太极拳群体表演的革命性天桥。在我看来,当隐喻里带有来自传统的、历史的、渊薮中的反光时,反光俨然已经成为了环绕喻体的松枝和向日葵,使本体成为了圣体,从而使隐喻成为了讽喻。
袁勇的豹子,完成了一场绝杀。当然,也使那些沉溺在隐喻修辞格深井中的观天者,失去了方向。我想,这也是周伦佑编选《刀锋上站立的鸟群》时,将《一只豹子闯进广场》置于袁勇诗选篇首的原因吧。
陈小蘩的豹子
陈小蘩的豹子,展示的是一场巨大病变来临时打量生命的速度。
小蘩是我素来敬重的诗人,她延续至今的诗性写作,在当代汉语中是甚为特异的。她的向内用力,有点近似思想随笔界的筱敏,但锋芒再转,又带出些女性的绵密情感。小蘩的诗作至今没有得到汉语写作界的广泛评介,这是1980年代非非横空出世以来,写作界追风逐浪而在审美方面露出的一个空洞。小蘩曾是高三年级的老师,她在数学与诗歌当中奔忙,她以最大的沉默护卫了诗歌的尊严。所以,小蘩的沉稳、庄重与向内用力,本身就是非非的一个隐喻。
陈小蘩的诗中,豹、马、乌鸦与鱼这些隐喻反复叠现,更多的与速度有染、与突围相关联。这既含有生命的阶段性隐喻,又暗示了她对自己生活的看法。也许某一天,在她向内用力的掘进过程里,一头豹子冲决开一切形容词,四只飞奔的爪子把泥土翻到天空成为了她的乌鸦,然后进入到她体内。她甚至来不及像但丁那样呼叫,她不需要贝雅特丽齐,她用花掩饰好豹子进入时的创口。从此,与豹厮守。这方面的作品还有《豹,从城市的大街上跑过》、《豹,蹑行于教室中》、《豹,蹑行于文字中》等。
在小蘩的教学视野中,豹行的敏捷,是那些青春的身影所点燃的:“潜伏是一种姿态。为更敏捷地出击/蹑足而行,贮存体力与思考/思维在这里被修剪,梳理,直到除却/许多细微末节。它的目标直接/现实。物质的光芒照耀豹的眼/在黑夜中闪烁,最后到内心//更静的美,在豹的守候中呈现/弓身前曲,它敏锐的目光/寻视,吞咽每一段意义(包括文字的/碎片)这只吞下知识的豹,智慧地/梳理,使它的皮毛闪耀金子的光泽。”(《豹,蹑行于教室中》)如果说,这样的豹影还是外在的,并没有与她体内的豹相遇的话,那么,持续的头痛宛如天庭的裂口,使得豹的双瞳与世界相遇,进而燃烧。外在的东西倏地消失,灵魂因为豹的四肢而变得宽广。一个躺在病床上依靠回忆来延续时光的人,再一次,再一次回眸自己的童年和长发飘飘的青春,都在飞速的奔驰中,把病痛甩在后面。她不是被狂蜂苦苦追赶的伊蛾,她是豹子!多么希望就这样飞奔,让腾起的泥块化作漫天乌云,使身后的病痛迷路啊。
《追赶豹的速度》⑧写于2003年9月6日凌晨的华西医院,那是在她第一次动脑部大手术之前的最后之作。写的时候,她已近失明。这首诗让我流下了眼泪。
……
我要完成这场奔跑,以豹的速度
和自身赛跑。生命在病中变得珍贵
焕发着豹在山林里俯视时
熠熠闪亮的光芒
奔向目标时的速度在瞬间加快
我已无法停止,时间流过
清澈明静,带我抵达
带我超越……
很奇怪,病痛总是带有一种令人感动的家园气息。
病痛可以使时光慢下来,慢到我们可以让手指感觉到时光的色泽和流质化的形体,慢到使自己的身体铺成旷野,体内的豹子从容而立,静静对峙。然后,发足狂奔。豹身如锯,颠碎了那只具有平衡效应的“田纳西的坛子”。坛子使凌乱的荒野向山峰围拢,荒野向坛子匍匐,但豹子却已将这些远远抛开,它打碎了静态美学的坛坛罐罐,锐意只身,回到了属于自己的草原。
《追赶豹的速度》计44行,除有两个明喻,均被连续的隐喻所高速替换。宛如一次无休止的接力赛,均在豹子的统摄中得到了稳立大地的安排。她没有像海子那般发出“诗歌的豹子抓住灵车撕咬”的喟叹,也没有如保罗·策兰那样一心委身死亡。她的豹子穿越了这些——
多年以后,在这场奔跑中
血的浓冽和血脉中世代相传的热情
使我没有时间悲哀
一生的日子都浓缩为花朵一季的盛衰
我们能记住的是花朵开放明丽的日子
同样也记住豹静止和出击的瞬间
……
我们都该“记住豹静止和出击的瞬间”,同时为豹铺排在空中的花朵而祈祷。豹的隐喻,不但让小蘩参悟了她的疾病哲学,更让她的思想借助隐喻而孕育出一次对生命的深度回望,就此,也大大强化了她此次转身后的诗写方向。
陈亚平的鸟或鸟群
近年,陈亚平已经不再穿着那身标志性建筑的红色衬衣穿梭诗界。我偶尔看见他站在公交站台上若有所思,似乎不是在等车,而是在等待喧嚣之上的鸟群。鸟把天空打开,把成都的阴霾划开,但城市就是一个建筑工地,陈亚平的鸟群开始寻找树枝。
毫无疑问,《建筑上的鸟群》⑨是一首毫无疑问的杰作。
这是一个最低限度的想象,一群鸟
并排地停栖在屋檐,轻轻撩开翅膀
我从侧面观察,一阵疾风所造成的转换
是短暂的,而声音在耳朵中重现出来
此时,鸟群力图巡视
精巧地运用了体积
空气,突出性之上的等级,与悬垂的砖墙相混合
遍布于光线倾斜的逼射之下。它们啼叫,又经历着
长时间的沉寂,一块乌云的沉重步子
与它们静默的内心,建立起呼应
而事物的性质正是如此,通过增长,倒转或类似的
秩序,我并不能否认
这群鸟,迈着无声的步子,所出现的一阵队列的突变
是因为一道亮光,正追逐着它们内部的
血液,和金属般的眼睛
在一个对话录中,陈亚平称此诗为“视知觉语体”,并说是对“可能性”的认识,哪怕就是很小的可能,也是革命性的。陈亚平早年熟读“作家们的作家”博尔赫斯,后来沉迷“诗人们的诗人”华莱士·史蒂文斯,这在他的文体中留下了难以消泯的痕迹。作为一个成熟的诗人而言,正如有的心理学家所言“视知觉就是智慧”一样,视知觉的确可以告诉我们这个世界的一切,因而,在视觉中隐喻的思想性,就维持着思想的隐喻性。陈亚平是狡黠的,他并不只是一个纯洁的自然记录者,他把自己的思想密码注入到了描绘的缝隙里。这就让我想起了卡夫卡在描绘契西克夫人的声音时使用的技法:“她的嘴巴逐渐张开,就像是发出孩童般怨诉似的,上面和下面形成柔和的弯曲,人们在想,这个将语句中元音的光辉扩散出来的、并用舌尖保持住语句纯洁轮廓美丽的构词,能发出空前绝后的清脆声音,并惊叹它的持久不逝。”⑩这玉雕一般的剔透文体,蕴含了卡夫卡对著名演员契西克夫人的极度高热、但又不敢外溢的爱情。陈亚平几乎不写这类感情,他紧闭嘴唇,有点儿乌,有“拙火定”一样的异能,把热量的亮光投向鸟群。正如利科所言:“我们说,形象化表达始终是‘看作’,但它并不总是‘看’或‘使看见’。
在我看来,陈亚平使用的是典型的“异质同构”方法。即通过观察者的情感与外部景物的同形对应关系,进行艺术的类比与对照,把内在的东西与外在的东西联系起来,借以实现情感、思想的对象化。“知觉活动所涉及的是一种外部的作用力对有机体的人侵,从而打乱了神经系统的平衡的总过程。我们万万不能把刺激想象成是把一个静止的式样极其温和地打印在一种媒质的上面,刺激实际上就是用某种冲力在一块顽强抗拒的媒质上面猛刺一针的活动。这实质上是一场战斗,由入侵力量造成的冲击遭受到生理力的反抗,它们挺身出来极力去消灭入侵者,或者至少要把这些入侵的力转变成为简单的式样。这两种互相对抗的力相互较量之后所产生的结果,就是最后生成的知觉对象。在这样的感官战斗中,陈亚平不但近乎完美地记录了每个阴影和细节,而且还昭示了自己的思想。这就意味着,陈亚平似乎已经洞晓了“五官感觉的形式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的真髓,即在“异质同构”之余,还可以“同质异构”。
如果说隐喻在诗中的基本功能就是造像的话,那么,唯有如此,诗性意义才可能得到直观的托举。无论是感觉、直觉、情感、灵魂的造像,对陈亚平而言已不是问题,他甚至在从事“由像返虚”的再度隐喻转换。
鸟是自由之象;就都市上空而言,鸟或者鸟群却是无从栖身的一群,空中的游牧者变成了都市的游魂,让自由的空中演绎逐渐漫漶在混泥土建筑的阴影中。所谓自由,开始成为了一种静默的拷问。
准确地讲,提喻是“共同承担”的意思。它包括以部分代替整体,以整体代替部分,以某种事物代替某类事物,以某类事物代替某种事物,或者以原材料的名称代替由其制成的东西。所以,鸟是鸟群的提喻。而飞、栖身、队列、啼叫、巡视等等,均是鸟的提喻。而在鸟群与建筑之间,飞翔与栖身之间,不存在比喻的关系,但它们之间肯定存在隐喻的关系。而“一道亮光”的追逐,既可能是陈亚平的火眼金睛,也可能是都市对鸟施加的危机穿刺。
就汉字构字原初意义来看,非非之非字,本就是鸟在空中打开翅膀之象。所以,作为符号的鸟或鸟群,在触及建筑之后,能指越发密集,反过来作用符号,已经成为了一个新的所指了。
周伦佑的大鸟和象形虎
周伦佑是隐喻的知音。某种程度上讲,隐喻不但是他的方法论,甚至也成为了他的本体论。他的道路其实是清晰的,顺着自己打下的路标——狼谷、猫头鹰、刀锋、石头、大鸟、猫王、火焰、遁词、象形虎、玻璃城,他亮出了反手剑。这就好比周伦佑之于成都,之于当代文学,就是一个绝大的隐喻。上面我说了,是那种超级隐喻。而从另外一个角度——创造性着眼,他使用的隐喻,往往带有极度个人化色彩,可以称之为创造性隐喻。
布莱克曾提出“激进的创造性假设”说:有些情况下,某些隐喻创造了某种相似性,在特殊语境下,比如图书馆与坟墓,比如兵器库与婴儿房,比如染料公司与向日葵,它们是可以产生隐喻的。在周伦佑的诗学世界里,他就像玛丽·雪莱一样,合成多种意象,创造出了“弗兰肯斯坦”式的超级隐喻。当然了,诗人袁勇偶见木头木脑的雷抒雁,就产生了“周伦佑”的错误比附(或超远距离类比),自然会遭到叶延滨之流的奋力解构和修辞清洁。幸好,不是隐喻啊!
创造性隐喻的震撼,不仅限于通过命题达到的奇异,创造性隐喻还要表达非命题效果。这在于他合成、吸纳的意象太多,意象并不那么听话的,它们固然朝着一个强力意志的方向前进,但在修辞的反复磨合、浸入、消解当中,会生发出一些奇怪的、完全陌生化的意义。就是说,对创造性隐喻的理解会产生复杂性、差异性和选择性。这样的现象,既是创造性隐喻之功,但未必就是它的激进所致。但理解肯定是可能的,应该掌握好对隐喻字面意义和隐喻所在的语境的动态顺应过程。这些创造性隐喻展示了铁幕时代和黑暗的当下,自由思想者寻求自我和重建纯正文化的主题。这一主题的持续锐进有赖于作品中众多隐喻的展开和变异,分析这些隐喻的起承转合,可以发掘周伦佑文本的诗学寓言特质。
大鸟有时是鸟,有时是鱼
有时是庄周式的蝴蝶和处子
有时什么也不是
只知道大鸟以火焰为食
所以很美,很灿烂
其实所谓的火焰也是想象的
大鸟无翅,根本没有鸟的影子
……
大鸟铺天盖地,但不能把握
突如其来的光芒使意识空虚
青年学者刘畅在《对解构的结构——对周伦佑诗歌类结构分析》一文里认为,我们可以把大鸟看做冥暗的表层之下存在的本真状态——“在众多物象之外尖锐的存在”(《想象大鸟》);可以看做诗人竭力追求而不可得的理想——“使我铭心刻骨的疼痛,并且冥想”(同上);或是未被文明同化的原始生命中的纯粹和活力——“生命被某种晶体所充满和壮大/推动青铜与时间背道而驰”(同上)……也许,根据周伦佑在《非非主义诗歌方法》中提出的主题不确定、意义不确实原则,对于不能把握的大鸟的把握本身即是徒劳。除了我们偶尔想到它时那种广大无边的感觉,我们实在不能多说什么了。其实,大鸟的创造性隐喻干扰了评论者的终极判断。前面我已经谈到,对创造性隐喻的理解会产生复杂性、差异性和选择性。但创造性隐喻当中,同样具有“主隐喻”与“次隐喻”的区分问题。在我看来,N个“不确定”均是方法,或者说是老周的障眼法,他的目的是很清楚的,他的隐喻是很精妙的。“大鸟”就是世界的意识,是世界的隐喻,是周伦佑的“绝对存在”,此诗展示了老周的世界观与方法论。这让我想起歌德的名作《游子夜歌》:“群峰一片沉寂,/树梢微风敛迹。/林中栖鸟缄默,稍待你也安息。”在这首写于他逝世前一年的千古绝唱中,“夜歌”显然与“沉寂”、“敛迹”、“缄默”、“安息”构成了强烈反差。我们均是天地间的“游子”,生命的烛火低微而恒定时,“夜歌”自然是大生命的隐喻。最美的生命,从来就是“沉寂”而“敛迹”的。
反过来看,“大鸟”展翅,可以向温馨的世界献上花朵;可以划翅为刀,直抵黑暗;可以举翅为霆,击破黑暗;可以说出,可以照亮……如果没有这样的体认,“当有一天大鸟突然朝我们飞来/我们所有的眼睛都会变成瞎子”。而一个没有世界观的人,还写哪门子诗呢?
“其实我们所谓的鸟/只是一种姿态/从文字变成飞禽/从飞禽变为文字/往返于书本与天空之间/偶尔有羽毛飘落下来/鸟便成为具体的东西。”(周伦佑《从具体到抽象的鸟》)“鸟”作为自证、自明的生命隐喻,难道不是我们孜孜以求的自我实现吗?
有关象形虎,限于篇幅这里只能略说。《象形虎》的问世,可以说是汉语诗界的一个事件。黑格尔说过:“隐喻的范围和各种形式是无穷的。作为东方王道文化的隐喻,虎一直在中国文化里举而不倒,吼声震天。《象形虎》首先使用了消解王道隐喻的策略,不是使用的逻各斯作手术刀,而是使用的转喻。在消解过程中大量使用了老虎散落的部件进行转喻,最后在转喻基础上进行重构隐喻:一方面拆散王道之虎,另一方面让真正的虎形精神归于大地——“一只披挂火焰的虎从我身上脱颖而出”。
对周伦佑来讲,解构是对王道隐喻的消解,重构就是对创造性隐喻的确认。
……
非非群体当中,诸如雨田的“乌鸦”,龚盖雄的“黑夜”与“马”,董辑的“破车”,马永波的“流放地”,邱正伦的“冷兵器”,孟原的“飞鸟”,余刚的“合欢树”,梁雪波的“断刀”、“修灯的人”等诸多隐喻,都是值得认真分析的,这些细化工作,只好留待后日继续努力,以期呈现出“非非话语链”的弧度和韧性。
隐喻视野下的非非诗性
学人刘小枫在1980年代中期出版过一本《诗化哲学》,讲的是德国浪漫派自席勒、费希特等人以降的罗曼蒂克式的美学思潮。即把诗不只是看做一种艺术现象,而更多的是看做为解决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问题的重要依据,并把美学视为人的哲学的归宿和目的,成为一种泛美学化的哲学。如此看来,作为一种思想系统,诗化哲学的终极,恰恰是人生的非“诗化”,它作为反抗单边权力与极权的操纵术,显得是那样的柔性。
诗性不同。诗性以智慧整合、贯穿了整个文学形态。作为人类文学精神的共同原型,诗性概念属于本体论的范畴。回到诗性即是回到智慧,回到文学精神的本原。作为对感性与理性二元对立的超越努力,诗性是对于文学的本体论思考,“它也是一种超历史、超文化的生命理想境界,任何企图对文学的本性进行终极追问和价值判断的思维路径都不能不在诗性面前接受检验。在此意义上,非非提倡的诗性精神,是指出乎原初的、直面现实、崇尚自由的人类普遍精神。
莱考夫和特纳在1989年出版的《超越冷静理性:诗性隐喻分析指南》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诗性隐喻的概念,并将生活中的概念隐喻作为诗性隐喻的构成部分。概念隐喻作为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渗入到生活和文学作品中。因此从根本上讲,隐喻已经是一种认知现象,是我们理解世界、进入事物的唯一口令。非非的诗性隐喻源于文学又不止于文学,包括:诗意思考、诗化批评、诗性哲学等层面。
从宏观的角度来讲,诗性首先指向的是文体跨界的发展。无论是早年周伦佑、尚仲敏的诗论,还是近年本人、陈亚平、马永波、龚盖雄、二丫、董辑、袁勇、张修林、梁雪波的断片、随笔、批评写作,都具有诗性抒写的烙印;其次,诗性在非非诗人笔下还有不同寻常的含义。诗歌的精神质地甚至已经成为一切严肃文本的灵魂,并内化到文本的叙事策略当中。
如果从微观角度考察,诗性当然拥有更加繁复的姿彩:语言结构上的延宕与浓化、消解隐喻、重构隐喻,力图实现整体架构上的诗性彰显。从内在事物的隐喻化,到精神的诗性张扬,非非的诗性精神尤其体现在如下方面:消解宏大叙事;再现诗歌场景;张扬自由精神。在当代汉语谱系下,非非主义的诗性是最深植的根性,它深于策略意义的诗化。诗性大于诗意,诗性也高于诗格。
【注释】
①《升腾与坠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1页。
②王铭玉:《语言符号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③汪堂家:《前言》,见《活的隐喻》,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版。
④《刀锋上站立的鸟群》,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93页。
⑤《误读图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页。
⑥《夫夫卡全集》(第5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5页。
⑦《超隐喻与话语流变》,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81页。
⑧《刀锋上站立的鸟群》,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页。
⑨《刀锋上站立的鸟群》,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4页。
⑩《夫夫卡全集》(第6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119页。
┝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