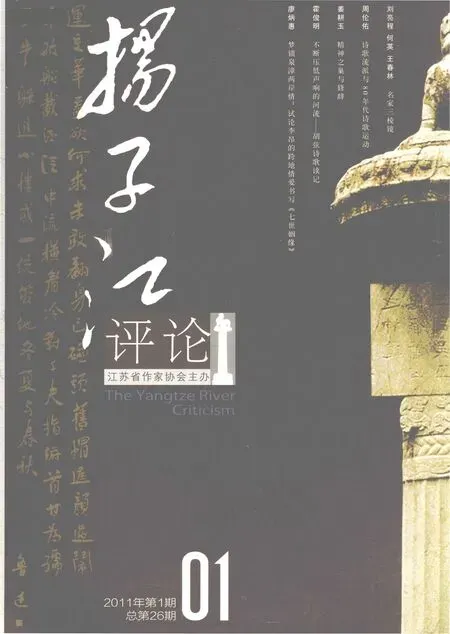关于王蒙与稀粥的随想
——编余琐忆之九
2011-11-20徐兆淮
徐兆淮
关于王蒙与稀粥的随想
——编余琐忆之九
徐兆淮
作为一名文学期刊的老编辑,委实已有许久未能面见王蒙了。虽然,常能从报刊传媒上读到有关他的各种信息。近年来王蒙到南京讲学或售书时,我也曾想去看望他,但终因诸多不便,而未能遂愿。对此,有时不免有些遗憾。而且据我所知,一些熟识王蒙的朋友,也都在关注着王蒙近期的创作、健康及其忙碌的身影。
尽管如此,作为上世纪80年代的老编辑,与王蒙的结识、相交经历,直到现在依旧在我脑海里清晰可见,印象颇深。盖因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起,在作家与期刊、编辑共建共存的文学史关系中,如果说,一批“右派”作家乃是《钟山》作者队伍的主力军,那么,北京的王蒙、李国文、刘绍棠、从维熙、邵燕祥,南京的高晓声、陆文夫、张弦、艾煊等便是《钟山》十分倚重的作家。而《钟山》和我与这批“右派”作家的友好合作,又正是建立在相同或相近的文学观念之上的。记得王蒙在《钟山》创刊30周年时曾题词“钟山美景三十年”。我以为,这既是对《钟山》的热情鼓励,也可以说是作家与刊物之间知音效应的结果。而1991年,王蒙为短篇《坚硬的稀粥》打那场关于粥的官司时,赠书、致信于我,当也是作家与刊物的友情显示。
诚然,新时期以来,作家与刊物之间的双向选择,都为作家与刊物、与编辑的友好往来,提供了十分便利的条件。自上世纪末,王蒙从新疆伊犁河谷返回北京住招待所,我与他见面初识,到他迁居光明楼、前门大街新址的约稿,再到东四小胡同四合院的生日拜访、席间叙谈,都一一镌刻在我的脑际。尤其是,他较早地应约在《钟山》“作家之窗”上发表中篇小说《风息浪止》,再到他夫妇俩应邀来宁访问,我陪同他们参观雨花台烈士陵墓,均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无论是作为编辑、朋友或是读者,我都会不时地忆念想起我所熟悉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恰巧的是,近日翻检旧时书札,忽而见到一本王蒙亲笔题签赠我的《粥》文学集和两封简短信函。闲暇时随意翻检浏览,竟不仅生出一些关于粥的联想,而且还追忆起与王蒙的某些交往经历。自觉这些陈年的细屑小事虽无多大史料价值,于我倒也不乏纪念意义,特小记于下。
随意翻阅这本17年前出版的《粥》文学集,忽而发现,除了题辞“兆淮同志一笑”颇令人玩味之外,这本只有14万字的小册子竟收录了王蒙关于稀粥的四篇文章,关于《坚硬的稀粥》的10篇争鸣文章,另收集了19位作家31篇关于粥的随笔。此书本缘起于王蒙的一篇寓意多重的讽刺小说,由小说引起文坛争论并不奇怪,再由争论而引起一场诉讼官司,这就令人惊诧了。更令人怪异的是,在这争论前后,竟唤起全国近20位著名作家、学者撰文就粥的话题洋洋洒洒地写作了20多篇随笔,而且这些随笔或考古论今,或意趣盎然,读之颇给人以旁征博引、痛快淋漓之感。明明是有所指向,并非无病呻吟,却又偏偏一字不提小说争论之事。难怪张洁在《潇洒稀粥》一文结尾处说:“无论如何,1991年稀粥年是稀粥史上值得记载的一年。”也难怪有人如此概括沸沸扬扬的粥年:粥文传中国,粥话满中华。
就我的饮食习惯而言,说到稀粥,首先唤起的,便是我个人关于粥的记忆与体验。起初年少时,在我的印象里稀粥总是与贫穷摆脱不了干系。幼时家贫,在农村常常是早晚喝大麦粥(又名罕子粥),中午吃菜稀饭或菜干饭。及至解放后直到上世纪60年代中期,我大学毕业跨入首都中央级研究机构的大门,仍然要经常喝玉米粥、吃窝窝头。那时,我方才醒悟到,原来告别稀饭与告别贫穷一样,毕竟不是靠空喊几句革命口号就能一蹴而就的。
直到上世纪90年代改革开放,市场经济勃兴,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有了较大幅度提高之后,生活方式生活感念起了较大变化之时,告别稀饭加咸菜这才有了可能。即使偶尔在连续享用丰裕美食之后,出于调剂口味,或是满足忆旧之需,想喝稀粥,那再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稀饭加咸菜,而大都变成了名目繁多的美味粥:肉粥、鸡粥、鱼粥、虾粥、海鲜粥、皮蛋粥等等。在告别稀粥多年之后,人们又常常不免怀念起稀粥来,每每在旅行归来时,我常让家人给我煮点小米稀粥,外加酱黄瓜。吃起来特别爽口,可见,尽管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粥也处于变化之中,但不管怎样变化,中国人仍然忘不了稀粥。
记得上世纪80年代以来,我作为《钟山》编辑去北京陈建功家组稿,他不止一次地亲自为我做海鲜粥,吃得我满口生津,直呼过瘾。因而前两年有两位京中朋友来宁,我即学建功之法,招待他们喝粥,只不过已不是我在家操持,而是请客人到潮州粥店撮了一顿虾米鱼粥。结果此举也赢得了客人的首肯与称赞。
看来,在古今中国,无论贫富,也不管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大约人人都有过关于粥的记忆与体验,都有说不完的话语。于是,我想,或许稀粥原本就是中国独特的餐饮文化的组成部分,与贫富贵贱并无多少直接的干系。可知,由小说引发的那场关于粥的争论,虽然看起来不免有点闹剧的意味,但闹剧的背后,却也似乎隐藏着、关涉到时代思潮的走向,那种动辄给人戴政治帽子,搞影射批判的做法,毕竟不大时兴了。
关于这场因粥而起的争论,如今已逝去了近二十年,成为一段尘封已久的文坛历史。应当说,这桩发生在90年代初期闹得沸沸扬扬的文坛风波,其开场与收场方式,是颇为耐人寻味和微妙复杂的。随着时间的变迁,孰是孰非,功过评判,也许已经无关紧要,更重要的是,如今的王蒙仍有一定的创作活力,仍有到处演讲的自由。那篇寓意丰满的讽喻小说,即使今天读来仍能给人以丰富的想象空间,仍有相当的生命力。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面对那些强加于人粗暴武断的批评之风,作家毕竟可以选择拿起笔甚至法律的武器,捍卫自己的正当利益。无论如何,这是值得庆幸的。
其实,《粥》文学集与其说是一本关于王蒙小说《坚硬的稀粥》的争论集,倒不如说是一本关于粥的随笔集。或者说,这本随笔集,皆因对王蒙小说的争鸣而引发的关于粥的话题,因而取名争鸣集,也无不可。然而,王蒙就是王蒙,他能机智地把对其小说严肃的政治批判化作了一场嬉笑怒骂的玩笑。应当庆幸他继八九政治风波中安全着陆之后,又躲过一场灾难。而其他写随笔的作家虽然只谈稀粥,不提王蒙及其小说,却又巧妙地表明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和文学观念。真可谓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这是王蒙及其撰写随笔的作家朋友的聪明机智之处,也应看做是时代的进步、政治的文明,为作家的创作自由提供了某种可能。记得王蒙常喜欢说,现在是作家创作的“黄金时代”、“最好时期”,或许正基于此。
作为一名当代文学期刊的老编辑,我自然十分清楚王蒙在当代文学史上的地位和他作品的份量:他的生平历经坎坷,屡遭挫折,但像他那样先后荣获全国性三次短篇奖、两次中篇奖,长篇《活动变人形》又颇具影响力,且身兼作家、评论家、学者、编辑的几重身份,就作品数量之大、变化之多、题材之广而言,实可称之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由此看来,对王蒙这样具有如此影响力的作家,罗织那样大的罪名,因而引起王蒙的强烈抗争,也招来一大批实力派作家群的呼应和声援,这场争论的结果可想而知了。应当说,这大约可视为解放后即将遭到诬陷、迫害的作家所发出的第一声强有力的抗争与呐喊。
从童年时企盼告别稀粥到如今老年怀念稀粥,时光已经走过了70年。从《粥》文学集记载的那场关于粥的争论,到如今也已过去近二十年。眼下,我和同辈的文学同人们无不庆幸时代的进步、文学的发展。仿佛记得早在1983年全国作代会之后,王蒙就在不断欢呼文学的“黄金时代”和“最好时光”尽快到来。倘从王蒙能安全度过一次次“危急时刻”来看,自然值得庆幸,但真正的文学创作“黄金时代”何时到来,恐怕还需待以时日。不知王蒙先生可以为然?凭借我对王蒙的理解,我想,他当知道,若无政治民主和思想自由的深入改革,中国文学创作的“黄金时代”的到来,或许便只能是一种欢呼和愿望,一种良好的期盼。
┝著名文艺评论家,原《钟山》杂志社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