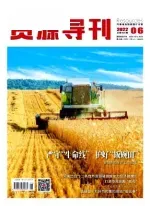我的西塬梦
2011-11-07刘泉锋
□ 刘泉锋
我的西塬梦
□ 刘泉锋

我们这地方,丘陵,也称西塬。南依秦岭,北濒黄河,展眼望去,尽是沟沟壑壑,藏有说不完的酸甜苦辣。我高中毕业后,复习了两年,没能跳过龙门,便带着满腔的失望与烦恼回到乡下。这时才发现,我对生我养我育我成人的这块土地,竟是那般的不满和鄙夷,它的身上竟有这么多邪恶和仇恨,于是我便学着用笔杆去作一种反击。这种反击,说穿了就是发泄,发泄到终,才知道自己太浅薄,有点愚蠢可笑。尽管这样,我却因此成了一个狂热的文学追求者。
那时候,正处八十年代初,还是集体化,还有生产队,生产队里还记着工分。一日三晌,早出晚归,地里来地里去,写东西只能钻空子。于是三伏天大歇晌,别人酣睡,我汗流浃背趴在桌上用功;冬天的夜里,暖被窝的诱惑是那样强烈,但我坚持在寒气入骨中爬格子——这样一种顽强的追求并没有感动上帝,我含辛茹苦写下的文学作品,换来的仅仅是一次又一次的退稿。
父亲的脾气很暴躁,动不动就发火,全家七口人的生活担子搁在他的肩上,他当然快乐不起来。那时候的生活非常苦,玉米面、红薯片都很难吃饱,闹粮荒是每年常有的事。至今我的记忆中还会经常浮现父亲夹着口袋去借粮的情景,真真切切,清清晰晰,一点都不掉色,一点都不模糊。那“电影”经常让我触景生情,在脑海里演了一遍又一遍。我高考的失意对父亲的打击很大,一个农民对儿子寄予的希望破灭了,他还会有什么期盼呢。他开始反对我看书写字,尤其对我的熬夜最为不满。他在考虑得与失,一夜几分钱的电费对我这个不可造就的人花得太冤了。因此,他在一次发脾气中砸了我的台灯。面对父亲的粗暴,我不敢吭声,我理解父亲的心情,我始终同情原谅父亲,所有的罪责归咎于自己的不才和无能。泪水暗暗地流入肚中,我只有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拼搏。这种拼搏不全是痛苦,因为文学的伴随,我时时感到自慰,我的精神是充实的。
非常感谢人们常说的那句话“有付出就有回报”,它让我坚信公平的上帝,一定会让成功降临于我。几年后,我的第一篇小小说终于在天津的《家庭报》上发表。我把寄来的12元稿费全部交给了父亲。12元,别笑,是少得可怜,但在那时,它可以买72斤食盐,可以买500块煤,可以缴全家一年的电费。重要的还不在于这些,而在于我和父亲都得到了一种空前的满足。我清清楚楚看见父亲的眼眶中汪满了泪水,我的眼睛也湿润了。仅仅这12元钱,使我们父子俩的感情得到了充分的交流。
1987年,我的短篇小说《生命》在《洛神》杂志上发表,后被其他刊物转载,又被天津电影制片厂改编成两集电视剧《马鲁他》搬上屏幕。全国各地的几百位读者给我写来了热情洋溢的信,他们中有工人、农民、教师、解放军战士等。这些,让我感动,让我的父亲感动。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我感到了生活的价值所在。
后来的十年间,我先后在《青年文学》、《时代文学》、《莽原》等诸多文学期刊上发表中短篇小说百余万字,作品甚受读者喜爱,并多次获得全国、省级文学大奖。其中:1990年,小说《二梗的冬天》获河南省青年文学优秀作品奖;1996年,《汉山保护神》获首都十家报社举办的全国优秀报告文学奖,还在人民大会堂受到当时国家重要领导人的接见;1999年,小说《人生细雨斜斜飞》获人民文学杂志社、鲁迅文学院、女友杂志社联合举办的全国青年文学大赛一等奖,后被多家刊物改编和转载;2001年,小说《爱情》获河南省优秀文化成果奖提名;很多作品还被杂志社评为“本期最受读者欢迎的作品”。1990年我加入了河南作协,1991年与我省作家王遂河(笔名行者)一道,被省作协推荐进入北京鲁迅文学院作家班进修。
多年后,我因为文学被当地一家黄金企业聘用,后又被借调到市国土资源局工作。近年来,因为工作繁忙,我几乎停止了文学创作,但是那种文学情愫还时刻在我胸中涌动。每当翻开一本本新杂志,看到我熟悉文友的新作,心中总会有一种失落感和落伍感;每当打开网络,面对文友收获的喜悦之情,我常会向他们发出由衷的祝福,同时在心里暗暗给自己鼓劲,制订下新的创作时间表。接下来,我要写一部长篇小说,写我熟悉的果园文化、矿山文化以及灵宝这块特殊的地域孕育出的其他文化,让文学永远成为一种诉说和交流,去感动心灵,去感染生活,去实现我们心中那个共同美好的梦想。
(作者单位:灵宝市国土资源局)